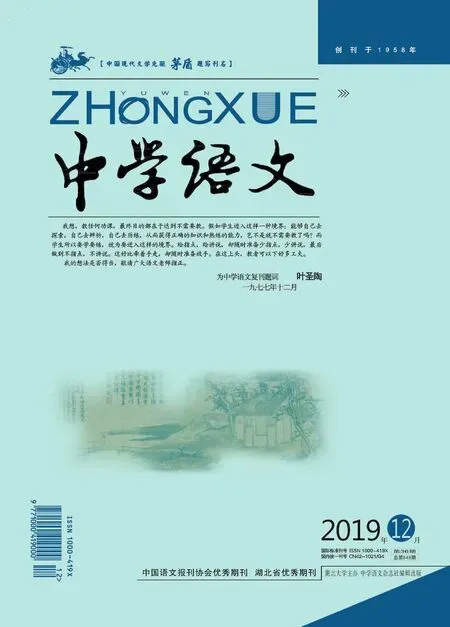漫谈中学语文教材里的“穷而后工”现象
吴 珺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 里写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句话是说,并非诗歌让人困顿穷厄,而是创作主体在人生困顿、饱经失意与忧患、背负枷锁艰难前行之时,会直达内心最深的体悟,创作出工巧精致、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这一说法,只要我们细细品味一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作品的作者人生经历,就很容易得到印证。
我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一些作家在被“贬”之后,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例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他的作品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有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中秋》《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词。
他是带着疲倦和伤痕来到这偏远的黄州的,可谁想,这一场命运的颠沛流离,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阶段,对他之后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尽了宦海炼狱的折磨,看淡了人生悲欢,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在他心中调和交融,他逐渐变得成熟,你看,他衣袂飘飘,欲羽化登仙而去的安宁自足;他哀叹生命须臾,愿抱明月长终的失意悲慨;他忘却得失,辩证分析变与不变的理性洒脱。清贫的生活、寂寞的黄州,命运转折带给他巨大的反差,英雄气短、伟人遭难,他只好用智者的目光去看向黄州山水,注入他的精神力量,跟自己和解,于生命突围,作品表达出或舒畅、或悲咽、或释然的情绪,达到情韵深致的艺术效果。
无独有偶。同属“唐宋散文八大家”、给我们留下了《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的柳宗元,其人生轨迹与苏轼基本一致。年轻时的柳宗元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后盛年丧妻,体会人生况味,32岁更因著名的“八司马事件”被贬至僻远的永州,此后的半生,他再未踏足京城。仕途失意的柳宗元于是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某个孤独的冬日,他于漫天大雪中感伤自己前路茫茫,于是就有了《江雪》。最为出色的还是《永州八记》,自《始得西山宴游记》始,以《小石城山记》终,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写出了自己满腹才华却被埋没的不平与怨恨,也写出了自己在极度的苦闷中渴望心灵平静的追求。
不同的地域,同样的心情,柳宗元和苏东坡在这诡谲的命运中,心有大志却请缨无路,于是他们只能寄寓笔端,以抒胸中惆怅郁结之意,这实在是令人唏嘘。
还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的白居易和他的千古绝唱《琵琶行》。一个秋夜,寒风瑟瑟,荻花飘摇,45岁被贬至江州的司马,听到琵琶女的美妙琴声,倾听她的凄凉身世,联想到自己的郁郁不得志,不禁悲从中来。朝堂中的明争暗斗,直言进谏却被诽谤非议的不公平待遇,江州僻远的孤独无奈……一幕幕在心中百转千回,于是他落千古失意者之泪,打湿了青衫,尤其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适何必曾相识”,千百年来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被贬的这段经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的消极情绪日渐增多。虽然这一点与苏轼的始终乐观旷达截然相反,然而诞生伟大作品的过程和结果却是大致一样的。
从柳宗元到白居易再到苏轼,我们发现,他们的生活中缺少了安适,文学史上便出现了一个泰斗。当然,因官场生活不如意而让中国文坛生辉的,远不止他们几个。陶渊明就是其中比他们更早的一位。因为感于“岂能以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他毅然辞去彭泽县令之职踏上回乡之途,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犹如虎口脱险一般愉悦的《归去来兮辞》,读到了他归隐乡间之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读到了他对《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的向往。
还有中学语文课本选入作品最多的“诗圣”杜甫。试想,若非遇上“安史之乱”,也许这位大诗人还继续安居长安追求他的“兼济天下”的理想,那我们焉能读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等这样“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句呢?
李白也何尝不是如此。若没有杨国忠、高力士等人的妒贤嫉能,我们哪能听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令人荡气回肠、掷地有声的豪迈之言呢?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必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也不必再说“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单是以上这些大文豪们的事例已足够告诉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的作家,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的论述——包括孔子、屈原、韩非等在内的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因平生贫困坎坷而发奋著述,终成“大器”。而司马迁本身,就是“穷而后工”的一个最好证明! 若非惨遭宫刑,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能成为史家之“绝”唱,称得上“无韵之《离骚》”吗?
如果没有苏轼们的被贬,谁敢肯定我们今天还会读到这些这么好的作品?他们的被贬,既是他们的大不幸,又是他们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坛的大幸,我们的大幸。
如果陶渊明甘为“五斗米折腰”,李白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杜甫不曾“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那,可能我们中国文学史都会改写吧?“诗穷而后工”,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