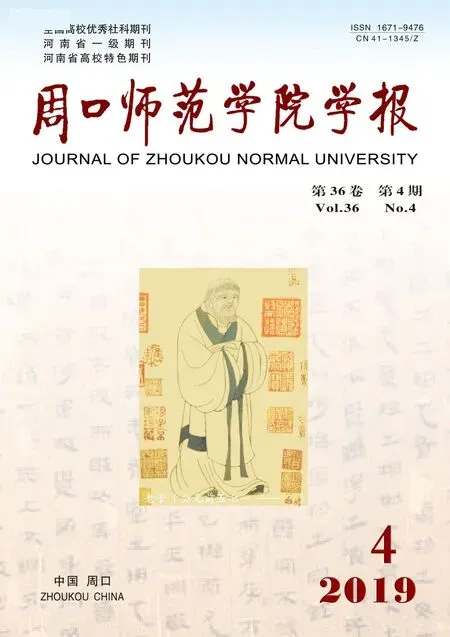论《古今和歌集》中的“菊”意象
——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
安佰洁
(枣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成书于平安时代前期的《古今和歌集》(下略称《古今集》),咏唱了各种各样的花。其中排在前5位的是樱(54首)、梅(30首)、女郎花(19首)、萩(16首)、菊(15首)。而在之前奈良时代编撰的和歌集中,这排名前5位的花中,唯独菊未出现。根据作者的生存年代及和歌所吟咏的场合来看,15首有关菊的和歌应该是创作于9世纪中下叶到10世纪初,属于平安时代前期(858-930年)。这就证明菊进入日本歌人的视野是平安朝之后的事。这时日本已经历了9世纪前期的唐风讴歌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深层次的吸收和消化,并且进入国风文化时代。作为从中国东渡到日本的异国之花[1],菊在《古今集》中绽放着异彩。
本文将分析《古今集》中“菊”这一意象,比较中日古典诗歌中菊的不同,并探究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菊”意象的影响,以及当时日本文学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时所做的取舍。
一、菊花的颜色
(一)白菊与黄菊
在这15首有关菊的和歌中,明确指出菊花颜色的是以下3首,且皆为白菊。
272 花耶抑否耶,捣岸浪花耶,吹上滨边菊,秋风拂白沙。
274 在此赏花人,待人人落后,篱边白菊花,误作白衣袖。
277 心事殊难定,折耶不折耶,初霜如白菊,白菊也开花。
272是说把随风摇曳的白菊误认作潮涨潮落时的白色浪花,而274说把其错看成自己所等之人挥舞的衣袖,277说分不清哪个是白菊哪个是白霜,都是运用比喻的手法描写白菊的美。
这15首咏菊和歌中,没有一首明确提到黄菊。但是,在平安初期及其之前的汉诗文中,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编撰于奈良末期的《怀风藻》有6首汉诗咏到菊,但未提及其颜色。平安时代的3部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出现了7篇提及菊花颜色的诗文。但除了《经国集·重阳节菊花赋》中的“或素或黄,满庭芳馥”一句提及白菊之外,其他尽是黄菊。之后,与《古今集》同时代的汉诗文集,如《田氏家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等,虽然多次提及白菊,但是在这些私家集中黄菊依然占主流。
也就是说,平安时代前期以及之前的时代,两大韵文体系——和歌和汉诗,对菊花的吟咏在颜色上有着完全不同的侧重。和歌更青睐白菊,汉诗却更偏向黄菊。这与当时日本对中国诗文的受容不无关系。《怀风藻》主要受《文选》《玉台新咏》《艺文类聚》等六朝诗歌和《王勃集》《骆宾王集》等初唐诗的影响[2]68。而在这些作品中,菊的色彩被提及的诗文寥寥无几,即使偶有提及也是黄色。白菊入诗,是在中唐之后的事情[3]。中唐诗人许棠《白菊》诗中说“人间稀有此,自古乃无诗”,也证明了中唐之前鲜有甚至是没有关于白菊的诗文。正如《礼记》所讲,“季秋之月,菊有黄花”,当时诗人们对菊的认知应该是局限于黄菊。
而平安时期的三大敕撰汉文诗集更多的是受到唐朝诗歌的影响[2]75。中唐以后开始出现大量描写白菊的作品,甚至有些著名诗人的白菊诗歌超过黄菊[4]35。在唐诗的影响下,日本汉诗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诗人也开始关注白菊,咏白菊的诗歌比之前有所增多。
《古今集》成立于敕撰汉诗集之后,这时文人对白菊的感知已经比较深入。同时,从这些有关白菊的和歌来看,皆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将白菊比作“白色浪花”“白色衣袖”“初霜”等。而这些正是深受歌人喜爱的日本式的传统意象。在歌人眼中,或许这些意象恰好与白菊相互应和。比起黄菊,白菊更符合和歌式的审美。因而,白菊也更受歌人关注,被多次咏入和歌。
(二)菊花的变色
在这15首和歌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多次提到菊花的变色。菊花的变色在日语中被称为“移菊”,是指在晚秋白菊花瓣末端变成紫色的样子。这种颜色变化原本只是因为寒霜侵袭,花瓣的植物纤维受到损伤而产生的。平安时代的贵族敏感地抓住了这细微的变化,并将其咏入和歌。
271 辛苦植花时,花开期待久,秋天菊盛开,颜色莫衰朽。
278 秋菊因霜降,花颜变色来,本来同一簇,二度似花开。
279 秋去重阳过,菊残尚有时,花颜虽变化,花色却增姿。
280 初开初宿地,今日已迁移,何叹菊花色,亦随秋草衰。
271惊叹于时间流逝之迅速,280感慨菊花凋零,对菊花的颜色变化含有惋惜之感。而278将遭遇霜冻而变色的菊花比喻成第二次盛开,279咏叹变色后的菊更加华美,并以此来暗示宇多法皇退位后权势更加强盛[5]149。
据小泽正夫的解释,在平安时代,菊花的这种颜色变化是受人喜爱的[5]146,所以在和歌中有对“移菊”的赞美。
在《古今集》时代以及之前的汉诗中,仅有菅原道真的“潭菊落装残色薄”一句明确地描写了菊花的颜色变化,但未提及“移菊”意象。可以说,“移菊”在日本是和歌中特有的。
唐前的诗歌中,没有一首提到菊花的颜色变化(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文本材料)。到了唐朝,在《全唐诗》700多首咏菊花的诗作中,却只有2首涉及菊花颜色的变化。
白菊为霜翻带紫,苍苔因雨却成红。
(《初冬偶作寄南阳润卿》皮日休)
正怜香雪披千片,忽讶残霞覆一丛。还似妖姬长年后,酒酣双脸却微红。
(《和吴子华侍郎令狐昭化舍人叹白菊衰谢之绝次用本韵》韩偓)
皮日休的诗提到了白菊因霜变紫,与下联的苍苔因雨变红相呼应。与和歌中描写的“移菊”相比,本诗对颜色的变化并无明显的赞美,只是起到了强调冬寒的作用。韩偓的诗虽然惊叹于白菊衰谢之前的色彩变化,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色彩变化并未被广泛关注。另外“残霞”的“残”和“长年”都不是积极含义的词语,带有慨叹岁月变迁、寂寥之感。
比起颜色的变化,中国诗歌中更推崇的是菊花的“不变”。如下诗。
灵菊植幽崖,擢颖凌寒飙。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
(《菊诗》袁山松)
中国诗歌中傲霜盛开是菊最突出的特征,诗人们看中的是其人格意义。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诗人有意识地回避菊的颜色变化,而对其不畏风霜、坚贞不屈的赞美不胜枚举。受此影响,以中国诗歌为范本的汉诗,同样没有将“移菊”纳入视野。但是在古代日本,特别是进入平安时代以后,人们敏锐地把握着时间的变化,并习惯将自然和人事都纳入时间的系统中——这也是日本本土特有的观念的形态[6]。所以,在和歌中色彩变化必然会受到关注。歌人更注重的是季节的流转和自然景观的微小变化,并从这些变化中找到美的体验。
二、菊花与长寿不老
在中国,涉及菊与健康长寿关系的诗歌,最早是西汉扬雄的《反离骚》:“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这种思想也为后世所继承,如唐朝杜佑编纂的《通典》中有关于菊水的叙述:“菊潭有菊水,傍水居人饮此水,多寿也。”这种菊可以治病延寿的思想的流行,又加上菊花盛开的时节恰好是重阳节前后,使菊与重阳节有了密切的联系。在古代中国,重阳节之时为了求得长寿有服用菊花的习俗。最常见的便是饮菊花酒[4]11。这种思想也在诗歌中屡屡出现。如陶渊明的诗句,“酒能去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并序》)。
在中国唐前以及初唐的诗歌里,谈及菊与长寿的关系时,背景多是在重阳节,方法是食用菊花(特别是菊花酒)以得长寿。日本汉诗受此影响,和中国诗歌有同样的倾向。如《菅家文草》第48首《九日侍宴,同赋喜晴,应制并序》中的诗句“献寿黄华酒,争呼万岁声”。
在这15首有关菊的和歌中,有3首涉及寿命。它们呈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
270 菊花和露水,手折插人头,花露能延寿,长如不老秋。
273 湿袖复干袖,山中菊露茂,何时朝露间,我已千年寿。
276 秋菊盛开日,折花插满头,身先花后落,知在几时休。
270说的是折了沾有露水的菊花戴在头上,祈求能够长寿。273讲的是走在菊花丛中体会到仙境一般的感觉:衣服被菊花上的露水打湿;在露水蒸发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或许人间已过千年。这里的菊花是盛开在通往仙境的山路上的。菊花和露水,让作者联想到人间与仙界在时间上的巨大差异。276讲的是面对人生无常将菊花插在头上来安慰自己。
270和276都有“将菊花插在头上”这个动作。在日本传统文化习俗中,常将盛开的花或者常绿树的枝叶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插在头上,希望得到其生命的力量以获得长寿[7]101。这种习俗在其他和歌中也多有体现。
另外,270和273在咏菊花的同时,也提到了“露”。这里菊花上的露水让人联想到菊水,菊水被认为是不老之药。这首和歌是受中国的菊水典故的影响,用“菊花露水”来祈愿长寿。同时273也受中国神仙思想的影响[5]146,认为这种人间和仙界在时间上的差异,给人带来长寿或是长生不老。那么这盛开在通往仙界的山路上的菊花,就是把人带往长寿或长生不老的一条途径。菊花以及菊花上的露水就和长寿、长生不老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在古代,日本人认为植物上附有神灵,在花草树木上感受到超自然的力量,为了获得植物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将植物插在头上。菊花随同重阳节的习俗一起传入日本后[7]127,日本人开始以佩戴菊花的方法来祈求健康长寿,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习俗与日本传统思想以及和歌传统的融合。
而和歌中没有出现“菊花酒”,这与《古今集》时代的审美意识有关。1100余首和歌中,没有一首出现“酒”字,也没有任何关于“饮用·食用”的语句。在《古今集》时代的和歌的审美世界里,不存在“酒”这一类事物。所以,在中国诗歌以及日本汉诗中吟咏的“菊花”之“酒”,也就无法在《古今集》中登场。
另外还有2首和歌虽没有直言菊与长寿的关系,但是从其语境中能够发现菊为象征长寿之花的意象。
268 移植复移植,非秋不发花,今年花纵落,根岂似枯枒。
269 云上朝天阙,悠然赏菊花,天空开灿烂,误认是星槎。
268是作者赠予友人菊花时,附在菊花上面的一首和歌。作者希望友人将这株菊栽到自己的院子里,“即使花凋零了,但是菊的根不会死去。每年秋天菊花都会盛开”。用生命力旺盛的菊表达了作者对友人无病无灾的祝愿。269是作者呈献给天皇的和歌。意思是“这真不愧是云上(宫中)的菊。如此光彩夺目,怕是会与天上的星辰弄混了”。菊在这里被比喻作星辰,并暗示这是天上之花。这也与上一节提到的菊与仙界以及长生不老的关系相通。用这种有特殊含义的花来表达贺意。
如上所述,在《古今集》的时代,菊寄托了人们长寿和健康的愿望。与中国诗歌和日本汉诗的“饮菊花酒”不同,和歌中咏唱的是“佩戴菊花”。歌人们一方面接受中国关于“菊水(露)”和菊花可以长寿的思想和风俗,一方面同日本自古以来的信仰和习俗相结合,巧妙地将菊咏入和歌。而且这种思想已经相当深入,菊被当作吉祥之花来表达各种祝贺之意。
三、菊花歌的分布规律
在《古今集》中15首有关菊的和歌中,有13首是收在卷五“秋歌下”中,另外2首被收入“恋歌”中。其中,“秋歌下”中的13首,分别是第268首到第280首和歌,从种植菊花开始,中间或赞美菊花的美,或用菊花来表达贺意,或用菊花来咏叹时间的流逝,最后为菊花的颜色褪去而伤感。以上两节从“菊花的颜色”和“菊花与长寿不老的关系”两方面论述了菊花意象。除了第275首和歌之外,其他的12首都可以归于这两种角度。
275 一枝秋白菊,水里卧横斜,大泽深池底,何人竟种花。
这首和歌原文中并没有提及颜色,但是杨烈先生在这里特意翻译成白菊,应该也是结合其他和歌中所提及的颜色而做出的合理判断。另外,因为其咏唱的场合是宫廷歌赛,可以联想到和歌中应该暗含着庆贺的寓意,这也就与菊花作为长寿良药这一意象相吻合。
而收入“恋歌”中的2首,分别是470和564。
470 风闻多白露,夜起为彷徨,及昼思无及,露消早已亡。
564 宅畔篱边菊,霜多压短垣,寒霜消且尽,我恋亦销魂。
恋歌卷内描写恋爱心理的和歌,是根据恋爱的进行过程来排列的(萌芽-产生-发展-获得结果-产生罅隙-终结)。470是恋歌的第2首,属于恋爱的初始阶段,因听到对方的传言而萌生爱意不能自已。这首和歌的中译文为了避免混乱而抹去了“菊”的存在。564的意思是“我家院子里的菊花上面的霜眼看就要消失了。我的心也是如此——因为太过于思慕那个人了”。用初冬的菊花上的霜,来比喻因为恋情而备受煎熬的内心。这首和歌中讲述菊的第一二三句是“消失”的序词,重点是描写恋爱感情的后两句。
恋歌中的这两首和歌,咏菊的部分都属于序词部分,是为了表达恋爱感情而服务的。470中菊的存在意义或许仅仅是因为“菊”的发音与“听说”相同,这成为咏“未见之恋”的一个关键词。而564吟咏的方法曾经在之前的《万叶集》中也有出现(春来花草上,偶亦降清霜,消去清霜后,我心恋不忘),只不过将“花草”换作了与霜露相似颜色的“菊”。而且,470和564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人公因为太过于思恋而“消失”。“消失”所对应的是“白露”和“霜”,而菊仅仅是这“白露”和“霜”的一个背景。
综上所述,在秋歌中收录的关于菊的和歌中,菊的印象鲜明,是整首和歌的主角。而在恋歌中,菊只是一个配角,为咏叹爱情服务,或者可以说是为技巧的运用服务,菊本身这个形象的存在感并不强烈。
四、结语
随着中国的古典诗歌和风俗制度传到日本,菊花这一深受中国文人喜爱,并且与重阳风俗密切相关的意象也给日本的韵文带来了新风。无论是汉诗还是和歌,都开始关注菊花。通过对《古今集》中15首有关菊花的诗歌的分析可以发现:首先,这个时代虽然已经受到了中国唐前以及唐朝诗歌的影响,汉诗中也多是吟咏黄菊;但是因为和歌的传统和日本式审美意识的影响,歌人眼中的“菊”多是“白菊”,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了菊花色彩的变化,使“移菊”成为和歌中独特的意象。其次,受中国关于菊的文学以及习俗的影响,日本这个时代的菊花也寄托了人们长寿和健康的愿望;但是与中国诗歌和日本汉诗的“饮菊花酒”不同,和歌中咏唱的是“佩戴菊花”。最后,咏菊花的和歌更多的是与时节相关,少有用来表达爱情;即使表达爱情,也仅仅是为技巧服务。
平安时代的歌人在摄取异国意象的同时,也做了符合和歌审美的取舍,巧妙地运用比喻等修辞技巧,偏爱白菊,将菊花变成和风的意象;同时,关注时节的流转,从菊的颜色变化中发现了新的美。也继承自古以来的植物崇拜意识,积极地吸取关于菊花延年益寿的思想。这些和歌与模仿中国诗歌的日本汉诗不同,呈现出了日本的本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