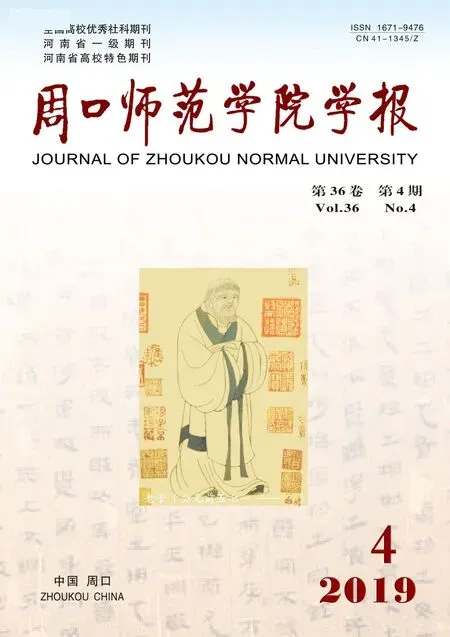论韩愈反佛的佛教因素
李格香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关于韩愈与佛教之关系,学者多以韩愈《论佛骨表》篇为据,冠以韩愈“排佛斥佛反佛”的帽子,但作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度引领着唐代文坛风气的人,韩愈真的容不下佛吗?据陈寅恪先生按,韩愈曾随其兄长谪居在新禅宗的发祥地韶州,且当时正值新禅宗学说宣传的极盛时期,当时韩愈虽然年纪尚小,但以其幼年之聪颖,未必不在新禅宗学说浓厚的环境氛围中有所感发,但这毕竟是幼年时期的熏染,对韩愈参悟佛理,理解佛教的影响必是很小的。陈寅恪还提出“退之之道统之说”实际上因为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并以此认为韩愈其实深受禅学影响。虽然如此,但从韩愈留存的与佛教相关的资料来看,韩愈于禅学上的造诣其实并不高。他虽然从小受到浓厚的佛教氛围熏染,拜官腾达后也不排斥与僧人交往,甚至还在被贬潮州后主动与大颠交往,探讨佛理,可见其对佛教、佛学并无深恶痛绝之感。另外,从韩愈的一生行迹来看,除了《论佛骨表》和《与孟尚书书》外,并未有太多其他关于韩愈斥佛反佛的证据留存于世,反而还有不少他与僧人交往和对佛学探讨的事迹留存于世,这些无疑都让人对韩愈的反佛心理进行更为深沉的思考。况且,在我国历史上,佛教不单是一种出世的哲学宗派,它与我国历代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发展、百姓的生活都有密切联系。既然如此,韩愈反佛背后的佛教渊源又是什么呢?佛教在唐朝的发展,对韩愈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至于韩愈不惜牺牲掉大好的仕途也要反佛呢?
一、《论佛骨表》与韩愈反佛说
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论及韩愈反佛,说其“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1]323,“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1]322。陈寅恪先生并不认为韩愈是完全反佛的,反而觉得韩愈的“原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贯彻了“济世安民”的儒家中庸学说和“贪心说性”的天竺佛学。“退之首先发现《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疑,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1]324可见,韩愈受过新禅宗的影响。而关于韩愈斥佛,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应当考虑其特别的时代性,即韩愈所处之时佛教徒数量甚多,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秩序。但相较之韩愈痛斥力诋道教,韩愈之斥佛,显然其力度与影响都远不及前者。汤用彤先生则认为韩愈只是代表一时的反佛潮流,其作为文人,既无反佛的理论建设,作为朝臣,也无取佛教势力而代之的实力,并认为韩愈作《论佛骨表》时高涨的反佛情绪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
唐宪宗时的宗教政策规定,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拥有免除赋役之特权,因此当时很多人为了躲避赋役从而出家修行,其中又以佛教徒最多,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在佛教徒给国家和社会造成诸多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唐宪宗非但未采取相关的整治措施,反而沉迷于宗教活动,为了个人的祈福延寿,坚持举行迎佛骨的宗教盛会,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故而,韩愈愤而上书《论佛骨表》,其中言辞甚是激烈,连宪宗都说:“愈谓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咸致夭促,何严之乖刺也!”[2]4200关于韩愈为何对佛及佛祖之骨的轻蔑和诅咒之词甚为激烈,有学者便提出,是因为宪宗奉佛导致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达到高潮,韩愈有着儒者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等,还有从韩愈的文学观和思想层面探究的。阎琦先生认为,韩愈斥佛言论之所以过于激烈,是因为韩愈受到了淮西战事事件的影响,同时还有他自身性格“褊僻”的原因[3]。以上诸家见解,不无道理,历年来众多学者对韩愈《论佛骨表》的研究和分析也颇为全面和准确,但其中忽略了佛教本身的因素。韩愈之反佛,实则是反对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对于社会和国家安定不利的因素而已,他自始至终并未对佛教所宣扬的理念和思想进行批驳。韩愈反佛,批判的也不过是佛教出于夷狄,非“中国”之法,与儒家正统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相悖,且由于当时宗教徒“不课丁”的政策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佛教带来的众多“惑众败政”的现象,一时之间就成了“为乱亡之源”。韩愈排佛跟历代大多数排佛的人一样,都是出于政治伦理观的原因,并未触及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也并未考虑到佛教在其本身的发展和僧侣修行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偏差和问题。而恰恰是这些问题,最终把佛教推向了与维护政权和社会安定的对立面,历史上所有的排佛斥佛活动都与佛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息息相关。
二、佛教弊病之“禅病说”
在一定程度上韩愈算得上中唐时期激烈排佛的代表,但无论在其排佛的过程中,还是在其与佛教僧侣及奉佛的士大夫的交往中,韩愈会受到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如其《送浮屠文畅师序》中“夫鸟俯而啄,仰而四顾,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4]250莫不透露出禅宗渲染的超脱生死的精神境界。虽然韩愈对于佛理的认知和领悟并不深刻,但不能否认他在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上所做出的尝试。更重要的是,韩愈虽未完成这个尝试,但其后继者李翱却在此有所建树,并对韩愈之排佛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李翱也承认佛教在当时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在《与本使杨尚书请停修寺观手状》中说:“天下之人以佛理证心者寡矣,惟土木铜铁周于四海,残害生人,为逋逃之薮泽。”[5]6405但其在《去佛斋》一文中也说“惑之者溺于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5]6424,认为佛教的宗教信仰中并不全是好的,大肆建寺造像敛聚钱财的现象更坏,但除了“禅病”使然的种种不良现象外,真正代表佛教禅宗的佛理和佛心是好的。因此,李翱主张“排其教,毁其寺,纳其理,证其心”[6]319。有学者提出,李翱的观点是韩愈对佛观点的延伸,大体可以代表韩愈对佛教的真正意见,同时这也是禅宗大师们通过援儒入佛而付诸实践的事。
对于韩愈包括历代反佛的缘由,鲜有人去探究禅、佛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盲区。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通过对禅宗及其所奉行的经论中对“禅病”有所揭示,无论是南北朝的《禅要秘密治病经》,还是唐代的《楞严经》《起信论》等,都有关于行禅致病的记录。关于行禅致病的记录,早先称为“禅病”,后来也叫“着魔”,主要表现为幻视幻听、疑神疑鬼,严重的话还会使身心扭曲、狂乱疯癫,甚至于自杀杀人、惑众闹事、奸盗反逆、违法犯罪。说到“禅病”,不得不提“神异”。随着外来佛教传入的神异功能,包括许多外来僧侣的惊世神迹传说,这些神迹和神异皆不超出“神通”的范围。而“神通”,则是流行于古印度多种宗教中的非现实幻想,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和古代方士的某些离奇虚幻的想象差不多。最通行的神通有五类,称为“五神通”,即天眼通(无所不识)、天耳通(无所不闻)、他心通(能知他人的一切心识)、宿命通(能知过去的一切行事)、神足通(能自由变化、飞行无碍)[6]15。在佛徒的诸多传说中,佛徒都能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神通,但佛教所普遍倡导的是从禅定中成就神通。在中国,早期流传的禅也与神通密切相关,甚至于早期一些高僧也是追求神通的忠实信徒,如康僧会(三国时期)便认为,只要完成“安般禅”,就可以无幽不睹、无遐不见、无声不闻,从而“制天地,住寿命,猛神德,坏天兵,动三千,移诸刹”。道安(东晋)也认为成为“十二门禅”就能使“神”精,“陵云轻举,净光烛照;移海飞岳,风出电入”。
自沮渠京声译出《治禅病秘要法》后,当时修禅致畸的经验便有了书面的总结。该书所列举的各类禅病多以精神错乱为主,它提出的治疗方案基本上也是一种标准的信仰治疗,即以禅治。这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能根治禅病。《起信论》也提到过坐禅入魔的病态,并认为这是“为诸魔、外道、鬼神惑乱”,而产生惑乱的根源则在于“贪着名誉利养”,过分“爱着世事”,利欲熏心。该书提出的应对办法是从哲学的层面出发,认为世界一切“皆为是心”,“心生种种法生”,只要心性纯明,就会明白神异功能不过是内心幻化的假象。就像僧叡说的,“神通变化,不思议心之力也”。可见,神通和禅病,一直伴随在佛教和禅宗的发展中,流行于行禅者的修行过程中,但是从未占据主导地位。禅宗要求行者做到“无念”,即心理上的绝对宁静、清明,但这在修行中是极难做到的,因此真正能够体道悟真的禅师也不会把“神通”当真。
韩愈《论佛骨表》提及的“焚顶烧纸”“断臂脔身”等行为,便是“愚冥”百姓们行禅致病的直观表现。《唐会要》又云:“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显重,乱政犹轻,惟有僧尼,颇为秽杂。”《坛经》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可见,佛家对修行者是有要求的,只要修行者们心性纯明,自然能认清内心幻化的所有假象,不为禅病所扰。而唐宪宗时,“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真心事佛”,臣民们自然是上行下效,“老少奔波”,“惟恐后时”。而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士大夫,则认识到了当时的崇佛政策及禅病盛行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一直致力于反佛,希望能够抵制禅病对佛教、对社会的危害。但唐宪宗迎佛骨这一盛举,却引发了禅病爆发的契机,随着该项盛举的进行,一时之间各种禅病行为在民间百姓身上愈演愈烈,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不安。宪宗迎佛骨事件也为此次韩愈上书反佛推波助澜,推动了韩愈反佛情绪的高涨。
三、逐步“入世”的唐代佛教
隋唐以前,各朝统治者实施的宗教政策各不相同。自444年魏太武帝灭佛失败之后,历代王朝对佛教或限制,或扶持,但都没有再采取过分极端的手段,因此使佛教有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机会,僧尼寺院的数量也持续上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577年北周武帝攻占了当时北方佛教的重镇邺都,并下令全境灭佛,殃及的僧尼近300万,在当时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因此,杨坚建立隋朝后,便下令恢复和重建佛教,其后隋文帝亦不断下诏令修寺建塔,招徕游僧。道宣“隋高造寺,偏重禅门”语便是隋王朝扶植佛教的有力证明。直到唐初,排佛倾向再出,《续高僧传·志超传》载,唐初严敕私度,禅师志超却“曾无介怀,亲度出家者四人”,甚至此举还得到了道宣的赞赏,僧侣们也都以违禁私度为荣。道宣在《静琳传》中有言:“度杂无私,宪章有叙;故使外虽紧固,内实流通。”可见,当时打着僧侣内部章法的旗号私度是普遍存在的情况,这种行为对后来宗教中佛教徒人数居于首位有巨大的影响。
唐时尊佛、排佛皆起于唐太宗。632年,唐太宗在法门寺礼佛,开启了唐王朝尊佛崇佛的先河。唐太宗与玄奘大师的亲密关系更是众所周知。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太宗不仅多次劝其还俗辅政,还为他建立了弘法寺,供其修行和译经。除此之外,太宗本人也深入藏经,研读《菩萨藏经》,致力于菩萨道的探索,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刻于石碑,即“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尽管如此,太宗依然采取过限佛措施,开元十八年(730)后,唐太宗为了进一步限制佛教,强化了度牒制度,不经官方认可未入官寺籍簿的僧众,皆为非法僧侣。但是这项措施非但没能解决流民游僧的问题、制止劳动力继续向释门流去,还使得更多的僧侣流散在朝廷监管之外,反而加重了禅众的失控。
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却给禅宗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随着两京的先后陷落,大量流民不断涌向南方,京派禅师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南方禅众的数量随着流民的涌入数量骤增。而中央集权的分裂、藩镇的割据等,都为禅宗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虽然禅宗分宗立派后地方色彩逐渐浓厚起来,但它们大都没有放弃效忠中央的政治倾向,从这些宗派争夺正宗法嗣的斗争来看,佛教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出世宗教,它与政治的联系愈发紧密了。700年,武皇亲自将神秀迎接进京,此后,不仅对神秀礼遇有加,还特地为他建造了多座寺庙,后来中宗继位,对神秀的礼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706年神秀圆寂,他的影响在其弟子普寂和义福的推广下仍旧盛极一时。神秀一代,是北禅宗在唐代最繁盛也是最稳定的一代,而佛教的经营也由原来的隐际山林、自给自足转移到半依靠皇权官僚、半靠自我经营的状态;在禅观念上,也开始由非政治化和非道德化的宴坐安心,转而承担起部分内训学徒、外化众生的教诫作用。其后,随着北禅宗逐步被唐王朝官化,禅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有很高的权势。直到唐玄宗时,虽然玄宗采取过限佛禁佛措施,制止滥造寺庙,沙汰僧尼,屡禁“左道”,对“妄陈谶纬”和妄说因果的行为打击尤为严重。但是,玄宗并非一心灭佛,他也倡导三教合一,甚至在佛教中独尊《金刚经》,还御注了《金刚经》,玄宗此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为南宗的崛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南宗直接将《楞伽经》传承改成了《金刚经》传承,其宗旨不但否定心外有神,同时也极少渲染神异,因此禅宗南宗的魅力逐渐为统治者看重。后来,由于神会在“安史之乱”对唐王朝始终追随效忠,南宗又赢得了肃宗特别是代宗的好感,加之南方禅众势力日益壮大,神会弟子们的多方经营,南宗最后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神会至此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向京派官禅争夺正宗地位并取得了成功的南宗禅师代表。神会所建立的慧能南宗法统,直到德宗时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德宗在宗教政策上除了继续信奉密宗外,还十分重视华严宗。贞元十二年(796),德宗诏澄观入殿讲经,赐号“清凉”,并尊其为国师。到宪宗时,佛教不仅在统治阶层深受推崇,在社会上也是深入人心,民间的礼佛奉佛氛围十分浓厚。但同时,佛教发展到如此鼎盛的时期,政教矛盾也必然会更加激烈。
对于统治者而言,接受和推崇佛教也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历代君王,无论奉佛程度的深浅,其实都保持着对佛教中消极因素的清楚认识,从而从未停止过对佛教的管理和限制。虽然宪宗对佛教的笃信很强烈,甚至于有些过于沉迷于佛教了,但为了维护江山社稷,他也绝不会在宗教问题上丧失立场。当越来越多的农民以出家为由躲避赋税,寺院建筑大量损耗社会财富,寺院经济严重侵犯到国家的利益时,宪宗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807年,宪宗就曾下诏群臣,谓男丁女工是耕织之本,严禁农民们冒僧、道、尼之名逃避徭役,他还批评了当时广兴土木、大造寺院的行为,称之为国家“耗蠹之源”,并颁诏严禁“私度”。除了帝王,士大夫阶层在对佛教信仰和支持的过程中,也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以协助帝王随时应对宗教带来的消极影响,韩愈反佛便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迎佛骨是唐王朝重大宗教活动,自太宗始,到宪宗时已经是第六次迎佛骨。据 《旧唐书·宪宗记》载:“(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2]466而关于这次迎佛骨事件,《资治通鉴》也有载:“(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僧众迎之。(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不及。有谒户充施者,有燃香烧顶供养者。”[7]《资治通鉴》所载此次迎佛骨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动荡和消极影响,正是韩愈上书《论佛骨表》所主张的主要原因之一,即“焚指烧顶,百十为群,解衣三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4]409。可谓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百姓的生活。又“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4]409。作为儒家道统的忠实维护者,当佛教威胁到国家和社会时,韩愈必然会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和抵抗佛教对国家对社会的残害。韩愈《论佛骨表》虽因言辞过激以致宪宗勃然大怒,把他贬至潮州;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佛教问题的要害,即佛教在当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动摇到整个社会基础了,让宪宗意识到了此次迎佛骨所带来的超出预期的不良影响。他说:“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他在谈及韩愈到潮州任上所上表“哀谢”时又说:“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2]420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愈反佛所牵涉的佛教本身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佛教本身的问题也并非是短时期内形成的,其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和消极影响也是历史累积的问题。除了一直伴随于佛法和修行者们的“禅病”外,统治阶层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对佛教加以利用,包括佛教自身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做出改变,都使佛教逐步走向异化的道路,并与政治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而于乱世之中鱼龙混杂的各色人等混入佛教,不仅严重拉低了佛教的品质,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是导致后来政教问题爆发的根本因素之一。对于韩愈反佛,历来就有公论,而对韩愈反佛的原因也有探究,但是关于韩愈反佛背后与佛教相关的深厚历史渊源及原因,也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