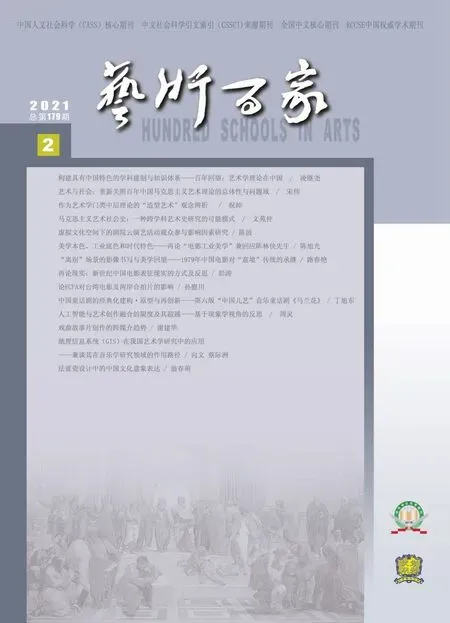《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褾轴》的史学体例及逻辑关系研究*
张 扬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论装背褾轴》从晋代一直追溯到唐代的装裱情况,明确记录装裱发展的时间(朝代)、人物、事件、影响、技术等内容,并作出相应的评论,是中国最早按照编年体史学体例来构建装裱史的著述,亦是以人为线索对装裱活动进行研究的装裱史。《论装背褾轴》与其它篇章的逻辑关系紧密,环环相扣,其位置顺序不能变动和更改,具有独立的学术与史学价值。
张彦远是唐代的书画理论家、鉴赏家,精通书画装裱,其著述的《历代名画记》是研究我国唐代及唐代以前绘画相关内容的重要文献。张彦远自幼家境优渥,家藏丰厚,世代喜爱书画,他耳濡目染,加之兴趣所在,最终痴迷于书画鉴藏并精于书画作品的保护与装裱。《历代名画记》约成书于公元九世纪中期,全书共十卷,主要论述了中国早期绘画的创作、理论、鉴藏、品评、市场、书画装裱、绘画名人、作品等内容,其中多篇章节对书画装裱的史料、技艺等加以记述整理。《论装背褾轴》在《历代名画记》的卷三中,是《历代名画记》中记载装裱史、装裱技艺最为详实的部分,亦是书画装裱编年史体例最为完备的章节。张彦远在该篇章中主要记录了晋代、刘宋初期、宋武帝、宋明帝、梁武帝、唐太宗皇帝时期的装裱名家,并对以上各时期的装裱水平阐述了个人观点。另外还对与作者同时期的装裱技术、形制、他人的装裱见解、装裱与气候的关系等作出记录和评价。
学界对《历代名画记》研究的成果颇多,如余绍宋在著作《书画书录解题》(2012年)中论述了《历代名画记》的通史性质,但是没有关注到其记载书画装裱史开端的历史价值;俞剑华在译注《历代名画记》(2007年)时忽视了装裱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研究价值;毕斐的《〈历代名画记〉论稿》(2008年)则系统梳理了《历代名画记》的研究史,阐释张彦远的家世、个人成长经历及写作背景、动机等,并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张彦远自幼收集书画,不仅沉迷赏鉴,还精于装池。”[1]79毕斐准确地把握了《论装背褾轴》的写作背景;陈池瑜在论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画史体系及史论研究》(2009年)中未深入探讨《论装背褾轴》的体例结构;吴利滨的《〈历代名画记〉体例研究》(2014年)虽然认识到装背褾轴是对画面装饰、保护、流传、收藏等的补充,但是忽略了装裱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可见,国内学者深入研究《论装背褾轴》的成果偏少,研究文章中几乎没有从理论高度、学术价值的角度切入对其史学体例进行研究的。关于中国书画装背褾轴的古代文献记载,主要还有《法书要录》《装潢短论》《书史》《画史》《装潢志》《齐东野语》《南村辍耕录》《宋史职官录》《清閟藏》《长物志》《赏延素心录》《小山画谱》等书,对《论装背褾轴》的讨论亦如前文所述,未曾透彻研究。国外学者关于《论装背褾轴》史学体例与逻辑关系的研究也处于缺失状态。日本学者对《历代名画记》的研究主要是译注、校勘和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如冈村繁、长广敏雄、谷口铁雄、伊势专一郎等人。西方学者关于《历代名画记》的研究,从早期的翻译、梳理延续为考辨、证史,并热衷于对片断进行专门研究。如德国学者夏德的《中国绘画史基本文献》(1897年)肯定了《历代名画记》的地位与价值,并重点介绍了部分篇章;美国学者艾惟廉的《六朝暨唐代绘画文献选编》(1954年)是比较详细的评注,但仍未涉及《论装背褾轴》的史学体例与逻辑结构的研究。
因此,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论装背褾轴》在《历代名画记》中的独立体例和逻辑结构进行深入探讨,以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与史学价值。
一、张彦远与《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褾轴》
《论装背褾轴》是中国第一部完善的传统装裱简史,开篇记载了书画装裱水平从“不佳到精妙”的历史发展过程,时代清楚、人物具体、评价直接,为晋唐之间的装裱史厘清了主线,使装裱史获得了真正独立的身份。
《历代名画记》将绘画作品、艺术家、赞助人、前人的绘画理论、绘画作品的品评、真伪鉴定、作画的工具、载体、材料、题写的跋尾、钤盖的印章、绘画作品的装裱、保存、修复等内容融合在一本论著中,具有严密合理的写作逻辑,各卷内容环环相扣,顺序不可改变,形成一体化的、完备的艺术史通论。《论装背褾轴》的装裱史内容与整篇《历代名画记》内容前后相呼应,逻辑性强,前文为本篇埋下伏笔,本篇与前文内容吻合,构成了体例中不可缺失的章节,对这样精心安排的体例结构,全然不同于之前或同时代其他论著对装裱史的零星记录,可以说,《论装背褾轴》与前后章节之间有衔接性与连贯性,具有独立成章的研究价值。
《论装背褾轴》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学地位,与张彦远深谙绘画鉴赏、擅长书画装裱技艺,并希冀保护书画本体、延续书画生命的意图分不开。
张彦远出生于世家大族,从其高祖至张彦远,五世人都十分喜好收藏,这为张彦远的书画创作、鉴赏、装裱提供了学习、品鉴、操作的客观条件。在《历代名画记》卷一的《叙画之兴废》中,张彦远自叙道:“彦远家代好尚,高祖河东公、曾祖魏国公相继鸠集名迹……乃以钟、张、卫、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顾、陆、张、郑、田、杨、董、展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历代共宝,是称珍绝。”[2]7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张彦远家的书画收藏极其丰富,包含钟繇、卫夫人、顾恺之、展子虔等名家书画真迹。张彦远从小在世代家藏的熏陶中,对书画作品的鉴赏能力必定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正因如此,张彦远曾自信地称自己“收藏鉴识,有一日之长”[3]1。关于张彦远擅长书画装裱技艺,可以在《历代名画记》卷二的《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篇中看出:“余自弱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2]35“鉴玩装理”是其生活习性,“孜孜葺缀”是其对待字画的态度,从中可见张彦远熟练掌握书画装裱技艺,并对其非常重视。
不了解书画装裱是很容易损伤绘画作品的,甚至会导致绘画作品的消亡,此即《论装背褾轴》在全书中必须编撰的重要原因。张彦远语重心长地言及:“夫人不善宝玩者,动见劳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便损;不解装褫者,随手弃捐。遂使真迹渐少,不亦痛哉!”[2]35此意为不明白装裱的原理便会在舒展、卷起画作时,导致作品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如展开画作时,用力过大易造成的撕裂;卷起画作时,速度力度掌握不当,挤压画作会造成折痕等。所以张彦远看到“得其地,则远古亦完全。其有晋、宋名迹,焕然如新,已历数百年,纸素彩色未甚败”[2]35。此谓了解装裱知识、妥善保藏远古的书画名迹,即使是数百年前的绘画作品,其纸张色彩亦可如新的一般。若是不懂得装裱、保存书画的知识,即使是作画不久的作品,也会损坏至消失。所以说,不了解书画装裱就会置书画作品于损毁的危险之地,而书画作品是不可再生的——“夫金出于山,珠产于泉,取之不已,为天下用。图画岁月既久,耗散将近,名人艺士,不复更生,可不惜哉”[2]35。张彦远为这种因为不懂得装裱而损毁绘画作品的后果深感痛惜,我们亦可以体会到张彦远对这种不可再生的艺术品进行保护的迫切心情。此篇也是张彦远提示阅玩鉴藏家,在鉴别绘画作品艺术水平的基础上,需要深入了解装裱知识,做到妥善取阅与保藏,才能使绘画作品安全地流传于世。
二、《论装背褾轴》的编年体史学体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著述的书画装裱相关内容,体现出他在书画装裱领域的丰富知识以及书画保护方法的正确性,更为关键的是,如余绍宋先生所言:“是编为画史之祖,亦为画史中最良之书。”[4] 6这说明了《历代名画记》的通史性质。我们通读全书后会发现,《历代名画记》不仅是记录绘画的历史发展,还涉及收藏、鉴识、装裱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历代名画记》不仅是绘画通史,还有其综合性、复杂性的一面,对综合性、复杂性的准确把握,体现在宗白华先生的《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一文中。他曾详细地论述道:“彦远的书名虽然是史,但是设有体系的论述。全书共十卷,自第四卷以下,是包括自轩辕至唐会昌时的三百七十二个画家的小传和品评,这就是纯粹‘史’的部分;自卷一至卷三,却是十五篇专门论文,我们只就题目看,就已经感到那博大和精详了。不特是前无古人之作,就是后来想模仿他的人,截至现在,已经十世纪多了,却也并无一人能及得上他……在上面许多的专门题目中,其性质当然是很复杂的,所以对于人们所引起的趣味也很不一律。”[5]453宗白华先生关于《历代名画记》的全面认识,正说明了该论著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画史,还包含其他与绘画紧密相关的内容。
《论装背褾轴》就是《历代名画记》中与绘画密切关联的部分,并且与全书的史学体例保持一致,是书画装裱史编年体史学体例,体现了张彦远高超的编史水平和力求全面的历史意识。正是由于张彦远精通绘画鉴藏、擅长书画装裱技艺,从保护绘画作品的历史担当出发,《论装背褾轴》才能够对装裱发展的历史、关键人物及其装裱水平进行客观的记录和评价,且从不同角度对书画装裱技艺等方面进行详细阐释。
从中国书画装裱的发展历史来看,书画装裱最初的形态既没有实物遗存,也没有文字记载,以致关于中国书画的装裱何时起源这一问题,至今无从考证。有学者曾认为湖南战国楚墓中《人物御龙帛画》的存在形式,是书画装裱的最早源头,但由于缺乏类比和明确的文字记载,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一直以来,从史学的角度对中国书画装裱进行的研究,极为缺失,由于年代久远,书画装裱起源时间、最初用途等在没有可以参见的装裱实物遗存的情况下,关于技艺具体如何,无从辑考,更多的是一种揣测。只能说晋代以前,书画装裱技艺的发展还处于稚嫩阶段,主要表现在托裱过的书画作品不平整、有褶皱等问题上。书画装裱技艺从稚拙阶段发展到基本满足装裱要求的阶段,已是刘宋时期,以装裱名家范晔为代表,到宋武帝时,书画装裱技艺日趋成熟,发展到唐朝,已是臻于完善。
《论装背褾轴》在开篇开始构建书画装裱史,时代明确、评论清晰。对晋代以前的书画装裱水平,张彦远以“不佳”二字评论:“自晋代已前,装背不佳。”[2]46《法书要录》卷四《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亦有记载:“晋代装书,真、草浑杂,背纸皱起。”[3]146说明在晋代,装裱后的书画作品不平整、有褶皱,托画心和覆背的水平低下,达不到书画装裱必须平整的基本要求。虽然我们对晋代以前的书画装裱技艺无法详细探究,但是《论装背褾轴》记载了中国装裱技艺在晋代就已经出现,是中国传统的书画保护、装饰与修复的技艺。
《论装背褾轴》概述晋代以前的装裱情况后,按时代顺序以不同时期所涉及的装裱人员为脉络,使用“以装裱名家为线索”的编年体史学体例对全篇进行论述。“史学应该以人为主,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6]58可以说,《论装背褾轴》正是以人为线索对装裱活动进行研究的装裱史。书画装裱技艺发展到晋代依然解决不了褶皱问题,直到刘宋时期,才基本达到书画装裱的要求,而后日趋精美完善。张彦远曾阐述道:“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宋武帝时徐爰,明帝时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次图书,装背为妙。梁武帝命宋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又加装护。国朝太宗皇帝,使典仪王行真等装褫,起居郎褚遂良、较书郎王知敬等监领。”[2]46时间明晰、人物具体、评价客观,是按照时间、人物、事件的模式,渐次概述了主要朝代的装裱名家,勾勒出装裱技术从稚拙阶段到精妙的发展全过程。从中我们看到,晋代以前是装裱技艺处在萌芽期,发展到刘宋时期,才算勉强满足装裱的基本要求。这些装裱名家,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为我们了解装裱人员的身份、地位、官职、背景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3个C/C-SiC样品的载荷-位移曲线的下降趋势有所不同,C/C-SiC1 500和C/C-SiC1 550样品的曲线达到最大载荷后经历短暂快速下降后缓慢下降,而C/C-SiC1 450样品的曲线达到最大载荷后下降非常平缓,说明三者的断裂行为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热解碳涂层对裂纹和载荷的传播扩展有影响。热解碳是纤维和基体中的界面层,载荷从基体传递到纤维的过程中,经过热解碳发生不连续的转移[18]。图9所示为热解碳厚度不同对基体裂纹的作用示意图。热解碳厚度不同,对裂纹传播和载荷转移的影响不同[19-21],界面厚缺陷多,裂纹传播受阻,材料的断裂韧性强,但载荷转移效率低。
《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褾轴》开创了以装裱名家为中心,装裱历史与评论相结合的编年体史学体例,从装裱人员的身份、素养、地位、官职来看,此篇亦是文人的装裱史。南朝刘宋时的范晔是《论装背褾轴》中记录的最早的装裱名家。《论书表》中有记“范晔装制卷帖小胜,犹谓不精”[3]39,唐人张怀瓘也称:“范晔装治,微为小胜。”[3]146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基本确定,范晔是装裱技艺从“不佳”到“小胜”过渡期的关键人物。
虽然范晔将书画装裱技艺从稚拙阶段发展到勉强达到装裱的基本要求,但仍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直到徐爰等人继续完善,才将装裱技艺发展至精美称妙的程度。“宋武帝时徐爰,明帝时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次图书,装背为妙。”[2]46从“范晔始能装背”到宋武帝、明帝时装裱师的“装背为妙”,是装裱技艺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妙”是张彦远对此时装裱技艺的肯定。徐爰对装裱水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将长短不一的画心方裁至相同长度,并将水平较低的作品去除,达到艺术作品水平高妙和装裱精美的结果,具体在《法书要录》中有如下记载:“孝武使徐爰治护,随纸长短参差不同……今所治缮,悉改其弊……是以更裁减以二丈为度……其有恶者,悉皆删去。卷既调均,书又精好。”[3]39由此看出,经徐爰装裱过的作品,达到了优化尺寸和顺序的目的。
宋明帝时的虞龢精通书画鉴赏,对装裱有着独到见解。《南史》对虞龢有明确的记载:“虞龢、司马宪、袁仲明、孙诜等,皆有学行……龢位中书郎、廷尉……”[7]1770另外,《宋书》中也有关于虞龢的只言片语:“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相承不复革。宋明帝自改舞曲哥词,并诏近臣虞龢并作。”[8]552从这些有限的史料记载中可知,虞龢不仅“有学行”,职务高(“中书郎”“廷尉”),还是皇帝的“近臣”。正是由于自身的才能和皇帝的赏识,才有能力和机会著有《论书表》,此文涵盖书法理论、书法评论、收藏、鉴定、作伪、装裱等方面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虞龢在《论书表》中将装裱内容编撰至书法评论文章中的做法,对《论装背褾轴》在《历代名画记》中的必要性产生了直接影响,是中国书画装裱史中的关键人物。
在书画装裱史上留名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既懂装裱又长于书画鉴赏的名家。“梁武帝命宋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又加装护”[2]46,这些历史人物“均是南朝梁时内府的书画鉴定家”[9]160。梁以后至唐这段时间的御用装裱能手在《历代名画记》之《叙自古跋尾押署》篇中,可以看到明确的时间、人物、事件:“隋江总姚察、朱异何妥大业年月日,奉敕装。”[2]39值得一提的是,《论装背褾轴》以编年体史学体例撰写,其他篇章相关内容的撰述,则以纪事本末体的史学体例对装裱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补充和诠释。
书画装裱技艺发展至唐朝,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国朝太宗皇帝,使典仪王行真等装褫,起居郎褚遂良、较书郎王知敬等监领。”[2]46关于唐代装裱名匠,在清代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厉鹗序》中有明确的记载:“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辈,要皆良工好手。”[10]21从“良工好手”可以看出,唐代的装裱技艺绝不再是“装背不佳”,而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甚至可以说是叹为观止的水平——“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因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模写,仍旧装背,一毫不差。”[2] 6毕竟,将临摹的作品装裱成与原作一模一样,要么是使用了原画上的装裱材料,要么是做到与原来的装裱样式完全相同。无论是哪种装裱方式,都显示出了极其高超的装裱水平。
唐太宗时期装裱及监领人员的具体作为,在《历代名画记》的《叙自古跋尾押署》中有更详细的记载,如文中言及:“贞观中褚河南等监掌装背,并由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官爵姓名。贞观十一年月日。兵曹史樊行整装,合若干纸,宣义郎行参军李德颖,数功曹参军金川县开国男平俨,典司马行相州都督府司马苏勖监,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扶风县开国男韦挺监。”[2] 41当然,这并不是装裱行为的全部过程,还有将仕郎直弘文馆臣王行直装,起居郎臣褚遂良监,以及将仕郎直弘文馆臣张龙树装,随后陪戎副尉王思忠装时,亦有张龙树装,直至王府大农李仙舟装背,内使尹奉祥监,才是形成最后的集贤书院书画。从这些几乎涉及到每一年的装裱、监领情况的记载中,我们能看到具体的时间、人物、官职等,如兵曹史、将仕郎、文林郎、陪戎副尉、王府大农等官职。这种记录时间与事件相结合的编史方式,是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书写方式交融于一体的编撰方式。
从《论装背褾轴》中历朝历代装裱名家的官职、出身、主要成就等看出,朝廷对书画装裱技艺非常重视,皇帝下命令装裱保护修理书画,并以重视装裱师、给予装裱师官职的方式予以体现,而这些出色的装裱师几乎都是文化和艺术水平均很高的人。“中国古代艺术系统,其画(书)史、理论、作品和作者基本上是由文人自己撰写的,因此,中国的美术史基本属于文人的美术史。”[11]“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一部文人绘画的史学。”[12]30同样,从上述绝大多数装裱师的身份分析来看,《论装背褾轴》记录的也是一部文人的装裱史。书画装裱技艺从萌芽时的稚拙,经历了千百年来一代代书画装裱师的研究、创新、发展,才到了今天这样完善的地步,他们为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论装背褾轴》的装裱史是按照朝代编史为体、装裱为例、装裱师为中心的编年体史学体例。
三、《论装背褾轴》与《历代名画记》其他篇章的逻辑关系
《历代名画记》全书共十卷,卷一至卷三,记述了绘画、鉴藏、装裱方面的内容,卷四开始至卷十,均为历代绘画名人的介绍和评论。可以说,卷一与卷二的前三篇,卷三的后四篇,与卷四至卷十,基本上都是对绘画史、绘画理论、绘画名人的论述,极少涉及绘画以外的内容,这些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缜密,环环相扣,前人多有论断,此不赘述。
与《论装背褾轴》关系最为密切的篇章是卷二的最后两篇和卷三的前两篇。卷二中最后两篇分别为《论名价品第》和《论鉴识收藏购求玩阅》。这两篇主要讲的是收藏、购买绘画作品以懂画、惜画为基础。《论名价品第》展示了装裱中的具体款式,是对《论装背褾轴》中装裱史的细节补充:“若诠量次第,有数百等,今且举俗之所知而言。凡人间藏蓄,必当有顾、陆、张、吴著名卷轴,方可言有图画……自隋已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障,故以屏风为准也。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2]32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卷轴、屏风这两种装裱样式在当时是绘画作品普遍的装裱形式。
卷二最后一篇《论鉴识收藏购求玩阅》阐释了装裱的重要作用,对《论装背褾轴》的装裱史进行铺垫。此篇开篇论述了有关鉴藏、购求和阅玩的关系问题——“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2]33。这是说,装裱知识是鉴藏阅玩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不具备就会严重影响绘画作品的安全和欣赏。
既然不懂得装裱,就会伤画、毁画、弃画,以致真迹损毁殆尽,那么为了使绘画作品流存于世,就必须掌握装裱知识,并在保存、舒卷、观看、收藏等细节处处小心,具体说来,即“非好事者,不可妄传书画.近火烛不可观书画,向风日,正餐饮唾涕,不洗手,并不可观书画”[2]35。这说的是,书画作品只能给同样精通鉴赏、装裱,并且爱惜书画的人来赏玩,观赏时不能靠近火源,大风环境也不适合观赏,以及在饮食唾涕不洗手等情况下,也是不能触碰书画作品的。若是观赏大型的卷轴作品,“宜造一架,观则悬之”[2]35,可见张彦远对于书画作品舒展赏阅时的细节问题极其关注。大型卷轴画作极易在展开观赏时受到折损的危害,因此悬挂在架子上,垂直观赏,比较安全。当然,不能为了减少危害而不舒展画作,反而应“时时舒展,即免蠹湿”[2]35,此意为保存书画时,应该经常打开画作,通风透气,避免虫蛀和潮湿的危害。
卷二的最后一篇处处都在阐述装裱技艺和装裱知识对于书画作品保藏、赏玩的重要作用,深入发掘鉴藏阅玩者具备装裱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直接开启《论装背褾轴》,二者之间的逻辑清晰,不能打乱顺序。
《论装背褾轴》作为卷三的第三篇文章,不仅与卷二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还与卷三前两篇文章之间环环相扣。卷三第一篇《叙自古跋尾押署》记录了前代御府所收藏的图画上的跋尾、押署,第二篇《叙自古公私印记》记录了历代图画上的印章情况。这两篇记录了宫廷的主要装裱师及书画作品的跋尾署名印记情况。从“唐太宗自书‘贞观’二小字印,分别在书画本身及裱边的连接处骑缝钤于内廷所藏书画卷轴的首尾部分”[9]142的论述上可以看到,这些赏玩鉴定后,书写鉴赏人员姓名、官职、评论或钤盖的印章,一般均书写钤印于书画作品以外的地方,如手卷的拖尾、装裱材料绫边等处。正是由于装裱技艺,使得跋尾押署和印记有了书写钤印的空间,由此可见装裱技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论装背褾轴》记载了之前四篇中的具体装裱师、时代、贡献等内容,勾勒出编年体的装裱史发展状况。《论装背褾轴》是《历代名画记》史学体例完整、结构完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缺失,亦不能打乱其在整部《历代名画记》中的位置和顺序。
四、结语
书画装裱的起源作为装裱史的关键性难题,在学界中,还处在一个众说纷纭、尚未统一认识的研究阶段。《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褾轴》虽未能完全解决装裱的起源问题,但是已将装裱史追溯至晋代,后来的装裱史写作几乎都遵循这一论断。该篇是最早的装裱史论著,改变了前人对装裱史的零星记载,开创了以装裱名家为中心的编年体史学体例,无论是在内容布局上,还是在结构体例上,都把中国古代装裱史提升至独立的地位。这说明在公元 850年左右,我国艺术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宽广,已经涵盖了绘画的发生、功能、发展脉络、画家、画论、画品、画材、画鉴、印章、题跋、赞助人、画之装裱等方面,这一全面性为早期西方艺术史所不具备,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一。《论装背褾轴》的辉煌贡献对之后的艺术史、装裱史的编撰体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独立的学术与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论装背褾轴》具有必要性、重要性和独立性,即如余绍宋所言,“论装背褾轴。皆分叙缋画所当知之事,亦为画史所必宜详录者”[4]7。绘画相关内容必须涉及书画装裱部分是中国早期艺术史的撰写特征,对中国当今艺术史独特的体例、完备的结构具有重大的范例意义。
其次,《论装背褾轴》装裱史内容中的史学批评既有客观性,又具备一定的主观性。张彦远在自己精通装裱的基础上,直接用“装背不佳”“始能装背”等词汇来对前贤的装裱水平进行评价,摒弃了含糊的语句,体现了张彦远以实践为基础,直书事实的史官精神。
再次,《论装背褾轴》治学态度严谨,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装裱人员,还录述了具体的监领人员,增强了史实感,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以及可供学习的对象。
最后,《论装背褾轴》的装裱史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为线索,这些人物大都是文化艺术修养甚高又精通装裱的人,对提升当今装裱师的综合素质具有借鉴价值。书画装裱技艺的历史发展与装裱人员的综合素质息息相关,《论装背褾轴》中对范晔、徐爰、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宋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王行真、褚遂良、王知敬等装裱师,以及参与装裱和监领名家的记录,说明影响书画装裱技艺发展的关键人物几乎全部都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质。此后各朝代具有较大影响的装裱师及著述装裱相关内容的作者,亦延续这一传统,如宋代的米芾不仅在书画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还在《书史》《画史》中标榜自己在装裱方面的独到见解和实际操作能力;明代的周嘉胄在《装潢志》中系统阐述了装裱相关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具重大影响;清代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中对装裱内容的详实记载展示了精通装裱的文人具备传承与探索的可能。《论装背褾轴》中对装裱师、监领人员的历史记载,纠正了现今对“书画装裱师及相关人员只是普通工匠”的误读,从源头上阐明装裱人员应该是文化、艺术素质均很高的综合人才。
概而言之,《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褾轴》详细地阐述了装裱技艺之于绘画流传的重要性,其对装裱史发展的记述更是超越了前代的文献记载,推动了装裱传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全书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不仅清晰明确地指出时间,还记录了对装裱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并且在其他篇章中对这些人物的装裱事件进行描述,再加上张彦远对于装裱技艺进行的史学评价,都为研究早期装裱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