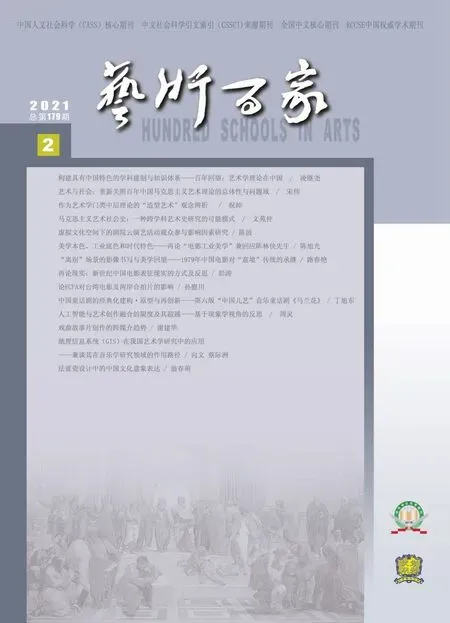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日传播与回流*
——以古代书画艺术的中日交流为例
叶 磊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是一种以书法、绘画艺术为代表的自成体系的静态视觉艺术,她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积淀的宝贵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即远播四方,通过对外传播不断扩大其海外影响力和辐射力,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海外传播历史中,传播交流活动以对同为汉字文化圈内的东邻日本的影响最甚。而在各种东传日本的艺术型式中,又以书法和绘画艺术的影响最为深远。正如日本学者北川桃雄所说:“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艺术的东传在顷刻间席卷了日本列岛,改变了日本原始艺术的落后面貌……在中国艺术的熏陶下,日本艺术由单调走向了丰富,由封闭走向了开放,进而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1]当然,在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长河里,文化总是相互传播和影响。在当我们注目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日传播及其深远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日本艺术在发展成熟后的反向传播与回流现象。也正是由于历史上中日两国传统艺术的互为传播、交汇与兼容,进而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绚丽夺目的东亚艺术。
关于中日两国的传统造型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的传播交流,就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中日两国书法、绘画艺术的单独研究较为充分,但是从传播学角度所开展的中日书画艺术交流研究却是相对鲜见。鉴于此,笔者以古代书画艺术的中日交流为例就此命题展开论述,旨在探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对日传播历程、日本传统书画艺术的西渐传播史实以及中日古代书画艺术传播交流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价值等,以期丰富中日艺术交流史与中日关系史的相关研究,同时也希望借此研究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传承。
一、古代书法艺术的对日传播与回流
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传播交流可谓是历史悠久、成就斐然。在双向互动的交流历程中,中国书法的对日传播是主流。在中国书法的影响下,日本书法逐渐形成了汉字书法与假名书法并存的双线型发展模式,其书风经历了从仿唐汉字到和风假名再到汉风复古的多次嬗变,而书体经历了从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的转化并用。此外,作为书法派生物的日本篆刻艺术也在中国造型艺术的传播大潮中应运而生。随着日本国风文化和民族自觉意识的日益生发,日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以作品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对华艺术传播,两国书法艺术自此不断交融,而中国书法也因此在传播与回流的过程中获得启发和受益。
(一)中国书法的对日传播
尽管目前学界还无法考证确定中国书法对日传播的具体开端时间,但普遍认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应是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萌芽期。学者任平指出,与中国魏晋之前以文字观代替书法观的情况相同,即自从汉字传入日本,日本就有了书法。[2]230根据这一观点,公元285年王仁携汉文经典赴日即构成了书法对日传播史的第一幕。毕竟汉字是书法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汉文经典的传日促使日本形成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同时也开启了日本最为原始的书法实践。公元6世纪,随着佛教的东传及其在日本本土的快速传播,用汉字记载镌刻的佛经、碑铭开始在日本大量流布。汉文佛典的传入,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以传播佛教义理为宗旨的写经热潮;而金石碑铭的流布则反映出日本对中国汉字书法的娴熟运用。如刻于公元607年的《法隆寺药师造像铭》其铭文皆为楷书,笔致圆润且线条优美,尽显中国六朝书风韵味。该造像铭的创作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书法对日传播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彰显出日本书法的萌发成长与进取态势。
隋唐及五代时期是中日交流的活跃期,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对日传播的全盛期。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七世纪的唐代中国雄踞在当时世界其他一切政体的顶峰,对日本、新罗、百济诸国影响深远,整个东亚的文化艺术发展几乎全盘唐化。”[3]107由于受到盛唐时期强大汉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日本宗唐学汉,争相临习晋唐名家蔚然成风,其中以王羲之、欧阳询和颜真卿的书风传播最广。这一时期频繁来华的遣唐使、画师和僧侣,在归国时总能携回在唐所得的大量晋唐书家名作。据史书记载,日僧空海在归国时曾满载216部461卷各类书籍,其中书法作品有《大王(王羲之)诸舍帖》一帧、王羲之《兰亭序碑》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张渲真迹》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李邕真迹屏风表》以及各色飞白、行草书等。[4]11357另据《请来目录越州录》记载,日僧最澄入唐后也带回了为数可观的中国书迹,如《王羲之十八帖》《王献之书法》《欧阳询书法》《褚遂良集一枚》《开元神武皇帝书法》《梁武帝评书》《真草文一卷》《古文千文一卷》《大唐圣教序》《台州龙兴寺碑》等。[5]98从书法传播的意义上看,这些晋唐书家的手迹无疑给日本书法带来了极大启示,日本仿唐书法悄然形成,自此书法在整个日本文化艺术中开始有了相对独立而重要的地位。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日书法交流的平稳发展期。尽管这一时期对日传播的总体规模不及前代,但是给日本书坛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仍不可小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与隋唐五代相似,仍然是由宗教所承载。中国宋元禅僧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禅宗,同时也将中国新汉风书法(禅僧墨迹书法)带到了日本。其中最为著名人物的有兰溪道隆、大休正念、一山一宁等。在东传的墨迹书作中,王羲之式的温文尔雅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苏黄一派的新书风,展现出宋代苏东坡、黄庭坚、张即之等人的尚意风格。中国书法发展到明代,在形式与内涵上均有了不少新的突破,而将这种“新的突破”带入日本的依然还是中国的禅僧。而从中国书法对日传播的主题出发,最应提及的是黄檗僧人的渡海赴日。据《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中国黄檗宗僧人隐元于明亡清立之际携弟子五十众渡海赴日,在开宗立派的同时也将大量宋明汉学著作及文人书画传入日本。[6]43无论是隐元,还是之后赴日的木庵、即非、独立等人,本身均精于书法篆刻,成为了明清文人书法在日本的直接传授者。在黄檗僧人的引导下,江户时期日本书家的学习对象由宋代的苏东坡和黄庭坚转向了明代的文徵明和董其昌。因此可以说,以隐元为代表的黄檗僧人的东渡,直接传播了明清文化和文人书风,对江户时期复古书风的形成和兴盛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论及中日书法,除传统意义上的纸书墨迹书法外,印学篆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篆刻交流史作为书法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同样焕发着绚烂的光彩。作为书法的派生物,篆刻与书法几乎于同一时间传入日本,但若究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汉倭奴国王金印”的东传。[7]1受隋唐印制的影响,公元7世纪末时日本形成了自己的官印制度,从而真正标志着日本篆刻艺术的开端。而在日本印章制度的形成过程中,频繁持续的中日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最值得一提的当属8世纪中期鉴真和尚的东渡,他在将中国佛法传入日本的同时也带去了书法、篆刻和绘画艺术,从此篆刻在日本成为了一种独特而广泛的艺术形式。12世纪幕府武家政权的建立,揭开了中日篆刻传播交流史的新篇章。一方面,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中国禅僧的渡海赴日将宋元禅林的私印之风传入了日本;另一方面,日本学问僧的赴华交流相比前代更加活跃。日本僧人在其归国时携回了大量宋元名家的书画作品以及唐代以来一些文人所用的书画印章,故令中世的日本印界重新焕发出了熠熠光彩。及至近世,日本的印章篆刻技术开始趋于成熟,而这主要归功于中国禅僧独立和心越。独立的贡献在于将中国地道的篆刻技术传入日本,进而改变了日本印坛一贯以来只善用印不善治印的局面;而心越的贡献在于将其东渡时所携《韵府古篆汇选》翻刻流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本篆刻界缺乏工具书的现实问题。[8]在独立和心越的引领和推动下,日本近世印坛充满了勃勃生机,涌现出江户派、浪华派、长崎派、今体派等诸多篆刻流派,日本篆刻艺术呈现出勃兴之势。纵观日本历朝历代,中国篆刻艺术对日本篆刻艺术的影响可谓是无所不在。就如日本学者神野雄二所述:“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日本篆刻艺术的源动力来自于中国,每一次中国篆刻技艺的传来都推动着日本篆刻艺术的向前发展……篆刻艺术的东传,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传统艺术的进展,对于人们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9]日本学者的这一观点或许可以视作为是对中国篆刻艺术对日传播效果的最佳注解。
(二)日本书法的西渐交流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情况来看,日本书法的首次西渐是《宋书·倭国传》所载升明二年(478)雄略天皇上书刘宋王朝的《倭王武上宋顺帝表》。该表文是中日关系史上唯一完整留存于史籍的日本汉字国书。从其书风情况来看,应是受到中国六朝书法风格的影响。尽管当前还无法确定书写者是日本书人还是中国移民,但鉴于书表来自于日本的这一事实,故学界通常还是将此视作为中国最早接触到的日本书法。
迨及隋唐五代,随着中日两国之间人物往来的增多,史书对传入中土的日本书法的记载也相应增加。就官方往来情况来看,《新唐书·日本传》云:“建中元年,使者兴能献方物……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册府元龟》亦云:“倭国遣大使兴能,自明州路奉表献方物。其本国纸似蚕茧而紧滑,人莫其名”。关于“兴能善书”一事,据陶谷所撰《清异录》记载:“兴能来华,译者闻其善书札,乞得章草两幅”①。以上史料表明,唐建中元年(780)时,日本使节的书法作品以及日本的本土和纸已传入中国。就民间往来情况来看,既有日本书人的在华创作,也有书法作品的渡海西传。空海在唐期间曾撰有《大唐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碑》②,碑文共1500余字,碑石虽已佚失但碑文内容却收录于空海《性灵集》卷二之中。[10]155此外,这一时期日本写经书法的相关抄本作品也通过多批次的商贸往来和宗教交流传到了中国。据唐代公文《明州牒》记载,日本僧人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求法,携《法华三部经》《屈十大德疏》《本国大德诤论》等5部22卷佛经典籍往天台山供养③。以上典籍均为日本写经巅峰时期的手抄经卷,其中《法华三部经》是用金粉缮抄的楷书写经精品。有唐一代,除最澄携带典籍来华外,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淡海三船的《大乘起信论注》、石上宅嗣的《三藏赞颂》等也相继通过宗教界人士传入中国④。可以说,这些抄本的西渐尽管在当时仅是以宗教交流为目的,但是却间接地将奈良至平安初期的书法艺术带到了中国。五代十国虽恰逢中国动荡纷争时期,但中日宗教往来却未曾中断,其中最具意义的事件是日僧宽建的赴华传书。据《扶桑略记》载,日本延长四年(926)兴福寺沙门宽建入华求法,天皇特令其将小野道风“行、草书各一卷”送往中国流传⑤。如果说此前的兴能留书唐人与最澄携抄本入唐仅是一次无意之举的话,那么宽建携道风书迹来华则是一次真正以书法传播为目的的有意识的文化输出,流露出日本民族对日渐成熟的国风文化的自信以及试图以和风书法扬名中华的决心。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日书法传播交流进入到一个双向流通阶段。由于明清以降的日本或因时局动荡或因闭关锁国,故两国间的交流特别是书法作品的西渐主要是集中在宋元时期。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名留史册的入宋僧达130余人,入元僧超200人,而事迹失考的来华僧人更是数不胜数。[11]254、305、420由于两国禅林交往密迩,日本书法的西渐已成规模,从而使中国书界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日本的书艺。宋元时期最为重要的交流事件当属日本假名书法的西传中国。据陶宗仪所撰《书史会要》记载:“日僧曰克全字大用者,颇习华言,云彼中自有国字,字母仅四十有七。全及以彼中字体写中国诗文,虽不可读,而笔势纵横,龙蛇飞动,俨有颠素之遗则”⑥。其中“国字”即日语中的平假名,“笔势纵横,龙蛇飞动”即为假名书作的和风特色,这是关于日本假名书法首次完整传入中国的珍贵记录,在中日书法传播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古代绘画艺术的对日传播与回流
与中国书法的传播交流相似,中国绘画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日传播。就其传播效果来看,日本绘画在中国绘画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实现了从佛绘、唐绘到水墨画、文人画的多次嬗变发展。五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绘画的对日传播,日本绘画也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反向传播至中国,从而使中国画界得以领略到日本画人的绘画技艺。
(一)中国绘画的对日传播
中国绘画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日传播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亦即日本的飞鸟至平安时代。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的东传,大批中国工匠和画师开始相继进入日本,为其寺院庙宇雕塑佛像、绘制壁画,从而极大刺激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尽管该时期木石造像和壁刻漆画已十分普遍,但从现代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以上作品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绘画作品。隋唐以降,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佛绘艺术趋于鼎盛,而在其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的僧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以鉴真为代表的东渡僧人为佛绘发展作出了创作示范,唐招提寺金堂的大量唐风塑像和绘画便是鉴真一行人等东渡日本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以空海、最澄为代表的日本僧人在入唐求法的同时,也将唐朝佛教密宗的佛画图样带入了日本(如《真言五祖像》《胎藏界曼陀罗》《金刚界曼陀罗》等[12]28-29)。于是,佛教美术由显教转为密教,显示出了与传统佛画所不同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神秘主义气息。
当然,中国绘画的对日影响不仅反映在宗教领域,世俗美术“唐绘”也是中国绘画对日传播的具体成果。所谓“唐绘”既指从唐朝传入日本的绘画作品,也指日本画师完全袭仿中国六朝及隋唐绘画的作品。唐代以来,通过两国大规模的互动交流,中国大量绘画作品输入日本,日本平安诗集和各类文献中对于唐绘的记载可谓是比比皆是。《释奠图像》即是唐绘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幅。据传是吉备真备入唐时从弘文馆获得,归国后交由本国画师图摹使用。总之,在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输入、仿制及观赏唐绘作品已成为当时日本贵族社会的一种审美情趣和流行风尚。
中国绘画的第二次大规模对日传播是宋元明时期,亦即日本的镰仓至室町时代。进入宋代以后,随着禅宗的东传,以禅宗往来为主体的两国文化艺术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绘画再一次流传到了日本,其中以水墨画的传入最具历史意义。从时间上看,水墨画的东传与禅宗东传的时间基本一致⑦,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东渡求法的日本僧人就是水墨画的实际传播者。
根据笔者研究,从镰仓到室町时代传入日本的绘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宋元明禅僧的水墨画作品,如牧溪的《远浦归帆图》、玉涧的《洞庭秋月图》、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等;第二类是宫廷画师的水墨画作品,如梁楷的《出山释迦图》《雪景山水图》、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雪中归牧图》等;第三类是以宁波为中心的江南佛画,如金大受的《十六罗汉图》、陆信忠的《涅槃图》等。日本室町艺人能阿弥所著《御物御画目录》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流传到日本的各类绘画佳作,其中以牧溪、梁楷、马远等人作品的出现次数最多。这是因为牧溪等人的水墨画十分符合日本禅僧的审美习惯。以画悟道、观画证性是禅宗绘画的主要功能之一,而水墨画所采用的象征及暗示手法与禅宗强调心灵感悟的求证方式是颇为契合的。[13]因此自水墨画东传后,便在日本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绘画的第三次大规模对日传播是在清代,亦即日本的江户时代。此时的日本绘画虽已有了较大发展,但两者间的交流仍以日本向中国传承为特征。由于同时期的日本实行了严厉的锁国政策,因此清代以来对日绘画传播多借助于书籍画谱的间接途径。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输往日本的画谱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主要有《芥子园画传》《图绘宗彝》《八种画谱》《十竹斋画谱》《晚笑唐画谱》《墨兰谱》《刘氏画谱》《天下有山堂画谱》《书画同珍》《无双谱》等二十余种[14],其中以介绍中国文人画画论的《芥子园画传》传播最快、最广。据日商田中清兵卫《唐本目录》等文献记载,该画传曾多次传入日本,初集首传时间大致为元禄元年(1688),传入次数不少于41次,传入数量不少于238套;二、三集首传时间大致为元文五年(1740),传入次数不少于24次,传入数量不少于117套;四集首传时间大致为天保十年(1839),传入次数不少于6次,传入数量不少于21套。[12]192-193以上画谱一经传日,文人画便受到日本画家的极大青睐,并迅速取代水墨画成为了近世画坛的新风尚。当然,中国文人画能够在日本快速传播,还得益于沈南苹、伊孚九、方西园、李用云等中国画家的交流示范。他们曾多次赴日传道授业,成为中日绘画传播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日本绘画的西渐交流
日本绘画拥有近两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而在其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受到中国绘画的直接影响。通过两国绘画艺术的互为传播,不仅有大量中国绘画作品流传日本,同时也不乏日本绘画西渐中国的具体事例。
如前所述,唐代是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共计遣使赴华19次之多,各类遣唐人员5000余人。[15]64借助于频繁的遣唐交流,日本在积极摄取盛唐文化养分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将本国绘画传入了中国。据显真《圣德太子传私记》记载,《唐本御影》(圣德太子绘像)曾绘制两幅,一幅留日,一幅由唐人携归中土。倘若此事考证属实,则该绘像将是日本绘画西渐的肇始。此外,米元章《画史》中所记载的《日本著色山水》以及江少虞《皇朝类苑》中所记载的《画牛》也是日本绘画西渐的又一例证。[2]82由于上述作品均经过南唐李煜之鉴定,因此可以判断日本绘画最迟在唐末五代之时已传入中国。当然,日本绘画西渐的方式除作品的直接输出外,还包括日本画师的来华创作献艺。据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记载,日本画师粟田家继在华期间(唐文宗开成年间)曾绘制十余幅作品,如《南岳思大和尚示先生骨影》《天台大师感得圣僧影》《阿兰若比丘见空中普贤影》等。[16]1084这些作品不仅向唐人展示了日本画人的绘画技艺,而且也促进了日本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宋代是日本大和绘艺术的繁荣发展期,大和绘亦称倭绘或倭画,是一种具有典型日本民族风情特色的绘画艺术。故这一时期输往中国的日本绘画也以大和绘作品居多,如《宋史·日本传》所载“倭画屏风一双”即为入宋僧奝然遣弟子入华进献朝廷的方物。在这一时期的两国绘画传播交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扇绘的西渐。据《嘉泰普灯录》记载,日本禅僧觉阿上人曾于淳熙二年(1175)遣僧向杭州灵隐寺馈赠“彩扇二十事”⑧。“彩扇”即绘有图案的扇子,这也是日本绘扇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至于扇面上的绘画内容,根据《皇朝类苑》卷六十《风俗杂志·日本扇》条中的说明,我们推测传入中国的日本扇绘基本上是以山水风景为主题的大和绘作品。这种殊乡异俗的画题和风格独特的技法令中国人士大开眼界,惊叹赞美者多有之。江少虞《皇朝类苑》认为“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吴莱《东夷倭人小摺叠画扇子歌》称其“素绘巧艳”;贡性之《倭扇诗》则以“巧艺夺天工”赞之。
元代日本入华交流者同样以禅僧居多,而禅僧当中又以画僧居多。如雪村友梅、墨庵灵渊、此山妙在、铁舟德济等均为两国间的绘画交流作出过贡献。至治年间(1326-1328)入元的墨庵灵渊曾遍访中国江南古刹,其在华所创作品《二十二祖图》先后得到了月江正印、了庵清欲、楚石梵琦等元僧的题赞,享有“牧溪再生”之誉。此山妙在亦是擅长画技的禅僧,《若木诗集》记载其入元后曾画《达摩祖师像》赠元僧圭斋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姓名失考的来华日本画僧,在华期间访求名师画友,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如《云山千里图》等⑨。
明清时期,由于长期海禁和闭关锁国,日本绘画西渐的规模已大不如前。日本绘画作品的输出情况虽鲜见史料记载,但日本画师(画僧)的赴华交流却是有据可考。在来华的画师(画僧)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雪舟等杨。雪舟于成化三年(1467)入明,师从院体画家李在并习得设色要领和泼墨技法。因其画技高超,受到时人的极大关注。据《鲁庵诗集》序称:“日僧雪舟,天性善画……取笔立成,生意逼真。绝无计利,凡求索者,偏应无拒”。可见当时向雪舟索求作品的明人不在少数。另据徐琏《送雪舟归国诗》中“剩有丹青落世间”一句,可知雪舟的画作在中国多有流传。事实也的确如此,雪舟等杨在华期间创作的画作颇多,主要有《芙蓉峰图》《育王山图》《镇海口图》《四季山水图》《宁波府图》《各国人物图》等。[17]这些作品的流传,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时也是中日文化艺术传播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中日古代书画艺术传播交流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海外传播历史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关于书法、绘画艺术输出海外的明确记载。数千年来,东亚、西域乃至欧洲诸国在不同程度上地接受着来自中国汉文化的强力辐射,但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情、民情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在与海外诸国进行艺术传播交流时的特征表现也不尽相同。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历史文化既有一定渊源也有很大差异。就两国之间的书画艺术传播交流而言,中国对日传播的方式与途径,日本接受中国传播的态度与做法,中日两国传播交流的效果与影响等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一)传播交流的态度:传承与改造并重
在近两千年的中日书画传播交流史中,中国作为日本的文化母国,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和文化传播者的姿态,毫无保留地将本国文化艺术精华输往日本。对于中国来说,传播与交流的重点是前者,对外传播实则为一种展示与示范。而作为文化后进国的日本,则至始至终是以虔诚学习者的姿态积极摄取着来自中国的文化滋养。对于日本来说,传播与交流的重点是后者,对华交流实际上是一种传承和吸收。需要说明的是,在唐代晚期以前的中日传播交流中,日本是通过完全袭仿中国的书画艺术来发展自己的书画艺术,其书画风格几乎与同时期的中国保持着亦步亦趋。正如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当时日本的造型艺术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流派,故而其书画艺术作品充满着浓厚的异国情调。”[18]84而在唐代晚期以后的中日传播交流中,日本则是在传承和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适时地对外来艺术进行了民族创意的改造。无论是平安时代从唐绘、汉字书法中衍生出大和绘、假名书法,还是镰仓室町时代对水墨画图式的革新以及强烈装饰印风的形成⑩,抑或是江户时代从明清版画中创造出浮世绘版画以及对浮华文人书风的反叛,均是日本对从中国“舶来”艺术的本土化改造。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对日传播态度始终是无条件、无保留的文化输出;而古代日本的对华交流态度,则是经历了由“全盘吸收”到“内化改造”的转变。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才使得日本书画艺术具有了本民族的风格和特色。
(二)传播交流的方式:东传与西渐并行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日文化传播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双向文化输出的问题,既包括中国文化的对日输出(即东传),也包括日本文化的对华输出(即西渐)。就中日书画传播交流的具体实践而言,中国书画艺术的东传是主流,主要通过官方(日本遣使团)和民间(中日僧侣)两个层面上的交流活动来实现。可以说,两国之间的书画交流基本上是以日本向中国的单方面传承为特征。从传播交流的内容上看,既有作品的直接输出,也有人物的互动往来,其中不乏中日书画艺人在彼国他乡从事书画创造的史实。日本书画艺术的西渐(反向传播)虽是支流,但是自唐代以来几乎历朝历代均未曾中断,只是这种传播活动大多依靠个体力量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平安朝以前的西渐传播多是以纯粹宗教交流为目的的无意识的文化输出;而平安朝以后的西渐传播则是真正以书画艺术交流为目的的有意识的文化输出,反映出日本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主意识的全面觉醒。总之,中日古代书画艺术的传播交流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东传与西渐几乎贯穿了两国传播交流活动的始终,而中日两国通过互动往来也均有不同程度上的受益。
(三)传播交流的载体:艺术与宗教并进
纵观整个中日书画传播交流的历史,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书画艺术与宗教(佛教)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两千年来的中日书画传播交流基本上都是由宗教所承载的。平安时代中日书画传播交流的第一个高潮便是由僧侣所掀起,中国方面以鉴真为代表,日本方面则以空海、最澄为代表,他们共同推动了日本佛绘艺术与仿唐书法的发展。镰仓至室町时代,僧侣仍是中日书画传播交流的主要媒介。中国方面有兰溪道隆和大休正念,日本方面有周文天章和雪舟等杨。正是由于双方的合力,日本的水墨汉画、墨迹书法以及私印风气得到了极大发展。江户时代,僧侣在两国的书画传播交流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隐元、独立、心越等中国禅僧的渡海赴日,日本或许就不可能出现文人书法和篆刻技术的隆兴局面。我们认为,书画艺术与宗教之间之所以关系密切,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日本佛教具有绝对权威,日本僧侣集团不仅能够参与国政,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阶层,身兼僧侣和画家(书家)的双重身份,具备鉴赏和传播艺术的能力;二是由于日本的最高统治阶层(天皇贵族、将军武家)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艺术极度尊崇,或许是出于迎合统治阶级趣味以及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日本的僧侣们主动承担起了文化艺术传播的重任。
(四)传播交流的成果:成就与遗憾并存
可以说,中日两国近两千年来的书画传播交流史可谓是波澜壮阔、灿烂辉煌。先论成就,其一是促进了彼此国家的艺术发展。就日本来看,中国书画艺术的东传无疑催生了日本的书画艺术并极大推动了其成长发展。日本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大受益者,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刺激和熏陶下,日本书画艺术实现了从写经书法到文人书法、从佛绘到浮世绘的多次嬗变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书画艺术在某些历史时期内还实现了一定的超前发展。例如,镰仓时代的宗峰妙超在创作挂轴书作之时,中国书坛还尚未出现此类形式。故学界猜测,后世中国明清挂轴的兴起很有可能是受到宗峰书法的启发和影响;其二是通过双向交流使得一些历史艺术珍品获得了最大限度地保存。起源于中国的一些书画艺术作品,或因时逢动乱而湮灭不传,相反在流播地日本却得到了保存和发扬。例如,牧溪的绘画作品在中国未能流传下来,但在日本却有大量收藏。再论遗憾,尽管日本的书画艺术是在传承中国书画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艺术演进毕竟无法做到像其文化母国那般的系统和完整,这一点在书法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帖学与碑学的发展自古极不平衡,由于缺少篆隶二书的熏染,以致书作中少了一些空间造型上的认识;因为缺乏魏碑的感召,于是书作中少了一些阳刚之气和雄强风格。日本在历史上之所以重“帖”而不重“碑”,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日中两国早期大规模交流所处的晋唐时代恰好是中国楷行书的成熟与鼎盛时期,故秦篆汉隶在其光辉掩映之下要显得黯然逊色。此外对于外民族而言,篆文书体确实难以辨识,以致篆隶二书、树碑立石的传统长期以来未能被日本所接受。总之不管其原因如何,篆隶碑额缺失的事实不能不说是日本古代书法史上的一大遗憾。
四、结语:对中日传统艺术传播交流的思考
综上所述,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日传播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历史中是主流,她催生和推动了日本书法、篆刻与绘画艺术的成长发展。我们也同时注意到,随着日本国风文化的不断成熟,日本书画作品也曾回流传播至中国,并给中国书画艺术带来一定的启发和影响,中日两国传统艺术也因此在不断交融中走向臻于至善的境界。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东传、日本的传承吸收、民族创意的改造、书画的西渐传播构成了中日古代书画艺术交流史的发展主线。这种互为传播的循环关系可以解释为: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潮流中,中国书画艺术造就了日本书画艺术,而日本书画艺术在传承和受容中国书画艺术精华并历经本土化发展后又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就其历史意义来看,如果历史上没有两国书画艺术的传播交流,日本或许就不会形成现今书画艺术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繁荣局面;如果历史上没有两国书画艺术的传播交流,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或许未必能够尽善尽美,而中国古代的许多书画艺术珍品也或许就无法流传、保存至今。就其现代意义来看,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其独有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最能够生动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今社会,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进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粹,不仅能够更好地搭建与海外受众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且在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进程中能够发挥良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中日书画艺术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传统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是展示国家魅力和软实力、提升海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艺术没有边界,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传播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共同推动人类艺术的向前发展。正如学者王莲所说:“艺术的发展只有通过交流才能不断地继承、创新和吸收新鲜血液,否则就会停滞、衰败和枯萎”。[14]这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在中日书画艺术传播交流史中得到了成功的印证。
①参见《清异录·卷·文用》。
②对于是否存在由空海撰文亲书悼念其师惠果和尚的《大唐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碑》,至今学界尚无定论。由于该石碑迄今未被发现,也不见历代中国金石书志著录,故日本学者常盘大定疑其“文成而碑未立”;中国学者梁荣若认为“文字繁缛,不合金石文字体”。笔者赞同王勇教授观点,即以惠果生前名声之显赫,死后葬仪之隆重,有文无碑说似不合情理。只是密教经不空、惠果而渐趋式微,以致石碑湮没无闻似有可能。具体参见王勇、上原昭一《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艺术卷》,第265页。
③参见最澄《显戒论缘起》。
④参见明空《胜鬘经疏义私钞》和《金刚寺本龙论抄》所引《延历僧录》。
⑤参见《扶桑略记》第二十四卷“醍醐天皇下”条。
⑥参见《书史会要》第八卷“外域”部分。
⑦有学者认为水墨画早在唐代就已传日,其理由是空海等入唐日僧所携回的大量白描佛画即是最为原始的水墨画。笔者认为,密教白描画稿并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水墨画。水墨画在宋代兴盛之后,最先接触并将其传入日本的应是渡宋求法的禅宗僧人。镰仓初期入宋的僧侣俊芿在归国时所携回的《送海东上人东归图》(作者不详)和《十八罗汉图》(贯休作)即是当时传日的水墨画之一。
⑧参见《嘉泰普灯录》第二十卷《日本国觉阿上人》条。
⑨参见伊藤松贞《邻交征书》初篇卷之二。
⑩日本镰仓时代强烈装饰印风的本土化意义在于创造性地将双边线、亚字形、葫芦形以及鼎、爵、彝等器皿之形融入印章并构成款式。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装饰精巧的印风在中国出现于元明时期,而在日本则是出现于更早的镰仓时代亦即中国的宋末元初,因此这一现象可视为是日本对中国传入印章款式的一种民族创意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