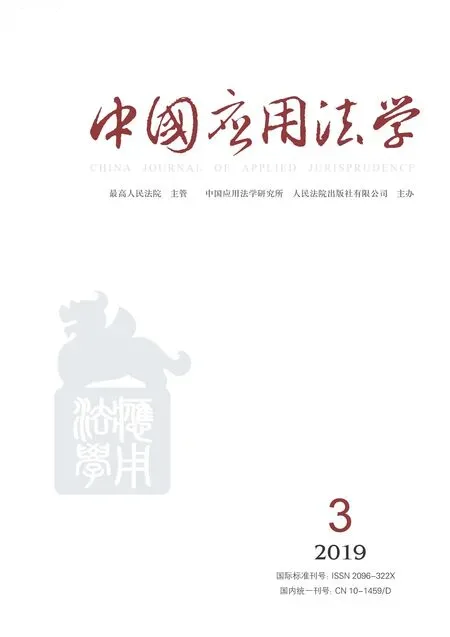论终身监禁的刑罚威慑效力
——基于美国“三振出局”制度之考察
吴雨豪*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最后一款规定,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人,“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也被认为是我国刑罚体系中设立“终身监禁”制度之起源。
应当说,在我国现有的刑罚体系中,终身监禁是仅次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刑罚制裁措施。在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谱系中,其无疑实现的是“从严”的刑事政策职能。而正如刑事政策制定者所阐述的一样,之所以需要在刑事审判中实现依法“从严”,原因之一就是“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1〕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换言之,通过终身监禁的严厉刑罚之特征,以刑罚的威慑实现犯罪控制机能,很可能是当今乃至未来刑事政策所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要素。然而,从现有的关于终身监禁的文献来看,学者对终身监禁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其正当性,而对这种刑罚是否具有独特的功利主义价值,却鲜有文献对其展开讨论。
事实上,早在古典时代,学者就对终身监禁可能具有独特的刑罚威慑效力展开关注。其中最让人广为熟知的,就是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对以终身刑替代死刑的推崇。在论证终身刑可能具有比死刑更大的威慑效力时,贝卡利亚论述道,一方面,“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想象”。而终身监禁能够使罪犯产生长久的痛苦,提醒别人“如果我犯了这样的罪恶,也将陷入这漫长的苦难之中”,进而具有持续的威慑效力。〔2〕[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另一方面,终身监禁“能够为国家提供无数次常存的借鉴”,通过时刻向潜在犯罪人显示法律的力量,从而具有明显的法律教育功能。〔3〕前引〔2〕,切萨雷·贝卡利亚书,第80页。
因此,本文正从贝卡利亚对终身监禁的论述出发,立足于刑罚威慑理论的一般原理,对下列问题展开思考:终身监禁与一般的自由刑相比,是否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否会直接影响其刑罚威慑效力的发挥路径?其中,在实证研究考察上,本文以世界上适用终身监禁最为广泛的国家——美国的“三振出局”为制度蓝本,以此回答两个问题:在终身监禁扩张适用之后,犯罪率是否出现了显著下降?以及当潜在的犯罪人面临可能存在终身监禁的刑罚制裁时,其是否会显著下降?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讨论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刑罚威慑的理论原理
所谓刑罚威慑,是指刑事制裁使潜在犯罪人产生恐惧,从而放弃或者减少犯罪行为。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引申出关于刑罚威慑的以下四个方面原理。
首先,刑罚威慑的核心要件是利用刑罚对潜在犯罪人制造恐惧。这种恐惧的来源一方面包括刑罚造成的法律后果所施加给罪犯的痛苦,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的对罪犯财产、生命乃至自由的剥夺;另一方面,潜在犯罪人害怕刑罚所产生的社会回应而放弃犯罪,也应当属于刑罚在发挥威慑效力方面的社会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罪犯因为受到刑罚而家庭关系中断,丢失工作,被社会谴责以及由此给罪犯造成的心理创伤和经济损失。而这种刑罚威慑的来源具有两重性,此将成为后文叙述终身监禁威慑特殊性的基础。
其次,在刑罚威慑发挥效力的过程中,在刑罚的客观属性与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决策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就是潜在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因为,如果客观的刑罚属性不被潜在犯罪人所知道,那么其自始不可能成为其犯罪决策的任何依据。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立法者和司法者加重刑罚的严厉程度或者确定程度的情形如果不被其意图施加影响的对象所知晓,其自始也不可能产生犯罪控制的效果。同时,常常因为各种原因,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并不能真实反映刑罚的客观属性,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甚至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正是许多刑事政策无法起到预期效果的根源所在。大多数潜在的犯罪人并不是法律人,其接触刑罚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因此,当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将刑罚变得更为严厉、确定和及时之时,这种刑事政策的变动很难传递到潜在犯罪人的主观感知之中,从而限制了刑罚威慑效力的发挥。
再次,从刑罚威慑的作用对象的类型来看,其可以分为一般威慑和特殊威慑。一般威慑是指刑罚对没有受过刑罚惩罚的一般社会公众产生的威慑效力,而特殊威慑是指刑罚对那些已经受过惩罚的人产生的威慑效力。因此,对于多数刑罚制裁措施而言,其可以产生二重的效果:一方面,刑罚使得一定的对象具有刑罚惩罚的经历,因此,在下次犯罪的实施时基于既有的经历而放弃实施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对罪犯动用刑罚,又会使社会公众中的潜在犯罪人产生畏惧感,进而放弃实施犯罪。
最后,从刑罚资源投入和威慑效果的关系来看,刑罚威慑又可以分为绝对威慑和边际威慑。其中绝对威慑是指给定一定的刑罚资源,刑罚能够实现的威慑效果。因此,绝对威慑是一个从静止、独立的视角看待刑罚威慑的效力。而边际威慑是指一定的刑罚资源的增加所能额外实现的威慑效果。因此,边际威慑是一个动态、比较的概念。对边际威慑的理解,必须放在一个整体的刑罚体系和时空范围之中才能完成。〔4〕Franklin E. Zimring, Gordon Hawkins, Deterrence; the Legal Threat in Crime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72.绝对威慑和边际威慑的区分在刑事政策选择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任何一个刑罚措施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其都以一定既有的刑罚体系作为背景。在刑事政策选择上,边际威慑相对于绝对威慑常常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例如,持死刑具有有效威慑效力的人的惯常论据就是,生命具有最高的价值,潜在犯罪人在死刑的危险面前有很大的可能会放弃实施犯罪。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死刑废除之后,并不意味着这部分犯罪人在生命不被剥夺之外无须承担任何的法律后果,事实上,这些犯罪人也同样面临极其严重的自由刑的惩罚。由此死刑是否具有有效的威慑力的关键并不是生命的剥夺是否能够遏制犯罪,而是生命刑相对于最严重的自由刑所增加的这一部分刑罚严厉程度是否足以影响潜在犯罪人的行为决策,因此类似死刑这样的重刑有效性论辩之中起到关键作用刑罚的边际威慑效力,而非绝对威慑效力。〔5〕吴雨豪:《死刑威慑力实证研究——基于死刑复核权收回前后犯罪率的分析》,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
三、终身监禁之刑罚威慑效力的特殊性
在论述了刑罚威慑的基本原理之后,我们的关注焦点就在,终身监禁在刑罚威慑形态上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刑罚的显著特征。从静态的外观形态上来看,终身监禁的执行方式与普通的自由刑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罪犯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承受被刑罚剥夺自由的痛苦。因此,上述刑罚威慑的部分原理可以当然地迁移到对终身监禁刑罚威慑效力之中。然而,与其他国家终身监禁的特点相类似,在我国,被判处终身监禁罪犯获得释放的情况只包括赦免和在死刑缓期2年执行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6〕黎宏:《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及适用》,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而这两种情况在实践中发生的概率都非常低。所以可以说,终身监禁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与一般监狱服刑人员普遍存在重归社会的预期不同,除非赦免和立功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况,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不存在重获自由的可能性。
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具有释放可能性”的特点,使得终身监禁的威慑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一般刑罚的特点。
(一)以刑罚的绝望性作为对潜在犯罪人威慑的来源
如上所述,刑罚威慑的来源既包括刑罚的法律后果,也包括刑罚的社会回应。齐姆林教授认为刑罚给罪犯造成的痛苦包括:(1)经济利益的损失。罪犯因为被监禁而工作中断,从而丧失的获取合法利益的机会。(2)社会权利的剥夺。一方面,刑罚可能通过剥夺政治权利、吊销执照等方式直接剥夺罪犯的社会权益;另一方面,监禁刑本身可能导致行为人失去原有的社会福利。(3)受到社会谴责。即社会上的其他成员因为行为人有犯罪和受到刑罚惩罚的记录而对其区别对待,行为人由此而受到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歧视,丧失工作机会等等。(4)因为刑罚造成的剥夺自由的痛苦。〔7〕前引〔4〕,Franklin E. Zimring 与 Gordon Hawkins书 , pp.175-194。在一般的自由刑中,只有刑罚对自由的剥夺无法在出狱之后弥补,其他几类刑罚的后果,例如合法工作的丧失、社会福利的减损、社会关系的中断虽然在罪犯出狱之后仍然将继续存在,但是尚可能通过出狱后各方面的努力得以修复。而由于终身监禁以服刑人员在监狱内自然结束生命作为刑罚执行的必然后果,因此服刑人员将丧失一切对正常生活愿景的期待,再加上终身监禁意味着服刑人员永远不可能回归自己之前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中,永久性地阻断其婚姻、亲子、朋友关系,所有这些刑罚造成的社会后果都是永久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终身监禁将永远地消除罪犯的社会存在意义。
而另一方面,与死刑不同的是,终身监禁仍然允许罪犯作为一个个体在监狱内延续他的生命。而这种社会存在的消除与生命的延续并存的状态,正如贝卡利亚所论述的一样,将使罪犯产生长久而持续的痛苦,这种痛苦相对于普通自由刑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其能够使罪犯产生一种绝望心理。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 v. Florida案中分析的那样,“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剥夺了服刑人员去高墙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剥夺了他们回归社会的可能,也剥夺了他们的希望”。〔8〕Graham v. Florida, 560 U.S. 48 (2010).
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进行的一项大规模针对终身监禁服刑人员的访谈中,许多服刑人员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绝望心理。“终身监禁就如同你被判了死刑一样,痛苦无处不在,你已经失去了生活的目标、生活的理由,那种痛苦和折磨将会一直伴随你到生命的终结,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以一种更加迅速的方式走向死亡。因为相对于你遭遇的痛苦和你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死亡反而是更好的方式。”〔9〕Letter to the ACLU from Libert Roland, Louisiana State Penitentiary, Angola, Louisiana, May 11,2013. Jennifer Turner, A Living Death: Life without Parole for Nonviolent Offenses,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2013,p.183.“终身监禁就意味着事实上生命的终结,因为你在周围人的脑海中已经不存在了。”〔10〕ACLU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Ricky Minor, Williamsburg 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Salters,South Carolina, Mar. 6, 2013. 前引〔9〕,Jennifer Turner书,p.183。“当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想到自己会在监狱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从此将见不到阳光,这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感觉。”〔11〕Letter to the ACLU from Antawn Tyrone Bolden, Jefferso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Monticello,Florida, Mar. 10, 2013. 前引〔9〕,Jennifer Turner,书,p.184.。正如美国监狱心理学家特里·库珀博士所言:“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希望和目标,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发展和心理都是最基本的需求,因为你至少可以期望,事情总有变好的那一天,但是,终身监禁使得这一切希望都归于幻灭,这种绝望将很可能导致不同程度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12〕ACLU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Dr. Terry Kupers, Oakland, California, Aug. 8, 2013, 前引〔9〕,Jennifer Turner书,p.183。美国量刑报告的数据显示,有18.4%的无期徒刑人员患有心理疾病。〔13〕前引〔9〕,Jennifer Turner书,p.186。这一比例在终身监禁的人员中应该更高。
因此,终身监禁所附带的绝望心理是其能够发挥特殊的威慑效力的重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威慑来源的存在,使得一些人认为,终身监禁可以具有比死刑更强的严厉性,从而期待其具有更大的刑罚威慑效力。
(二)以永久隔离代替特殊威慑实现对罪犯的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刑罚的一般预防,二为犯罪特殊预防。上文第一点探讨的是终身监禁对社会上潜在犯罪人的犯罪遏制效果,其属于刑罚一般预防的范畴。而特殊预防的对象是犯罪人本人,其是指在监狱内服刑的经历会改变罪犯,使之不再实施犯罪。其包括刑罚的剥夺、威慑与再社会化功能。其中,在刑罚威慑效力中我们专门探讨的就是特别预防中的威慑功能,即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痛苦,使其认识到,犯罪后的刑事责任的不可避免性和罪有应得,从而不敢再次犯罪,重受痛苦处遇。〔14〕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或者说以行为人自身的服刑经历提高行为人对刑罚确定性和严厉性的主观感知,进而影响其犯罪决策。与之相关的还有特殊预防的再社会化功能,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使犯罪人养成良好的规范意识,树立和强化对法的信仰和忠诚,从而不愿再次犯罪。
上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在一般的自由刑中均可能发挥作用。然而在终身监禁中,由于罪犯不可能再次回归社会,因此特别威慑和再社会化的特别功能均对阻止其犯罪失去了意义。而剩下的就是特别预防中的剥夺功能,即是指通过永久性地限制罪犯的自由,使之永远不能再次实施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终身监禁与死刑相类似,在刑罚威慑效力中,仅具有一般威慑效力,而不具有特殊威慑效力。其遏制罪犯再次犯罪仅能够通过施加外部条件,而非通过塑造其内心世界得以实现。
(三)以不具有回归社会可能性消弭监狱考核机制的正向激励效果
事实上,即使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产生犯罪的冲动。而与监狱外主要依靠刑罚威慑潜在犯罪人遏制其犯罪不同,在监狱内,规范罪犯的行为主要依靠的是监狱考核机制。
我国《监狱法》第56条规定:“监狱应当建立罪犯的日常考核制度,考核的结果作为对罪犯奖励和处罚的依据。”此外,司法部1990年8月31日施行的《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奠定了我国罪犯考核制度的基础。应当说,量化的罪犯考核制度对于正确执行刑罚,促进罪犯改造具有重要意义。〔15〕赵国玲主编:《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套量化的罪犯考核制度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实际上是和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的。司法部《关于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2001年10月12日)中更是明确指出,计分考核的结果将作为减刑、假释的依据。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自由作为激励的方式鼓励罪犯进行改造,方便监狱管理;另一方面也为了实现刑罚的动态化。每个犯人在服刑期间的悔罪表现并不相同,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再犯罪可能性程度消长变化情况不一致。行刑机关就是要根据这种不一致,及时有针对性地分别进行有效的改造教育。对于其中确有悔改、立功表现,再犯罪可能性明显降低的服刑人员,依法予以减刑、假释。〔16〕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但是对于终身监禁罪犯而言,其在开始执行刑罚之前就已经被完全剥夺了减刑和假释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这些罪犯是否遵守监规、服从管理将不会对他实际服刑期限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原来我国监狱中实施的量化考核和激励机制对于这些罪犯将会失去效力。在美国,相关学者曾经做过实证研究,那些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服刑初期,将会成为监狱内最难管教的“超级罪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不遵守规定将不会产生任何损失。〔17〕Blair , D . (1994 ) ,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Why Life without Parole should be a Sentencing Option in Texas ,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22 : p.213.因此终身监禁将大大增加监狱的管理难度。同时,这也将使刑罚丧失灵活性与动态性,假释制度原本所具有的鼓励服刑人员改恶向善、救济量刑失衡、为服刑人员重返社会架起桥梁、贯彻刑罚经济原则、增进监狱责任感以及维持监狱秩序等功能也将不复存在。〔18〕吴雨豪:《论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的终身监禁》,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监狱内实施犯罪的决策模型显著不同于一般的被判处自由刑的罪犯。一方面,只要其没有实施足以将他的刑罚升级为死刑的犯罪,由于他的刑期没有再次延长的可能,因此刑罚的威慑效力在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不可能重新回归社会,监狱考核机制也对规范他的行为没有正向激励作用。这些因素的综合很可能提高终身监禁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犯罪可能性。
四、美国“三振出局”制度的变迁与启示
在我国,终身监禁制度自《刑罚修正案(九)》颁布之初才开始实施,并且其仅适用于犯贪污罪、受贿罪的被告人。从第一例判决至今,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例尚不足十例,如此少的样本尚不足以展开有意义的实证研究。本文将选用一个替代方案,即以上文提到的终身监禁广泛适用的美国蓝本展开研究。当然,两国在司法体制、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将美国的实证研究结果迁移到我国,存在一定的逻辑跨越。但是,在现阶段,其仍然对于未来我国终身监禁的制度走向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从事实学的角度研究终身监禁效力问题,其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终身监禁的广泛使用,是否真正能够导致一部分潜在犯罪人放弃实施犯罪行为,从而导致整体意义上的犯罪率下降。然而,在探讨刑罚制度变迁与犯罪现象的过程中,始终需要克服两个问题:〔19〕前引〔5〕,吴雨豪文。一为反向因果,即虽然终身监禁的适用可能对犯罪情况产生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犯罪情况也会对刑罚的适用产生影响。例如,当我们发现一个地区犯罪率伴随着终身监禁的适用率同步上升时,我们并不能当然地得出终身监禁无效。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正是因为大量恶性犯罪的存在,司法者不得不因罪动刑,从而导致终身监禁率上升,而如果不如此适用终身监禁,该地区的犯罪率可能更高。二为遗漏变量。由于影响犯罪的情况多种多样,单独比较适用终身监禁与否和犯罪率高低的关系并不能有效得出终身监禁是否具有威慑效力的结论。例如,虽然美国与欧洲相比,前者终身监禁广泛适用,而后者将其排除在合理的刑罚范围之外,但是在犯罪率上美国依然显著高于欧洲,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终身监禁没有威慑效力,因为影响犯罪率的因素多种多样,在控制这些额外因素之前,我们无法排除是由于这些刑罚之外的因素遮蔽了终身监禁的真实威慑效力。
因此,一个相对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就是“准实验设计”的方法,即寻找一个突然产生的“外生变量”,以这个变量对终身监禁适用的影响为线索,分析犯罪率的前后变化,以此考察终身监禁的威慑效力。在美国,这个“外生变量”就是“三振出局法”的引入。
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是美国联邦层级与州层级的法律,其核心理念就对犯第三次以上重罪的累犯采取强制性的量刑规则,从而大幅度延长他的监禁时间。从现在的法案来看,拥有“三振出局法”的州,对于第三次重罪的量刑最低年限是25年,最高是无期徒刑。并且,第三次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被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终身都不得减刑、假释,从而形成事实上的终身监禁。在2012年,全美国有27个州及联邦政府都颁布了“三振出局”的刑罚制度,其中有13个州直接将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强制适用于犯第三次特定重罪的被告人。〔20〕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Washington Sentencing Guidelines Commission (2012).Third Strike Offenses Triggering Mandatory LWOP in Washington 1999-2012. Statistical Survey of Adult Felony Sentencing. Washington Sentencing Commission, p.8. 资料来源于华盛顿州政府官网,http://www.ofm.wa.gov/sgc/, 2019年4月20日访问。
在制度变迁上,得克萨斯州是第一个颁布了三振出局法的州,该法案的内容是“第三次犯重罪者处以25年以上99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21〕Texas Penal Code Section 12.42(d).后来最高法院在1980年第一次做出该法案不违反宪法的认定。〔22〕Rummel v. Estelle'' 445 U.S. 263 (1980).而后,在1994年,时任的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联邦政府的三振出局法案,并获得了国会的通过。〔23〕H.R.3355 -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 US Congress.联邦政府的法案迅速带起了各州的效法。
1994年加利福利亚州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第184号议案,开始在全州范围内实施三振出局法。〔24〕California Proposition 184, the Three Strikes Initiative (1994).根据该法案的内容,所谓的每一振(strike)就是指被告人犯有一个严重或者暴力类的重罪,其中包括谋杀、抢劫、强奸、引起身体伤害的故意伤害、入室盗窃、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等等。其中被告人在一振之后,即以上述罪名被定罪一次后,其在第二次犯重罪被量刑时,无论其是否属于严重,或者是否属于暴力类犯罪,他的刑期都会当然地被翻倍,并且在服刑80%之前不得假释。当被告人两振之后,他犯任何重罪都会被处以2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的刑期,并且在服刑25年的80%之前,不得减刑假释。由此,加利福利亚州虽然颁布三振出局法的时间不是最早的,但却是全美国对该刑罚制度执行得最彻底的。〔25〕Shepherd, Joanna M (2002), Fear of the First Strike: The Full Deterrent Effect of California's Two and Three-Strikes Legisla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1(1):159-201.并且从执行结果上来看,从1994年开始,在加利福利亚州,因为第三次实施重罪并被判刑的被告人,尚无一人获得释放,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监禁。〔26〕Eric Helland and Alexander Tabarrok (2007), Does Three Strikes Deter? A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2(2): 309-330.因此,在美国,对终身监禁威慑效力的研究大多是以加利福利亚州为样本而展开的。
三振出局法虽然饱受争议,但是仍然两次获得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承认,在上述所说Rummel v. Estelle案之后,2003年3月5日的Lockyer v. Andrade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次以5比4的多数意见认为,三振出局法并不违反“禁止酷刑与非常刑罚”的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其中,撰写多数意见的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分析了加利福利亚州严重的罪犯累犯问题,以合理根据进行审查,总结道:“我们并不是作为‘超级立法机关’对这些政策决断做事后评价。加利福尼亚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明显加强对于习惯性重罪加重刑期,有益于达成在犯罪司法系统目标,这就足够了……的确,厄文的刑期是很长。但是这反映了一个理性立法判断,即犯下严重或暴力罪行的被告在累犯时必须被重判,这应当遵从。”〔27〕Lockyer v. Andrade 538 U.S. 63 (2003).
由此可见,三振出局法以一种对累犯强制适用与其罪责不相适应的刑罚的方式,显著地扩大了终身监禁在美国的适用。因此,以三振出局为线索,美国犯罪学界开始展开对终身监禁威慑效力的研究。
五、实证检验:不同研究方法下的结果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对于“三振出局”威慑效力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时间序列的研究,第二个部分是基于潜在犯罪人行为选择模式的研究。
1. 时间序列的研究
所谓时间序列的研究,就是通过比较三振出局法引入前与引入后,犯罪率变化的状况,以此来得出三振出局法和终身监禁的广泛适用是否具有特定的威慑效力。其中,最早的研究来自加利福利亚州检察总署的评估报告,根据该项报告,法案施行前与施行后相比, “案件数”和“犯罪率”多有大幅降低现象。其中,在法案颁布4年以内,加利福利亚州全州的谋杀案件减少了4000起,犯罪被害的报道减少了80万起,从而支持“三振出局法”具有明显的威慑效力。〔28〕Lungren, Daniel (1998),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eport on Three Strikes,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http://www.threestrikes.org/cag98_pgone.html,2019年4月20日访问。
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所言,简单地比较一个总体地区在“三振出局法”前后的犯罪率变化,尚不能完全推断出刑罚具有威慑效力的因果机理。一方面,整个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上述所说的犯罪率下降很可能仅是一个整体趋势,而并非是由于终身监禁的大规模适用所导致。另一方面,影响犯罪率的犯罪因素非常之多,例如关于美国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解释,就存在堕胎合法化、警察活动的增强、可卡因市场的管控等多种因素。〔29〕Steven Levitt (2004), Understanding Why Crime Fell in the 1990s: Four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Decline and Six that Do No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 163-190.在没有控制这些多方面变量之前,从相关关系中尚不能推断出因果关系。
因此,学界开始采用更加严格的方法分析“三振出局法”引入前后犯罪率的变化。其中,斯图伯格教授和阿利索教授通过分析加利福利亚州10个城市在实施“三振出局法”后犯罪率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其对犯罪的影响,他们的论文在方法上做了以下改进:(1)除了分析严重犯罪的犯罪率变化之外,他们还专门选择了轻微盗窃罪作为研究的对照组。因为后者并不在“三振出局法”适用范围之内。如果“三振出局法”真的具有特定的威慑效力,那么在这一政策引入后,不受其威慑的轻微犯罪的犯罪率不应该呈现明显的变化。(2)他们使用了每一个月,而非每一年的犯罪率作为研究对象,从而能够更加精确地分析犯罪率的变化趋势,判断在引入“三振出局法”之后,犯罪率的下降是否是先前已经存在的变化趋势所引起的。(3)为了排除不同城市固有犯罪率的差异,他们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相关的虚拟变量。
然而,在统计方法上做了以上优化之后,研究结果发现:一方面,虽然严重的犯罪在引入了“三振出局法”之后下降了15%,但是那些不适用“三振出局法”的轻微犯罪也下降了7%,因此之前官方提供的犯罪率下降很可能是由于社会总体犯罪率下降所致;另一方面,时间序列的因果推断显示,无论是严重犯罪还是轻微犯罪的犯罪率在法案颁布之前就已经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后续犯罪率减少只是先前犯罪率下降趋势的延续,换言之,“三振出局法”本身并没有对犯罪率的下降提供额外的因果力。〔30〕Stolzenberg, Lisa, and Stewart D’Alessio (1997),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 The Impact of California’s New Mandatory Sentencing Law on Serious Crime Rates, Crime &Delinquency 43(4):457-469.
2.三振出局法下潜在犯罪人的行为选择研究
正如斯图伯格教授和阿利索教授在论文中承认的那样,虽然他们的研究质疑了宏观犯罪率的变化是否是由于“三振出局法”的引入所致,但是如此宏观视角下的研究却无法直接回答,一些可能已经犯有一个或者两个重罪的人,是否会因为害怕自己可能会适用“三振出局法”而面临终身监禁刑,进而放弃实施犯罪行为。〔31〕前引〔30〕,Stolzenberg, Lisa与 Stewart D’Alessio 文。研究这个问题的难点,是我们无法建立起一种“反事实的因果关系”。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数据知道,那些只要再实施一次犯罪就会被“三振出局”的犯罪人中有多少人不顾终身监禁威慑效力的存在继续实施了第三次犯罪行为。但是我们无法直接知道,如果没有“三振出局法”的存在,这部分比例会更高还是更低。因此,取而代之的一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构建起一个可以比较的对照组。即各方面与那些再犯一次重罪就会被“三振出局”的潜在犯罪人相类似,但是却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不可能受“三振出局法”威慑,从而比较两者在犯罪行为上的选择差异,进而得出“三振出局法”是否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力。
对此,埃兰教授和塔巴罗克教授非常智慧地选取了一组对照组:那些虽然犯了两次重罪,但是在前两次重罪的刑事诉讼中,其中有一次由于一些案外的因素,例如辩诉交易、证据不足等等,最终只被法院认定为 “一振”的潜在犯罪人。进而比较他们与上述已经被法院成功认定实施“两振”的潜在犯罪人的行为模式相比较。应当说,这个对照组的选择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他们之前的犯罪只被法院认定为“一振”,因此在他们再次犯罪时,即使实施了重罪,也不会被“三振出局”而被直接适用终身监禁;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事实上实施了两次犯罪行为,之所以只被认定为“一振”,只是由于一些不可控的案外因素。这使得对照组的潜在犯罪人在人身危险性上与实验组的潜在犯罪人尽可能相近。通过对两组潜在犯罪人的数据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在种族构成、过去的犯罪形态上,两组对象均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因此,这个对比研究可以视为是一项“准实验的研究”。
在这个方法的指导下,埃兰教授和塔巴罗克教授通过对38624名1994年从监狱中服刑完毕的罪犯的再犯行为研究发现,那些已经犯有“两振”的潜在犯罪人相对于犯有“一振”的潜在犯罪人,在出狱后1年被重新逮捕的比例减少12%,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少4%到7%。从整体而言,因为“三振就会出局”的刑罚威慑将再犯率减少 8.3%左右。同时,他们还将从加利福利亚州被释放的罪犯的再犯情况与纽约、伊利诺伊州的再犯结果相对比。与加利福利亚州不同,这两个州的“三振出局法”虽然规定了被告人第三次犯罪会被处以延长的刑期,但是并不直接被适用终身监禁。而与从加利福利亚州获得实证研究结果不同,在这两个州,那些已经犯有“两振”的潜在犯罪人在再次犯罪时与对照组的行为人并没有潜在的区别,从而肯定了终身监禁具有部分的威慑效力。〔32〕Eric Helland and Alexander Tabarrok (2007), Does Three Strikes Deter? A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2(2): 309-330.
综上所述,在美国,关于“三振出局”的实证研究在宏观与微观上呈现相反的结论:一方面,在宏观上, “三振出局法”和终身监禁扩张适用与严重犯罪的数量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上可以证明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将终身监禁适用于第三次重罪又的确可以威慑住那些已经犯有“两振”的潜在犯罪人。当然,在援引美国三振出局的研究结果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终身监禁在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在“三振出局法”中,终身监禁可以适用于所有第三次犯有重罪的潜在犯罪人。在美国,重罪是指可以被判监禁刑1年或1年以上的犯罪。由此,其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的罪行不是十分严重的非暴力犯罪,而这类犯罪中,对于累犯施加与其犯罪严重程度极度不相等的刑罚,的确很可能可以阻止他们继续实施犯罪。但是在我国,从现有的立法上来看,其倾向于将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其中在未来很可能适用于一部分严重的暴力犯罪,而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暴力类犯罪相对较难受到刑罚的威慑,在此情况之下,终身监禁是否还能继续对潜在犯罪人发挥威慑效力,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结 语
《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在贪污贿赂罪中设置了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这是我国政策推行过程中常用的“试验性”立法方式,立法者正是想通过小范围的试点,对这一制度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从而为终身监禁的推广适用积累经验。
在刑罚威慑效力的发挥上,终身监禁具有以刑罚的绝望性作为威慑来源,以永久隔离代替特殊威慑的特点。因此,一方面其可能对潜在犯罪人产生巨大的威慑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各种本可以约束服刑罪犯行为的措施都归于无效。
从刑事立法实践上看,终身监禁的广泛适用主要是在美国,从美国学者提供的实证研究看,其虽然没有在宏观上显著地导致犯罪率的下降,但是仍然对一些累犯的再次犯罪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
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当然地扩张适用终身监禁制度,这是因为:一方面,实证结果显示,终身监禁的扩张适用对宏观犯罪率并不具有显著的降低效果,而只对累犯的个人决策可能施加额外影响。目前为止,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并不适用于累犯的加重惩罚,终身监禁在美国适用所具有的优势并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
另一方面,在以刑罚威慑效力作为刑事政策的依据时,还必须考虑该刑事政策的成本。而终身监禁制度的一项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罪犯会在监狱中自然结束他们的生命,而这将为公共支出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根据美国相关判例中援引的数据,平均每位监狱服刑人员1年所耗费的财政支出为2.5万美元到3万美元之间。但是由于医疗花费的显著提升,这笔支出将会随着罪犯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最终,一位年长的服刑人员每年的开支可以达到6万到7万美元之间。〔33〕United States v. Craig, No. 12-1262 (7th Cir. Dec. 18, 2012) (Posner, J., concurring).加利福利亚州的一项数据说明,监禁55周岁以上罪犯的平均开支是55周岁以下平均费用的3倍以上。〔34〕Joan Petersilia, Understanding California Corrections, Cal. Pol’y Research Center for Evidenced-Based Corrections, 2006, p.15.虽然我国的监狱医疗保障设施没有美国那么完善,可能不存在这样悬殊的差异,但是,随着监狱管理人道化的不断推进,由终身监禁及与此相伴的监狱老龄化所引发的制度成本,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些成本最终将会分担到每一位纳税人身上,因此,在实施刑罚措施改革时,一定要审慎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