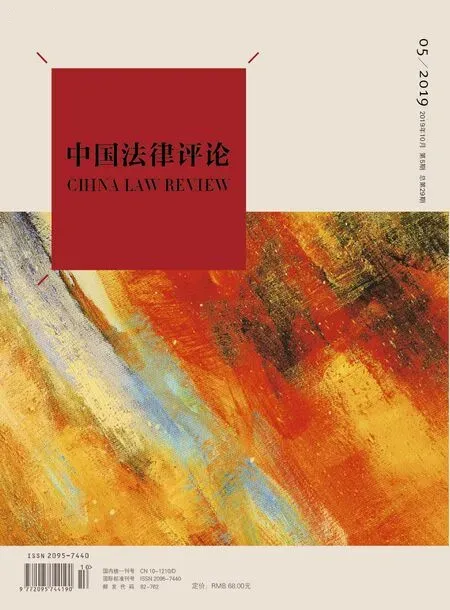中国死刑七十年:性质、政策及追问
林 维
内容提要: 七十年来,死刑制度作为中国刑事法治艰难反复但不断进步的缩影或侧面,其改革与完善成为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死刑从作为革命暴力的阶级斗争工具到惩罚犯罪的法律武器,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脱敏,促进了这一制度乃至整个刑事法治的变革。而严格控制死刑的理念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严打斗争的反复,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从失控泛滥适用政策到刑法规制背景下的扩张适用政策,逐渐转型为法治语境下的限制适用政策,通过死刑适用罪名的削减和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从而实质性地贯彻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未来,建议应当明确“暂时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继续推动死刑改革的讨论,立法上继续明确限制死刑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则要更大范围地公开死刑核准与否的裁判文书,继续担当大量削减死刑适用数量的政治责任,并适时公布死刑数据,促进死刑的进一步削减直至最终废除。
生或者死,这是个问题。这一问题从来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满腹愁绪的年轻人在饱食终日后的虚无之问。作为一种终决地处理主体生命的刑罚方式,死刑也因此成为一个困扰我们的“终极”法律问题。死刑本身的生死问题或者存废问题,亦成为今日法律的焦点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它远远超越了作为一终极哲学问题的不可解性。正是法律问题不可回避的实践性和可诉性,它是,而且必须是可解的,要求立法者、司法者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
七十年就其时间跨度而言并不算长,但正如国家和社会所经历的快速、巨大变化一样,我国死刑无论其理念还是制度,无论是实体适用的限缩还是程序的严格控制,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是,我们如何面对死刑,如何看待死刑,如何“处理”死刑这一法律手段,如何审视死刑之死,等等,仍然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七十年的死刑变迁,对于厘清我国死刑未来发展的方向,就具有了更为特殊的重要意义。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死刑作为刑法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其七十年的演变也是我国刑事法治艰难反复但不断进步的七十年,死刑制度的进步正是我国刑事法治乃至整体法治发展的缩影,同时又折射出多元的困惑和复杂的理性选择。七十年之间,我国的死刑制度变革成为法治进步的重要内容,未来我们仍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法治理念,以迎接更加文明的法律新时代的到来。
一、死刑七十年来的性质演变
(一)作为革命暴力的阶级斗争工具
死刑问题,既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自古以来,死刑就一直存在,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种适用极其广泛的刑罚,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也就由来有自。近七十年来,死刑问题交织着太多的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因素,相互纠结缠绕,而远非一般法律问题所能覆盖而论。
溯至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要“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肉刑”。1中央档案局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这是作为一个新兴政党面对时局而就社会的未来所提出的前所未有之主张,并以此作为准则之一而与其他政党产生鲜明对比。宿命或者使命使死刑问题不可避免地内在于一个新兴、先进政党的目标之中,并自此毫无争议地使有关死刑的讨论在很长时间内首先具有政治的色彩而非法律的意蕴。死刑问题的讨论在特定的时期内不得不具有政治的规训意义,而直到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达到一定的完备阶段之时,有关死刑的讨论才可能政治脱敏而更为强调其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
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艰巨的斗争现实以及复杂的革命形势,不允许放弃死刑作为打击敌人、保护革命成果的武器,在根据地的不同刑事立法中均保留了死刑。例如1931年《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总则即将死刑作为主刑之一,而分则中则有19个条款规定了死刑。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有26个规定具体罪名的条文,每个罪名之后均规定了“处死刑”的表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囤货取缔伪币条例》《晋察冀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规范性立法均有死刑规定,死刑成为革命的暴力工具。恰如列宁所说:“任何一个革命政府没有死刑是不行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该政府用死刑这个武器来对付哪个阶级。”2[苏]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死刑的这一性质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并未有任何改变,这当然同20世纪50年代初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相关。政权生存的必要性成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正当性理由,各地对旧的恶势力大量运用包括死刑在内的惩罚手段,极大地树立了我们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因此,“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3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但是,死刑适用的数量也呈现扩大化的倾向,以北京市为例,到1952年年底,共处决反革命分子940人,4张浩:《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7期。而据公安部1954年的统计,“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处决反革命分子71.2万人,甚至有学者估计全国范围的实际处决人数可能还要大大超过此数。5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年初到1952年2月的“镇反”,共有反革命分子87.36万人被判死刑。6纪彭:《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载《文史参考》2010年第20期。毫无疑问,死刑在这一时期的运用极大震慑了社会各种敌对势力,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起到了稳定政权、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死刑适用中压倒性的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因素,使死刑成为绝对的革命武器和阶级斗争的锐利工具。死刑的政治性、革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法制遭受巨大破坏,而死刑仍然无法逃避其革命的暴力性质,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指导下,阶级斗争严重扩大,死刑成为打击现行反革命的利器,乱打滥杀使死刑的适用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之下。
作为一种国家控制下的绝对的暴力,死刑与政治的纠结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蕴藏于死刑最为隐秘之处而时刻等待爆发的时机,但是死刑高度的甚至绝对的政治化使死刑的适用完全出于政治策略的考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逻辑在死刑上面投射了巨大的烙印,尤其是在欠缺相关死刑立法,仅有粗糙的、原则性的规范体系背景下,死刑的滥用以及由此必然招致的错用几乎不可避免。并且,在阶级斗争这样一种语言框架内,死刑的诸多问题都无法得到充分合理的思考和讨论,因为围绕死刑的一切学术争论也都可能毫无例外地被高度政治化,从而引入歧途甚或死路,而死刑的法治化更是无从谈起。
(二)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惩罚犯罪的法律手段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事业逐步深化,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善,促使死刑的内在性质从革命暴力性转变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性,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惩罚犯罪的手段。这样一种转变意味着死刑政治性的弱化和法律性的强化,具体而言:首先,死刑的正当性在政治性的话语框架中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结论。死刑的必要性是由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所决定的。7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但是在法律性话语框架中,死刑首先需要得到正当性的确认,也只有在此时,人们才会去思考并且尝试着论证死刑的正当合理性以便坚持死刑的合法性。其次,只有在死刑的政治性弱化、法律性强化的背景下,死刑的实效性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节俭性乃至比例原则等才有被导入思考的可能性。因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性必然要求手段的有效性或者工具的效率问题得到充分的论证,而革命暴力性则是一种天然的色彩添附。再次,死刑的适用应该依法进行,必须要求具备充分合理的、成体系的法律规范,而不能唯政治论,单纯地依赖党的文件或者政治决定。最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死刑问题进行更为开放的涉及法律技术层面的分析和论证。这也是在晚近四十年尤其是在晚近二十年间有关死刑的争论能够蓬勃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
不过,这样一种转变仍然需要一定的过程性和过渡性。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分则”规定的27个死刑罪名,其中14个与反革命罪有关,清晰地说明了死刑的打击重点仍然聚焦于阶级斗争。并且“总则”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将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作为刑法制定的指针,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8刘春花:《向死而生: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政治抉择》,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但是死刑的政治性已经显著弱化,尤其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治安恶化、经济犯罪增多,一系列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增加了44个死刑罪名(包括《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涉及的死刑罪名11个以及其他单行刑法增加的33个死刑罪名),总计71个死刑罪名,9由于过去并不存在罪名的司法确定制度,因此1997年之前我国死刑罪名的数量存在多种说法,上述数字请参见[美]Jerome A.Cohen、赵秉志主编:《中美死刑制度现状与改革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也有人认为补充刑事立法增设的死刑罪名有50余种,从而使死刑罪名达近80个之多,参见刘仁文主编:《死刑改革与国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或认为1979年刑法典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之后的单行刑法补充了40个死刑罪名,参见贾宇主编:《死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或认为后续增加的共计52个死刑罪名,参见张文、米传勇:《中国死刑政策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等等。死刑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张,反革命罪在其中的比例显著降低,死刑的政治性更加淡化。尽管这样一种基于严峻犯罪形势而对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力度扩张死刑适用范围的做法,和镇反运动时期对反革命犯罪多杀的策略非常相似,具有异曲同工的功利色彩,但是仍然存在根本的差异:前者更多的是基于死刑工具主义,认定死刑对于打击此类犯罪具有实际效果,因而从手段的实效性出发而并非出于敌我矛盾的政治判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所指出的:“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及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0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153页。死刑的政治性渐趋淡化,同时彼时对于死刑威慑效果产生确信甚至盲信,工具色彩愈加增强。
(三)作为学术问题而存在的死刑
1997年刑法颁布时,王汉斌副委员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明确“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也不增加”,彼时68个死刑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仅占7个,危害公共安全罪14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16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个,侵犯财产罪2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8个,危害国防利益罪2个,贪污贿赂罪2个,军人违反职责罪12个。
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最终使死刑在1997年刑法典中,更加彻底地恢复了其作为刑罚的质朴的一面,套用《刑法》第1条,死刑的本性即作为惩罚犯罪、同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得以彰显,愈加清晰。尽管法律整体本身不可能脱离、隔离政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法问题的思考都是一种政治考量、一种意识形态考量,因而所谓刑法知识完全混同于政治常识、意识形态教条,刑法知识的学术化完全无从谈起。刑法知识的政治化以及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政治对刑法学的一种侵蚀,有损于学术的独立性和知识的纯粹性”。11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2页。民主法治理念的进步使刑法不再阶级斗争化或者泛政治化,由此死刑或者说死刑问题在政治上的脱敏,使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更为科学、理性地讨论死刑问题的效果、效率、效益乃至死刑的正当性、合宪性等本质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刑法修订的过程中,有关死刑的有效性、死刑的正当性、死刑的程序、死刑的存废、限缩等问题得到了热烈讨论。按照不完全的统计,1979年共有3篇论文讨论死刑,整个80年代共有24篇论文讨论死刑,而在90年代,截至1997年就有95篇论文围绕死刑而展开,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有关死刑的讨论仍未降温,截至2006年共十年间,有854篇论文以死刑为题展开讨论。12具体的论文篇目请参见[美]Jerome A. Cohen、赵秉志主编:《中美死刑制度现状与改革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附录五“死刑研究参考论著”。迄今为止,有关死刑的论著更是数量惊人,考察视野更为宏大,论述深度更为深入精细。
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背景下,才有可能更为理性、冷静地研究讨论死刑,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削减死刑,并最终实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才有可能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一次性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并进而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再次成批量地减少9个罪名。与其说死刑罪名的两次大量减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毋宁说这是高层一次英明的政治抉择。但是易言之或许也同样具有深蕴:这样的立法行为,是一种理性而果断的政治决策,但也更是法学智识和法治理念的胜利。
二、死刑七十年来的政策演变
必须指出的是,政策和理念不同,政策更强调实际的运作,因此实际的政策和宣称的理念之间有时可能存在差异,理想的理念有时在现实社会形势的需求和期待下,可能形成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把握和实践。这一点尤其在七十年死刑的前期发展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理念主张和实际政策的运用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差异的现实。七十年来,我国的死刑政策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而不断演变,限制适用和扩张适用交织反复,而每一次演变几乎都建立在深刻教训的理性反思、吸取和对于死刑本身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每一次演变都足以成为刑事法治的生动案例。刑事法治正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得到了螺旋式的发展。
(一)失控:少杀、慎杀理念下死刑的泛滥适用政策(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死刑理念一般均表述为坚决保留、决不废除死刑,但强调少杀、慎杀。无论是领导人的主张还是相应文件,均表现出这样的理念。例如1948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即指出“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越少越好”。1950年10月10日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也规定要防止乱杀错杀。
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某种程度上,这些宣言仅仅是或者更多的是某种理念或理想,实际的政策运用远非如此。由于这样的理念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甚至保障,因而使其无法真正地、实际地指导政策,最终落实为具体法律措施;甚至这样的理念本身就缺乏对死刑本身理性而坚定的认识,“这种谨慎的态度并不是出于对死刑的非人道和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的认识,而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13刘春花:《向死而生: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政治抉择》,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例如,出于避免可能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或者出于杀了不利、无助于强大国防、收复台湾、增加生产,等等。相应的政策既然仅仅是一种策略,就必然受制于社会形势的风吹草动,少杀、慎杀的理念就缺乏政策的连贯性、制度的确定性、实施的原则性和执行的坚定性。
正是存在理念和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的死刑政策一方面呈现出积极适用的性质和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反复、摇摆、矛盾的心态。
例如,1950年3月28日,刘少奇批示:“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对已经过宽待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于长期徒刑以至死刑。”14刘少奇:《对两则匪特破坏案件通报的批语》(1950年3月1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3页。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以及1950年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均规定对所有类型的反革命案件最高都可以判处死刑,这些文件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重要根据。但在此期间,少杀错杀的理念仍然在不时发挥作用,例如考虑到国内局势的稳定要求以及政治力量的联合,屡次强调要防止错杀乱杀,甚至上述“双十指示”仍旧突出强调了要防止“左”的偏向,继续要求“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甚至有时仍然担心类似运动的扩大化,要求适度降温、注意策略。又如一些省份如河南将近一年执行死刑3000人,就敏感地发现各地捕杀开始出现草率现象,因而在1951年1月就迅速决定一般停止逮捕和杀人。15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但这一理念并未坚持多久,1951年1月之后,全国范围内各地放开手脚处决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甚至还按照人口比例给各地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2月21日政务院又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并且根本上否定了“已遂”“未遂”的概念,至于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有关要件的规定又缺乏具体细致的解释。
但党和政府迅速意识到运动扩大的现象,1953年5月10日紧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承认,“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因此必须及时地“从大胆放手的方针改变为适当地加以收缩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16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同时重申了死缓政策。此后死刑的适用数量相对减少。正是遭遇了这样的教训,50年代中期开始重提少捕少杀,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即指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1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页。必须注意到这些表述正是在经历了死刑的扩大适用的教训之后所提出的。甚至在1956年9月15日至17日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同志所做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以死刑的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18参见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不过,1958年董必武同志的说法略有不同,他针对当时的司法工作也提出,“死刑我们从来不说废除,但要少用。死刑好比是刀子,我们武器库里保存着这把刀子,必要时才拿出来用它”。19董必武:《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未来的废除说还是少用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相应文件能够提出并在有的时间内坚持这样的理念,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也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死刑问题开始了初步的、理性的认识和探索。
但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经历太多时间,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对于包括死刑问题在内的政策理性完全停止,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完全被否定,彼时的死刑政策严格意义已经不能被称为死刑政策,因为法律秩序完全陷入了不正常的状态。社会失控导致法制紊乱、秩序动荡,令数以万计的人成为冤魂。在极“左”路线指导下,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乱打乱杀现象普遍蔓延。以1970年为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22人。“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多少人被不正常判处死刑,答案或许永远无人知晓。20刘平远:《文革死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载《文史参考》2010年第20期。
(二)控制:刑法规制背景下死刑的扩大适用政策(1979—2007年)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间,多次政治运动导致我们党正确的死刑理念未能得到长期、一贯的坚持,相反死刑的实际政策出于政治策略考量,长期在多杀少杀、滥杀慎杀问题上摇摆,经常是在死刑滥用乃至失控之后才又痛定思痛,力图返回正确做法,但又往往被另一个运动所打断,而陷入再次的失控状态。个中原因复杂,不过刑法规范体系的缺乏是加剧这一局面的重要法律制度原因。尤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法制的破坏这一惨痛教训,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目标出发,国家格外注重法律制度建设。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诞生标志着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也更意味着“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了法律规范体系的支持,从而为将少杀慎杀的死刑理念转变成死刑政策奠定了规范基础。实际上,也只有从这个阶段开始,我国对于死刑才真正开始具有了现代法制意义上的控制的探索。也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策的回归同样也是因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死刑完全失控的惨痛教训。
1979年刑法对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控制死刑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分则把规定死刑的条文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仅有7个条文规定了死刑,而且均同时规定无期徒刑和长期自由刑作为选择刑,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其次,刑法从犯罪主体方面对死刑适用作了限制,明确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需要指出的是,历次草稿中并没有“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规定,而是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代表意见而仓促增加。再次,把我国刑事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从而继续发挥这一制度的威慑力和改造效果,减少杀人以促进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第43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还就死刑复核程序和死刑判决的执行程序做了进一步详尽规定。彭真在对刑法草案的说明中恰当地诠释了1979年刑法典的死刑政策,即不能废除死刑,但要贯彻少杀的方针,应当尽量减少。21彭真:《关于刑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说明》(1979年6月7日),载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精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
但是,当人们还暂时停留在对新刑法的最初认知之时,死刑政策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死刑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产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急剧增多,尤其治安形势恶化,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王汉斌在《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几个法律案的说明》中指出:“目前许多地方社会治安情况仍然很不好,从主观上来说,主要原因是,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不坚持,对一些犯罪分子该捕不捕,该判不判,或者该重判的没有重判。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一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刑法都规定了可以判处死刑。对这些严重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惩处。同时,这几年出现了一些严重犯罪的情况,性质恶劣,危害严重,民愤极大,应当判处死刑,但是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不能判处死刑,需要修改补充……对这种犯罪不严厉惩处,是不可能搞好社会治安的……决定草案对这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规定可以判处最严厉的刑罚,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的,是会大得人心的。我们决不能容许那种社会治安失控、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妇女夜间不敢单独上班走路的严重现象的存在。”基于这样的考虑,从1983年开始第一次“严打”,少杀、慎杀的理念又未能坚守而被轻易突破:首先,死刑罪名大幅度增加,从《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将7种犯罪的法定刑提高至死刑开始,《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9种犯罪增加了死刑,并增设了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最高刑为死刑。1981—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二十多个单行刑法新增设死刑罪名44个。其次,单行刑法中多个条款规定了绝对死刑,例如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罪规定绝对死刑,1991年《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组织他人卖淫罪、强迫他人卖淫罪规定了绝对死刑,等等。最后,正如后文所述,原本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的死刑核准权,大部分陆续授权省级高院行使。
之所以并未将这一时期限定或者截至1997年刑法修订,而是延至2007年,其原因在于几次“严打”跨越了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而1997年刑法典对于过去增加、积累的死刑罪名,“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也不增加”。22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6日),载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精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71—872页。在几次“严打”过程中,死刑都成为最为重要的惩罚手段,死刑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即使在1997年刑法实施之初,尽管对此有所反思,但也并没有采取很积极的措施着手大力限制死刑,而仍然对死刑的适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当然,一方面,通过不断修订立法最终使死刑政策转向成为扩大适用,形成与初始的慎杀理念截然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第一次“严打”自1983年始至1987年初,其中第一阶段就处决了2.4万人。23唐明灯:《“严打”的前世今生》,载《时代周报》2010年7月1日。在整个时期中,尤其由于1997年刑法对于1979年刑法以来的死刑规定的承继性,使死刑的扩大适用政策和做法即使在1997年之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人们仍然无法摆脱死刑工具主义的理念。但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坚持慎杀政策的基础立法,即使死刑适用扩大化,也始终坚持在法律规范体系的框架内运作。而1997年刑法也并非完全照搬照抄原有的立法规定,而是通过直接取消、位置转移、内容吸收、条文分解以及罪名合并等方式,24钊作俊:《死刑限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7页。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使死刑罪名的数量和绝对死刑条款有微小调整。因此,即使历经数次“严打”,尽管呈现出扩大化倾向,但是死刑的适用显然没有像前一阶段那样失控而仍然处于规制的框架范围之内。尤其若干次“严打”和各种专项整治活动尽管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实务人员都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刻地反思,并且达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即这样的“严打”措施或许短期内可能取得社会治安的一定好转,但犯罪的产生、发展自有其规律和逻辑,“严打”措施无法根本上取得遏制严重犯罪的上升趋势,而且其短期效果也逐年递减,无法从实质上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甚至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错误判决导致执行死刑的结果。25目前披露出来的错案例如聂树斌是在1995年4月27日执行死刑,呼格吉勒图案件是在1996年6月10日执行死刑。因而越到后期,死刑的扩大适用政策越呈弱化趋势,而限制死刑的适用则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某种意义上,这个阶段正是从泛滥适用的失控状态走向目前慎重适用的限制状态的一个过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众多学者围绕死刑的多侧面进行了深入反思,有关死刑论著的发表和出版达到了一个高峰,恰恰是死刑极度的扩张适用引发了死刑理论的背反。死刑在适用上的凯歌高奏成为扩张政策自身的挽歌前奏。这一时期刑法学者的深刻反思(即使是死刑保留论的辩护本身也是反思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数百年间有关死刑争议的循环演奏,但是在特定语境、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理论重述、复新,不仅仅为晚近阶段的立法乃至司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通过学术的争论所达致的问题的清晰,推动了一般性共识的缓慢形成,而且这样一种学术性思考和限制死刑的公开宣传和传播,使司法实务人员乃至一般公众对于死刑不复怀有神秘感、疏离感并因此具有盲目的崇拜感,公众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备了期待并做好了心理的准备。显然,刑法学者为削减死刑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26张明楷:《刑法学者如何为削减死刑作贡献》,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1期。
(三)限制:刑事法治语境下死刑的慎重适用政策(2007年至今)
所谓死刑的限制,大体包括实体的限制和程序的限制。过往的扩张政策一方面体现在实体法上适用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死刑核准程序的松弛。就此而言,对刑事政策的反思促成死刑理念的真正落实,死刑政策真正从泛滥、扩张转变为限制,其标志性事件首先是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统一收回死刑核准权,从而结束26年的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至高级人民法院的历史。熟悉这一过程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判断,而更是一种政治决断。其次则是《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死刑适用罪名的减少。
1.死刑核准权的“下设—上提—下放—收回”
死刑核准权的归属和死刑的扩张、限制紧密关联,从而跟随死刑政策的反复而反复,历经“下设—上提—下放—收回”的过程。
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法会议决定一般死刑案件由省级以上人民法院核准执行,重大案件送请上级人民法院核准执行。同年的政务院《人民法院组织通则》和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规定,县(市)人民法庭(分庭)判处死刑的,由省人民政府或者省人民政府特令指定的行政公署批准;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法庭(分庭)判处死刑的,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中央直辖市判处死刑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批准。27杨宇冠主编:《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页。尽管意识到死刑适用过于扩大,但是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仍然规定,死刑的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案件判决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案件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上诉、不申请复核,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这当然是一种权宜之计,加上此后吸取了死刑滥用的教训,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指出,死刑案件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这才有了1957年7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从而统一收归死刑核准权于最高人民法院。28实际上,1957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第22次稿)》第47条第2款就已经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此后的第33次稿、第37次稿等遵循了这一规定。尤其1963年的第33次稿曾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志原则审查过,参见1979年6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彭真所作的《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精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考虑到这一规定和此前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不合,1957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和核准的决议如何执行问题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又作了重申。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程序又完全被搁置,完全不存在所谓核准程序。
“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死刑的控制政策表现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法》第43条第2款也同样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也作了同样规定。按照彭真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刑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说明》所说的,“为了贯彻少杀的方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死刑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审核批准”。29不过在彭真所作的《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又表述为“为了贯彻少杀的方针和力求避免发生不可挽救的冤案、假案、错案”,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精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
但这一时间是如此之短促。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的死刑,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进一步确认、扩大规定为,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同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即据此发出《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将前述范围的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至高级人民法院。1991年6月6日、1993年8月18日、1996年3月19日、1997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和贵州等6个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刑法又继续重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因前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并未修订,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继续授权,甚至在1997年刑法生效之前的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再一次延续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30对此,很多学者认为,1997年刑法生效后,其法律效力位阶仅次于宪法,此前包括人民法院组织法在内的有关核准权下放的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均违反了其所重申的死刑核准权规定。死刑核准权自刑法在1997年10月1日生效当时就应当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直至2006年10月31日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其第13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彻底、正式收回死刑核准权。
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在程序上为死刑扩张提供了制度空间和可能,客观上造成大部分死刑案件均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架空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权,并且使二审程序和核准程序合而为一,核准程序名存实亡,保障作用几近丧失。尽管我们的死刑理念一直是少杀、慎杀,但大部分时间,核准权一直处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控制之外,造成死刑适用标准产生极大的地方差异,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下滑,死刑数量扩大,误判误杀概率上升。在收回核准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了更为整体的死刑政策的贯彻规划,先后单独或联合出台了《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等司法文件。核准权的收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控制效果,当年判处死缓的人数在多年来首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31《肖扬:中国今年判处死缓人数首次超过判处死刑人数》,载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ce.cn/law/home/scroll/200711/24/t20071124_ 12719153.shtml, 2019年9月20日访问。2007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倪寿明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当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死刑案件仍然占到总数的15%左右。32《最高法发言人解读报告回应贪官免死等热点问题》,载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ce.cn/law/home/scroll/200803/11/t20080311_ 12867649.shtml, 2019年9月20日访问。实际上死刑下降比远不止15%,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这一举动本身带给各地法院严格控制死刑的信息。据估计,2007年收回死刑核准权后,中国的死刑执行数至少减少了1/2甚至2/3。
死刑核准权收回十余年来,其巨大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死刑制度本身。诚然,死刑核准制度改革使这一最严厉的刑罚措施的适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通过更大程度地严格限制适用死刑,死刑的数量得到了大幅减少,从而使死刑的合理控制成为可能。仅仅就死刑数量的减少而言,最高法院的这一举措就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司法史上人权保障的巨大进步,成为中国司法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之一。但是我们绝不能单纯地将这一改革的意义局限于此。由于死刑核准制度改革所要处理的生死问题极其敏感复杂而重大,因此在无形之间逼迫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重塑我们的刑事司法理念,重构相关的具体刑事司法制度,重新合理认识刑罚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对于死刑司法的制度改革,从而产生巨大的涟漪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理念的革新进一步辐射、扩及刑事司法整体,带动其他刑事司法制度产生相应同步的变革。毋庸置疑的是,宽严相济政策、非法证据排除、庭审实质化等理念的提出和制度的设计,都和死刑案件的审理经验和教训直接相关,并因此和死刑制度改革之间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和呼应。这都是死刑核准权收回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忽略这一事件对于整体刑事司法所带来的影响,忽略死刑制度改革和刑事立法之间的互动,忽略这一司法事件对于司法文明的推动,就会使我们无法在十余年之后正确全面地认识这一改革的巨大成功。不仅如此,死刑核准制度改革也缓慢而坚定地、不断地改变着公众的死刑观念乃至刑罚观念,从而形成更加文明的法治观,为司法不断迈向更加文明的阶段奠定了更好的民意基础。
2.死刑罪名的立法减少
如前所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并进而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再次成批量地减少9个罪名,刑法典中的死刑罪名已经从68个降为46个,从而在实体上进一步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两次修正案所废除死刑的罪名几乎都是实践中死刑适用数量极少或者多年来鲜有适用死刑的罪名。因此死刑罪名的减少和死刑数量的减少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就少杀慎杀而言,死刑罪名减少的效果和核准权的收回其意义不可等同言之。目前,除去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19个死刑罪名,剩余的27个罪名中,死刑适用数量的主体压倒性地集中于其中8个罪名。因此,通过立法废除死刑罪名从而实现死刑的严格、限制适用,当然仍然存有可能。但是考虑到其中某些罪名,例如贪污受贿罪,尽管死刑适用量已经极少,但是从政策意义上仍然具有保留的意义,因此立法上试图废除某一个死刑罪名,恐怕都将存在不少难度。
因此,通过立法减少死刑的数量在最近一个阶段将会进入慢速通道,在很长的时间内,通过各级法院审慎、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加强死刑的控制,并且充分运用核准权对于死刑政策的指引,就成为司法的政治责任。
三、追问当下的中国死刑
(一)死刑存废的讨论过时了吗
有关死刑如何最终废除的讨论仍应继续进行,正是晚近四十年间有关死刑存废的讨论促进了死刑政策的逐步合理化。但它也许不应该仍然是学界内部的讨论,诚如有学者所言,既然我国刑法学界内部已经就削减死刑达成了共识,便没有必要在学界内部就应否削减死刑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讨论,而是应当将削减死刑的刑法理念落实于具体的结论。主张削减死刑的刑法学者应当撰写通俗读物、一般短文,做电视演讲或现场报告,让仅仅回荡在刑法学界的削减死刑声响彻漫山遍野。33张明楷:《刑法学者如何为削减死刑作贡献》,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1期。重要的并非是言论,而是要让公众听到,并且付诸行动。我们也更应该讨论究竟如何以具体的步骤推动严格限制、逐步减少死刑目标的实现,以便在时机到来之时,引导民意作出选择而废除死刑。死刑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死刑适用范围在立法上的逐步限缩到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死刑适用的标准平衡、死刑替代措施的改革,乃至死刑辩护质量的提高、死刑救济程序的完善、复核的审限以及执行时限,乃至法官的死刑观念等问题,无一不是巨大的课题。只有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研究、解决,才能真正地实现目标。
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死刑的正当性,它同我们的社会发展、社会观念的进化、社会控制手段的丰富性、刑罚理念的进步等息息相关。当下保留死刑是因为作为一种刑罚措施,它仍然同民众的一般报复观念存在契合之处,同整体刑罚制度仍然内在包含的报应观念存在逻辑上的一致。刑法制度必须要回应普通民众普遍的报应需求和正义期待。但这种回应不能掩盖这样一种趋势:死刑应当在比较短时间内进一步地大幅度减少,并且最终被实质性废除。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内部地了解死刑的误判、死刑的不均衡、不公正以及某种程度的随机性,废除死刑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因此,“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并慎重适用死刑”作为短期政策并无不当,但在更长远的角度,应当树立“暂时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理念。相应的讨论都应该围绕这样的目标而务实地进行。在此特别重要的是,讨论的重点应当返回到生命的哲学问题以及死刑的宪法问题,而不再是死刑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死刑的有效性问题和死刑的正当性问题的根本区别。一种手段并不绝对地因为其有效而证成其正当性。事实上,完全可能存在比死刑更为有效但令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刑罚。姑且不论死刑的有效性或者无效性是否能够得到实践的证明,问题在于:即便死刑具有某种效果,其正当性就能够得到完全的论证了吗?
通过这样的讨论最终达到死刑的废除需要一个时刻表吗?必须明确,死刑的变革不太容易也似乎不应该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加以实现,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我让中国在一天之内废除死刑。34邱兴隆:《死刑的价值分析》,载游伟主编:《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但是如果认为废除死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35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则又过于缓慢。刑罚体系的变革应当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不应当不计后果做激进的考虑;死刑的废除将是一个革命性的标志,但其存留与否,不应当做过于单一的考虑,而应当全面判断,审慎决定。尤其必需考虑到对于特定犯罪,公众的舆论仍然存在特殊预防和一般威慑的期待,因此在目前阶段,严格限制、逐步减少直至废除死刑的路径仍然是一个稳妥的选择。但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大体的时刻表,以便形成倒逼机制,推动这一进程的实现,尽管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
(二)死刑的条款还能够减少吗
如果对此前两次修正案死刑罪名的减少给予过高的甚至里程碑式的赞颂,可能会让人们忽略了以后的每一步都会面临深水暗礁,举步维艰。死刑的立法削减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个“瓶颈”期、停滞期。因此在很长时间内,通过审慎、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加强死刑的控制就主要成为最高法院的政治责任。但是,这并不能替代死刑罪名的立法减少的重要意义和无可比拟的政治影响。
在讨论死刑罪名的立法废除之前,应当明确,除了死刑罪名的废除,立法首先应该考虑进一步限制具体罪名的死刑适用情节范围,以收立法限制死刑之效。刑法不应该一般性地在结果或情节加重犯中普遍地规定死刑,而应该对死刑所对应的情节事实作出更为明确、更为限定的规定。例如《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的八种情节均笼统地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尽管在实践中除了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外甚少判处死刑,但是在立法中就应该明确死刑仅仅适用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而不包括其余几乎不再适用死刑的七种情节。又如对某些可能判处死刑的模糊性加重情节,应当要求对死刑的适用情节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此或者将致人死亡可以判处死刑做独立规定,其余特别严重情节就不能适用死刑,或者如果考虑到可能仍会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需要判处死刑的,就必须明确其特别严重的具体内容,而不允许在死刑适用上选择概括性、笼统性、模糊性的兜底规定。通过这种立法技术的变革,大幅度地减少死刑适用范围,将实务上判处死刑的可能性、灵活性减至最小,这是目前更为可行的稳妥措施。
进一步,按照目前的态势,如何减少非暴力的甚至未致人伤亡的案件如财产性、经济性的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的死刑条款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死刑在这些犯罪治理中的作用,尽管不可准确测算的所谓有效性并非死刑公正性的根据,但是其无效性恰恰是否定对此类犯罪判处死刑的有效理由。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深入地分析保留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政治、文化、法治影响和废除其死刑的后果之间的平衡。例如,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包括监察体制在内的各种机制体制相互结合形成严密的法网之后,在贪污受贿行为得到根本性治理的背景下,尤其在已经适用终身监禁作为替代刑的背景下,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是否仅仅因政治宣示的考虑而需要长期保留?
而从另一方面,毒品犯罪死刑的效果更加值得我们反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先后分别对韩国、喀麦隆、斯里兰卡、伊拉克、苏丹和伊朗等国提交的人权报告评论指出,与毒品犯罪相关的行为不应属于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的范畴。死刑在毒品犯罪的遏制上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尽管适用了如此之多的死刑,毒品犯罪的数量为什么仍然在上升,甚至因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通过死刑遏制毒品犯罪无法实际收效,毒品犯罪继续增加,进而进一步形成对死刑的渴望和依赖。我们必须对死刑之于毒品犯罪的有效性做一个理性冷静的战略判断。诚然,如果没有死刑或者没有之前较大规模地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毒品犯罪可能更加猖獗,形势更为严峻。但是目前的状况至少表明,死刑适用对于毒品犯罪的作用并没有我们所想象、所期待的那么大,死刑的适用即使有一定效果也收效甚微。对于毒品犯罪的治理,不应该惰性地完全依赖于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惩罚和打击,或者依赖于重刑乃至死刑的规模化适用,而更应该思考、设计一种更为合理、更为有效、更为全面的制度,真正减少毒品犯罪的数量。在此背景下,毒品犯罪的死刑也应该进入废除通道。
(三)死刑的数量还能够通过司法减少吗
死刑的数量必须还要减少,而且通过司法减少死刑仍然具有空间。这一判断建立在我们社会治理的手段日趋丰富,社会秩序更为好转,社会容忍度更为提高的前提之下。截至目前,死刑在适用上的大量削减也从来不是主要通过立法完成,本质上仍主要是通过司法的努力加以实现。正是这样的经验促使我们可以也应当要求,即便在立法的死刑条款没有根本性减少的前提下,高级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的控制一定不仅仅来源于自身的努力,而应首先来源于社会状况和社会意识的变化,最高人民法院所承担的限制死刑的政治责任一定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社会意识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之间应当进行良性互动,司法政策要善于运用社会意识的细微变化并且加以引导,而不应滞后、盲从于社会意识而无所作为。坚持不懈地提高死刑适用的标准,对于死刑适用的模糊、综合判断标准不断加以剔除和明确限定,从而在立法即使不加以明确的背景下,司法上也可以不断通过排除的方式对死刑适用情节加以具体化、明确化,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冲击死刑的限制政策。
就司法上死刑适用的具体罪名而言,除去个别的非暴力犯罪如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以及虽未涉及人身死亡但情节极其严重的强奸、拐卖人口的死刑适用以外,实际上已经大体可以把我国的死刑适用案件区分为涉及人身死亡的案件和毒品犯罪案件。目前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某种意义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占据死刑总量的比例过高,就可能实质性地改变死刑的适用格局,淡化、抹灭甚至歪曲死刑设置的正义性,使死刑仅存的那点正当性更受质疑。对于毒品犯罪大规模地适用死刑,无论如何是无法得到正当性的确认的,公众也会越来越多地质疑毒品犯罪死刑的公正性问题。绝不应该将毒品犯罪的治理押注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上,这是司法所不能承受之重。因此,下一步限制死刑的有效领域一定发生在毒品犯罪领域。因为只有毒品犯罪,才可能在死刑适用的数量上还有大幅度、批量减少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在积极的意义上讲。法院应当进一步提高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对死刑适用的犯罪情节予以进一步的限定。在目前的证据标准和毒品犯罪认定标准下,毒品犯罪也可能是死刑适用出问题的危险性最大的领域。死刑中的误判可能性、随机性、不公平性等固有缺陷在毒品犯罪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运输毒品罪这样的犯罪的死刑,应当立刻废除。因此,我们必须对毒品犯罪的死刑时刻保持足够的警惕,以便我们能够在准确适用、不致出现冤错案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予以限制、减少死刑。
进一步,在社会状况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内部应该硬性地设定死刑数量的控制目标,力求为了倒逼自身实现数量的管控而不断提升死刑控制的潜力,为在某一时刻实现死刑数字的公开而奠定基础。
(四)最高人民法院可能出现死刑的误判吗
这一问题如果转换成为“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就不会出现死刑的误判”,可能就更容易让人理解。
就死刑执行而言,目前我们比较庆幸的是,迄今发现的死刑执行错案都并非最高人民法院所核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仍然能够以一种纠错者而非犯错者的身份来树立司法权威。但是在死刑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成为重重审判关卡之后保证死刑司法正当性的最后一道保障,司法权力的集中同样意味着错案概率的集中。固然核准权的收归意味着审判机制更加严密公正,死刑的裁量标准更加严格、统一,意味着死刑案件的质量应当会有实质性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死刑错案的概率就会绝对消除。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只要死刑制度存在,就仍然蕴藏着这样的潜在可能,即司法机器仍然可能会继续杀错人。因此,对于正在行使死刑核准权的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压力一方面来源于如何能够做到严格控制、减少死刑案件数量;另一方面则来源于随时可能出现的具有潜在可能的误判性在何时转变成为现实的误判。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就不是纠错者,而是犯错者,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案件上的误判,对公众对于司法权威的信赖的冲击显然要远远大于高级人民法院的死刑执行错案对司法信任的冲击。如果说严格执行死刑政策是一个更为宏观、难以具体测算的标准,不易成为评判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工作成绩的一个指标,那么死刑执行错案零的突破是一个更为具体、显见的事实,直接影响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工作的评判。
死刑案件的复杂敏感性对法官的法律素养、事实认定、政策把握提出了最高要求,死刑的严厉性要求法官担当最高的司法责任。十余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克服诸多困难,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保证了死刑政策能够自觉、坚决、稳定的贯彻实施,死刑裁量标准得到有效规范和明确,死刑案件质量稳步、显著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作为死刑案件的最终把关者,付出了巨大努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需要多少智慧、理性,才能代替上帝或者替代自然力量去决定另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并且丝毫不犯任何错误?理论上,只要死刑制度存在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就存在误判的可能性,误判仅仅是时间早晚问题。这是悬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死刑复核的每个法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好了承受这种可能性转化现实的心理准备?
(五)死刑的数据应当公开吗
死刑数据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幽灵,它寻觅不得但必在某处。死刑的数据应当公开,只不过仍然是时间问题。司法数据对于我们了解司法运作、成就、现状、问题,具有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欠缺这些知识或者信息,民众对于现实的了解往往浮光掠影、支离破碎,更多地来源于对身边事物的直觉判断和道听途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对司法的判断。简言之,包括死刑数据在内的权威司法统计数据的公布,是国家治理透明、民主、公正的标志之一。
保持死刑数据的神秘性固然有种种原因和顾虑,例如数据如果过大是否显得我们的司法过于严苛,从而影响对我们国情的判断,等等。这一数据的公开确实需要各种价值平衡和周密考虑。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当对自身的司法制度具备充分的自信,在对这一数据具有公众的可接受性和论证的科学合理性怀有自信的前提下,应当予以公开。事实上,在死刑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进步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有一个远期的时间规划,在将来对于死刑的数据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予以公布,来获得国内外舆论的理解,自信、自觉地接受各方的挑战质疑。当下,我们更应该始终为死刑数据的可公开性创造条件,严格控制死刑,不断削减死刑数量,直到这一数据可以大大方方地公示。
司法数据的保密,造成公众无从了解我们的司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导致人们对司法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更无法通过数据的比较而认识到我们法治的进步。死刑数据就是如此。尤其对于法学研究人员而言,无法考察司法全貌,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鸿沟,使学术研究并不具备扎实的实证基础,实务人员对理论颇不以为然,法学研究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因为事实有差异、语言亦不同,这也成了法学共同体难以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经常说,要用证据说话,但是我们更应该提倡用数据说话。如果我们不了解死刑在具体罪名中的适用数据,就无法考量死刑废除的影响和未来走向,也无法向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阐释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成效。在当前阶段,如果公开死刑整体数据仍有难度,那么至少应该更大范围地扩大死刑裁判文书的公开,或者至少全面公布不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以便公众能够从反面明确死刑核准的标准,使不核准文书的效力不仅仅及于案件本身,而成为公众对于死刑核准进行监督的标准。因为有关死刑核准程序的裁判文书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其指导意义和规范价值毋庸置疑。相关裁判文书关于不核准的理由应当尽可能详细,固然这中间存在很多细微的政策把握,甚至其判决理由可能无以言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有着种种顾虑和压力,但是至少不核准案件的公开将使死刑的负面清单、消极标准更加明确可靠。
事实上,目前死刑不核准的裁判文书在最高法院内部都没有做到完全的检索公开、内部通用,更没有在全国法院系统内统一检索,造成死刑裁量的全国统一性未能尽早实现,甚至出现已经得到解决的同样问题在最高法院内部的不同合议庭、不同时期反复争议、讨论、认定,既影响司法的效率,也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因此,应当就核准案件或不核准案件中的典型问题建立参考案例汇编的数据库,避免死刑适用标准横向、纵向的不平衡以及无原则、无规律地变动。长远来看,分步骤地公开死刑相关司法信息,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如此,死刑的裁判标准可以更为公开,死刑的判处更具有可预测性、可比较性、可验证性,从而进一步实现死刑裁量的均衡和控制,并最终实现司法对死刑的最大限制功能和削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