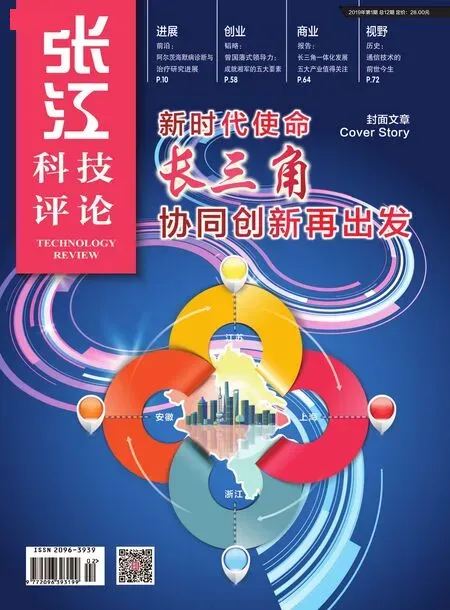共同构建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生态
■ 文/赵宇航
面向2035年的下一轮发展,长三角地区应该建立创新高地,以创新来引领长三角产业集聚,打造中国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产业。
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代技术进步,都是一个产业链的集体进步。有任何一环落下了,这一代技术肯定就进步不了。集成电路是一个系统创新,系统创新依赖于创新生态的建立。
集成电路发展依赖于系统创新
什么是系统创新?首先来看两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集成电路兴起之后,原来用手工绘制电路图的方式已经无法跟上集成电路发展的脚步,于是芯片设计开始依赖于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但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软件的运行,取决于计算机的性能,而计算机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由CPU的性能决定。于是,现实就使发展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我要设计出好的芯片,要有好的软件,但这个好的软件又要靠好的芯片来运行。幸运的是,集成电路产业突破了这个瓶颈,最后进入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有了更好的软件,就能生产出更好的CPU,并渐渐演变成为一个创新耦合系统。
这样的情况在随后的30年中几乎没有再发生过,直到最近,我们又再次面临类似的问题——机器学习。机器学习主要依赖于处理器的性能提升来处理海量数据,同时大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又大大加强了工艺、装备、材料的研制能力,推动处理器芯片的进步。如果没有更好的机器学习来提升处理器性能的话,工艺、装备、材料都无法进步。目前,这个瓶颈只是初现端倪,预计5年之内一定会发生数据无法处理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也有望形成下一个创新耦合系统。如果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创建这个创新耦合系统,就有可能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
未来,我们应该瞄准产业应用,系统整体设计和单项技术突破相辅相成,形成清晰的技术发展路径,并从应用需求牵引,立足本土和开展国际合作相结合,共建生态系统。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后摩尔时代,技术进步逐渐放缓。这个放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位面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已经无法实现18个月增长1倍了;二是单个晶体管的制造成本已经无法进一步下降,但我们的要求是它还需要下降。这种情况是不是代表着集成电路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终点?答案必定是否定的。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物联网等技术的涌现,我们可以看到今后几年,每年会生产500亿颗物联网的芯片、8 900万辆自动驾驶汽车、每人每天要用40ZB的数据量……因此,集成电路必须要突破物理瓶颈往前走。
现阶段,能够挑战摩尔定律的主流技术路径主要是4个:一是平面图形的持续收缩,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集成电路晶体管都源自图形,要使图形缩小必须用更先进的光刻机,主流将采用极紫外(EUV)光刻和图形计算技术;二是晶体管器件结构和材料创新,5纳米制程以下的器件将从现在主流的鳍式场效晶体管(FinFET)结构发展到纳米线多栅、围栅等多种结构,二维材料的应用也会加快;三是器件级多层堆叠技术,推动系统级芯片(SoC)从目前的平面到三维立体集成;四是智能计算架构革新和应用,主要采用能加快向量、矩阵等AI运算的新型存储计算。
系统创新生态的形成
说到系统创新生态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国际上集成电路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他们是怎样发展的。首先看美国的硅谷,硅谷的特点是从原创发明到产业集群。硅谷的企业数每年在飞速增长,集成电路从1955年实验室发明以来,通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了集成电路的原创群。到目前为止,硅谷已经集聚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如英特尔、苹果、谷歌、惠普、思科等公司,融科学、技术、研发、生产为一体,这就是系统创新形成的一个效果。2016年,硅谷地区共申请发明专利近2万个。
第二个地区是中国台湾的新竹,新竹是一个科学工业园区的扩展。一开始是在新竹成立工业园区,然后在新竹集聚了像台积电等一批企业,待到这些园区运行得比较完善之后,再复制到台湾的其他地区,然后再进行新的园区的扩张。这样一来,整个台湾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的规模越做越大,从新竹工业园区一直扩展到中部和南部,这也是一种整体化的发展。
第三个地区是韩国,其特点是以龙头企业牵引城市群协同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韩国的产业主要由美国、日本投资。1973年,韩国政府开始扶持半导体产业。1983年,韩国采用“政府+财团”的经济模式专注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1984年,三星公司开始批量生产64K的DRAM,并首次出口。1992年,三星公司成为世界第一大DRAM制造商。韩国半导体产业分工明确,设计、制造、加工、包装、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细致的企业分工,以龙头半导体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配套企业。目前,韩国的水原、华城、龙仁利川、平泽、安城等多个城市都有半导体产业基地,支撑韩国整体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欧洲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也独具特色,以坚实的城市工业基础支撑产品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光刻机作为芯片制造产业链中的一环,也是技术难度极高的一环,目前世界上先进光刻机基本被荷兰的阿斯麦(ASML)公司垄断。阿斯麦公司自1984年创立以来,就采用了和用户共同合作、分享利润的模式,用户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购买到产品。这种整合现有资源,并最大利用外部资源的商业新形式最终成为如今企业的新理念:开放式创新。阿斯麦公司的合作单位遍布欧洲各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工业都非常强,可以用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来支撑尖端的集成电路装备的研发生产以及持续的研究,保证了阿斯麦公司在高端光刻机领域持续拥有绝对领先地位。
上述4个地区的半导体集聚发展以及创新生态的形成极具代表性,对长三角地区建立创新生态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共建长三角创新生态
长三角地区一市三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集中度最高、产业链最完整、制造技术水平最高的区域,产业规模占全国半壁江山,代表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水平,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缩影。
正因为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所以面向2035年的下一轮发展,长三角地区应该建立创新高地,以创新来引领长三角产业集聚,打造中国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产业。这是长三角地区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下一步发展中的使命和任务。
在创新生态方面,长三角地区可以做哪些事呢?我认为,首先是共建整机牵引的装备、材料及零部件创新生态系统。以光刻机为例,光刻机已经不单单是一台设备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生态,可以解决很多集成电路制造的问题。光刻机发展能给硅片刻下更小的沟道,从而能实现在芯片上集成更多的晶体管,进而提高芯片性能,继续延续摩尔定律。光刻技术是一个技术群,将工艺、应用、设计、设备、材料合为一体。未来,我们应该瞄准产业应用,系统整体设计和单项技术突破相辅相成,形成清晰的技术发展路径,并从应用需求牵引,立足本土和开展国际合作相结合,共建生态系统。
其次是建立整合元件制造商(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IDM)的创新生态系统。IDM是半导体芯片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集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多个产业链环节于一身。其优势是设计、制造等环节协同优化,有助于充分发掘技术潜力,能有条件率先实验并推行新的半导体技术。其劣势是公司规模庞大,管理成本、运营费用较高,资本回报率偏低。早期多数集成电路企业采用这一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国的三星公司和美国的德州仪器公司,目前仅有极少数企业能够维持。现在,我国量产大的生产线都是代工厂,但代工厂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例如硅片,自主研发硅片的应用,到代工厂去认证,认证之后,代工厂的客户要进一步认证,这加大了我国国产材料进入生产的难度。从产品的角度来看,IDM是对代工的一个补充。那么,是否可以基于国产装备来探索建立一些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生产的IDM产业模式,从而丰富我国集成电路的产业形态,抢占一些重大的芯片产品的国际市场?长三角地区在加大代工规模、扩大力度的同时,应把IDM作为一种战略来发展。
第三是建立支撑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基础学科研究。随着摩尔定律物理极限的临近,我们要抓紧关注下一代计算架构和芯片形态的革命性变化,例如原来的二元逻辑运算会变成多元运算,算法将成为芯片架构的决定性因素,晶体管将从控制电子转为控制量子。这些颠覆性的变化都需要基础学科的支撑。现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有望成为延续摩尔定律的有效手段,但面临巨大的理论挑战,亟待突破基础理论和应用创新。目前,我国的整个基础研究理论都是偏弱的,而且和应用是脱节的。因此,我们呼吁能够集聚长三角的基础学科的优势,强化基础科学跨领域的创新研究,支持建立若干非营利性基础学科的应用研究机构,为形成集成电路产业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打好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