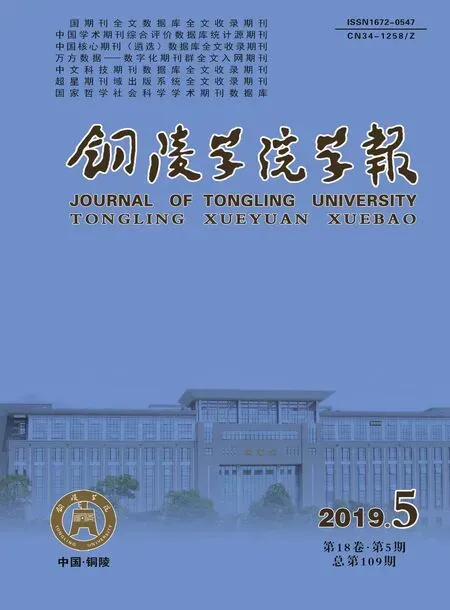《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怪诞意象的美学研究
范娇娇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主流作家,她一生中共创作了5部长篇小说,不论是第一部叩响美国文学大门的《心是孤独的猎手》,到扛鼎之作《伤心咖啡馆之歌》还是鸿篇巨制《没有指针的钟》,都描写了同一个主题,以“身体疾患隐喻精神困顿”。麦卡勒斯本人性格的执拗直接体现在了她的主要小说均执着于同性恋,“畸零人”的怪诞形象和整个作品氤氲着的“孤独”与“精神隔绝”的氛围。作家本人也在其散文《开花的梦:写作札记》中写道:“精神隔绝是我大多数作品主题的基础。我的第一部作品与之有关,几乎全部有关,并且此后我的作品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有所涉及。”[1]新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各种文学批评的影响,对麦卡勒斯的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空间诗学,酷儿理论,新批评,残障学研究等全面发展,笔者在对卡森·麦卡勒斯代表性作品《伤心咖啡馆之歌》(以下简称《伤》)的研读中发现作者笔下看似粗鄙丑陋的畸零,怪诞意向实则具有一种反讽张力,是作者精心铺陈,意图达到的美学效果。本文试图从身体残缺,情感残缺,和孤零空间来解读《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美学表征。
一、怪诞人物的美学效果
“美学”(Aesthetica)一词首先是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Alexander Baumgarten)提出。在其巨著《美学》里,他指出: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感性认识的完善即“审美的真”。英国浪漫主义第二代大诗人约翰·济慈也在其《希腊古瓮颂》中表达过同样的诗学观: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由此可见,主人公肉体的残缺并不会影响其感性认识的表达,肉体本身是一个美学概念,如马克思所言:感性的身体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的奥秘和源泉。[2]而在麦卡勒斯笔下,这些感性认识的依附体——身患残疾的“畸零”人有着他们自己独到的美学价值。
《伤》的女主人公爱密利亚小姐是个身材魁梧,骨骼异于一般女性的“怪人”。由父亲独自抚养长大的爱密利亚从父亲那儿继承来了这所杂货铺,还有酿酒厂。爱密利亚勤劳能干,她所经营的杂货铺和酿酒厂的生意都不错,“她靠自己的一双手,日子过得挺兴旺,她做了大小香肠,拿到附近镇子上去卖...她只花了两个星期就在店后用砖盖起了一间厕所,她木匠活也很拿得起来。”[3]此外,她还有着不错的医术,对妇女和孩子的疑难杂症有她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法。麦卡勒斯有意塑造了一个与小说中传统女主人公截然相反的形象,她赋予了爱密利亚以男性化的身材和男性化的社会特征。传统的身体研究视女性为亚当的肋骨,屈服于男性的统治之下。爱密利亚这种“怪诞”的女性形象突破了对女性的身份限制,是麦卡勒斯有意挑战传统男/女性别二元论,打破南方淑女弱不禁风的社会标签,试图发出自己反政治话语的尝试。而《伤》中的男主人公李蒙却是个身材矮小的罗锅,他天生驼背,长相丑陋,对于自己的家乡,过去的经历甚至自己的年龄都语焉不详。然而这样一个怪人甫一出现,就轻轻松松地赢走了爱密利亚小姐的心。爱密利亚在李蒙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同情与怜爱,视其为情感的寄托,而李蒙也正是利用自己的柔弱挥霍着爱密利亚的金钱,并最终盗走她的所有财产。实际上,麦卡勒斯塑造的李罗锅是一个社会身份女性化了的人物,他身材的娇小与孱弱,他对爱密利亚经济上的依赖无不是个被异化了的女性形象。麦卡勒斯有意刻画男女性别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矛盾与不协调,在他们的外表和作为之间,时常出现一种断裂与不和谐,以此造成的反讽张力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在美学上,作为一种感性的舒展形式,肉体以它对快感的执著而尽心的追求和对欲望真实的表达展现着审美理想最基本特征。”[4]《伤》中的残缺肉体却也是麦卡勒斯美学思想的独到载体,身体的残缺却完善了其感性的程度,以其肉体的怪诞衬托出男女主人公精神的异化,作品中的美学表征也在这种“畸零”肉体的本能欲望中得以充分体现。
二、怪诞情感的美学张力
《伤》的主要冲突也是最令读者侧目的是书中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怪诞至极的情感体验造成一种如鲠在喉的不舒适感。这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很少会有这种极端的体现。而“畸零”群像的情感冲突碰撞出了麦卡勒斯所独有的审美张力。
小说中,特立独行不善与人交际的爱密利亚对丑陋粗鄙的罗锅李蒙一见钟情后,她用尽浑身解数来获得对方的感情。对于这样一个陌生人,她愿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来换得他的逗留,保障他生活的衣食无忧。这是她向他示爱的一种方式...只有他一个人有办法取到她的银行存款和她放古董的那口柜子的钥匙。”[3]甚至为了排解他的孤独,将这间杂货铺改成了咖啡馆。如此温情的爱密利亚却对自己曾经的丈夫马文马西,一个长相帅气且对自己异常迷恋的男人毫无理由得厌恶至极,婚后三天就将他扫地出门,并使他锒铛入狱。然而当马文马西再次回到了这个南方小镇,决心向爱密利亚复仇之际,罗锅却不可救药地突破性别障碍爱上了这个压根瞧不上自己的男人,并伙同这个男人洗劫了爱密利亚的财产,无情地践踏了她的尊严。在爱密利亚/李蒙,马文马西/爱密利亚,李蒙/马文三对关系中,前者都对后者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高峰情感体验,而后者却对前者的爱深恶痛绝,并“爱”将仇报。几位主人公索取爱的方式近乎疯狂,怪诞异常。艾·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中这样描写悲剧式的爱情:“这种爱情形式开始时的特征是爱情体验的强烈性和突发性。这种形式的爱情常常被看作是真正伟大的爱情;但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强烈性和深度却表现了那些恋爱者的饥渴和孤独。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爱情形式结合下的男女在严重情况下会给人一种疯子的印象。”[5]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麦卡勒斯对这种怪诞情感的刻画是为了凸显这几位“恋爱者的饥渴与孤独”。然而试图通过爱的方式去排解孤独却忽略了自己是否具备“爱”能力,其结果往往是徒劳的。如同麦卡勒斯在小说中概括的那样 “爱情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共同体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有关的两个人身上所引起的反响是同等的。”[3]三对失败的恋爱关系强有力的佐证了麦卡勒斯的爱情观,同时揭示了爱与被爱难以平衡的本质。如前文提到的,这段奇异的三角恋爱是彼此对情欲的真实表达,爱密利亚尽管行为举止异于常人,情感内敛的她却有着对情欲的原始欲望;李罗锅冲破道德束缚与性别的禁忌,基于对“本我”的追求,激起人性深处本能欲望的涟漪,而全然忽略他人对自己情感的付出,不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骗子与无赖;马文马西因爱而不得而暴露的人性狰狞与贪婪的一面。而这一切的悲剧都源于身体残缺造成性格扭曲后对爱所抱有的极致幻想。这种对极致爱情的追求,全然不顾被爱人接受与否,甚至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令人唏嘘。麦卡勒斯用紧凑的叙事节奏,铺陈了这一整出戏剧反讽,当故事的结局之处,爱密利亚与马文马西决斗之时,她被人群中突然冲出的自己所爱之人—李蒙亲手毁掉,整个故事达到审美价值的高峰。人类尽管有着对爱情飞蛾扑火的追求,但由于爱与被爱不平衡的本质,才决定了她让人欲罢不能却又无能为力的特征。这样的一种反讽张力赋予了读者极度的审美体验。
三、孤零空间的审美体现
麦卡勒斯作为“南方”代表人物,几乎每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扎根于美国南方。但与久居美国南方腹地的本土作家不同的是,麦卡勒斯17岁时就离开了南方小镇。乔居纽约的她甚少回到故乡,因而对南方小镇的情感是复杂的,她游离在故乡之外,一方面带着近乡情怯的矛盾心绪,将感情的触角延伸到记忆深处的年少时期,寄以对故乡的遥思;另一方面,她深悟南方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及小镇人在工农文明夹击下的茫然无措。麦卡勒斯小说中的南方往往带有疼痛与疏离感,而有限的空间场所却能折射出无限的虚构想象空间,从而使小说具有政治话语的象征意义。《伤》故事设定的场所就是这样一个空间极其有限的南方小镇,与北方工业城市的欣欣向荣相比,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她是落后于时代的边缘化的小镇,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还未消失殆尽,这里的人们固步自封,孤独的疏离感始终笼罩在小镇上方。小镇主要人物的交集都是围绕着咖啡馆这个封闭空间展开的。“咖啡馆”是南方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缩影,同时也是不同群体,阶层和等级的交集的点。这样一个看似封闭的空间,却具有极强的开放性。看似原本只能容纳南方传统文化的封闭场所却不得不接纳着外部文化的侵入。在这种封闭与开放间,咖啡馆这个空间场所就被赋予了极强的张力,它不仅朝向内部更朝向外部,因而它被 “建构成了未被编码的‘越界空间’”,“打破了南方阶级社会的屏障”。[6]书中爱密利亚为陌生的异乡人李蒙所吸引,正是映射了南方一方面排斥外部对自身生活的入侵,却又因其陌生感而为其吸引的矛盾性。爱密利亚小姐作为南方小镇人,她本身代表的是个封闭的空间,这个封闭的空间被李蒙“闯入”后,原本的安全与稳定就不复存在,也导致最后将自己置于毁灭的边缘。在这样一个开放与封闭的空间悖论中,麦卡勒斯的隐喻是非常明确的,封闭的南方社会在外界空间的侵入下尚没有找到与之合适的相处模式,强行改变南方社会,以北方的现代性打破南方社会的宁静其结果往往是毁灭性的。这种空间的悖论赋予了麦卡勒斯笔下的南方以不同的色彩,它不仅仅是怪诞人物怪诞情感的纠葛的场所,同时也是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关于南方小镇居民无所适从的巨大隐喻。她笔下的南方是一个自立的诗性世界,这里的人还在追求着原始的“真我”情感。如此狭小的物理空间却被创造出了无限大的虚构世界,这是麦卡勒斯的南方为我们所打开的审美维度。审美形式不仅仅是作家对于语言与谋篇布局的规划,更是社会思潮和文化规范的体现。
四、结语
如海德格尔所言,“为了发现事物之美,我们必须让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纯然以本来面目出现。”[7]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不惜以揭示一切令人不舒服的怪诞与“畸零”来还原人性的本来面目。她是特别的,更是真实的。笔下的畸零人是真实的,情感的纠葛与冲突是真实的,被现代社会所遗弃的孤零的南方小镇是真实的,因其真实性而冲破了理性的障碍,实现了感性认识的完善,也同时在这种怪诞的叙事下赋予了作品“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