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我想跟你谈谈钱
纳塔

顾长卫,朱一南 摄01 F-X010Y044
喜欢导演顾长卫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我们这些文艺青年。
每年春天来的时候,不少人都要再看一遍《立春》,片子一开场,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重复王彩玲那段旁白:“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的心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这个女人说好听了是执著,拥有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力量;说不好听是“疯了”,摆不清自己的位置,不能审时度势。当然也许真实的生活中不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但是那种在不尽如人意、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境遇是常有的,而王彩玲依然值得羡慕——她有精神世界的庇护。
哀而不怒,怨而不伤,却让人不断回想。这是顾长卫拍电影的特点,而他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
看红了眼,看白了脸
文艺不是不谈钱,反而钱是~一个最直接的去触摸这个社会的媒介。
大约在2013年,顾长卫做起了摄影。他用微距镜头对准人民币百元钞,记录下一系列超近距离关于“钱”的细节。在此,人民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形态,就像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微观世界一‘样,纸币的每一个局部都成为一个抽象的图案。
“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钱,它就放在你的兜里,可能也放在了你的心里。这张普通而又不普通的纸,有一种难得的意味和魅力在里面。”顾长卫说。大约2013年,顾长卫上一部电影《最爱》已经上映2年,在筹拍下一部电影《微爱之渐入佳境》,他的助理回忆,虽然那阵儿事儿不少,但在晚上会看到顾长卫一个人在工作室一角的几盏灯下,沉默不语地对着人民币拍照。

币纸上卷曲盘绕的线条、数字、水印、人物形象,甚至油墨本身,以及人在纸币流通中留存的痕迹都是他聚焦放大的对象。通过微距镜头,当百元纸币上的局部有规律地呈现,那种精密的肌理让人陌生而错愕。而每幅作品也并非是随意堆砌的一组“乱码”。“X”和“Y”代表的是百元纸币上的坐标,“F”表示钱币的正面,“B”表示钱币的背面。
“这些细节有些成漩涡形的运动,有些成线状的排列,有些像极少主义的作品,只有隐约的痕迹和偶然的色点。也有近乎单色的平面,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浅淡的‘100符号。从整体上看,抽象的图案是主要的效果,‘抽象似乎是潜在的主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易英在看过这组作品后评价。
就在这张只有长约15厘米,宽约8厘米的小小红色“道场”之中,顾长卫从表面一直想方设法深入人民币的内部,从而拥有了一个无限的图像空间。一张普通的百元钞票,天天在使用它,可能从来没有人仔细观察过它的形式。偶然的机会,在微距摄影的帮助下,顾长卫才发现它有那么复杂、丰富和神秘的图样,而这种神秘性拥有让很多人将自身的命运交给它的魔力——而这也正是消费社会中人的物化。
“在拍摄时,我就一只手使劲儿摸钱,一只手使劲儿摸自己的脑门。摸着自己的心口,一直到看红了眼,看白了脸。”顾长卫描述,“究竟看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找到了一些去观察、跟它对话的角度。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有多少悲欢离合,阴晴圆缺,都是和钱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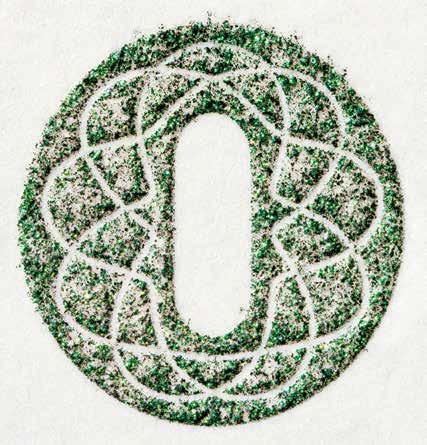

沉静的,也是有力量的
顾长卫刚来北京时特别瘦。1987年在跟张艺谋合作拍《红高粱》时,当时演男主角的姜文看见他,“特别瘦,还留着点胡子,眼珠儿基本上不动,还有一半藏在眼皮里边,我说,这是个什么人呢?他说我叫顾长卫。”
那一年是张艺谋首次执导自己的电影,就找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顾长卫担当摄影师。在上学时顾长卫的专业就很好,1982年毕业后他回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师,与陈凯歌导演合作《孩子王》,和滕文骥导演合作《海滩》,都让他获得了专业上的认可。后来有媒体问张艺谋,为什么要找顾长卫?他回答说:顾长卫是摄影班的第一名!
《孩子王》和《红高粱》的高水准表现,让顾长卫收获了1988年双料金雞奖。而在此之后,他还和张艺谋合作了《菊豆》,和陈凯歌合作了《霸王别姬》,和姜文拍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鬼子来了》等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中闪光的佳作,其中《霸王别姬》还收获了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并获得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的提名。
1994年到1999年期间,顾长卫辗转到美国好莱坞工作,先后参与拍摄了《迷色布局》、《浮世男女》以及《纽约的秋天》,之后决定回国发展。2003年,编剧李樯创作的剧本《孔雀》辗转来到了顾长卫的手里,而这也让他成就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孔雀》讲的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三人命运遭遇的故事,却让观众感受到了作为时代囚徒的人们一边生活其中、一边建构囚牢的悲怆,颇具有第五代导演那些经典电影的气质。而他也被业内称为“迟来的第五代导演”。这部电影最终得到了崇高的荣誉: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顾长卫正式以导演的身份进入公众的视野。在《孔雀》之后,他又先后推出了《立春》《最爱》,等等。
在执导的电影《立春》上映时,顾长卫曾接受媒体采访说:“从小爹妈就教育我说‘咱家的孩子没啥出息‘咱家孩子不聪明也不会来事儿,所以一直都没什么理想,老老实实随大流儿就行了。我就特别想成为王彩玲(《立春》的主人公)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经历那么多与众不同事儿。同时这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我自己做不到的并不意味着我内心深处不这么想。电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房间里的大象
100元纸钞本身没有价值,而让它产生价值的是交易。
“我有时候触摸着这张钱,会想每张纸币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经历。”顾长卫说,而他奋斗的三十年,也正是中国经济最急速变化的三十年,“我对钱的感受,是建立在一个时间跨度基础上的。这些年,人们对钱的价值,对钱的理解,交易的改变,是有很大变化的。”
这张红色的纸片包罗万象,有汗水、泪水与血水,也有蜜汁、苦水和狼奶。财富所遮掩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之困: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事实颠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之间的冲撞与拷问,让这张红色纸片的故事变得暖昧不明、前途叵测。往往,人紧捏着手里的钱,却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

“明天,你的期许或许都在这里。可能是美满,可能是罪恶,这个我说不清楚。”顾长卫说。在他的工作室中,这组摄影作品被以整面墙的大小,一幅接一幅地悬挂着。
在激荡的时代里,在跌宕的人生中,人最终能守住的财富到底是什么?這是顾长卫电影里用故事包裹的精神之问,也是这组红彤彤的艺术作品,在他的工作室空间里敲出的落槌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