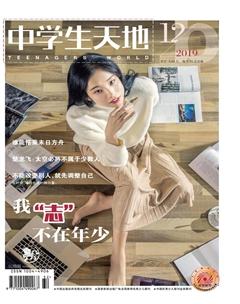楚龙飞:太空必将不属于少数人
朱诗琪

我们为什么去太空?
了解宇宙演化及现象;探寻人类和地球生物在宇宙中的地位及意义;发展太空技术,并将其运用到不同领域……
这些都是我们探寻太空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对做客本期中天会客室的火箭工程师楚龙飞来说,驱动他探寻太空的,还有一个重要却简单的原因——星空在那里。
楚龙飞是谁?他是火箭工程师,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火箭公司翎客航天的联合创始人、CEO。2014年,他辞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工作,联合创立中国首家民营航天公司。凭借着12年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学习经历和多年的火箭研发经验,他带领团队完成中国第一发可回收火箭原型机的研制和数百次飞行试验,实现中国在该领域零的突破。他相信,“太空的价值是无限的,而太空必将不属于少数人”。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航天航空产生兴趣的?
楚:我高中时喜欢看《科幻世界》杂志,其中跟宇宙太空有关的作品我都爱看。我觉得这种作品特别有吸引力,而且觉得作品中常写到的“人类一直在向往飞行”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不管是飞机、火箭,反正是能飞起来的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
记:您提到了人类一直向往飞行这件事,您的微信名“阿飞不会飞” 也和飞行有关。您本身也很向往飞行这件事吗?
楚:不仅是我,我觉得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过飞上天的想法,飞起来就代表着自由、广阔、好奇心,这些都是人类的天性。
记:所以是天性使然,让您选择了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这个专业?
楚:上高中的时候,课程基本都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高考完填报志愿时,我看见一个专业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器”这个词一听就很科幻,名字里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火箭、导弹,当时我想这里的“飞行器”肯定不是指这些传统的东西,会不会是指宇宙飞船?怎么大学还有这种奇怪的专业?我被这名字吸引,立马报了这个专业。志愿填报时可以选好多备选专业,但我就只选了这一个。
记:真正接触了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后,觉得它跟您想象的一样吗?
楚:很不一样。本科阶段学的那些课,其实看不出跟飛行器有什么关系,基本都是材料、力学、高等数学、化学、物理等基础课。到本科快毕业时,我才接触到一些跟飞行器,比如飞机、导弹、火箭相关的专业课。除了课程外,学校还有一些航模协会、小飞机协会和创新基地。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动手做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航模。另外就是可以去大型的研究所、研究院、工厂参观实习,看看飞机是怎么做出来的,行业是怎么运作的。
记: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下设众多不同的研究方向,比如导弹、航天飞机等。您为什么偏偏把火箭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方向?
楚:真正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的方向应该是在我博士快毕业的阶段。其实我博士学的是飞机设计方向。但学校里的一些课题、项目,大部分都跟火箭相关。这两个专业虽然应用领域不一样,但其中的分工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北京大部分的研究所都和导弹、火箭相关。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毕业前跟着做了长时间的运载火箭研究项目,所以那时我也没怎么想,就顺理成章地去了火箭研究院,把火箭研究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博士毕业后,您先是在火箭研究院工作了3年,之后辞职成立了一家民营航天企业。当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火箭工程师和民营火箭公司联合创始人这两个身份对您来说带来了什么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楚: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会发展得很好,加上自己又擅长做这个事儿。另外,自己成立公司,可以比较自由地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也有一些创新的优势。
至于两种工作模式有什么区别,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更像是一台运转特别完好的机器的一部分,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这套系统就是非常可靠、高效率的。在研究所里,一个队伍里有几十上百号人一起研究。但是创业就得全靠自己摸索。最开始,我们团队只有三五个人,现在才有20多人。但是人少也有好处,我们可以把全部的事儿闭环在十几个人的小团队里,比如,我做完设计,画完图,就得自己到车间去管制造、加工、安装、测试。在接触不同环节的过程中,我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快速成长。
记:创业初期一定非常辛苦,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据说您和您的团队是在江苏省高邮市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两室两厅里生活、办公。创业初期那段时间,有没有发生一些让您难忘的故事?
楚:迫于当时的条件,高邮试验场里的储箱、管路、台架,甚至一砖一瓦都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高压气瓶的货车自己修,路也自己来建。因为试验场在京沪高速的旁边,我们在那立了一个类似路标的东西,放了三个箭头,分别指向北京、上海、太空。箭头上写着北京908千米,上海335千米,太空100千米。大家觉得太空离我们特别遥远,但其实跟高邮到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绝对距离比起来,太空其实反而离大家近得多。大家觉得它远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交通工具。
记:到现在为止,您一共完成了上百次不同状态下飞行的相关试验,其中最让您难忘的是哪一次呢?
楚:最难忘的是T3火箭成功实现自由飞行的那次试验,那是在2018年1月。这算得上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因为在中国,这算是第一次有一个火箭动力的飞行器离开地面,并且安全回来。还有就是2014年10月一个深夜,我们第一台发动机点火成功时,发动机后面发射出马赫环,听着轰鸣声,我确实被震撼到了。虽然我学习航天航空10年,在体制内工作了两三年,但在辞职创业之前,我连火箭发动机点火都没见过。
记:今年8月,您和您的团队又进一步进行了中国进入飞行试验以来规模最大的可回收火箭发射回收实验,还向广大观众进行了直播。这一次飞行实验和您之前的实验相比,你觉得最大的突破在什么地方?
楚:这次的火箭有8米多高,接近3层楼,重量达到了1.5吨,这和我们2018年的那个300多千克、不到5米高的火箭相比,无论是高度还是重量,都提高了许多倍。另外,原来的T3火箭最多能飞10米左右,而这次火箭能飞300米左右,飞行高度比之前高了将近30倍。简单地说,就是火箭变得更大,飞得更高,对发动机要求更高,所以实验更难,但是它技术的进步也就更有意义了。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次敢做直播。我们正在影响更多人喜欢航天。有些人觉得航天就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不是这样,航天和每个人都有关系。
记:前面提到您和您的团队专注于研究火箭发射后的回收功能。我们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回收火箭呢?
楚:其实大家之前都是被误导了。你想一想,有没有人问过“手机为什么要充电”或者“为什么没有一次性汽车或一次性飞机”这类问题。为什么火箭发射完就必须得摔坏或者不用,这可是价值几个亿的产品呀!生活中高价值的东西当然是使用的次数越多越好。之所以之前火箭没有被回收,只是因为这件事有难度。火箭开始出现时,工程师和科学家就已经在思考怎么解决火箭重复使用的回收问题,只不過实现起来很难。一发火箭几个亿,发射一次就损耗,这严重限制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火箭回收和重复使用能够从根本上降低发射成本,这是必然的趋势。
记:火箭回收工作主要有哪些流程,涉及到哪些不同的专业领域呢?
楚:火箭回收其实和火箭研发所涉及的专业是一样的。说得具体点,动力专业的人才给火箭设计发动机;结构专业的人才计算火箭能承受多大力量,着陆腿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另外还需要有人能画设计图,画完后送到工厂生产加工;还得有人管理材料、工艺;在火箭飞行控制过程中,得有控制系统、电气系统,就需要有人能做电路板,做控制算法和代码。所以,电气、控制、算法、结构、动力,还有弹道、制导导航、地面保障等专业人才也缺一不可。
前面说的这些专业内容可能跟中学生,或者是刚上本科的一些大学生所学的课程没有特别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这些其实都来源于基础课,比如力学分析、弹道计算的大部分技术基础来源于物理;发动机燃料怎么燃烧,能产生多大推力等是与化学相关的内容;火箭发射卫星到了轨道后,怎么绕着地球转,这个卫星覆盖性是什么样的,还会用到地理知识。我们中学学的这些知识,其实对今后的研发都是很有用的。
记:您觉得我们研究太空的意义是什么?
楚:太空是重要的,是有用的,它的价值是无穷的。不管是在军事国防领域应用的重要战略地位,还是卫星火箭航天技术已经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帮助和改变,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芯片、吸尘器、气垫鞋等都拥有太空技术带来的价值。未来的太空旅行可能会像飞机、高铁、互联网、自动驾驶一样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
记:也许现在正在看这篇专访的中学生未来就会成为像您一样的太空发展参与者、领航者。您能否从自身经历出发,给他们提供一些实际的建议?
楚:可以选择看一些纪录片或者电影,比如 BBC的《太阳系的奇迹》《超级工厂》。《超级工厂》里就有讲巨型火箭是怎么设计、生产制造、发射的。这些纪录片会让大家对整个宇宙,以及火箭、卫星建立基础认识。因为我觉得研究航天航空,必备的专业技能是第二层面的事,首要的是从全局上了解太空。
我推荐一个游戏给同学们,叫“坎巴拉太空计划”。在游戏里,你的角色就是一个航天工程师,你要运用各种零部件去设计航天器,完成航天任务。游戏里会涉及火箭该怎样设计,飞船该怎么造,轨道怎么设计,什么时候发射火箭,发射过程中要怎么处理等专业问题……专业门槛没那么高,但趣味性很强,会一步步引导你更好地了解航天任务和飞行器。
整理:金文先 吴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