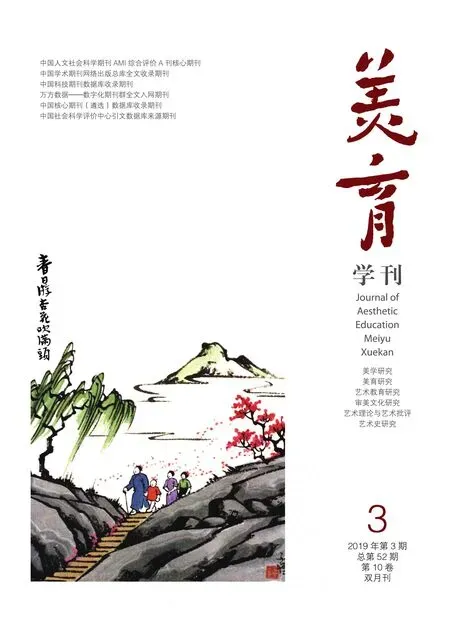试论儒家艺术理论的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
李心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在今天的儒学研究当中,关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政治学说等的研究比较充分。相比较而言,关于儒家的艺术思想、儒家的艺术理论,虽然也有一些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学家和儒学家在对其进行研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有一点处于边缘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至少没有得到研究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学者们足够的重视。
对于儒家的艺术思想、艺术理论,笔者有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对于儒家艺术思想、艺术理论的评价,过去人们一般会说儒家的艺术思想、艺术理论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说法貌似给予儒家的艺术思想、艺术理论比较高的评价,但实际上是太平淡、太空洞化、太套话化了,并没有清晰地阐释清楚儒家艺术思想、艺术理论在儒家学说当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地位,其与儒家整体思想、学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等问题。我们认为,儒家的艺术思想、艺术理论恰恰是儒家学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儒家那些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学说,假如离开了儒家的艺术思想,是根本说不清楚、说不完整、说不透彻的。
儒家的艺术理论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儒家的艺术理论、艺术思想,当然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十分丰富的艺术理论观点。但是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观点,还是要到孔子的《论语》当中去寻找。走进曲阜的孔子研究院,一进大门,就能看到两个牌坊,第一个牌坊上面写着“志道据德”,第二个牌坊上写着“依仁游艺”。这两句短语,出自孔子《论语·述而》如下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中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理念。其实,这也是儒家艺术理论的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理念。这里讲的是志道、据德、依仁,最后要“游于艺”。就是说,儒家的人格养成和道德修为,不经过“游于艺”的阶段,是不完整的,甚至达不到它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的儒学研究,以后应该更多关注儒家的艺术思想、艺术理论的研究。当然,《论语·述而》中所说的“游于艺”的“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是有区别的,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但是,一般认为,这里所谓的“艺”,包括当时所说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当时所说的“六艺”里边,包括今天被称之为音乐和书法的“乐”与“书”,这都是与艺术有关的。总之,对于儒家而言,不管是“道”还是“德”,还是最核心的理念“仁”,都离不开“艺”来提升完善它的境界。
儒家另外一个重要的艺术观念就是《论语·泰伯》所记述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诗使人兴起、感奋,自觉地进行修身,但立身的根本却在于礼,即“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然而,仅仅掌握了君子所必备的礼的修养,对于一个“成人”来说,仍不完整、全面,还需要经过最后一个阶段的陶冶,即通过对“乐”的学习掌握,将诗与礼乐融会贯通,才能说最后完成了一个人的培养过程。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所说的“若臧仲武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意义与前文所说基本一致,也是把礼乐的修养的养成作为“成人”形成的最后阶段。之所如此,是由于这种乐的修养是在确立了礼这一立身的根本的前提下得以养成的,所以乐实际上是把礼这种外在的制约升华为内在的需求,由理性的强制变为感性的愉悦,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无疑是人的生存境界的升华。总之,就是把这个“乐”即今日所谓艺术[注]拙作《中国三代艺术的意义》曾论及先秦时期所使用的“乐”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一词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概念与今日所说的‘艺术’一词意义相当接近。这就是先秦时期所使用的‘乐’这一概念。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就因为音乐的享受最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郭沫若:《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3月,第163页。)应该说,三代所谓‘礼乐’中的‘乐’,是可以包括所有艺术形式在内的,或至少可以指称以音乐为代表的各种艺术样式吧。”见李心峰:《艺术学论集》,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342-343页。,看作是人格的最后的完成。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言,最后要成于“乐”。只有“成于乐”,这种人格的养成才能真正达到完整,真正达到完善。[注]徐复观先生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看作是孔子把“乐”放在了比“礼”更高的位置上。他说:“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所以他说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话。”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页。这既是儒家最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是其核心的艺术思想。就是说,儒家的“礼”或“仁”,离开最后的“成于乐”,是不完整的,也不能最后完成通往仁学和礼学的道路。
儒家艺术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礼乐一体、仁美统一的思想。孔子继承周代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思想,提出自己的礼学思想体系,一个重要特点是用他所创立的“仁学”来阐释和补充他的礼学。这种仁学有两个要点:一是政治上主张推行仁政,二是在个人伦理道德上提倡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人”。他认为,只有实行了仁,才能推行其理想中的礼乐制度。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孔子经常将礼乐并提,把礼乐作为衡量天下有道无道的一个标志:“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在他看来,礼乐与国家政事密切相关、相互作用:“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
而对于礼与乐的关系,孔子严格按照是否合乎礼这一标准评价“乐”的价值和人们所从事的乐舞活动。他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是由于在他看来《关雎》所表达的情感符合于礼;他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则是由于季氏做为士大夫违背礼乐等级制度,僭用了天子才能用的“八佾”的乐舞。他讥笑“三家者以《雍》彻”,即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祖时唱着为天子而作的《雍》诗来撤除祭品这一越礼行为时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
由于孔子所继承和竭力维护的礼乐思想和制度,是行将成为历史的周代奴隶主贵族阶级思想制度的反映,这使孔子在艺术上往往体现出一种向后看的保守性。他理想的艺术是旧时代的雅颂之声、《韶》《武》之乐,而对于一些民间的或新兴的乐舞艺术,则持一种厌恶或排斥的态度。比如“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对郑国的新兴的、民间的音乐取抵制的态度。“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则说出了他排斥郑声等的理由。《孝经·广要道》记载的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集中地反映了孔子对礼与乐以及礼乐与政治伦理的密切关系的思想。
儒家艺术理论再一个重要的思想是“中庸”“中和”的艺术观。“中庸”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色。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论语·雍也》)所谓中庸,也就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意思。这一思想用之于艺术领域,便是对艺术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进行调合,达到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不只乐与礼应该和谐统一,礼乐与治国安民的国家政事应该和谐统一,而且个体与社会也应该和谐统一,即所谓“群”(和而不流);不只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美与善应该和谐统一,即所谓“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而且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必须适中适度、无过无不及,即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记·经解》曾引孔子的话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可以说相当典型地表达了孔子中庸的礼乐思想。早在孔子之前,人们对于艺术之“和”便有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孔子中庸艺术观既是对此前中和艺术观的继承,又是对它的改造和发展,并成为中国古典艺术论的基本观念之一。
孔子关于艺术功用的系统论述,也是儒家艺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于艺术功用的论述,在其艺术论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他对艺术功用的看法,与其礼乐艺术观是密不可分的。孔子关于乐要符合于礼,礼乐要为国家政事、伦理道德服务的思想,实际上便是孔子对于艺术功用的一个重要规定。除此之外,他还讨论了艺术所具有的其他功能作用。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提出诗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说提出了一个相当系统的诗歌艺术的功能理论:所谓兴,在这里不是指作为诗之手法的“引譬连类”之兴,而是指作为诗之功能之一的感发志意、使人兴起修身的“兴”。所谓观,讲的是诗对于认识社会、考察民风民俗、民心向背的认识作用;所谓群,就是讲诗能使个体的人与社会相沟通;所谓怨,则是指“怨刺上政”。
与孔子礼乐观和艺术功能论相联系,孔子还大量涉及艺术的文与质、美与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对这一艺术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思考。首先,孔子的理想是上述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达到高度的统一状态。他论君子时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孔子关于内容与形式应高度统一的理想在他对《韶》《武》的评价中充分表现出来:“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对于《韶》的尽善尽美与《武》的尽美未尽善的比较,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他实际上把艺术作品的美与善、形式与内容明确区分开来,看到艺术的形式之美既有与内容之善相统一的情形,也有不相统一的情形。而不相统一的情况,有时是内容之善胜于形式之美;有时则是形式之美胜于内容之善。不管怎样,孔子已经看到了形式对于内容、美对于善的相对独立性,对于艺术理论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应该说,当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发生矛盾时,孔子的基本态度仍是反对形式压倒内容的形式主义。“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可见他是极力反对对于礼乐的形式主义理解的。他常常表现出一种重视内容的倾向。如他评价《诗》时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便完全是从内容角度评论的。有时甚至认为形式只要足以表达意思就可以了,即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他的中心思想,还是主张内容与形式、美与善高度统一的尽善尽美的境界。
由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艺术理论,徐复观先生将其概括为“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1]。我们很认同徐先生的这一概括。在笔者看来,儒家的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理论或艺术精神,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西方近代康德所代表的艺术观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近代以来的艺术观就是把艺术与生活割裂开来,把艺术看作一个单独的自律的小宇宙,追求它的纯粹性,追求它的内在的自身的发展动力。而儒家的艺术思想不是把艺术与人生相割裂,而是要把它沟通起来,相互交融。另外,儒家的艺术思想就是礼乐交融的思想,礼和乐之间有它的内在的一致,当然也有区别,但是礼离不开乐,乐离不开礼,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观点。这一思想,对于西方近代以来自律论的艺术观点是一个巨大的反拨,而且西方近代以来的自律论的艺术观在今天来看,它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和解构这样一种康德式的自律论的、纯艺术的艺术观念。但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反思和解构它呢?可以说,儒家的礼乐交融的思想,是一种可喜的、必要的矫正和补充,是一副十分有效的解毒剂。
回到儒家艺术思想、艺术理论的价值与意义上来,可以认为,儒家的艺术思想、艺术理论,包括上述的这些基本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来看今天的艺术观念、艺术理论,越来越强调艺术与人生的相互的沟通交流,也就是我们古代所倡导的艺术人生化、艺术生活化,同时也是人生艺术化或者是生活艺术化。这一点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甚至具有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也可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正如徐复观所言:“由孔门通过音乐所呈现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善(仁)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的最高境界,对于目前的艺术风气而言,诚有‘犹河汉而无极也’之感。但就人类艺术正常发展的前途而言,它将像天体中的一颗恒星样的,永远会保持其光辉于不坠。”[1]
日本著名的比较哲学和比较美学学者今道友信在他的美学代表作《东方的美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读一读《论语》就会发现,它的内容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关于艺术的大文章,人们果真是理解的吗?”[2]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论语》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都在讨论艺术,而且是讨论艺术的“大文章”!这个观点我们认为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在今道友信看来,我们所说的礼乐的“乐”属于艺术的范围没有问题,在他看来,“礼”也属于艺术的范畴。因为这个“礼”,其实就是礼仪、典礼。而所有的典礼,他认为都是生活的艺术形态,是一种“典礼艺术”。假如我们认同他的这一观点,就可判断他有关《论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讨论艺术的说法所言不虚![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也指出:“对礼的基本规定是‘敬文’或‘节文’。文是文饰,以文饰表达内心的敬意,即谓之‘敬文’。把节制与文饰调和在一起,即能得其中,便谓之‘节文’。在多元的艺术起源说中,‘文饰’也正是艺术起源之一。因此,礼的最基本意义,可以说是人类行为的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物。”(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总而言之,我们研究儒学,研究孔子,研究《论语》,对于其中的艺术思想、艺术理论理应给予更多的重视、更系统的研究、更深入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