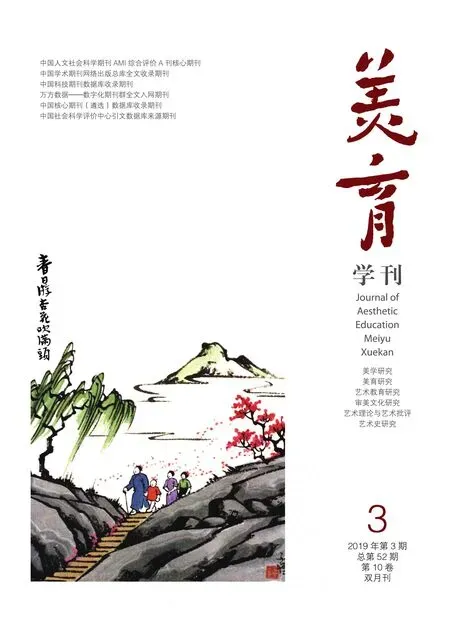东汉时期佛教美学意蕴的初始酝酿
王振复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所谓中华佛教美学意蕴的初始酝酿,发生在东汉时期,是指它最初的积渐过程及其结果。自大致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于中土,经东汉约二百年初传,其广度与深度,都处于初始阶段而难称普及与深入。佛教先是在朝廷、王族与极少数士子中间传播。这是在中印异域文化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充满艰难与误读的人文“对话”,彼此深感惊奇、困惑、恐省而又同情。
佛教的最初入传,开启了中华文化、哲学与美学的剧烈嬗变。当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学为浮屠”的贵族楚王刘英“信佛”,当第一位初信佛教的帝王汉桓帝刘志“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裴楷传》),当严佛调作为第一人“出家做和尚”[注]《晋书》卷九五《艺术·佛图澄传》载“王度奏章”云:“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但临淮(今属安徽)严佛调于汉灵帝末年赴洛阳,与沙门安玄共译《法镜经》,为第一位汉籍僧人。只是汉末未传译佛经律部,估计严氏“出家”未受“具足戒”(比丘戒)仅思想信仰而已。又,严佛调参与译经为汉光和四年(181年)。之时,人们也许始料未及,这种初始的剧变,已经在酝酿之中,仿佛能够让人听到它那奔腾而隐隐涌动的潮声了。
一、禅定“守意”(寂)与般若“本无”(空)之“乐”
这主要始于安世高所译介之禅数学与支娄迦谶所译介之般若学。安译禅数学,属印度小乘一系。禅,指禅定禅观;数,指数息数法,皆重于身心修持。吕澂云:“所谓‘数’,即‘数法’,指毗昙而言。”[1]禅数学是禅学与毗昙学的合称,二者在身心入定的修为上,具有共通性。
安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云:“安般守意。何等为安?何等为般?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念息不离,是名为安般。[注]《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一,安世高译,《大正藏》第十五册,P0165a。此指修持者控制呼(出息)吸(入息)而禅定,便是《安般守意经》所谓“从息至净是皆为观,谓观身相堕,止观还净,本为无有”[注]《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一,安世高译,《大正藏》第十五册,P0167c。。
这一佛教修为“常法”,似乎与审美无甚联系,其实并非如此。早在印度佛教入渐中土之前,先秦儒、道两家,作为中华先秦美学的主要学派,一主“有”的审美,体现于道德人格及其艺术等(儒),如《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一主“无”的审美(道),通行本《老子》所言“致虚极,守静笃”与《庄子》的“心斋”“坐忘”之说,都指审美过程中主体审美心灵以“无”为美这一问题。“有”与“无”的审美,起于经验、形下又上升为超验而形上,从而达于哲学意义的本原本体。
仅就道家“无”的审美而言,审美的发生、过程与境界,主体必瞬时忘其功利荣辱,收摄纷散之心而刹那凝神观照,它是对于儒家所主张的“俗有”之境的挥斥。《安般守意经》的“数法”“禅数”,其要旨在于通过数息入定,“眼不观色,耳不听声,鼻不受香,口不味味,身不贪细滑,意不志念,是为外无为。数息相堕,止观还净,是为内无为也”[注]《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一,安世高译,《大正藏》第十五册,P0169c。,从而达成“六根清净”,拒绝世俗美的诱惑,破斥俗有、超越道无而入于佛之空幻。这种不同于儒“有”、道“无”的修持方式,蕴含着第三种“审美”因素,为吾皇皇中华旷古所未有。
斥有、祛无而守空(守意),是《安般守意经》关于“寂”(空)之审美的根本点,在于“断内外因缘”、跳出轮回而得趣于禅定之“乐”。《安般守意经》有“四乐”说:“守意中有四乐。一者知要乐;二者知法乐;三者知止乐;四者知可乐。是谓四乐。”[注]《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一,安世高译,《大正藏》第十五册,P0164a。其须经初禅“离生喜乐地”,二禅“定生喜乐地”,三禅“离喜妙乐地”,四禅“舍念清净地”。以此“四禅”(“四乐”),对治于俗世“四欲”[注]《法苑珠林》卷二所谓“四欲”,指“情欲”“色欲”“食欲”和“淫欲”。,而得“乐”必“非身”。所谓“非身”,须作人之肉身的“不净”之“观想”。所谓“观想”,比如眼见肉身肥硕,当念死尸肿胀;白净肌肤,只当是一副白骨;浓发黑眉,看作朽败发黑;朱唇明眸,意想腐血紫赤。凡此,是对人之肉身欲望的断然拒绝。这种“四乐”,与审美相构连,并非指五官的快感,亦非精神臻于道无之境之本原本体的美感,而是消解五官快感与道无之美感时所实现的那种精神状态与境界,由禅定禅观而臻于空寂之境。
破斥世间“有”“无”,关键从缘起说领悟世俗的苦厄与烦恼。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即苦、集、灭、道——人生本苦,苦必有因,苦可解脱,解苦之途,成为其教义的基础。人生本苦作为四谛说的逻辑原点,惟在彻底渲染人生之苦,才得凸显从一切苦厄拔离的必要,惟有离苦才能得乐,离苦即得乐。
“守意”,不使心神纷散而染机巧与分别之心等,有类于尚“无”而瞬时审美的凝神观照,即物我两忘、主客浑契、排除杂念、分别与功利等,进入主客一如之境。而禅观之“守意”在“寂”,瞬时的凝神审美在“无”,两者“异质同构”。
佛教“守意”又称“非身”,即对肉身作“不净”之观想,做到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受香,口不味味,身不贪细滑,意不志念,对肉身及其欲望进行彻底的精神洗涤与否弃。否弃人的肉身和五官欲望的真实性,肯定“禅数”“禅观”精神(念)的真如性,则入定于禅乐之境。
其“美感”的“洪荒之力”,真如释道安《安般守意经注·序》所云:
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2]
“寂”作为“禅观”“神通”之境,不可思议,其空寂之伟力,无以复加。从美学角度看,禅寂这一“美感”体验,无疑显得更深邃、更精微、更恢弘,“美”得令人惊心动魄。
支译佛典的历史与人文功绩,是将印度大乘空宗一系的般若思想,初译于中土。其般若之学,从此参与了中华古代美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并施加影响于深远。
支译般若学,以缘起说、因果论为其基本教义,在这一点上,它与安译禅数学无有多大区别。然则,安译小乘学重在宣说“业感缘起”而高标“人无我”即“非身”说,倡言“安般守意”。大乘空宗般若学,主张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称说“人无我”而“法无人”[注]称“无我”。在“有我”与“无我”问题上,印度小乘之学内部曾有论争。部派佛教犊子部,以“不可说之补伽特罗(pugadala)”为“我”。此“我”,意为“常一不变”,而世间万法因缘而起,刹那生灭,故性空。“无我”之“我”,不可称为“五蕴之我”,亦并非“离五蕴而存有之我”。经量部提出“胜义补伽特罗”说,此指“真我”,与犊子部所持不一。“无我”说的逻辑是,正如《中阿含经》卷三十所言,“若见(引者:现)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既然万法五蕴集聚,空无自性,那么,诸法性空,即是“无我”。,人、法二空而立“无有自性”(空)之说。
对于中华美学而言,般若与佛一样,是一种全新的人文哲学理念。般若,梵文prajā音译的简称,亦称般若波罗蜜,意译为“智度”,“觉有情”与“自觉觉他”之谓,意即通过“菩萨行”,以般若之智成就空幻而普度众生,大不同于中华本土所言“智慧”,而是一个全新的佛学、哲学与美学范畴。般若学的译介,遂使中国美学从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它的思维广度,加深其思想深度。
先秦亦有“智慧”说。《论语·雍也》记孔子言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即原始儒家所倡言的人生智慧。孟子则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3]。意谓人生的最高智慧,在于审时度势。纂编于先秦战国中期的通行本《老子》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将儒家的“智慧”说贬得一无是处,推崇其作为最高“智慧”的“道”。然则无论儒、道的思维与思想域限,都在此岸世间,与入渐之印度佛教的智慧观及其美学意蕴迥然有别。般若智慧,一指圆融涅槃之境,洞见佛性,烛照实相,所谓照彻名智,解悟称慧;二指圆成涅槃的方式途径。解粘而释缚,涤垢以离尘,出离生死、登菩提岸而转痴迷者,佛教曰智慧,简言为“空”。
众生心总是囿于世间“持想”而“想入非非”,是世俗芸芸堕入虚妄深渊的一大病根。般若学提倡“无想”,此《道行般若经·道行品》所言“不当持想”,指心识的无所执著,以“无想”为般若之智。“不当持想”,亦即“无生”,指“心无所动”而无有贪求,此则为净观。“无想”即“无相”,指不落名言,斥破虚妄的现象世界。这一实现,便是佛教的“无得”“无著”[注]见《道行般若经·强弱品》“经法本净,亦无所得”。。将世俗意义的事相、形象、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美,加以彻底扫除,从而做到心灵与境界“空诸一切”,一种被称为“般若性空”的“美”,在否定之时被肯定。
般若性空之“美”与“美感”究竟何以可能?很难对其进行知识论意义的定量定性分析,惟在彻底否定世俗分别、功利、生死、悲喜的念想与真假、善恶、美丑之时,才可被观想领悟。无论“诸色”(一切事物现象)抑或主体、主观(痛痒、思想、生死、行识)所引激的苦乐与美丑等,皆处于“无住”之境,即是所谓“无著”“无缚”“无晓”,“无所生乐是故为乐”,“是为乐无所乐”[注]《道行品第一》,见《道行般若经》卷一,《大正藏》第八册,P0428c。。
般若学教义亦讲“自然”,指主体无著、无缚、无知即空。对于痛痒(触)、思想(念)、生死与行识而言,所谓“过去色”“当来色”(未来色)与“现在色”,一切皆空。在先秦老庄美学那里,自然作为原朴之美,是道是无。这里所谓“自然”,是借老庄之言来说般若空智的一种新的“美感”体验,指性空这一般若智慧,以本土“自然”“误读”佛教之“空”。
般若“自然”之“美”及其“美感”,《道行般若经·清净品》又以“清净”二字加以概括。“舍利弗白佛言:清净者,天中天!为甚深,佛言甚清净。舍利弗言,清净为极明。天中天!甚清净。舍利弗言,清净无有垢。天中天!佛言甚清净。舍利弗言,清净无有瑕秽。天中天!佛言甚清净”[注]《清净品第六》,见《道行般若经》卷三,《大正藏》第八册,T08,P0442a。;清净,离弃尘世之物欲与烦恼,以智慧的“清净”为至要,归根结蒂一句话,“清净者,天中天”。
佛教所谓“天”,有最胜之光明、自在与清净之义,亦称“无趣”。趣即趋。佛徒所向往的菩提,最胜、最乐、最善又最为妙高,故称“天中天”。其“美”的庄严与崇高,达到“清净”的极致。佛教入渐中土之前,中华本土,惟有道家所言“清静”而断无“清净”一词。清净作为佛家语,有无垢、空寂、明觉而无所执著义,此《大智度论》所以说“惔然快乐者。问曰:此何等乐?答曰:是乐二种。内乐涅槃乐。是乐不从五尘生。譬如石泉水自中出不从外来。心乐如是”,而“能除忧愁烦恼心中喜欢,是名乐受”[注]《大智度初品中放光释论第十四之余》,见龙树《大智度论》卷八,《大正藏》第二十五册“中观部类”,P0120c-0121a。。
二、得风气之先,创造中华佛教艺术审美新品类
东汉佛教初传、佛经初译时,佛教美学意蕴的初始酝酿,大凡体现于三大方面。
先说佛塔佛寺的新建与佛像的绘塑,得风气之先,创造了中华佛教艺术审美的新品类。
《四十二章经·序》有云,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感梦遣使求法,“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言之更详:“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象。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4]
这里,暂且不说明帝感梦遣使求法记载的真实性问题。关于中华佛塔佛寺的创建源于印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长阿含经》第四《游行经》称,传说释迦圆寂,其舍利(灵骨)分为八份,建塔以为供奉。据《八大灵塔名号经》,八大佛塔分别建于:迦毗罗卫城蓝毗尼(佛陀诞生处)、摩揭陀国尼连禅河畔(佛陀成道时沐浴处)、波罗奈斯城鹿野苑(初转法轮处)、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说法处)、曲女城(说法处)、王舍城(说法处)、广严城(说法处)、拘尼那揭(说法处)。《大般涅槃经》亦有相似记载。渥德尔云:“这些早期宝塔也许不过是半圆形土冢,有点像史前期的坟墓,非常不同于后来的砖石高塔结构。”[5]塔,梵文写作stupa,巴利文thūpo,汉译“窣堵坡”“塔婆”,本义为“累积”。“窣堵坡”的最早型式,是“一个坟起的半圆堆,用砖石造成,梵文名安达(anda),其义为卵,其下建有基坛(Mēdhi),顶上有诃密迦(Harmika),义为平台,在塔周一定距离外建有石质的栏楣(vēdika),在栏楣的四方,常饰有四座陀兰那(torana),义为牌楼,这就构成所谓陀兰那艺术”[6]。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保波尔附近,有山奇大塔,始建于公元前273至前232年的阿育王时代。塔四周建石质栏楣。栏楣四方,饰以牌楼者凡四,亦称天门。其形制,于两石之上戴以柱头,上横架上、中、下三条石梁。石梁中间以直立短柱相构,其上饰以对称性浮雕,多取材于佛陀本生故事或佛传故事。在犍陀罗艺术来临之前,当时印度尚未受到希腊神象雕塑艺术的影响,在当时的佛教理念中,佛陀如此庄严而伟大,凡胎俗子,如果直接面对佛陀形象,便是冒渎神佛。因而,雕刻佛陀形象在当时不被允许。即使雕刻佛陀说法情景,“也只是弟子围列左右,中央却不设佛体,而留下一棵菩提树或莲座算是象征”[注]参见拙著《建筑美学》“塔的崇拜与审美”有关章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台北)地景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
印度佛塔起源悠古,它是中国佛塔的“印度元素”。印度部派佛教时期,相当于中国西汉,尚无成文佛经,亦未造佛象,仅以佛塔为崇拜对象。印度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时代(78—123),佛教隆盛,遂逐渐出现成文佛经,其大多书于桦树皮与贝叶之上。公元一世纪后期,印度出现原始佛象。据考,后人曾从地下发掘迦腻色迦王时古钱币一枚,上刻镌释迦佛象,四周有一“佛”字,以希腊字母拼写。在今阿富汗西部(毗邻于古印度的迦尔拉巴特),有佛塔遗址发现,年代约在公元一、二世纪,证明此时印度佛塔等艺术,已向外传播。
但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华传小乘,迄今尚无直接证据称其同时携来小型佛塔等佛教艺术品。这不等于说,汉明求法使者归来时肯定未将塔寺理念等输入中土。鉴于印度佛陀圆寂未久便有塔的建造及其崇拜,且此后曾极为繁盛,有佛塔“八万四千”之传说。因而印度佛塔理念较佛象为先传渐于中土,是可能的。似乎可以说,《四十二章经·序》所言“登起立塔寺”,要比《牟子理惑论》所谓“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等记载,显得更为真实些。
正如中华佛教一样,佛寺佛塔的建造,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中国化”之路。
方立天曾说,所谓佛教“中国化”,既是中华佛教学者从大量入传经典文献中精炼、筛选佛教思想、制度和修持方式的结果,又使之与中土固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宗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特征。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后,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傣族等地区佛教三大支,是佛教的汉化、藏化和傣化。[7]
印度佛教初传,在佛寺佛塔的建造上,必与印度原型大异其趣,首先是其哲学或文化哲学及其美学的“中国化”。
就佛塔佛寺而言,“据说,我国之塔,当以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所建之洛阳白马寺为最先”[8]。“当初白马寺的主题建筑,为一方形木塔。塔据寺之中心位置,四周廊房相绕。稍后,三国时笮融在徐州建造的浮屠祠,亦建木塔在祠域内”。这一塔例,已与印度佛塔大为不同。其舍去了印度山奇大塔的四座天门牌楼,改为木制结构,且建于寺院中庭。这一合建形制,源于印度“支提”窟。“支提”建于石窟或地下灵堂之内,称“塔柱”,以供佛徒绕塔礼佛。在中土,原先的塔柱,已演变为中土的方形木塔,窟殿已由地下升到地面,改制成脱胎于中国古代民居、宫殿一般形制的寺了。由此开启了寺塔彻底“中国化”的文化与审美历程,继而寺、塔分建,将塔建于寺外,或仅建寺或仅建塔。
据南朝齐王琰《冥祥记》所言,《牟子理惑论》称“时于洛阳西雍门外起佛寺”,指的就是洛阳白马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有云,“白马寺,汉明帝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这大约据后人传说而追记,连同前文所引刘敦桢所言,其历史真实性待考。然则佛寺包括佛塔的“中国化”,确是必然早晚要发生的文化和美学事件。
金文有寺字,刻于沃伯寺簋,写为上“止”(趾)下“手”结构。寺字本义,手足之谓。供人使唤者,寺。《周礼·天官·寺人》有“寺人”之记,其注云:“寺之言侍也”。《六书正》卷四称,“寺,古侍字”。《诗·大雅·瞻仰》有“匪教匪诲,时维妇寺”的吟唱,以“寺”与“妇”并提。从秦代始,宦侍者所居官舍称为寺。西汉景帝中元六年设太常寺一职,为九卿之一。北齐亦设太常寺。又有作为中国旅舍原型的所谓鸿胪寺,始造于秦。秦至汉初称典客,武帝太初初年改名大鸿胪,东汉有鸿胪寺这一建筑样式,可能是中国佛寺之“寺”这一称谓的原始。相传明帝求法使者蔡愔等归汉时,有印度僧人迦叶摩腾(或称“摄摩腾”)等首度来华。[注]《魏书·释老志》、梁慧皎《高僧传》称,与迦叶摩腾同来中国洛阳的,亦有竺法兰。竺法兰与迦叶摩腾,为中天竺人。鉴于鸿胪寺本有接应宾客之功用,迦叶摩腾等初次来华住于洛阳鸿胪寺,是可信的。这大概为何后代供佛像、僧人住地奉佛与信徒烧香拜佛的处所称为“寺”的缘由。至于中土最早寺塔之名白马,据称因当时迦叶摩腾等曾以白马驮带印度经卷、佛像来至洛阳之故。
中华寺院,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化与审美意义的本土化之路。
印度“支提”窟内设“塔柱”,而中土佛寺佛塔终于分而建之,使得有可能将寺塔造得尽可能的广博、巨硕而高大,体现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崇尚正大、端严美学风格的中国气派。有如以体硕、高耸形象为主要特征的楼阁式塔与密檐式塔,在建筑美学的理念上,显然较多地汲取中国传统建筑亭台楼阁的深刻影响。
中土佛塔的檐层,绝大多数为奇数,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甚至十七层等,偶数檐层的塔例极为罕见。这在文化与美学上,也是本土化的体现。早在殷代,当关于“间”的建筑意识发生时,“一座建筑的间数,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采用奇数”[9]。尤其在先秦道家哲学创立、发展为东汉道教之后,土生土长的道教,正如葛洪《抱朴子》所言,崇尚“道生于一,其贵无偶”[10]的哲学与美学信条。中国佛塔檐层尚“奇”,显然与此相关。而中华佛塔的平面,有多种。圆形平面象征佛教的圆寂、圆融、圆圆海等;正方形平面,象征四圣谛、四大皆空等;正六边形,象征六道轮回、六如、六根净等;正八边形,象征八正道、八不中观等;而正十二边形者,象征十二因缘与十二真如等。
中华信徒一旦开始建造佛寺佛塔,寺塔的地理、环境之位置关系,亦是本土化的。传统民居、宫殿与陵寝等平面,皆崇尚中轴对称,如明清北京紫禁城(现北京故宫)的平面布局然,中土佛寺的平面布局,追求中轴对称格局,常为三大殿层层递进,有严格的中轴线,主题建筑设在中轴线的高潮点上。从美学而言,中国人不喜欢那种阴郁、局促与小家子气的建筑风格。
一些考古资料,可印证东汉佛教艺术的历史存在。据南京博物馆、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沂南古画像墓发掘报告》,“山东长清孝山堂祠堂佛像、四川乐山城郊麻浩和柿子湾崖墓浮雕坐佛以及四川彭山东汉墓、四川绵阳何家山一号墓、白虎崖墓中出土摇钱树上的陶制或铜铸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雕像中的佛像等”,则“基本可以确认”[注]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4页。此资料与看法,由《中国佛教文化史》一书采自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载《文物》,1980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其头部周围刻一圆环,可以看做佛光之状的刻画。佛经指释迦牟尼眉宇间放射光芒,象喻佛的无上智慧普照,又称宝光。东汉画像墓的立童佛光,显然是画像石艺术中所出现的佛教因素,其艺术与宗教灵感,可能来自印度犍陀罗佛教造像头、背部有佛光之造型的借鉴。佛教,无论中印,都具有虔诚的光崇拜。所谓“放大光明”者,喻佛之智慧。破暗为光,现法曰明。从佛经所言可知,佛光普照及众生心田而袪世界之丑恶、不公与人生之苦厄、无明,为大智大明、大净大德。以佛光之照临一切,不仅是佛教的光崇拜(此源自印度原古火崇拜、太阳神崇拜),而且因崇拜而蕴含以“光世界”这一“理想”诉求,不免趋入审美之域。
据考古,四川乐山一个东汉石墓的石刻佛像,为坐姿式,高39.55厘米,宽30厘米,其面部已残损,但其头部佛光的雕刻颇为清晰,坐像似身披通肩袈裟,其右手作上举状,伸出五指,手掌向外,好似作“施无畏印”[注]施无畏印,佛教手印之一。《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云:“右手展掌,竖其五指,当肩向外,施无畏。此印能施一切众生安乐无畏。”。据考,该作品完成于东汉后期。[注]参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石选集》第59图,北京:群众出版社,1955年。这是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入渐于川蜀的明证。
东汉始造佛塔佛寺与绘塑佛像作为风气之先,为中华美学史及其佛教美学,首度触及了一个佛教崇拜与艺术审美的关系问题。
宗教崇拜,是对象的被神化同时是主体意识的迷失。崇拜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主体心灵“跪着”的缘故。崇拜夸大了对象的尺度,扭曲了对象的性质,它是与主体心灵的被贬损和被矮化同时发生、同时建构、同时消解的。而艺术审美,又偏偏是积极性的人的本质力量通过意象系统(形象与情感等)方式的一种对象化,作为对主体意识的肯定,是审美意义的主体意识的现实实现。因而,佛教崇拜与艺术审美是背反的。可是,佛教崇拜又偏偏在迷幻的崇佛氛围中,让人体会到佛(神)的绝对崇高的“真善美”。佛的完美或称圆美,恰恰是属人而非属神的审美理想。佛的空幻与慈悲,曲折地体现出人所向往、追求的人性的自由与人格的伟大。就此而言,佛教崇拜与艺术审美二者又是合一的。
据不完全统计,一部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收录词条凡三万六千余,几无一个词目是直接、正面谈论与肯定世俗之美的[注]丁福保《佛学大字典》仅收录“二美”词条云:“定慧之二庄严也。《吽字义》曰:‘二美具足,四辩澄湛。’”此“二美”之“美”,指“禅定”“智慧”。。然则,艺术、审美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现实的基本实践方式之一,本具顽强的文化生命力,亦是人性、人格的构成要素之一。中华初始的佛教艺术包括塔寺与佛像之类的美,作为佛教“方便说法”的一种方式,又在教义宣弘之时被肯定。
三、审美:从“乐”到“悲”以及“乐”“悲”相系的历史与人文转递
印度佛教东渐,开始促成中华文化与哲学的历史与人文嬗变,从“乐”的审美,开始趋于“悲”(苦)以及“乐”“悲”相系的审美。
中土从先秦至西汉的文化及其哲思美韵,原是以“乐”为主流的。“乐”是传统“礼乐”对立而统一的文化因素,是中华漫长历史时期的重要美学范畴之一。并非先秦与西汉之时不存在“悲”这一世俗情感,浩瀚的文化典籍有关悲苦的记述甚多。其关于“悲”(忧患)的审美意识,发蒙很早。在《易传》称文王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之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就有“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之说,“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诗经》有云,“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心之忧矣,不遑假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等等,给人以忧思如焚的感觉。至于战国末期大诗人屈原忧愁、忧思而作《离骚》,“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等,是典型的悲苦离忧的审美。
然则印度佛教入渐中土之前,中国人有关“悲”(苦)的美学理念与意绪,大凡都是“伤时忧国”型的。“伤时”,是对于时世的忧虑;“忧国”,忧家国社稷天下之谓。《庄子》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生之“忧”,大凡是生活(人生)之“忧”。《庄子·秋水》说,“得而不喜,失而不忧”[11],是很“哲学”很“美学”的放达,仅止于现实人生之“无”的境界。
佛教入渐之前,中国人固然以人生之悲(苦,忧)为美学诉求之一,而比如老庄所谓人生之“乐”,是指从世道、人生忧苦境遇之中“出走”的“逍遥游”。儒家《易传》有“乐天知命,故不忧”与“和兑(悦)”等易学命题,亦能证明中华民族有关悲喜、苦乐的人文理念与意绪,重在生活之悲而非生命之悲;重在人格之悲而非人性之悲。中国人原本以为,人生快乐既然在世间此岸,就不必去向往出世间的“乐”与“美”。先秦儒家称“性与天道”,“圣人存而不论”,更何来、何谈彼岸的“美”及其“乐”?
可是,自从印度佛教始传、东汉佛经初译,这种关于“乐”的审美格局,开始被打破,成为东汉“悲”(苦、空)的美学诉求所发生的一个历史与人文触因。
众生从佛教“四谛”说逐渐生起了一种苦空观,体会到人生的无论成毁与否,都苦海无边,以为世间的欢愉安乐,皆虚妄不真。佛教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乃至一百十种苦等“无量诸苦”说。如生老病死为四苦,再增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为八苦等。尤其是欲海难填的“求不得苦”,绝对而无有穷时。佛教种种“苦”(空)说,好比久旱逢甘霖,当时尤得中华本土文化的“心印”,遂使东汉朝野得风气之先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华原有的人生悲喜、苦乐观,将人之生命而非生活、人性而非人格的“悲”(苦、空),营构为一种新的哲学与美学理念。大教东来,拓进了中华审美形上的思维与思想,开始改变中土原本仅从生活与人格维度看待、认识苦乐悲喜的“思维定势”,以佛教“究竟智”为“根本”之乐、“根本”之喜,可以看作一种深层的“美学”在成长。
关于这一点,诵读一下《古诗十九首》,大约不难理解。该诗第三首云,“青青陵上陌,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陵陌、涧石,本无情之物,勾起诗人有关人生寄旅的忧思。第四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似乎是对第三首的生动诠释,人若微尘,倏忽而逝。第五首,“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弦歌”“何悲”,歌“苦”而“知音”难觅。第十一首,“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四顾”茫茫荒草,喟叹人生速朽,不免悲从中来。第十四首,“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悲风”四起,愁绪“杀人”,“故乡”安在?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命如此短促,“苦空”意绪,难以释怀。第十九首,“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出户独徬徨,愁思当告谁”,月光如水,“忧愁”难抑,不免心起“徬徨”,无以诉说。
《古诗十九首》反复吟咏的,主要是佛教关于“生命空幻”的美学主题,却以类似先秦道家“虚无”之言来组织诗章。这一东汉末年的无名氏之作,真正是当时民族文化心灵开始受到佛教美学精神濡染的典型体现。
四、拓展出一系列关乎审美的新名词、新概念与新范畴
东汉时期佛经的初译及其流播,为中国美学史及其佛教美学,拓展出来自佛教的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与新范畴,它们都统一于佛教之“空”这一理念,遂使中国美学原本的哲学基石即其本原本体,开始丰富、改变其风色。
正如前述,佛教改变、丰富了中华本有的“智慧”观,创造了“清净”等佛教语汇,关键在于输入了印度的“空”观,却以“本无”这一采自中华老庄的哲学名词,来译介佛教的空谛。
支娄迦谶曾一再以“本无”一词译读佛教的“空”。《道行般若经·照明品》云:“般若波罗蜜即是本无。”“何所是本无者?一切诸法皆本无”,“一本无,无有异。”[注]《照明品第十》,见《道行般若经》卷五,《大正藏》第八册,P0450a。“过去本无,当来本无,今现在怛萨阿竭本无等无异。是等无异为真本无。”[注]《本无品第十四》,见《道行般若经》卷五,《大正藏》第八册,P0453a。注:怛萨阿竭,如来早期译名。一切事物现象因缘而起,刹那生灭,故空无自性。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皆无例外,均为“本无”。“本无”是佛教最基本范畴“空”的中华早期译名。它丰富了中华美学的本原本体论。人们体会到,美与美感的根因根性,可以是儒之“有”、道之“无”,也可以是佛之“空”,或者是三者合一。从而为中华美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老子》云,“是故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本无”,虚静无为义,而《道行般若经》以“本无”说性空、真如、实相,开始拉开尔后魏晋佛教所谓“格义”的哲学与美学之灿烂的人文序幕。
一是“本无”这一译名,暗合印度小乘尤其“说一切有部”关于“一切法自性有”的佛学主张。所谓“自性有”,指事物现象皆“空”而本质尚为“实有”。尽管《道行般若经》是大乘空宗的般若类经典,这无碍于支译对所谓“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佛理有所传达。在佛教史上,《道行般若经》的经义,有自小乘“实有”说向大乘“性空”论转嬗的理论倾向。支译以“本无”说“性空”,竟然无意之间,在言说与肯定般若性空之“美”的同时,亦稍稍从“自性有”角度,触及了现象“空”而本质为“有”之“美”这一问题。
二是支译以“本无”代“性空”、以《庄子》所言“野马也,尘埃也”指喻“本无”,这一“误读”,却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哲学尤其老庄美学的顽强生命力。当印度般若性空之学及其美学诉求开始逐渐传播于中土之际,这一佛教教义的中国化即“方便说法”,可让一时难以为人所理会的般若学,在中土变得亲切可人而容易被接受,就佛教之“空”及其一系列新范畴而言,“本无”这一理念有接引之功。
三是般若性空之学,原旨在于无所执著。《道行般若经·清净品》说:
知色空者是曰为著。知痛痒、思想、生死、识空者是曰为著。于过去法知过去法是曰为著。于当来法知当来法是曰为著,于现在法知现在法是曰为著。如法者为大功德,发意菩萨是即为著。[注]《清净品第六》,见《道行般若经》卷三,《大正藏》第八册,P0446b。
这里一连用了六个“著”字。著者,执也,滞累己心于对象义。执包括法执我执,起于妄见。无所执著,指既不执于俗有又不执于空幻;既不执于假有又不执于真如;既不执于空、有二边又不执于中道,这是大乘般若性空、中观学最根本而重要的思想。无所执著作为佛学命题,同时也是一个美学命题。两者区别在于,般若性空之说,彻底斥破法执我执,连斥破本身亦不能被执著。否则,好似“药到病除”而“药”未出,依然止于滞累妄境。老庄亦言“无所执著”,包括不执著于功名利禄与社会意识形态等,道家反对“造作”,提倡“自然无为”[注]牟宗三云:“照道家看,一有造作就不自然、不自由,就有虚伪。造作很像英文的artificial人工造作”;“道家一眼看到把我们的生命落在虚伪造作上是个最大的不自在。人天天疲于奔命,疲于虚伪形式的空架子中,非常的痛苦。基督教首出的观念是原罪original sin;佛教首出的观念是业识(karma),是无明;道家首出的观念,不必讲得那么远,只讲眼前就可以,它首出的观念就是‘造作’”,并将ideology(意识形态)译作汉语“意底牢结”。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5、87页。。而“无”本身,确是其执著对象,此亦《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从美学言之,般若性空之学,以彻底的无所执著为“原美”,它是彻底消解了世俗质素与色彩的“本美”,《道行般若经·泥犁品》云:“般若波罗蜜无所有,若人于中有所求,谓有所有,是即大非。”[注]《泥犁品第五》,见《道行般若经》卷三,《大正藏》第八册,P0441a。此是。
时至东汉,中国美学史因佛教东来而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开始形成新格局。且不说汉字原本并无“佛”及其概念与理念,这一汉字的创设,对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与美学而言,真乃非同小可。甲骨文至今未检索到“空”字。空,从宀(音mián),工声,本指建筑物空间,未具任何哲学、美学的形上意义。《论语》有“空空如也”这一命题,意思是“什么也没有”,属经验层次的思想与思维,未涉于哲思美韵。而正如前引,安译《大安般守意经》“气灭为空”这一命题,尽管以“气灭”译佛教“刹那生灭”不免是“误读”,却是中国佛教及中国佛教美学关于“空”从未有过的新的理念与思想。刹那生灭者,空也。因其哲学意蕴葱郁深邃而具美学品格,使原本“空”义,一下子从形下向形上之义提升,无疑开拓了中华民族的哲学与美学的思维空间。《牟子理惑论》称,“佛者,言觉也”。佛即空,悟“空”者,“觉”之谓。众生觉悟即佛,悟“空”为第一义。这与审美攸关。先秦有“禅”字,义为封土为坛,洒地而祭。“禅让”一词,表帝位让授于贤者。此“禅让”之“禅”,本无哲学、美学的思维与思想深度,岂料初译佛经以“禅”(禅那)一词译“禅定”,“思维修”与“静虑”诸义,不仅为教义且为哲学、美学意义的一大创设。“色”字本义初浅,初译佛经又以该字指称一切事物现象,有变碍、质碍、假有义,其义深矣。又如“法”义,亦较中华本义大为开拓而尤显深远。
佛经初译,带来了中国哲学、美学初步然而深刻的嬗变。尽管初传之际,固有“夷夏之辨”的中土信徒或士子,曾以“道术”比拟佛法,以“神仙”称述佛陀,以“灵魂不灭”类比“佛性常住”,以“无为”言说“般若”,等等,而中国文化、哲学与美学的转递,是实实在在而值得充分肯定的。
据《四十二章经》,“佛言:财色于人,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愚也”。“财色”如“刀刃有蜜”,如“小儿舔之”,乃为“割舌之愚”,这并非“美”而是丑,美的观念转变了。又,沙门夜诵《遗教经》,其声悲苦,思悔欲退。“佛问之曰:‘汝昔在家,曾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弦缓如何?’对曰:‘不鸣矣’。‘弦急如何?’对曰:‘声绝矣’。‘急缓得中如何?’对曰:‘诸音普矣。’佛言:‘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这一“弹琴”之喻,多持老庄口吻,其中如“调适”之“适”,直接采自《庄子》。这是“误读”亦是释、道二者的融通。不取“弦缓”“弦急”二分,而“适”于“急、缓得中”,传达了佛教大乘的“中观”精神而不滞累于此,“美”之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