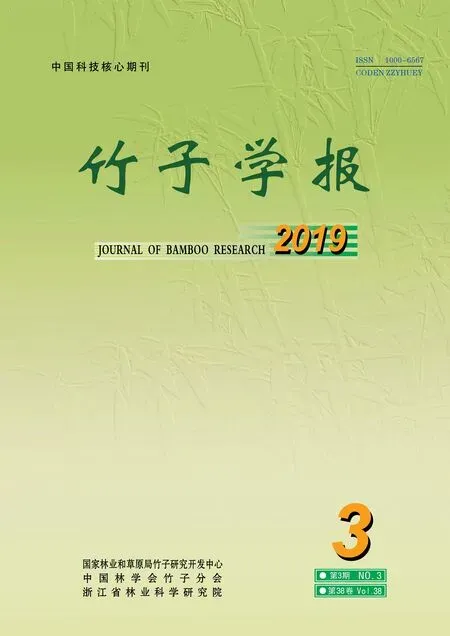遮蔽与揭示
——中国古代竹文化意象成因的初步探讨
张成勇
(怀远县茆塘学校,安徽蚌埠233000)
自陈寅恪先生提出“竹的文化”这一崭新命题以来,关于竹文化的探论日益觉醒并为之渐多。竹的植物品格及其神化属性亦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双重交叉、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全面释放。与此同时,伴随美学热、文化热的兴起,诸多学者力图从符号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入手,对竹作了深入地考察。何明、廖国强先生在其《中国竹文化研究》中指出,竹的研究应当立足于竹文化景观和竹文化符号两大系谱,并运用符号学释明竹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的文化心性和价值;稍后,皖西关传友教授撰写的《中华竹文化》从物质成就、精神成果2个方面论述竹的文化特质及其精神内涵,具有鲜明地普泛性;贵州的王平研究员则在《中国竹文化》中言道,竹的文化形态必须根植于民俗学的视野下,尤其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用竹、事竹等其他活动进行全方位考察,其地域特色饶有意味。近些年,林业学家彭镇华、江泽慧教授集结《中国竹文化:绿竹神气》一书,以“个字探源”“竹诗百篇”的形式将自然科学渗入竹文化研究之中,甚属可贵。
竹作为植物,既包罗大量的自然属性,亦是人类造物历史和艺术审美的积淀。然,任何时代的学术研究都有其历史、认知等诸多因素的局限,竹文化亦概莫能外。笔者认为,当前有关竹文化的研究视域仍囿于3个方面。其一,是竹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勾连甚少,普遍按实用、观念的二分法加以阐述,竹文化中观层面的认知断截和底表叠层的含混不清;其二,割裂造物与审美的天然联结关系,否定物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哲学观;其三,轻视学科的交叉和互补优势,造成相当一批粗俗浅陋、重复研究的劣质成果。因而,提倡跨学科的交叉立体式研究在某种程度即是破解上述问题的隐秘符码,对于审视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1 竹意象的考释与流变
在植物世界里,竹属单子叶植物科,常与稻稷同称禾木科。然“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故用竹亚科以示区别;又据《中国植物志》载:“竹为植物体木质化,常呈乔木或灌木状。竿和各级分枝之节均可生至数芽,以后芽萌发再成枝条”[1]。其节多为中空,根系发达、繁生甚强。在中华民族的造物史上具有特殊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意蕴。
1.1 中国竹貌概观
中国是竹的故乡。虽不知培育竹始于何时,其上界亦无从考证,但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早在约7 000 a前,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已有竹的遗迹。诸如距今7 800—7 500 a前的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发现绘以“”图案的彩陶残片;稍晚距今7 000 a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则出土了竹子的实物;1976年发现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葬中,发掘出锥型小竹篓,做工颇为精巧;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江陵县楚国墓葬出土的彩色竹编席编工致密,纹路严整。由此可见,中国植竹、育竹历史十分悠远。至于下限,竹类研究专家温太辉先生认为:“中国的竹子利用已有3 000多年历史,竹子长距离引种己有2 260 a的历史,种竹子已有2 440 a的历史”[2]。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南北竹生植物从品类上大致可分9类,兹择其要者如下:(1)簕竹超族,分梨竹属簩竹属、泡竹属、空竹属、泰竹属、梨藤竹属;(2)簕竹族,分新小竹属、簕竹属;(3)牡竹族,分慈竹属、绿竹属、牡竹属、巨竹属;(4)倭竹族,分刚竹属、倭竹属;(5)北美箭竹超族,分香竹属、镰序竹属;(6)北美箭竹族,分为筱竹属、悬竹属、箭竹属;(7)玉山竹;(8)北美箭竹亚族,又分酸竹属、少穗竹属、大明竹属、巴山木竹属、井冈寒竹属、矢竹属;(9)赤竹亚族,又分异枝竹属、赤竹属、铁竹属竹属,等。
由是观之,古人在漫长的劳作过程中逐渐地完成了原始经验的累积,在“器具”与“物象”的范畴中掌握了竹的神秘的“性能”“内核”,即植物的实用与审美。《尚书·禹贡》有云“筱簜既敷,筱,竹箭。簜,大竹”[3];唐人孔颖达疏曰:“传‘筱’,竹箭。‘簜’,大竹。正义曰:《释草》云:‘筱,竹箭。’郭璞云:‘别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节相去一丈曰簜。’孙炎曰:‘竹阔节者曰簜。’郭璞云:‘竹别名。’是筱为小竹,簜为大竹”[3];竹的形状不同,孳生的明目亦不等同,其功用按照人的需求而“纹化”“设计”;西周中原地区则受礼仪文化的浸染,从农耕角度得出“湿润不谷,树之竹苇莞蒲”[4]的结论。人与自然生境成为操控竹形成、扩布、流变的有力推手。竹与生活生产有着密切的关联,进而不断地衍化、增殖,使其涵融自然某种特殊属性并将人性从中剥除;扩大植物种类于人的日常生活,求得万物神灵的庇佑,投射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中的造物心态和精神属性,孕蓄出庞大的“竹场”意象。
1.2 古今竹区分布
中国地跨寒、温、亚热带,植物资源极为丰饶,竹作为中华大地上的普通植物,分布十分广泛。稽诸文献,最早记载关于竹区的上古文献《尚书·禹贡》将中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9州,设牧官掌执。其兖、青、徐、扬、荆、豫6州为竹产区,皆须上贡竹类器物。荆州为当时重点竹区之一,所谓“荆及衡阳惟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3],即今湘、鄂地区,盛产竹类箘簬;淮扬亦是重点区域,当时的扬州很大,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中南部与浙江、江西,也就是淮河以南及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5]。《禹贡》所载九州之中以扬州最详,胪列如下:淮、海惟扬州。北据淮,南距海。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彭蠡”,泽名。疏曰:“扬州”传“彭蠡”至“此泽”正义曰:“彭蠡”是江汉合处[3];三江既入,震泽厎定。震泽,吴南大湖名。疏曰:传“震泽”至“震泽”正义曰:《地理志》云,会稽吴县,故周泰伯所封国也。具区在西,古文以为震泽,是“吴南大湖名”[3];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少长曰夭。乔,高也。疏曰:传“少长”曰夭。乔,“高也”正义曰:夭是少长之貌,《诗》曰:“桃之夭夭”是也。“乔”,“高”,《释诂》文。《诗》曰“南有乔木”是也[3];厥篚织、贝。织,细缯。贝,水物。疏曰:传“织细”至“水物”正义曰:传以“贝”非织物,而云“织贝”,则贝、织异物,织是织而为之,扬州纻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为衣服之用,知是“细纻”,谓细纻布也[3];厥包橘柚锡贡。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锡命乃贡。言不常。疏曰:传“小曰”至“不常”正义曰:橘、柚二果,其种本别,以实相比,则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3]”
“彭蠡”为今鄱阳湖,“震泽”为今太湖,“苞”为冬笋[5]。用“篚”作为容器将竹类及其他生需产品沿淮扬水路运达所往之处;“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既旣敷”,即是等洪水退之,太湖上竹林便显露出来,现今浙江的安吉、余杭均有此等景象,《禹贡》所言亦绝非谬论,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南北竹区分布的覆盖之广、种类具多。
上古地理方志《山海经》是研究神话传说、原始宗教艺术、地理雏形的重要资料,对于当时的植被亦有较详的记录。其中,就“竹”而言,除开《南山经》外,其余各山经记载“竹”多达20余次。如: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有草焉,其名曰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彘[6];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嚣水出焉,北流注于汤水。其上多桃枝钩端,兽多犀兕熊罴,鸟多白翰赤鷩。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华而不实,名曰蓇蓉,食之使人无子[6];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6]。
“竹箭”依晋代郭璞注解,为“篠”也;袁珂按说文谓之小竹。“桃枝”为钩端,桃枝属;袁珂照尔雅释草,谓之桃枝,桃枝四寸有节,凡竹相去四寸有节者,名桃枝竹。据谭其襄先生研究,《山经》记述的范围基本是中国上古时代居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黄河流域[5]。
如上指陈,上古时代无论是北方黄河流域,亦或是南方长江流域,竹区覆盖完整。但据现有资料显示,南北朝时期河南淇水流域的竹区出现几乎灭绝的情态。渭河平原、秦岭北麓竹区在明清早已颓败,北方流域很难寻觅大片的竹林。究其缘由,古开弼先生扼要4点:其一毁竹拓地;其二兵燹毁竹;其三横征暴敛;其四自然灾害。另外,“受第四冰期的影响,喜暖的植物自北向南后退”[7],成为暗含于“人为自然”背后的规律和趋势。南方地域充当喜暖孑遗植物、活化石和植被类型的庇护所,大量物种被保存下来,呈现层次多、物类多的态势。从历史环境的变迁来看,南方沼泽丘陵险阻,且开发程度较低,成为原始竹区有利的屏障。
因此,当今竹区大部分主要集结于南方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诚如学者薛纪如先生指出,中国西南部山地不但是亚洲竹子的主要起源地,也是现代竹子的分化和分布中心。广袤的南方地域,气候温暖湿润,竹作为喜光植物,尤为充裕。自先秦伊始,就有诸多少数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中原的礼乐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发生碰撞、吸收,衍生不同品格的竹文化景观机制。应当指出“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8]”,这一点对于消解地域的差异性,促进文化的交流、合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工艺美术的角度亦可觉察,竹向南扩布并呈现动态移动的过程体现竹从早期的实用粗野向精细内涵式发展模式,丰富竹的文化语言和内涵层次。
1.3 释“竹”
中华民族历史绵长,其文脉未曾间断,文字如薪火世代相传。自汉字出现以来,整体部件不断发展扩充,形成体系完备的形、音、意、美四位一体的语言符号。“生态环境是汉字产生、演化与发展的土壤,是汉字发生、发展物质基础”[9]。自古以来中国竹林分布广阔,“竹”与汉字有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上的渊源。至于“竹”字出于何时,尚无确切定论。但“观物取象”的思维命题方式始终贯穿于整个造物当中,它是《易传》对《易经》扬弃、改造的必然结果,具有浓郁的宗教巫术色彩,反映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及模仿。
《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10];许慎在批判地吸收《周易》精髓基础上,开明宗义道:“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11],可见仿生是象形核心因子;固不言待,“这类字的字形象某种实物,它们所代表的词就是所象之物的名称”[12],不会发生任何歧义之见,较好地保存原始文字的概貌;与此同时,亦可大致推察其字形成的时间早晚。“值得注意的是,许慎为何以小篆为说解对象。这是因为在形体上从古籀到小篆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13],象形作为“观物取象”的表征形式,力求达到“立象以尽意”的功效。
总之,单纯的视觉形象无法承载、表达变化多端的动态语言,模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并据此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驱使造物活动的规范、合理。通观“竹”字的生成、演义,即是升华自我情感的表达。如果把象形比作物质地、感性的形态;那么,会意指向的便就是纯化的精神内容。“纹化”决定器物的“人性”尺度;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个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就是审美意向,也就是美。”[20]
2 观物取象:物化的自然尺度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生态决定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属性。竹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镜像之一,无论在文化史、艺术史、美学史及宗教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扩展和深入,‘自在自然’就逐渐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改造的对象,成为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资源”[21],“观物取象”亦是人造自然向诉诸情感的表达媒介。《易传·系辞传》有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貌,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2],万千自然,诡秘多端,唯有仰视、俯察才能深刻地把握其观照对象的核心功能和属性。
植物中竹类是集中体现人类改造自然的重要载体,着重表现在依存与演化方面。即在生活中对植物的属性把握,随之吸纳、创造,凝固成具体的物质化语言。就此问题,笔者爬梳典籍,略作一番探讨。
上古时代,人未开化。“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23];又“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24]。人类混沌初化,以自然造物为端。神农氏作为人界与自然沟通的大神,尝遍百草,将植物纳入平日所需。汉代伪托神农之名,结成《神农本草经》医书传世,对竹的功效有详细记录。
“竹叶:味苦平。主咳逆上气,溢筋急,恶疡,杀小虫。根,作汤,益气止渴,补虚下气。汁,主风痉痹。实,通神明,轻身,益气”。作为药材,以祛病为主,未作其他赘述;通神明,轻身,益气显然是受道教的影响。“我案《九合内志文》曰: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于玄轩之宿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公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全,诞亦寿考,微着之兴,常守利贞。此玄人之秘规,行之者甚验”[25]。“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的繁殖、类比功能在梁代陶弘景看来是克服不孕的天然良剂;从宗教学上看,“人类的精神生活,不仅经常具有和需要理性的东西,而且常常还需要非理性的精神生活作为补充”[26]。诚然,正如史学家陈寅恪所说“天师道对于竹之为物,极称赏其功用”。道教的竹是催生、唤醒植物异化力量的特殊物体,但终究宗教与中医本质不同,自然始终是制约物化成形的价值尺度,亦是“竹符号”向其他文化蔓延的滥觞;尔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进一步阐释了竹的形态、功用:“淡竹叶:味辛,平、大寒。主胸中痰热,欬逆上气。其沥:大寒。消毒。除烦热,风痓,喉痹,呕逆。消毒;竹叶:大寒,无毒。温气,寒热,吐血,崩中,溢筋;苦竹叶及沥:治口疮,目痛,明目,通利九窍。竹笋:味甘,无毒。主治消渴,利水道,益气,可久食。干笋烧服,治五痔血。”
与《神农本草经》不同,陶弘景对竹的实用属性认知是从整体抽析至局部,以求竹各个部位都能发挥作用,这种动态地、能动地观物方式十分难得。既照顾竹的自然性,使其沿续作为药的形式而存在,又将人为性植入其中,竹从神秘的“神坛”走向了民间,成为传统饮食的文化符码;晋代嵇康《南方草木状》亦记载了五岭以南地区云丘竹、簩竹、石林竹、箪竹越王竹的分布以及特征。
魏晋时期,士大夫阶级培竹、食笋成风,尤晋人南渡过之而不及。南朝道教徒戴凯之所撰写的最早植物学专著《竹谱》即是在清玄虚素的人伦品藻背景下产生的。开篇便指出竹属植类“既刚且柔,非草非木”的总特性;次文按竹的种类逐依加以释读,包罗竹的地理分布及生境形态。“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按戴凯之所言:“夫竹之大体多空中,而时有实,十或一耳。故曰小异,然虽有空实之异,而未有竹之无节者。故曰大同”,概括竹类实体、空心、有节的总特点;“竹生花实,其年便枯死,竹实也。必六十,亦六年”则上溯庄周“练实”一词。意为竹开花后结成的果实,又谓竹实或竹米。多数周期长,甚至60 a方能结果;因稀,又与六十花甲子相叠,古人认为必凶,所结食物亦只解饥荒;“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即竹喜暖易生长,具有较强的南方地域特色。唐代徐坚《初学记》载《竹谱》收录竹类多达60多种,可惜战乱频繁,竹林焚毁严重,今鲜有30余种流布于长江流域。直至宋代,竹的自然功用被充分挖掘,虚幻“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24]”的非物质境地,竹成为文人超脱现实社会的有利支点。吴兴僧人賛宁(919-1001年)《筍谱》是为特色。全书是汉魏降宋以来有关竹类植物的集成。賛宁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援据奥博,以笋为中心铺陈4份。诸如“一名筍生成,谓之笋。一名萌初生,谓之萌。言绝蒻也。一名箬竹土内,皮中,谓之箬也”,以示笋的别名;“凡植竹,正月二月引根鞭,必西南而行。负阴就阳也”,主要阐述笋的栽培人工栽培方法;二之出,“渭川筍。《史记》曰:渭川千亩竹,其人与千户侯等”,说明渭川在宋以前产笋;三之食,议述笋的烹制方法。如,“干法。将大笋,生去尖鋭头,中折之,多盐渍,停乆,曝干。用时,乆浸,易水而渍,作羹如新笋也;脯法。作熟脯,搥碎姜酢渍之,火焙燥后,盎中藏。无令风犯”等;四之事,即有关逸闻趣事。如,“江逌作《竹赋》云‘望春擢筍,应秋发坚’”等历史掌故,亦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五之杂说,则是余论,就前人对笋的认知,谈及自身看法。
明代朱橚采取“采竹嫩筍熟,油盐调食。焯过晒干,煠食尤好[27]”的方式,萃取竹笋的精华部分作为救荒充饥之物;而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木部·竹》则立足于竹的医用功能,按释名扼其要旨,集解诸家所言。分气味、主治,详述竹的药性、用药要点。如,淡竹茹。气味:甘,微寒,无毒;主治:呕啘,温气寒热,吐血崩中,溢筋[28];前人有所失察,另以修治、附方、发明查之。淡竹沥,修治:一法,以竹截长五六寸,以瓶盛,倒悬,下面一器承之。周围以炭火逼之,其油沥于器下也;附方:旧十二,新九。中风噤竹沥,姜汁等分,日日饮之[28];竹黄,发明:时珍曰,竹黄出于大竹之津气结成,其气味功用与竹沥同,而无滑寒之害[28]。由于竹类受宗教、民俗等影响,自然成分杂乱诡异,李时珍以实用为本剥除竹的人为臆造部分,故纳入《本经》中品;其后,嘉庆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对竹类的产地、性能亦均有详载。“淡竹叶,详本草纲目,今江西、湖南原世禄”[29];又,“箬,古今以为笠蓬,亦呼为簝。御湿所亟,本草纲目始著录。弃物有殊功,故备载诸方,以着无弃菅蒯之义”[29]。当然,由于时代的认知局限,竹的濡化呈现较为单一的演化进程,但凡论竹其自然属性始终浸泡在狭隘的地理方术范畴。
合上所述,古人以全方位、多维度的“观物”思维方式对竹类进行了漫长的考察,竹的深层次意蕴得到发觉。其中,竹天然属性与人的文化精神高度契合。通过竹的梳理明晰实用是人类探寻自然的客观语言,亦为自然哲学提供丰沃的土壤。“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30],能动地认知、精准地思考,如同“道”“器”水乳交融的联结关系一般。形而上的思辨涵摄早期抱朴含真的取象心理和生命化的造物意识,给人以自然启迪。
自然的极端异化即是宗教的神化。“自然一词涉及的是某种使它的持有者如其所表现的那样表现的东西,其行为表现的这种根源是其自身之内的某种东西”[31],因而,自然不仅是外化的客观世界,亦是古人在造物活动中内心深层次的阐释与表达;析言之,自然界的植物是人类较先崇拜的对象,古人由于缺乏科学的认知,往往将植物的功能和形状加以膜拜,并臆造各类植物神力,祈求禳灾祛魅。竹是中华大地常见的植物,与人类生产劳动息息相关,竹延及同一类别的植物成为“神”而存在即是必然现象。它包含信仰崇拜、民风习俗和“礼化”巫术。
竹孕成人的神话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流布广泛,认为竹与本宗族有直接血缘关系。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生动地记录了竹王的诞生,遂剥如下: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王水是也,破石存焉[32]。
显然,这种现象与“玄鸟遗卵,简吞之而契”如出一辙,竹与水成为祖源崇拜的输出管道,扮演欲言而不能言的功能,表现人类牢不可破的植物情结,是竹所构筑的自然体系,进而成为信仰;从民俗学的角度亦可考量,“当人类社会以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为基本单位时,相应的各类民俗文化就孕育产生了”[33],其本质仍是信仰崇拜的原层意蕴,繁殖、神化成为次生表象。又者,汉族亦流传远古时期洪水暴发,伏羲兄妹得到神仙指点,并用赠送的竹篮渡过劫难结为夫妻的传说。后世为纪念人祖,每至祭祀,用竹篮盛放贡品以表心意。与“竹生式”不同,中原地区由于受周礼的熏染,古人用仪式诉诸对竹的感恩。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竹所派生的自然意象从地域上看,主要根植于南方的土著文化。神话学家叶舒宪在其著作《中国神话哲学》中亦指出:“植物一般都生长于春季,繁茂于夏季,衰败于秋季。所以从春到秋之间,是植物生命最旺盛的时期”[34]。据北魏刘勰的《文心雕龙》所载,培竹的最佳时期是5月13日,谓之“竹神节”;清代园艺家陈淏子亦记述“五月十三为竹醉日,是日种者易活”的观点。古人以节气事农桑,大致为清明至小满节段,此时南方受季风气候影响,进入梅雨季节,雨量充沛。青龙司雨水,培竹日又云“龙王节”,其皆指向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故此观点是可以成立的。通观整个文化史,人在造物活动中显示巨大的原创思维力,竹的生命力在客观现实中的得到升华,充斥着丰厚的神象内涵。
信仰一方面联结群落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则反映民间习俗在物质中的浸染。竹一旦作为“圣物”,“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力量”[33],具有“法器”的功效。诸如上古时期的《神异经》就曾记录有关“竹”的故事:“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虾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着火中,爆烞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而変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皆有之”;梁宋楚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亦载“正月十五,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魈恶鬼”。竹为空心,以火烧之,滋拟“爆”声,驱鬼赶魅;福建闽侯地区每至正月十五,凡是过门新娘,其旁系亲戚皆手持竹杖拍打新娘,意为拍走晦气。又“竹”的繁殖旺盛,求子得福的心理在具体的民俗行为中得以体现,即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提出的“交感巫术”范畴,“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35]。正因如此,竹所死亡的只是躯体,活着的永远是自然高蹈的灵魂。
论竹而言,它是古人植物“礼化”观的遗存。“礼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占卜。卜筮始于伏羲,古史辨派学者认为“庖牺氏作,始有筮”。“筮”,《说文解字》云,“易卦用蓍也。从竹”。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金文说·史懋壶跋》一文中辨“”为“筮”,楚文亦是此写法。《周礼·春官·簭人》载:“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相筮。凡国事,共筮”[36];郑玄解云:“此九巫,皆读为筮,字之误也。”筮即为竹制占卜工具。说明原始占卦应在殷商之前就已产生;《周易·系辞传》亦有云“分朷五十根筮竹”的卜法,体现了巫持竹具占卜在周代十分流行,春秋战国时代更甚。如《左传》所载战争、立王二事,皆需卜卦而明察。附之如下: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37](《左传·僖公十五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37]”(《左传·昭公七年》)。
无论国家战事或民间生活琐事皆可以竹制卜筮,其功用与龟甲、兽骨等同。胡朴安先生所著《中华全国风俗志》引《文昌杂录》:余昔知安州,见荆湘人家,多以草竹为卜。楚辞云:“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卜之”[38]。《荆楚岁时记》亦记载占卜的方法,“掷教于社神,以占来岁丰俭,或折竹以卜”;唐贞观玄应的《众经音义》录:“筮者,揲蓍取卦,折竹为卜,故字从竹也”。以竹制占卜的香火延续千年未曾间断,“礼化”式的巫术是竹频繁使用的诱因,以卦象论兆凶,消解人对自然的恐惧。
综理上述,竹的自然功能与宗教属性,在人类探寻竹内核的进程中恰相熨贴。它凝聚的不仅是原始的造物“器具观”,亦是“观物取象”思维的深化;拘狭而看,竹作为器具,延伸了人生理以外的器官,使自然更富有人性的情怀,形成浓郁的竹文化意涵,摹勒天然而又诡秘的植物神象。
3 美地观照:人化的自然心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39]。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高级表达形态,亦必然涉及对其核心“美”的探讨。那么,何为“美地”?即知觉对自然物象能动的反映。它是复杂的视觉现象和认知体验,包罗抽象性、典型性等诸多精神元素于一体。
蛮荒时代,人类“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竹的天然属性成为生产狩猎的首选。随着器具的精良,生产力的发达,造物活动逐渐从清晰的自然物象挪向混沌的文化意象,有意识地思考成为关键。诚如爱德华·泰勒所说:“一个人的才能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成就,是暂时的东西,而这些顽强的植物却经受着任何风暴的考验,并在最不利的土壤中生出顽强的根来”[40]。竹不畏霜寒、生命力顽强,作为自然植物,受审美观念、文人画论等影响,自魏晋肇始流传至今始终是人观照植物艺术的母题,竹的艺术旨趣更加纯化,继而成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气节和人格象征。现略作撮述,以求明之。
竹作为一种自然植物,其本身就具有符合人类审美的价值。当然,这种情况早期主要表现在不录文字的口头文学时代,如《诗经》所云: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41](《国风·邶风·谷风》);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41](《国风·卫风·竹竿》)。
这种直抒胸臆的言物方式实为人类审美的初创层次,即取物象表征加以涵咏诉诸情感。由此可知,直观形象是阐述艺术本质的有效方法之一。张道一先生亦曾反复强调,艺术创作不能脱离形象思维。再者,在客观物象中摄入主观精神的多少,是竹是否得到正真纯艺术化的依据;又,《礼记》有云:“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42]。站在美学的立场上看,以自然植物比德喻人,即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移情作用;而审美反省时期的美,皆是人脑对客观物象的直接反映,并由此作为判断事物美丑的标准。直观的审美范式在“品题人物”的影响下十分壮大,由外向内的美在“澄怀观道”的支配下稍即土崩瓦解,取而代之是注重精神的浩然之气。竹更多地被赋予除它本质之外的诸多审美趣味。
画竹是人对植物的艺术观照,产生于审美自醒时期。近人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认为画竹始于“王献之竹图”;《贞观公私画史》则持顾景秀《杂竹图》一说;后有三国关羽画竹臆说,不作为凭。从美术学的角度亦可觉察,魏晋时期绘画题材不断扩大,主观因素不断纯化。花鸟虽服从人物,但溢出端倪。诸如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画像砖,通幅画面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及春秋时期高士荣启期刻画得形象生动,“他们或手捧酒陪衬,说明装饰题材的发展已由以动物纹为中心向以植物花草为中心的内容过渡”[43]。审美方式的演化是人对竹的咏叹或描摹历久不衰的内在因子,即“美地“提炼。查《世说新语》中有关此类记载,颇为生动。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中兴书曰:“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颇过度。时人钦其才,秽其行也”[44](《任诞·第二十三》);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44](《简傲·第二十四》)。南方成片的竹林对南渡后的晋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至王徽之寄居客家亦要植竹,又不顾主客之分失礼观竹,足以看出文人士大夫爱竹成性,“无此君”成为晋代以后区别雅俗的审美符号和哲学思辨的象征。从画史上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在宋代。其中,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论述“诗画本一律”的审美观非常精彩: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45]。
一个人体验到的是被作者所描绘的整个世界,而不是异质的精神状况或意图[46],苏轼所认为文同成竹于胸的创作是源于对竹的深刻观察、体验;从论及对象方面看,苏轼以竹而论的背后是对“诗画一律”的回应。说明画的核心是“气韵生动”,即自然物象与主观精神必须互相冥合。竹,是植物,具有不加雕琢的天然属性;诗,为不曾粉饰的《诗经》。置诗、画的平等,诉诸文艺创作中或审美状态下的自然平常之心。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则说:“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因此,艺术创造始终是意象生成的问题”[20],郑燮的《题画·竹》最能说明: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疎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有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47]!就艺术学而言,胸中有竹、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在构成完整视觉图式的同时,又是审美的对流与整合;而创作活动中,抽取物象中那部分人为性便会达到宗炳所说的“降明神”境地。多重感官作为媒介,是准确处理创作中整体与局部、内容与形式的前提,“需要说明的是‘形象思维’或‘思维中的形象’中所说的‘形象’就是‘意象’[48]”。又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47](《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这实是感情与想象力和在一起的活动”[49],以竹雨交击的声音,喻作黎民的疾苦,竹所迸发的力量在“吾善养浩然之气”的感召下,弥散着醇纯的文化意蕴。人进入自然并在物化、同构对象的同时,竹的精神属性与人的审美观念才能一齐得到净化和共鸣。
黑格尔把“认直接知识为真理的标准还可以引起另一种结果,即把一切的迷信和偶像均可宣称真理[50]。”因而,在人类看来,竹以“神”的方式指向物质的功用,另一方面则浸润在人化的物象中,是一种视觉认知上的真理,即物的人像观。蕴含人类对植物审美的纯粹化、理想化,求得群落对竹的深信不疑。另者,就其本身来论,竹是社会的产物,亦必定包括那部分不以人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竹的社会属性成为艺术史上永恒的经验题材,其象征意义被奉为圭臬。
上文所谈,远古人类愚蒙,随着造物认知的深化,器物无法承载大量非物质的隐性信息。托付自然植物成为具有高级人格的现象极为普遍,图腾信仰、习俗观念等通过艺术管道得到阐释,人的理想缺陷亦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得到补偿。如,陈寿在《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所载,孟宗本名为皓,湖北江夏人,因避吴王孙皓,易焉;及后,裴松之引晋人张方《楚国先贤传》注解: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51]。
笔者查阅《十三经注疏·孝经》部,只得“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句[52],宋人邢昺未提孟宗及笋一事;汉代刘向《孝子传》亦未收录。据郭居敬编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集》文曰:“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53],故尔,关于孟宗与笋流于魏晋,成型于元代较为稳妥。俗语有云“百善孝为先”,孝即是礼的具体实践,“天人感应”下的笋得到“礼”的升华。从民俗角度看,纪永贵教授认为“孝的道德身份与文人的艺术精神不相合拍,所以不能激起他们的诗情雅兴[54]”。但,孝作为一种礼的方式,依存在传奇、戏剧里十分丰盈。孟宗哭泣,为母求笋,曲折地反映当时南方诸江流域食笋之风日尚和竹笋已难寻觅;另一方面,亦觉察到当时“孝观”的缺失。“从‘孝感’模式到‘情感’模式[55]”的嬗变,它所象征的全部意义付诸在自然的植物中,并在儒家思想的观照下成为公众的精神符号。
神话传说既是极端的个性产物,对于“竹的人格”塑造亦极具表现力。“湘妃竹”的传说即是竹的私立象征之典型,晋代张华文曰: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56]。与张氏相比,任昉的《述异记》更加详实: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班班然[57]。取竹的直观表象加以抽思、联想,又以具体的娥皇、女英事例澄证它的存在,竹所显露的不再是普通的象征意义,而是一种稳固的人化形态;现量亦在客观物象的刺激下,引起诸多感官的连锁反应,竹的文化内涵随着复杂的抵牾心理,在神话传说中得到根本的消释。
“四君子”中的竹,最能反映植物的高级物化形态,即“植物人格”的象征系谱。画史记载,唐代花鸟发展迅速,阵容强大,诸如刁光胤、薛稷、滕昌佑等;1971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懿德太子李重润墓葬的壁画中发现数根绘以俏拔的竹画,这些充分说明竹被正式吸纳为花鸟题材的地位得到确立,竹的社会功用亦在现实和虚幻的环境中,裹挟着更多的民俗文化信息;五代十国时期,花鸟无论是题材、技法均有所突破,画坛中充斥着“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现象。然而,花鸟题材大放异彩却是在宋代,尤“靖康之变”宋人南渡临安后,竹得到前所未有的神化。文学方面,辛弃疾曰“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飨,春兰可佩”;绘画上“梅、竹在宋代成为一种独立画科,标志着此时的绘画,不仅内容愈加丰富,题材也愈加专门化[58]”。笔者仍需指出的是“四君子”在此并未得到全配,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卷三》亦只载松、柏二物,竹作为艺术符号亦多以“岁寒三友”的配式出现,如赵孟坚、马远等诸家的《岁寒三友图》。竹在宋代与松或梅并称,其原因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宋代文学艺术发达,统治阶级重文轻武,对于文学艺术十分提倡;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有力推动,以及“书画同源”说的误导;三是战争频发,民族关系得不到调和,以竹不畏严寒的天然属性,鼓舞士气,竹的象征寓意进一步得到强化。继后,明代天启年间,徽州黄凤池刊刻、孙继先所绘《集雅斋画谱·梅兰竹菊四谱》引陈继儒《题梅兰竹菊四谱小引》的“四君子说”,由此,竹正式被赋予“君子”的品格。
承接上言,人是自然的实践者,自然反之亦制约着人对物象的审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说:“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最早提出气候对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理论”[59],近人梁启超在探讨审美的地域差异性时,提出“地理环境、天然景物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12]”,并延及审美风貌的论断,从竹而言,亦可窥探一番。
竺可桢先生等人研究,上古时期的长江流域夏冬两季温差不大,黄河流域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3℃,竹域分布繁茂、普遍,竹的审美地域性已显示于咏物的对象。“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倚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60](《卫风·淇奥》)。淇,即河南汲县淇水一带,地处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按郑玄笺:“兴也。奥,隈也。绿,王刍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馀烈。绿竹并如字”[41]。以殷商纣王时期的竹箭园起兴,直咏为清气秀伟的大丈夫形象,从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地域以外象取美的风尚;然“五胡乱华”时期,华夏大地平均气温跌至2~4℃,战祸连连,生灵涂炭,晋元康2年出现竹开花的景象,百姓结实裹腹,审美的风向标在地理环境、人文气候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左右下指向困顿的内心。如,江逌所作的《竹赋》:有嘉生之美竹,挺纯姿于自然,含虚中以象道,体圆质以仪天,讬宗爽垲,列族圃田,缘崇岭,带回川,薄循隰,衍平原,故能凌惊风,茂寒乡,籍坚冰,负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润本,承清露以擢茎,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10]。与《淇奥》相比,《竹赋》更多注重竹的人文思辨性和南方地域特征。衣冠南渡后的中原审美观念在“以形媚道”的自然哲学中肢解,痛苦与理想随着客观的竹类进而溶解、顿悟,这种背景下的审美图式是南方稻作文化的反哺与蒙养。
综上所观,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功能及内在的应果关系[60]。透过对竹的文脉梳理,可以清晰地体味到竹的精神价值。它既是人类认知自然物象程度的缩影,又反映人类在造物活动中普遍的艺术心理。物质与意识相互交叠,形成不同的审美感知;当然,由于客观的差异,不同的物象蓄孕的审美形象亦不相同,这种层次性丰富和累化成风格截然相反的“竹场”意象,人类审美历史的攀援在竹文化的意象中得到“美地”观照。
4 余论
但凡探讨竹文化及其意象的成因,多以“文化”作为研究据点。《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化,在先秦典籍中即为以人性的方式改造自然,它是一个民族物质、精神文明的缩影。泰勒在《原始文化》中亦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和习惯[40]。这种思想倾向对竹而言,应当包括竹制器物、以竹为表现对象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心理的总和[61],需要更正的是:文化只有先吸纳竹的植物属性,才有可能转成主观意象生成的客观条件,排除竹的植物或生物属性谈论其文化性皆不妥当。另外,竹的各种意象亦就是人与自然发生冲突并继而涵容的结果。有鉴于此,笔者仍要指出的是学术界长期忽略的两个话题:一是竹文化的背后是稻作文化的蓄孕、支撑;二是重视楚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竹文化的互动、交融迹象,现将两者合而论之。
稻作是自然经济,一半靠人,一半靠天,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依大自然的时序变化进行劳作[62],这一农耕现象与儒家的比德思维互为合拍。精细化的微观心理亦必然会在生活“器物”中显露,由此成为人类攫取自然植物神性的特殊方式。再者,笔者大胆构想:若置稻作与竹为同心圆,其两者相交的阴影部分即以历史地理、艺术等学科求得,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交叉研究中重新得到认知和诠释。站在造物史的立场上看,稻作为人类提供生理的基础,而竹则为人类改造自然获取动力支持;反之,竹的功用最大化亦定然使稻作产生剩余价值。客观物质的丰盈对其精神享受提出更高的要求,原生的粗质美感难以满足人类诸多感官的需求,“人造美”成为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竹的功用在稻作的蔓引下能动地趋向审美,即竹的文化意象。
通观考古遗物和史料亦可得知,无论是南方或是北方“竹文化”的兴起无不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稻作基础之上,稻作文化作为旁结文化的重要母体,改变了“竹”的结构和形态,衍生诸多文化信仰与民俗意象,稻作的种种涵义亦必然会对“竹”实施同化和类比;又,受历史地域限制,不同稻作的土壤根植不同的竹性品格,其中以南方江浙的沼泽类型和西南的丘陵类型最为显著。诸如宁绍平原东部,四明山北麓与慈溪西部的河姆渡文化,是已知最早种植水稻的文化群。其先民普遍采用竹作为建筑材料或以竹材为辅筑构巢居。只不过由于年代悠久,加之竹易碳化,难以窥探原貌。但,孕育出干栏式的建筑雏形却是显而易见;西南地区民族多攘,文化民俗迥异,封闭稳固的境态中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竹楼、竹筒或是神化的占卜圣具,皆能体现两者的互动与交融,竹与稻作亦成联结民族之间心理自我认同的重要载体。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殷商时期楚人南徙过程中,在吸纳中原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又与江汉三苗、西南百濮等土著文化合为一流。出土于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彩漆编花竹扇一件,编织手艺可谓出类拔萃[63]。楚文化的浪漫气质,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造物文化、审美观念均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结合上文言之,竹所蕴含的造物文化及其审美意趣复杂多变,体现自然与人文耦合的内在机制。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亦可觉察,竹意象的生成、扩布始终是一个运动地“视觉图式”;人类的符号和构建都是记录,说得更确切点,它们表达了既跟符号表意和组建结构过程区别开来,但又通过这个过程而实现的思想[64]。竹,记录了中华民族在漫长造物活动当中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它既是客观的实物,亦是自然抽象的哲学思辨,并与民俗、艺术、地理等诸多因素交叠成蔚为壮观的东方“竹场”,而有关更加深层的“竹意象”的特质揭示,仍有待在时间长河中得到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