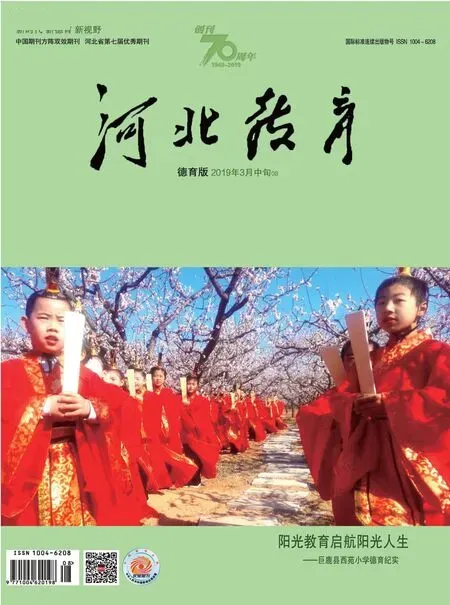猪进门,百福臻
○米丽宏
上中学时,班里有个男生乳名“小猪”。他不喜欢这名儿,我们一喊,他就暗暗咕嘟起一双淡眉。可气的是,有人还发挥一下,叫他“二师兄”,他的眉,就更攒成了一个疙瘩。但他没办法赖,父母起的名,想赖也赖不掉。
他父母呼他“小猪”,定是带了满满的爱意与暖意。小胖猪儿蛮有喜感:粉红皮肤,四只蹄儿,呱嗒着耳朵,撅嘴唇儿。小猪往大里长,像吹气儿,转眼就胖墩墩、圆乎乎了。一副圆满之态,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句号。
怪不得,传统的甲子纪年法,以圆滚滚、胖墩墩的猪,来完成十二生肖大结局呢。
然而,我那个“小猪同学”,好像故意跟他的名字反着来,越长越接近一根麻秆儿。那时,我们的学校坐落于一片民舍之间,连个围墙也没,乡亲家的鸡啊鸭啊鹅啊,随时都能听凭自己的意愿,闲闲地一路溜达就进了学堂。那天,班主任正声情并茂地朗诵朱自清的《春》,忽然,教室门开了,进来的,赫然一头黑猪!那猪老大也不认生,昂头竖拱地向着我们“哼哼、嗯嗯”地发出问候,众目偏移,都憋着不敢笑。班主任觉察,停止朗诵,四下里看。大家却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小猪同学。他先是埋头不理,最终承受不住我们目光里的戏谑,抓起破书包,将那不速之客抡了出去。
多年前,那闯教室的“萌”猪和那赶猪出门的“萌”人,实在都是家里的宝贝。小猪同学,如今已是中科院的博士,在我们县里都是鼎鼎有名的。而那时候啊,喂大一头猪,不比养孩子省心。万瓢水,千瓢糠,三天一锅猪食菜。妈妈们一天三顿拎了桶、端了糠去猪圈边伺候。
槽边的猪,呱嗒呱嗒吃得香甜,小尾巴滑稽地绕成圈儿,喂猪的人就会眉开眼笑。猪怠惰挑食,就不惹人喜。有的主人家好脾性,好言好语跟猪商量,请它来吃一点。多吃一点,肉厚了躺着舒服,像哄小孩一样。
若懒猪碰上躁脾气,主人一看那烂怂样儿,就会挥着搅食棍狠狠砸向猪脊背。懒猪狠命一声叫,蹿起来,往角落里去了。边躲避,还用小白眼儿呲弄主家。
也是。摊上一只不爱吃的猪,就像遇到个不靠谱的人,怎么说都是败兴事儿!那时候,村里家家养猪。猪,是一个家庭的家境、运势和财富。肥猪拱门,是好人家的梦想。除了过大年杀猪腌肉,补贴寡淡的胃肠,养猪还能挣工分。靠什么呢?猪粪。猪爱吃、混吃,就长得快,拉得多。猪圈里的粪肥多,工分就多。
因此,逢春集,选猪苗的时候,家家户户是千挑万捡,猪市上转无数个圈圈儿。那年,我家费劲巴力地挑选,终于买回了一头半大猪。半大猪我们叫“壳篓”猪,一听这名字,就是那种已搭好了架子、只剩往里面装东西的货!买来时不到二十三斤,养了两个月零十五天,斤数原封没动。我娘气得见人就讨办法、问原因,这是猪吗这?这就是个败家精啊。
想方设法,卖掉这个败家精,又斥重金买回了一只“壳篓”猪。主人说,是怀了猪宝宝的;要不是孩子娘生病住医院,哪里舍得撇下它?
“准妈妈”猪,被隆重接回家;娘像照顾产妇一样,无微不至。有天,我上厕所,见“妈妈猪”拖着沉重的大肚子,往窝里叼谷草,肚子上嘟噜着两排“纽扣”擦地而行。我一溜烟儿跑回家,说可不得了了,咱家的猪要吃干草了!娘把手里的活计一扔,跑到猪圈边,见老猪已经躺下。她说,老猪要生了!
娘简单拾掇一下,去当接生婆。那次,老猪生娃,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我们放学回家,娘把最后出来的那只小崽儿拿在手里给我们看。它眼睛半闭着,身体粉红鲜嫩,被一层水样薄膜儿包着,冒着热气。娘给它剪了尾巴尖儿,挽了脐带,擦干身体,一抬手送它到娘怀里去了。
我们探头一看,老猪的“双排扣”上,挂满了小崽儿。它们整整齐齐地挂着,不停地挤,不停地抢,不停地拱。它们叼住奶头,将娘的乳头拉得老长,然后,顶上去,狠劲一拱,借助压力,奶水就吸到嘴里去了。每一头小猪都是这样,每次吸奶都是这样。它们没有人教,天赋才能。
猪妈哼哼着,幸福地释放奶水,它的怀抱里热闹,喧腾,你拥我挤,喜气洋洋,一派多子多福的景象。
这胎小猪卖掉,换来的是我们的学费、作业本、花衣服还有稍好一点的饭食,每当换上新衣,我都心负愧疚,不敢去看老猪。这是用它的孩子换来的呀。
老猪后来又生过九个,生过七个,给我家挣了好多工分。生了几年猪娃后,老猪成了一个皮松肉沉的、名副其实的“老人家”,再也生不动了。杀掉?自然是舍不得。毕竟人家任劳任怨,贡献了一窝一窝的孩子,还有无数的粪肥。
那只有卖掉,明明知道卖掉,也逃不了被杀的结果。总归图个眼不见、心不疼罢了。我们的老猪,卖了个不错的价钱。我爹那个高兴啊。可是,我娘那几天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做出的饭都少滋没味儿的。
听说,她还跑到买家那里去探望老猪,早已不见。娘偷偷抹着眼泪回来了。
我知道娘的难过,绝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挣钱的助手,而是,她依恋着那种人唤猪应的和谐生活。猪,帮助过好多好多我娘一样的村妇实现了自我价值,喂大一头或几头肥猪,是她们的骄傲和自豪。
可是,在不懂得衣食艰难的孩子们眼里,猪,就是一次又一次成长中的热闹和佐料。我们见过大限将近的猪,忽然拒绝进食,对世界露出冷漠恐惧的神色;见过它们被掀翻在地,捆绑上车时夹紧了恐惧的尾巴;见过它们被吹胀的、褪光了毛的白花花身体,四脚朝天,像给天空最后的拥抱;还看见过被割下的猪头,眯着眼,叼着自己的一截儿尾巴,几乎有一种入定的慈悲。
我无法定义猪的一生。它来世上一遭,只是吃吃喝喝,但似乎也不缺乏意义。它是为人传送福气的使者。
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家”是个会意字,“宀”下有“豕”。意思是,只有住处养得起猪,才称得上是家。俗语云:猪进门,百福臻。此言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