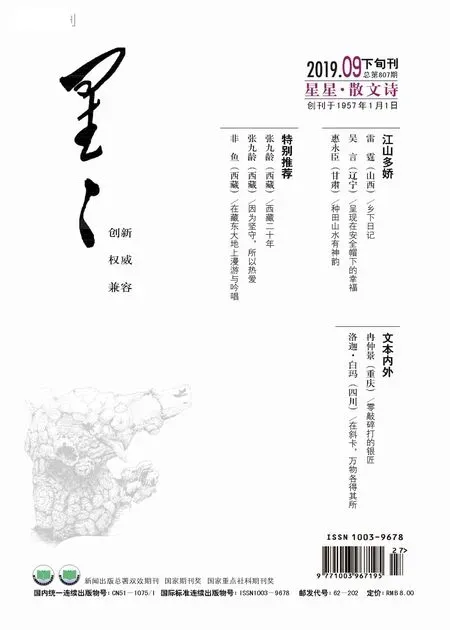东方之龙(组章)
巴音博罗(辽宁)
颂
龙兴之地,那东方的小小婴孩诞生了。像大海簇拥着千枝百朵的雏菊
盛开在时代的披风上,像黄肤色列车穿过沉沉长梦把清越的笛音留驻。
像嵌饰在纪念碑顶尖上的一颗寥廓星辰……
人们在广场上肃立,寂静也屏住气息。一阵灵思吹拂的风掀开了夜色。
凝重的大氅,一阵灵思吹拂的风吹来的香草气息……
远方的大厅灯火辉煌,座无虚席的人们多么像那篇著名宪章上的黑色字母排列有序:“我们接纳了东方古国的遥遥敬意,我们倾听了
龙兴之地的美丽传说,我们也把我们的祝福一一回报。”
就像远古时代吟诵《神龙赋》的秀才,挥着长长的袍袖涕泪满襟,就像除夕夜舞着龙灯的英俊小生把蒸腾的汗气迭迭推动……
那大风骤起之前祈祷者的隐隐悸动,把爱情和权杖的指向徐徐描述。
他用紫气东来的背景为我们伴奏,用云霞的气势烘托着广场上的庄严氛围:
一首新汉诗在人群中暗暗传唱,像海平面上浪花递给浪花,像那位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把美妙绝伦的歌喉向天涯吹送……
第一章
惊蛰已过,那唱着“引龙归”谣曲的乡民回到旧宅。水呀水呀,环绕我们眼眶中的饥渴更深更浓了。
“把路引过来!”神情肃穆的老人们说完,又沉回了地下。
一条灰烬的路连接着天庭,一条灰烬的路连接着厚土里的丝绸腰带……
而我们的古都多么威严,屋脊高耸的琉璃瓦壮丽无比,太阳那辉煌的车轮隆隆滚荡——穹窿万里,彩云上的节日妙不可言,像一道大红的御墙拦截住我们的视线……正午的旗帜没有阴影,正午的旗杆浓缩成一点,那高悬的徽章傲视环宇万物。
“把路引过来!”我们有十块钱就能丈量古都的白色小面的。
在公正的阳光下,我们像路畔那墨绿色松枝一样,可是人头攒动的乡民们又懂得什么呢?
一碗龙须面还是剃龙头的手艺家什?!
我有幸亲耳聆听商代的大磬和盛唐的羯鼓,我有幸沿着那灰烬之路效法殷殷龙吟和八面来风——
风箫辍吹的人,请让我的灵魂歇憩在你律动的指尖上,像蜻蜓般的小飞机停落于扑闪闪的黑睫毛……
那灰烬之路也许不宜做降落跑道,那灰烬之路通向异乡通向迅疾奔驰的地平线……
“把路引过来……”母亲们的泪比盐还重。
第二章
现在,当一切都暗下来,当一片古老大地成为收留亡魂的大墓——甚至连幽灵本身都失去了活力和生气。啊……沉寂!还有什么能比你那蝙蝠似的翅膀更锋快,更具有切割时光的魅力。(黄昏是你切下的一块祭奠的大蛋糕,还有冬日的钢铁大桥——那现代文明的黑色钢琴,如今它静卧在冰冷的河冰上),
如今它把沉思的粗糙之沙缓慢梳理。
也把丛丛枯树点燃像点亮白色烛盏。
坠落!我对你满怀空想,就像舞蹈之焰对灰烬的痛爱,就像羽衣道士在披发若风的霞霭中挥剑将烛火劈为两半。一座繁华殆尽的城市比少女的闺房还沉闷。
雨呀雨呀你为什么不愤怒?
天神地伏,龙吟虎啸。现在,当一切都暗下来,当一个青翠欲滴的红缨牧童挥起小小的皮鞭将羊群从天穹急急赶回,恶风暴起山岳崩摧。天堂之鼓在剧响,滚滚霹雳像落地雷将罪徒之心劈碎。
看哪,那黑云翻卷的老海躁动不安……
呵, 龙即闪电!
第三章
戏剧上演。在寥阔的荒漠上,一座非人间的大理石剧院夜色阑珊,
紧锣密鼓的戏剧正在上演,
在给不毛之地的黄沙看,给荒凉看,
给堆堆遗骸上的漂浮磷火看,
给直上青天的孤烟看……
今晚,那来自西方的财宝探险家远涉重洋,
他们和东方的取经朝圣者在这里相汇——
他们相互寒暄彬彬有礼的大家风范被卫星频道转播给修梯田的人们收看。
戏剧上演。这白云织成的悠悠牧场,这海市蜃楼般突现的南天门……闪电编结的帷幕多么安谧,天庭深处的仙乐搭起的化妆台多么宏阔瑰丽。抽象的美远不如具象的美,那天神之吼远不如替身演员模仿的滚滚雷吟……
远不如观众席间那目光似电的大导演!
第四章
1
仅仅因为你的双乳被覆盖,你就不是汉白玉雕就的龙泉青瓷花瓶,你就不是千年古墓中身披金缕玉衣的长眠女王。饰镜里的绿色床幔远比闺楼里的寂寞更宽松。刺绣呵,即使是双面绣也不能满足封闭的欲望。——我听见远嫁异邦的汉家公主哀伤的歌声……
这民间画家的青铜油彩!这雕塑家刻刀下石灰岩质的精品!远销海外的典故足以为夜晚堆积硫磺和火,
和黑夜的代言神——乌鸦奏响为亡灵的法号:
2
那骑马过海的豪杰,那群马渡海的壮景!
哦,马的气味。马的嘶鸣。浪花飞溅有如爱到极点的啜泣……(安静,我要你安静!)有如老海龟在沙滩上一拖千年的擦痕。星球快速旋转,显微镜下一个细胞四个精子的海洋多么浩瀚。龙啊,用你大红的绣花锦缎将摇摇晃晃的洞房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盖住吧!将整个沸腾的宇宙星体都装在你的胃里碾碎吧——
我记起了户口卡上未填注的空白和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官员们的冷漠:姓名、籍贯、成分、种族、从降生至今的简历以及
一颗星球与另一颗相撞的精确时间。
我要在海上跑旱船,我要用一吨海水一筐火苗和一捧流沙来制造受精卵——日产值八百万颗,像肥硕的白蚁王后那样埋头苦干。我要在小小的(像苍茫大地上的一颗小小眼瞳一样灵动的) 池塘里孕育大自然的神奇伟力——荷尔蒙——
情欲在隆起的青藏高原上呼啸,宛如饿狮凌空扑入羊群。
这咏叹调的月光夜,全让你占尽了。
第五章
当将军在黄昏时的大海边清洗兵器,落日与死亡达成了默契,悼歌压抑着月亮的凉唇。
“白天的战争为什么不挪进黑夜?”
“既然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就要在沙场秋点兵之后建立礼仪之邦,我们就要让汉高祖的《大风歌》传唱至今……”
猛士易失,故乡安得?猛士在花圈的顶端露出惆怅,而母亲们是失去记忆的扫墓妇……
当然,我还要建立古代的战争道德。
高声叫阵,互通姓名,主帅在城垛上观敌料阵,十万大军在白骨上扎住阵脚,
两员勇将捉对厮杀,大战二百回合不分胜负……哦,旌旗如画鼓声隆隆,这棋盘上的永恒活力需要我们凝神谛听、轻轻呼唤,那近在咫尺又远隔万里的箫声——
那季风期伟大人类最朴素的品质——留在了观望者的沉默中,仅仅因为鸣金收兵,仅仅因为不能将鏖战挪进黑夜挪进二十四史的传统风尚……
人民是青铜之剑上的磨砺之水 。
声音啊,是什么样的声音翅膀一样扑打着暮年的胸膛!
第六章
离开了一片火海的营地,守门的石狮子高昂着安详的面庞。家园啊,除了闪动烈焰的火炭之路、灰烬之路,什么能与时光的地平线对峙?而高峻山崖上站满了劫后余生的人,这生死同群的追随,总是在漫漫无尽的语言之途上沉没。
男人把凝血的战袍浸入母亲河。男人从胸腔中掏出的苍鹰,照耀着大地上的所有地方。
种族古老。我们的额头古老。从亚洲高地上一浪一浪吹来的天光,盘桓在今晚的枯骨堆……
一条满载牲畜的长河开进了老酋长的陶罐里。
而痛苦高呼的女人抓紧了河床……她双唇翕动犹如巫师念咒,分娩!黎明前的曙光是不是最开篇的神? 即使此刻发生日食,即使集善与恶于一身的接生婆展示出灵魂中蒙昧的日子……
孩子在阴影里怀着敬意说话。
第七章
当挂满勋章的光明之树在我的酣睡中轰然仆倒。呵……我梦见在梦幻的梯级上,
用自然博物馆中的恐龙化石做功课的孩子喃喃自语。他被这水面上的伟大光辉眩晕了——他暗自吃惊梦话连篇——仿佛唱诗班的童声演员看见了神的微笑……
我自己也被这首伟大诗篇震颤了。魂不守舍,这横亘大地的秘密通道——我感到气脉太短劲儿太小,我感到我像是招集象形文字的仓颉王,以高贵的身份轻俯我烟尘熏黑的额壁……啊,感激!旋律与音节的功绩,快乐劳动的主人——
你就是颂扬,就是把空酒坛抛向大海。
啊,骏马和大河穿过我的胸膛隆隆远去。我的美德我的意志我智慧的气息,像面颊上流淌着真理的奶水……
我的血液呼啸着,在比黑夜还深的睡眠中。
曙光曙光,让草绿色的曙光也沐浴着死者吧!
他们没学会生活,必须重新开始!
第八章
我在一百个童声合诵队一齐歌唱,一百条江河贯通了血脉,一百个帕瓦罗蒂站在地平线放开了喉咙,用振颤托聚太阳:啊,大陆漂移学说多么伟大!茫茫昆仑和乞力马扎罗的雪多么洁白!一百只凤凰就是一百缕青烟。在哀伤的大树下的人们,你们席地而居,仿佛微风拂过庙宇之怀的白银铃声,仿佛祭坛周围的巨钟将合唱队的大静徐徐传送……哦,天堂!天堂毁灭也只是光芒一片;地狱呈现也只是假盲人深陷的眼眶,
也只是一百个屈子九歌过的蕙草幽香缭绕。
我用诗述说过的荣光必将在诗句中得到减缓。
我用母语填注的进行曲必将得到验证!
时代的宫殿呵。我不知道你矗立的海平面苦痛的重力,我也不想倾听殿堂正中大红灯盏下的低低絮语。仿佛又一道圣谕,仿佛心灵因为长久的哭泣而坚忍的缄默。
一百只雄鸡炽烈的啼唱呵。当原野上风驰电掣的高速动车将暗夜一分为二,
当星宿之海从苍穹浇灌徜徉梦乡的村庄和城镇,当孵卵期微温的丰羽用悠悠岁月的回忆加热它的母爱……
请你把我从我的血液中解放出来吧!
用花岗岩块堆砌的莽体,用飞鹿之角奠定的法律,用雄狮之口颁布的御令,用鲤鱼之鳞镶嵌的皇袍。用如电的目光划分的疆土领地……
恢复。用烟波浩淼的水面上的碑石,用广场上合唱团的严整步伐,用花腔女歌唱家的千百只婉转之鸟,用大海那千褶万迭的绣花莽袍,用轰轰隆起的青藏高原的怀孕之腹……
诗人呵,你扬名显赫的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