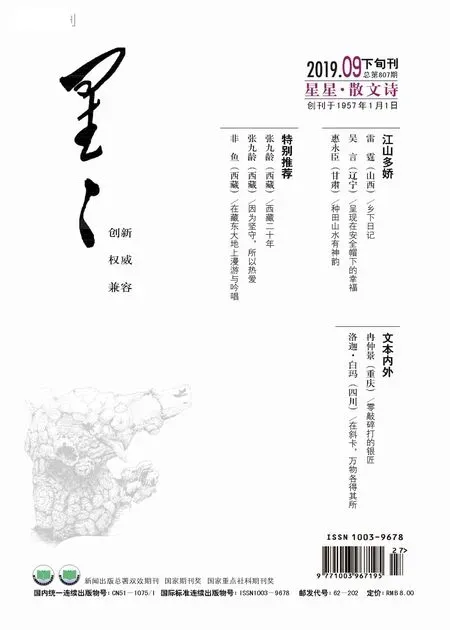呈现在安全帽下的幸福(组章)
吴 言(辽宁)
车间,车间
如果能用合同的形式按部就班地打上时光的印记,
如果能用旋转、磨损和锈蚀的形式分析青春的消失,
如果能用噪声产生方言的形式解读未来和过去,
如果能用散落灰尘的形式填写人生的履历。
那劳动服留下的汗渍对得起工人的称呼;
一次次俯下的身躯对得起工人的称呼;
用扳手创造的奇迹对得起工人的称呼。
此刻,我自己已经不属于自己。
机器喷涌的呐喊,随时将微弱的听觉占据。
此刻,车间已经不是车间。
它是熔炉的胃在不停歇地肢解白天和黑夜的美丽,而我愿成为其中流程里的一个数据。
大机车
向前,向前,在奔跑中获得无限的蔚蓝,我完全沉醉于一瞬间的魅力,还有那惊艳了春天的画卷。
庄稼、房屋和山林,与一种醒着的冲动无关。向左一转,是红尘苦旅;向右一转,是面朝故乡。
一声尖叫,不知经历了几度夏雨寒霜;
一窗入梦,置换了几次皎洁的月光;
一路勾勒的恋歌,领着我见识了芸芸众生的绵延。
小车站,连同三三两两的乡亲,依旧没能隐去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一步之遥的风声袭来,仅有云峰在向远方挥手。
搬运工
我总是喜欢搬运时光沉甸甸的模样,从清晨到黄昏,直到空无一物。招摇的身姿,挥动的手臂连同一抖一落的风,走神儿的疲惫在休息时悄悄抵达。我在影子略显清瘦时,走出厂房。
当我不停地搬运钢铁、水泥和货箱,像一次次搬运着种子、阳光和希望。一双手套,接近着生锈了的昨天、半截的泥块和被企业转型造就的精品。小时候为了听老爷爷讲故事,我还搬过凳子,长大以后,还搬过成箱的啤酒,以及将别人的梦搬进自己的梦里……
也许,有一天我搬不动了,那一定是因为,我把自己搬空了。
铁在烧
在工厂中,铁像片膏药,透过烧焦的月色和生动的粗话,呈现安全帽下幸福的红润。
铁丝,铁锈,铁屑,铁水。会安睡,也会剥落,会怀孕,也会变形,每一次与火焰相亲都是一次新的爱恋,每一次与机器相认都是一次新的生命返工。
铁与铁拥抱,从来都是火花四溅;
铁与铁拐弯,挤窄了车间的宁静;
铁与铁卷曲,闪闪发亮成为梦的豁口。
铁,在撒欢地燃烧,在延伸的过程中燃烧,在不知所措地燃烧,在我心里燃烧,在无休无止的流水线上搁浅,直至灵魂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