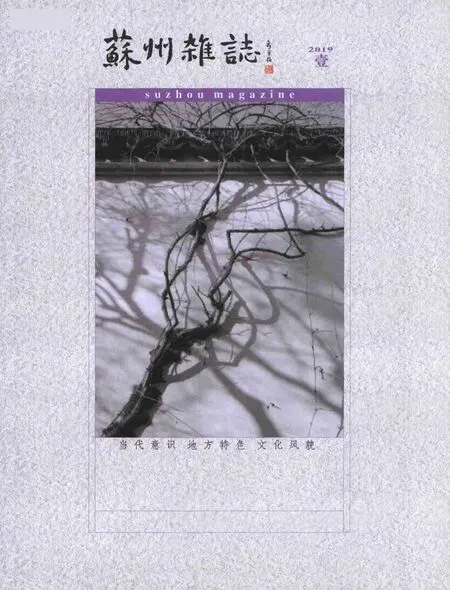不舍:总还是要离别
——忆范先生
陈国安
我在1991年时读大学,第一次全院学生大会在校门口的大礼堂。大会讲话的系主任是范先生,我们的老师说,这是小范先生,前任再前任的系主任是老范先生。
第一次见到老范先生是深秋的一个午后。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吴培华和曹惠民老师带着我们读现代文学名著并教我们做小说概括。我那时是学习委员,这是第一个学习兴趣小组,我也就是成员了。教我们现代文学的是吴培华老师,那天正是他在给我们讲巴金的《家》。他以《家》为例教我们怎么样写情节梗概,如何把可能用得着的原文摘录下来做成卡片。那天吴老师正讲着时,教研室门被推开了,吴曹二师站了起来。我因为背向门,不知何事,一转头,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二师几乎齐声招呼道:范老师。我知道,这就是老范先生:范伯群老师。
范老师人很高大,西服领带,头发花白,嘴角微翘,架一副那时很流行的细框眼镜。虽然,吴曹二师那时上课也是西装革履领带整齐的,但范先生一出现,真的,脑中一下子关于大学教授的形象就瞬间定格了。范先生笑着说:“你们在上课啊,你们继续。”然后就退出去了,吴曹二师说着:“课外小组活动,没事的没事的!”跟着追了出去。他们在老文科楼的走廊上说着话,我们在木地板的老文科楼的房间里静静地等着。一会儿,吴老师先进来了,曹老师继续跟范先生说话。吴老师便向我们介绍起范先生来了,当时我们文学史课在讲鲁迅,于是就从范曾(华鹏)二位先生的《鲁迅小说新论》开始,一直讲到他参加的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吴老师说,现在范先生已经不做系主任了,也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只教现代文学研究生的课。刚才就是约了博士生来教研室谈话,现在地点冲突,范先生只能去资料室和研究生谈话了。我想,好遗憾啊!听不到范先生的课了。
年轻的日子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已经大四了。中文系变成了文学院,突然改革了大四的课程。学院的名教授在大四上学期组团给我们做专题系列讲座为一门课:“名家专讲”(似乎这门课也就开过我们这一届),阵容很庞大,没给我们开过课的严迪昌、吴企明、孙景尧和范培松(小范先生)诸位先生,我们都是在这一门课中得以聆听教诲的。范先生当然也在其中!范先生来讲的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体研究。我们一下子觉得很新鲜。范先生上课的时候有个口头禅很令大家注意:“这个,这个……”而我印象最深的是,范先生课上一再说到:“研究要关注那些被遮蔽的对象,其实有时也许很有价值。”这句话我是一直牢记在心上的。
记得范先生来讲了三次课,每次课三节。都是下午的课,最后一次课,下课的时候,从新教学楼出来,正好和范先生一起下楼,我竟也壮壮胆子上去问了三个傻问题:古代的通俗小说就是古代白话小说吗?《红楼梦》是清代的通俗小说吗?是不是只有通俗小说从明清到现代写法和思想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想想还是觉得那时的问题好傻,所以已经完全不记得范先生是怎么说的了,只清晰地记得陪着范先生一直走到刚修建好的存菊堂门口,才道了一声“谢谢”而转头回宿舍的。后来,我留校了,范先生到办公室来时看见我还说过,你们班最后一次课就你还问了问题的呢。其实我自己知道那次就是有点假装,实际是纯粹为了避免一路从三楼与范先生下来默不作声的一种紧张和尴尬。那次我俩走在最后,范先生收拾带来上课用的书比较慢,我又习惯性地走在最后。
我留校之后先在院办公室做科研秘书,于是工作中不断与研究生导师们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记得不止一次去过北校门外的范先生家里,而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去拿博士生的作业。当时博士生就很少,范先生同一年就招了八位,其实共同指导的有曾徐(斯年)二先生。当时指导研究生就是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式,这种方式即使现在看来也是挺好的。院里基本是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才会去统计成绩与学分,除了入学时填一些表格之外,科研秘书对研究生的工作几乎就是发放一些资料复印单。大概那时觉得现在是文学院了吧,一切都该有些变化,要正规起来了。于是研究生的作业要按实际课程的学期提交并统计成绩,这是个新举措,催交作业也就成了我的事情。一般脱产在读的研究生补起作业来比较容易,而在职攻读学位的老师补交作业真是很困难。那时通讯只有寄信,作业也都是手写版,没有打印稿。在学院规定时间之内没有提交作业的研究生就要被学院张榜公布,范先生的研究生多是外地在职的,因此张榜出来就成了问题。张榜之后大概第四天,接到范先生电话,让我去他府上一趟。
那天午后,敲开范先生家门时他已经在等着了。进入书房,范先生给了我一杯茶,让我坐下来。然后转身在堆满书的一个三人沙发上拿出一个很大的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叠不同稿纸的作业,递给我一张他手书的清单,一边指着一位博士生的名字一边把几份作业放到我的手上,一份一份地交代课程名称,语调没有什么起伏,像是账房先生在报账。好一会儿,总算结束了。我一直在收作业,茶也没喝,既然收完,站起来就要告辞了。范先生摆摆手,让我坐下,喝口茶。我想不喝一下茶好像很不礼貌了,便把作业塞回大信封中——连同那张清单——放了下来,端茶浅饮。同时,耳边,范先生的声音响起来了,大概是:小陈啊,你刚参加工作吧?我本该把作业交到系里来的,这些天实在太忙了,在赶稿子,所以麻烦你来取一下了。(我说,没事的,应该的。)听说系里公布了没交作业的学生名单和导师名字,我是最多的吧?学生的作业早就交来了,我忙起来就忘记了。(我这时候很尴尬了,没说话。)(范先生停顿了一会儿,我也没敢再喝茶。)以后再有类似的通知,小陈啊,提前电话告诉我一下,好吧?以免我弄得很尴尬哦。(一番话,我听得尴尬到不知道如何解释了,因为我只是个具体办事的小卒子哎。)当然啦,你刚工作还不太知道,只是照章听命,将来一定会工作得更好的……
那天,我不知道怎么从范先生家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回到办公室的,更不知道我怎么去院会议室门口把那张“榜”揭去撕掉了的。总之,我很内疚,但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时真的很年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忘了这次内疚。见到范先生时还是那样地说笑几句。
我从办公室转到教研室,就不常去院里了,除了上课。我开始过上闲云野鹤的日子时,文学院已经从本部维格堂搬到东区凌云楼十楼了。见到范先生的次数就少了。
凌云楼十楼,一个傍晚,我上完最后一节课,去院里看看有没人在,想坐一会儿再回家。那是个深秋,天黑得早,十楼黑乎乎的。走廊上一两盏灯像倦恹恹欲眠人的眼。我就折返回电梯间等电梯。另一头走来一个人,啊?范先生!赶紧走上前去打招呼。他手里拎了一扎书,笑着问:“这么晚?”我说:“今天最后一节课刚上完。”我要帮他拎书进电梯,他坚决不要,说:“把放在教研室的几本书拿回去了,我退休了。”我一下子愕然在他旁边了。我没有敢看说这句话的范先生脸上的神情。电梯很慢地到了一楼,出奇的慢。
凌云楼下,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分别的。但是,那天,范先生对这个校园不舍的情绪我至今难以忘去。他上了一辆车离开了。我也骑自行车回里河新村的家去了。
后来,听说从苏州大学退休的范先生被母校复旦大学聘去做教授了。苏大校园里就绝少见到范先生了。
还是深秋,也是傍晚,我回家,在里河新村的菜市场旁边,竟然看到了熟悉的范先生。赶紧上前打招呼。站在我们家楼下聊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范先生已经搬到里河新村居住了,和我是同村村民了。范先生不常住上海了。
大概也就是偶遇范先生之后的一周吧,上午十点多些,我刚起来,就听到有人在揿门铃,一问,竟然是范先生。赶紧开门往楼下迎去。我住四楼,走到二楼,就已经接到范先生了。到我书房里聊天。
范先生那时正准备整理姚鹓鶵的集子。姚氏的外孙曾出钱请人整理旧体文学作品,而诗词集整理得又不如人意。范先生那天带来姚氏诗词集两册(《姚鹓鶵诗词集》和《姚鹓鶵诗续集》),让我也读读姚氏的旧体诗词,看看能否写篇姚氏的旧体诗词的研究论文。(后来我虽然写好了,但总觉得不太满意,就没敢给范先生审阅,他也没再催过我。再后来电脑坏过,也没有备份的,如今一想到便很是难为情。)然后就聊起了姚氏的一部小说《江左十年目睹记》,也就是《龙套人语》,我说我读过的,家里有的,就从书架上找到拿出来了。(后来,我到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时选题“南社旧体文学研究”大概也始于这一次的聊天。)接着就聊晚近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了,范先生很会讲掌故,我也听得入神。一直到内子喊吃午饭,才发觉,时间很长了,已经正午了。于是请范先生留下便饭,范先生很率性地答应了。我知道范先生是喝红酒的,家里也有,就提议开一瓶红酒。范先生说:好的。我们三人边吃边聊,红酒半瓶,一直吃到下午一点半过些才结束。
有了这次,我跟范先生的来往就多起来了。有时他到我们楼下小公园散步会按门铃上来坐坐喝杯茶聊会儿天,有时会打个电话让我去市图书馆复印一本书,有时会让我送一本他要用的书,(譬如有一本关于词谱词牌的词典现在应该还在范先生的书架上呢。)有时我会去范先生家坐坐聊聊天。有段时间我常闻着范先生家“五色汤”(五种颜色的蔬果一起煮汤,他说是章培恒先生教他的秘方)的特殊味道,在他书房兼卧室靠阳台的门口坐着喝茶聊天。后来范先生还在我们家吃过一顿午饭,这次他还表扬了做菜已经略有样子的内子的厨艺呢。我们两个小辈都很开心,我猜范先生也很愉快的,一直笑眯眯的……
我从里河新村搬出来前,特地去了范先生家一趟,告诉他我要搬到园区新校区附近去了,有事请他照样电话给我。那次我给他带去了两瓶红酒,他看看说,现在已经不喝红酒了。我知道之前他是常喝点红酒软化血管的。那次,我觉得范先生真的有点老了。
搬到园区,我与范先生的见面就少了,记得似乎只去看过他两次。其中一次,聊的是我说受到他“两翼说”的启发,提出语文教育白话文和文言文系统的教育之两翼不可或缺,书面语和口语教育之两翼不可偏废,雅言和俗语教育之两翼不能不兼顾,传统和现代文化之两翼不能不贯通,总之是:语文教育要寻找回另一翼,要两翼齐飞。他笑得可厉害了,几乎有点往后仰过去的样子了,对我说:这就是触类旁通吗?我也大笑了起来。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窗外暖暖的落日斜斜地射到屋内,范先生脸上泛出一种特殊的光芒,温润而慈祥,我至今不能忘却。
后来越来越忙,范先生那里就没去过。
去年冬天,一个早晨,在往相城的苏州大学实验学校的上班路上,翻看微信空间。突然看到祥安老师发了一串流泪的符号,很奇怪,就微信发了三个问号。祥安老师回复说:范先生走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电话过去了。一切才知道。
我是之前一点消息也没有的,所以很震惊。总觉得范先生很健康,他自己也很注意的。没想到范先生离开的日子就突然到了面前。一下子,泪往下淌着也不知道。
下午,和内子去了范先生家,吊唁。范先生家,我们坐着聊天的那椅子静静地还在那,范先生已经离开了。
第二天,在学校,文学界四处发来的挽联。
第三天,一早,去殡仪馆,悬挂写好的那些挽联。
与范先生告别的那天,很冷,初冬。朔风已起,树梢头的叶子飘飘然而下,无论多么的——不舍——总还是要离别了。
范先生离开已经一年了,虽然一直在读他签名给我的著作,但我是说不出什么来的,所受到的启发及其他粗浅的感想也在跟他聊天时都说过了。现在眼前时不时地浮现出的就是跟范先生这些点滴的如跟邻家长者交往一样的画面。在这样的冬天,一经想起,便有一种温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