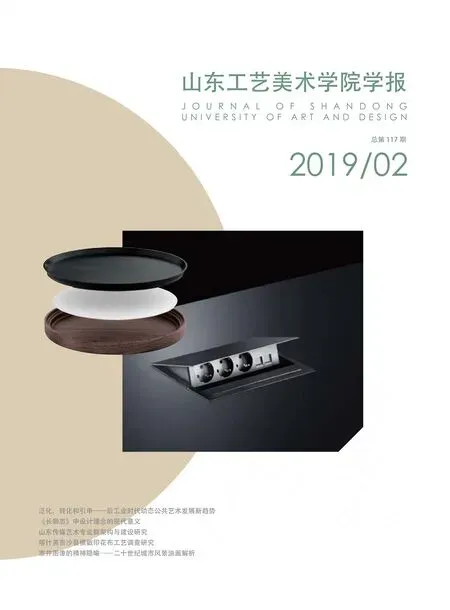市井图像的精神隐喻
——二十世纪城市风景油画解析
刘玉涛
城市风景油画在二十世纪的具象绘画体系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以现代化为体现形式,进而展现为都市化。城市生活也成为越来越多的当代人共有的生命印记、情感之源。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油画艺术已经历着视觉经验从自然形态向人工形态的深刻转变。油画尤其是具象油画在二十世纪的历程可谓筚路蓝缕,但仍然涌现了许多伟大的画家,他们中不少人都创作过优秀的城市风景。二十世纪的城市风景油画继承了风景油画的悠久传统,也呈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它像一面镜子,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二十世纪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深刻解析了人们在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中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这些都使得城市风景绘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城市风景油画的历史及内涵
十七世纪富足而自由的荷兰人首先使风景摆脱了人物背景的卑微角色,赋予它独立的审美价值。从此,风景画就一直是西方绘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起,风景画就分为以自然风光为题材和以人造环境为题材的两个大类。它们分别承载了人类对待其所生存环境的不同情感。自然风光的描绘歌颂了造物的神奇与伟大,在优美的田园风光中人们又找到了浪漫的温情以及对我们这个物种漫长的过往的回忆和依恋。而在大自然狂暴的威力面前人类显得渺小而谦卑,充满敬畏。而城市风景的描绘则颂扬了人的力量,人类按照自己的需求改造环境的期望和成就,人的法则、人的力量在城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高耸的塔楼和宏大的建筑院落都展现着人征服自然的自豪和骄傲。进入二十世纪后,城市风景画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感和审美表达。这就是过分发达的城市和城市生活给人造成的束缚感和压迫感、失落感和焦虑感,以及人性在这种束缚和压迫下的挣扎与反抗。所以说城市题材绘画在人类复杂情感的表达方面已全面超越自然风景题材绘画,展现出更为丰富、完整的情感表达和更为直接、现实的人文关怀。
2.常见画面元素的隐喻性
城市本质上是一堆冰冷坚硬的石头和钢筋水泥。这些材料既无生命也无情感。现代建筑在外形上更多的是简单的几何线条。要在这些枯燥、单调的无机线性中传达人的情感、人的思考就需要画家把自己的情感和思考投射到这些冷漠的景物中。亦即“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中的著名说法“情感误置”,是指将人类的情感归结到非人的题材尤其是风景的元素之中。”[1]因此,城市风景绘画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形象语汇,许多元素都有着复杂的隐喻和象征。
2.1 空间
风景画首要的是空间,所有的景物都必须在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空间有物理的,也有心理的。物理的空间,在西方绘画的传统里,被想象成物体的立体框架般的静止媒介。而心理的空间,心理上的“远”更是一种境界与诗意的传达!空间的开阔与狭窄、通达与纡回、连贯与跌宕在心理上会有完全不同的情感表达。
美国画家霍珀的作品《夕阳下的铁路》,展现了城市风景油画的一种典型的空间处理。画中前景水平的铁路和小楼隔断了我们的视线,形成了浅近的前景。远景则是空旷辽远的天空。这里“那创制于迫使我们在就近的边缘猝然止步的单薄前景,与从那里开始沉思更易为情感而非双脚靠近的开阔的远景空间之间。”[2]暗示了城市人肉体的被约束禁锢和精神上对自由的渴望。
另一种典型的例子可以在西班牙画家洛佩斯的作品中见到。从高处的观察点一览无余地远眺整个城市,空间开阔、深远、毫无遮拦。观者仿佛凌驾于庞大的城市之上,冷静旁观“以准宗教的沉静沉思着自然最平凡无奇的日常剧的神秘”。[3]
2.2 高大建筑
城市中的教堂、楼宇、高塔、烟囱等高大的建筑容易吸引人们的视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往往是城市的地标,在构图中能够提供风景画中较为缺乏的垂直线,往往能够统治一大片的空间,因而经常成为城市风景油画的主题。高大建筑因为在工程上投入技术和财力较高,一般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是人类财富、技术、意志的集中体现。法国画家郁特里罗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圣心大教堂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郁特里罗画中的圣心教堂是一座白色的圆顶罗马式大教堂。他的圆顶经常出现在远景树丛、屋顶的上方。它那挺拔尖耸的穹顶像一座纪念碑直指苍穹,代表了地上的一切造物对上帝的归属和向往。同时他又像是坚定的保护者,给那些在寒冷和迷惘中游荡的人们一个可靠的支撑。而正面全身“出镜”的巴黎圣母院则体现出了庄严、和谐的秩序之美。
2.3 人群(或无人)
城市是建筑、街道的聚合体。街道就是人群上演活剧的舞台。城市风景中的人往往会被看作是“我”的投射。而人群就是人的倍数,他们自己的倍数。在城市中熙来攘往的人群就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灵魂。他们代表了城市的活力,代表了繁琐而意味深长的日常生活。二十世纪以来的绘画里,人群更多地被表现为群体的特性、盲从的特性,而很难是十五、十六世纪绘画里那样是每一个个体,是个体的集中。因此人群也隐喻了重复和麻木,平凡和卑微。另一方面,完全没有人的街道和城市是描绘人群的另一种极端形式。现代城市随意的一瞥,视线都会撞见或多或少的人,完全没有人的城市必定是画家可以为之。用人的刻意缺席来强调建筑的牢固和恒定,更加凸显了城市的每个个体的忽视和抑制。空洞的街道、令人目眩的光线增强了人们心中的孤独和无助感,是对压抑、异化人的现代化生活的无声控诉!
此外,道路和桥梁往往为画面的构图提供了长长的结构线,加强了画面的空间透视感,暗示了强大的离心力、向心力,因此会给人超越、渡过、脱离等等心理上的暗示。灯光、阳光给人温暖、希望、信仰的暗示。树木会打破建筑无机线形的枯燥乏味,给画面带来生动有趣的斜线、曲线,它们暗示了对自由的向往、对束缚的抗争。当然,单一元素象征意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多种元素的组合所营造的情景意象也会更加完整、清晰。
3.城市风景油画的不同语境类型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高速发展,全面进入了现代化阶段。新的社会生活带来新的生命体验,新的精神意象催生新的艺术表现手段。二十世纪人们面对全新的城市生活,对反应和态度变得更为复杂,相应的二十世纪城市风景油画的意象表达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
(1)闲适亲切:城市的发展首先带给人们的是清洁、高效、安全、富足。这一切似乎是人们长久以来所渴望和追求的理想生活环境。便利的城市会给人们带来闲适、亲切、温情的内心感受。夏加尔笔下的巴黎正是这种内心感受的艺术形象化。那里色彩斑斓、线条柔和、光线清透。城市的描绘并不是具体、客观的真实写照,而经常是在画面的下方符号式的简略的一片建筑,象征性地表明画面主体人物所处的位置。这里的巴黎只是一个温馨、浪漫、平静的理想城市的象征,是爱与乡愁发生的地方。同样郁特里罗的画里仍是巴黎。但郁特里罗画里的巴黎多了一些陈旧、杂乱,多了一些为生计所困的忧愁和烦恼。但是他爱着那里,那是他出生并长大的地方,那些水泥的电线杆、斑驳的砖墙、修剪过的行道树等等都是他的童年记忆,融入他的生命,如同家人一样亲切而随意。
(2)宏大壮丽:城市的高度发展体现在城市体积的不断扩张,也体现在城市建筑高度的增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二十世纪的城市都达到了空前的广大、空前的繁荣、空前的复杂和拥挤。洛佩斯的马德里全景肖像从远处俯瞰全城,城市的恢弘和复杂展现无遗。洛佩斯在马德里生活了四五十年,他“看着它扩大了四五倍。他熟悉并热爱那些保存着历史遗迹的旧街市,也对楼群林立的新街区感到陌生、新奇,甚至振奋。时间的流逝、日月的临照和社会活动,把自然景物与人为建设、新与旧、今与昔、内与外、地下与天上……都谱入一首结构宏伟、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城市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旋律。”[4]人类正在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地球的面貌。这些人造的漫无边际的立方体与无机线条在夕阳下静静伫立,恍如超越时空。
(3)冷漠、压抑: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血脉联系,人被局限在社会化的生产环节中,被异化为社会机器的零件。渺小的个体的人在宏大刻板的城市里,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感到茫然和寂寥。这与城市的繁华喧嚣无关,即使身处人群也难以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甚至会被外界的浮华映衬得更加深刻。美国画家霍珀的作品中这种冷漠与压抑感被表达得非常充分而真切。荒凉的城市边缘、无人的车站剧院,孤独感如影随形,无处不在。这种孤独并不是美国人独有的,而最终是人本身、“现代人”本身所共有。霍珀深刻洞悉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悲剧性,揭示了其生存困境和心理压力。庞大的城市使他们都成为了大世界里的小人物,挣扎在不足道的最下层。冷漠的人在一起只是形成了“陌生的群体”,他们彼此相交集,又相互隔离,表面常来往,而实际不兼容。每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个人又身处边缘。霍珀特有的生涩的色彩、僵直的笔触、迷离的光影都能打开现代人坚硬的盔甲,直达心灵深处的隐秘伤痛。
二十世纪以来,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集中了人类的先进科技和物质财富,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和困扰。城市发展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城市来解决。不论愿不愿意,我们都已离不开城市生活。城市也正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意象象征成为绘画的主题,丰富了现代绘画的心理诉求、人文关怀和技术语言。
注释:
[1]库克,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现代画家>约翰·罗斯金作品第五卷》,伦敦,1904年,第201-220页。
[2]罗伯特·罗森布卢姆:《现代绘画与北方浪漫主义传统》,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3]同[2],第15页。
[4]啸声:《20世纪欧美具象艺术—洛佩斯》,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