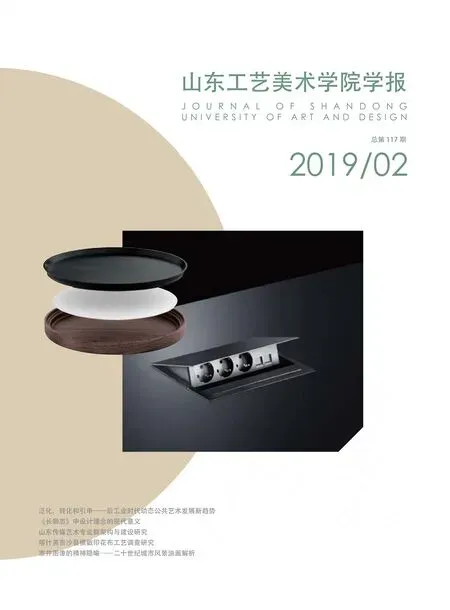近代上海土山湾工艺院中的工艺教育浅析
吴嘉祺
明清之际,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成为了西方美术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西方的工艺品与工艺技术也大量地传入中国,逐渐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术与生产方式。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更便于传播西方的宗教观念,部分传教士开始在中国设立教授西方工艺的机构。这其中,建在上海土山湾的工艺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
土山湾孤儿院创始于清咸丰五年(1855),由天主教教士薛孔昭设立于青浦县的横塘,继而迁至上海西乡之蔡家湾。同治三年(1864),又从董家渡迁至沪西徐家汇土山湾,即今之蒲西路448号。随后孤儿院的事业逐渐扩充,并添设了工艺院。工艺院的建立不仅为了训练孤儿学习现代工艺之用,而且使孤儿长大成人后,可以有工作谋生的一技之长。
土山湾工艺院,又称土山湾画馆,主要是由范廷佐修士和郎怀仁主教创办。范廷佐(1817-1856)是西班牙人,年轻时到罗马学习艺术,加入了耶稣会。1847年,他被派到上海进行传教。随后,在郎怀仁主教的支持下,开办了一所美术学校,专门培养中国人从事天主教绘画与雕刻,以便更好地进行传教。1856年范廷佐去世之后,就由他的中国门生陆伯都(1836-1880)接着主持美术学校的工作。直到1864年,美术学校并入了土山湾孤儿院,从此美术学校就转变成了艺术工场。最初的美术学校只有绘画和雕塑两个工场,在并入孤儿院后,又添设了印刷工场和木作工场,这样土山湾孤儿院的工艺院才初具规模。下文主要论述土山湾工艺院在工艺教学方面的三个突出特点。
1.系统的培养模式
虽然与现代设计教育相比,土山湾工艺院的整体教学结构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教学内容也比较粗浅。但作为我国近代工艺教育的雏形,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工艺教育的发展。工艺院最初的目的就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开设,具有“教而兼养”的功能。所以工艺院最初招收的学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来自于孤儿院所收养的孩子;另一部分是来自于贫寒人家,为了谋求生路而来。这些进入工艺院学习的孩子男生女生都有,“年龄最小者七八岁,以能自衣食不需人扶助者为合格,大者达弱冠以上。”[1]也就是说那时进入工艺院学习的儿童,至少也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儿童入学年龄,这也符合儿童身心发育的基本规律。而且也并不是一进入工艺院就开始学习各种专业技术,首先是令儿童先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至少要粗通文字,然后才可以进入正式的工艺学习阶段。“初入内之儿童先令识字。俟其粗解文义,乃使之入工场学习技艺。”[2]掌握基本文化知识这一阶段的学习,是在由土山湾孤儿院所开办的“慈云小学”中完成的。整个小学分为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实习班二年。并且在“高级小学期,即遣至各工场稍稍学习,以窥察学童之个性。”[3]使学生能够对于工艺技巧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也可以顺便观察不同学生的专业兴趣,为以后选择的具体的工艺场作准备。而一旦达到了“粗解文义”的程度以后,“必视其性之所近,而为之选定科目也”。[4]这里所说的科目,即是土山湾工艺院中所开设的各种工艺课程。也就是说,在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这批学生就会进入土山湾工艺院所开设的工艺训练班,进行为期两年的工艺训练课程。通过这两年学习,最终是为了“使孤儿们于学业上,具有初中程度,工艺上获得灵巧之手腕”。使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还为以后进入工艺场进行更加专业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工艺基础。这个两年的训练班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初中阶段,当然,在土山湾工艺院中,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大量的工艺训练课,这一阶段也起到了很好的衔接作用。在完成了两年的工艺训练班学习之后,为了使这些学生在日后身处社会能有谋生的能力,管理他们的修士将会视孤儿的天赋和才能不同,以及他们各自性情的特点,分派到不同的工场(如图2),学习专门技艺,这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工场共分五大部:图画部、印刷部、发行部、木器部、铜器部。每部有一位富有经验的修士担任管理,“使孤儿于良好环境中,发展其身心之德能,凡上课游戏、饮食休息,均有规定时间。”[5]通过在工场不同部门中的学习,学生可以学到更加专业的技能。土山湾工艺院这样一种较为系统的培养模式,按照儿童身心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培养其专业的实践能力,使其毕业后的学生都能自食其力。
2.专业的教学方法
在从“慈云小学”毕业后,学生就会进入专门的工艺训练班,其中的主要教学内容,我们根据当时的资料记载可以了解:“孤儿高小毕业后,继以两年之初步工艺训练,半工半读,上午七时至九时,上国语、代数、物理、化学、地理、外国语等课,下午一时至三时,上修身、打样等科,每日除上课外,其余在工艺训练所实习雕刻、木工、铁工、机械等工艺。”[6]这个阶段的学业,每天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是花在理论课程的学习上,而更大一部分的时间则是用来实践专业的工艺技能,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阶段。从这个阶段的工艺课程的安排可以看出,因为还是最基础的技能学习,所以课程的内容范围较广,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工艺领域。这样一种基本功的训练,能够为后一阶段的分科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完成了两年工艺训练班的学业后,就将进入专门的工艺场学习。工场的教学采用的是突出实践,并辅以理论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除了每天九小时的工作之外,晚上还有夜课,“仍继续授以应用之基本知识,如公民、经济、史地、簿记、外国语等;务使学成后,不惟有工作之技能,更有充分之国民常识与道德基础,而于劳动界中,可为模范工人。”[7]可见当时土山湾工艺院的这种教学方法,已经跟现代的一些艺术设计教育理念相吻合。不是一味技能传授,也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工艺教育和设计教育的发展。
工场共分五大部:图画部、印刷部、发行部、木器部、铜器部。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图画部了。图画部对于我国近代西画的启蒙教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近代美术史上著名的人物周湘、张聿光、徐咏青、张充仁等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所以徐悲鸿先生曾说这里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虽有过誉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山湾画馆对我国西画发展的重要意义。图画部的教学,先从学习铅笔画开始,然后是水彩画,最后再学油画,遵循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而且所有的教学都是以写生为主,这与我国传统的以临画为主的教学模式有很大的不同。1938年曾经在土山湾画馆学艺的忻百忍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先学习用铅笔画画线条,石膏像写生、临摹、速写。再画水彩,加深练习。三四年以后学习油画,画教会里的圣像、画圣母玛利亚。”[8]这种从素描开始的教学方式,与当今艺术院校美术专业的培养模式非常相似。在教学过程中,土山湾画馆还出版了一系列的绘画书籍作为学生的教材,从中可以看出,其教学过程规范而严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图画部绘制的五彩玻璃,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首创。“先以彩画施于素玻璃上,入窑烧之,其色即永不脱落,嵌入窗中透明而有色彩,仿佛如一幅图画也。”[9]土山湾出品的彩色玻璃特别受洋人的欢迎,所以多售于洋人。上海的各大教堂装饰门窗所用的彩色玻璃,也都是由土山湾工艺院所绘制。
3.大量的实践机会
工场中的另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印刷部,是我国最早引进国外先进的石印、珂罗版、照相铜锌版的印刷机构,比商务印书馆还早了几十年。其间有铸字间、排字房、机器间、石印处、照相房,凡关于印刷上所要用到的器具、设备都非常的完善。并且每部均有一名主任进行管理,而以在印刷部学习的学生作为他们的助手,所以这些先进印刷机器都成了学生实践的重要场所。印刷品的种类繁多,“如中西书籍、杂志、月刊、学校简章、文凭、公司商店发票、收据、信封、名片、医学说明书等”[10]应有尽有。印刷部下属还有发行部,专门负责书籍的装订与发行。“凡装订书籍,中式线订、西式布包、皮包,力求精工,式样新巧。书面金字,非常美观,字体、颜色可任凭选择。”[11]可见当时的印刷部拥有着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这样就能够为学生提供最全面的实习机会。学生在里面不仅能够学会这些先进设备的使用方法,而且还可以逐渐掌握编辑设计的基本原理,包括编排、字体等重要的设计手法。在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的训练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必然能够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工艺以及设计发展的生力军。
而木器部主要负责“制造中西木器,学校家庭用具,及儿童玩具等,雕刻各式立体像、人物、鸟兽、金银彩绘、油漆器具,色色俱全。所制各体石膏像,惟妙惟肖。该部有数种雕刻之世界名塔教堂,曾得罗马、巴黎、南洋展览会之奖章。”[12]并且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先由打样间设计好图纸,然后再交给工场进行制造。“每制一器必先令打样间绘成精密之图样,然后交由木工场依样制造,此则与中国木工不同也。”[13]这也正符合现代工业,设计与制作分离的要求。也正是这种西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对我国近代的工业发展与设计教育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还有一个铜器部,分铜器、银器、电镀、铁工、翻沙、机械等工程。铜器部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小到酒杯酒壶,大到病车手术台,都可以在工艺场中生产。学生在其中实习,就能够得到大量的生产实践机会,能够接触到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工艺,为以后走上社会,谋求一份职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这些由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现代工艺技术,以及提倡的工艺教育,在客观上影响了我国近代工艺设计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萌芽。在土山湾有过求学经历的学子在毕业之后或自己成为了设计师,或又培养了一批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设计人才。如徐咏青的学生杭稚英、何逸梅、金梅生、戈湘岚等都是民国时期月份牌广告画最重要的设计师。而张聿光除了自己从事舞台美术设计以外,还培养了张光宇这位在中国近代设计史上也非常重要的设计大师。所以说,正是由于土山湾工艺院中的这种专业的教学内容、先进的教学理念,才使得从土山湾走出来的一大批学生,成为了我国近代设计事业和设计教育事业的先驱。土山湾工艺院也成为了我国近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发端。
注释:
[1]《参观土山湾工艺局纪要》,《申报》,1917年7月11日,第11版。
[2]同上。
[3]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编:《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概况》,1944年。
[4]同 [1]。
[5]同 [3]。
[6]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编:《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一览》,1945年1月。
[7]同 [3]。
[8]转引自高蓓:《土山湾孤儿院美术工场研究》,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3页。
[9]同 [1]。
[10]同 [6]。
[11]同 [6]。
[12]同 [3]。
[13]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