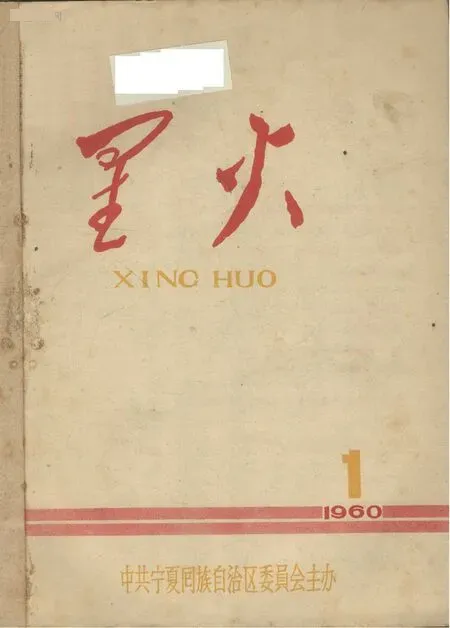孤独者黄金明
○陈培浩

不知不觉,认识黄金明已逾十年。依稀记得,十几年前某天晚上突然接一电话,说是广州的一班作家来,有某某,某某,都是熟人,过来唱歌云云。素不喜K歌社交,但有朋自远方来,心情复杂前往。在灯光昏暗的包厢,震耳欲聋的歌声,觥筹交错的场景,习惯性游离。当我深陷在角落沙发上听着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们动听或不那么动听的歌声时,突然发现了像我一样蜷缩在角落里的黄金明。毫无疑问,他也是这个场合的游离者。喧嚣的环境像一个筛子一样把两粒孤独的石砾筛选出来,我们谈到了对这种过分吵闹环境的不适感,调侃了现代人用透支身体的方式挣钱,又用透支身体的方式花钱的生存,也谈到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必须说,在那个场合中,孤独者黄金明拯救了我那无聊的二三小时。我们在包厢里震耳欲聋的重金属声音中倔强地用自己微弱的声音对话,因一个同类的存在仿佛获得了对抗世界的一个支点。必须承认,正是那个晚上,使我始终对黄金明谬托知己。后来,读黄金明的诗、散文、小说,不少也写了评论。这似乎是一段文学友谊写了主标题后自然而然的下文。
如果问我,黄金明是个什么人?我会说,黄金明是个孤独者。孤独感很多人有,但孤独者并非人皆可为。在我看来,所谓孤独者不仅是感受到孤独的人,而是把孤独提炼为一种生存方式,借以瞭望人和世界内在经验的人。灯红酒绿、滚滚红尘中顺流而下、如鱼得水的人断不可能是孤独者。但不妨碍很多感受到孤独的人依然选择顺流而下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孤独者,孤独是一种疏离主流、逆流而行的生活方式。唯有孤独者才能成为智者。你若读黄金明的《洞穴》,读到那个不断挖洞,并不断深陷其中的挖掘者,“蓝天越来越远,那个洞穴似永无穷尽之日”时,必会感受到他那种充满哲思的存在主义式的孤独。
这个越来越高速越来越亮丽的世界对孤独者的馈赠常常是失语症。孤独者之所以孤独,常常就在于现实中思想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他们认同的观点很难获得传播的媒介。所以孤独者索性就拒绝说话。这是黄金明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大抵孤独者都讨厌自己成为滔滔不绝的饶舌者,为世界增加一堆没有意义的噪音。不过,孤独者绝非真正的失语者。真正的孤独者始终倔强地在自己的频道上发出声音,寻找知音。所以,假如环境合适,我们便会看到一个音量巨大、滔滔雄辩的黄金明。每逢笔会等文学活动,交流从正式的会场转换到私下的三五成群,话题也从或正襟危坐的正题或驳杂游离的调侃转为文学自由谈时,他的博学,他的雄辩,他的高亢,他那雄兵百万于胸的自信和思想寸土不让的坚守便自然化为平时不可见的手舞足蹈、脸红脖子粗的另一个黄金明。
黄金明是多变的。多变来自于内在的丰富性。当我因为《洞穴》《会议记录》《木头记》等优秀诗篇而以为他会当一辈子诗人时,他写了《少年史》《与父亲的战争》《田野的黄昏》等优秀散文为正在消逝的故乡和乡土景观立传;当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兼写散文的诗人时,他又用小说集《拯救河流》来书写乡土世界的风俗、情爱、伦常、权谋和现实哗变,用“地下人”系列荒诞科幻小说透视了环境破碎、乡土不再的现代乡愁。这里且说说小说家黄金明。
何谓小说家?毕飞宇有个有趣的说法,他说小说家就是身体倍儿棒的人,他的眼力好,旁人能看厘米,他能看毫米;旁人能听十米,他能听一里;旁人能辨五味,他能辨千滋百味。他说的是莫言,是作家那超人的感受力。不过,黄金明并不是莫言式的作家,他不是那种用身体写作的人,他是用思想写作的小说家。他没有用耳目口鼻让世界变得五光十色、五味杂陈万花筒般旋转起来,但他始终探索一种必须用宏大的思想坐标和敏锐的心智结构才能理解的先锋性十足的智性小说。
在我看来,写作多年之后,“地下人”系列小说使黄金明的写作面目得到了全新的生成。“地下人”系列包括《剧本》《寻我记》《实验室》《蝉人》《看不见风景的房间》《倒影》《小说盗》《讲故事的人》等八篇。小说采用了橘瓣式结构,每篇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想象了人类在21世纪中叶的生存境遇、精神生活及其出路。“地下人”系列小说既通过对未来世界的空间及变形想象(胶囊公寓、人造天空、人造宇宙、逆进化的人等等)而包含了对现实的寓言化指涉,同时,这批小说由于内在的多声部复调特性和对小说本体的探讨而具有相当强的实验小说、元小说特征。某种意义上说,“地下人”系列的最大价值恰在于它的现实关怀和实验激情的融合。
在我看来,“地下人”系列的叙事实验,具有鲜明的套层叙述特征。故事套故事,或者多个叙事层面的交错是现代小说乃至于后现代小说的常用手法。事实上,套层故事在古典作品中也层出不穷。《奥德修纪》就是通过奥德修斯向斯克里亚岛国王追叙海上十年漂流故事而展开的。《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也都是套层故事的经典。传统叙事虽然常倒叙、插叙不同时间层的故事,但某个支配性的时间层是清晰易辨的。可是我们看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寒冬夜行人》《宇宙奇趣》等作品,会发现叙事时间层的等级性和秩序性被一种后现代的文本嬉戏热情所消解。不难看出黄金明对卡尔维诺的服膺。多个叙事时间层的交错和“倒影”关系的设置正是“地下人”系列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套层叙事同样在最新的《窥视者》中得到贯彻。“地下人”系列小说也具有博采众收的复调性和形式探索性。地下人兼容了科幻、侦探、反乌托邦等元素,它有现实关怀,但并非荒诞现实主义小说。这些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兼容性,它并置了大量小说类型而成为抵抗分类的文本。事实上,《窥视者》的套层叙述中同样把爱情小说、荒诞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等元素并置其中。
《窥视者》的背景虽是果城,但时间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延续“地下人”那种未来主义的科幻想象。小说通过一个现代浪子的奇特情感经历追问了现代人的情爱危机。小说中那个终于成为唐璜式浪子的男主角其实一直怀着对真诚永恒爱情的渴望。当他和妻子感情日淡之时,他真诚地渴望和Y重建一份身心合一的婚姻。问题是,生活一次次戏弄了他:因为妻子性冷淡而生离心的他却不得不接受妻子三年狂风暴雨般的性要求,终于离婚可以和Y结合了却发现二人的感情已经不复从前,曾经沧海之后终于决定洗心革面与后来的妻子厮守终身却发现妻子无法收起自己的“花心”……凡此种种,小说追问的其实是: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有没有一份爱值得坚持,人心的猜疑又如何破坏爱的恒一性这样的问题。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同样对现代的情性危机有着过人的洞察,在《爱的多重奏》中他写道:“在性爱中,每个个体基本上只是在与自己打交道”,“在性中,最终,仍然只不过是以他人为媒介与自身发生关系。他人只是用来揭示实在的快感。在爱之中,相反,他者的媒介是为了他者自身。正是这一点,体现了爱的相遇:您跃入他者的处境,从而与他人共同生存。”今天的世界普遍存在着爱的虚无症和性的肥大症。以性的方式去确证自身往往会使主体陷入更深的虚无危机。爱和性的危机都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哲学危机和价值危机。现代爱情与古典爱情最大的不同何在呢?在于古典爱情甜蜜或磨难背后的那份坚信不疑消失了。《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赠送巴萨尼奥定情戒指时说,戒指在情在;可是当巴萨尼奥毫不犹豫把定情戒指送给帮安东尼奥打赢官司的律师(鲍西亚假扮)之后,他们的感情并没有改变。因为他们分享了义优先于爱的价值观。现代最大的坍塌在于那种恒定性的价值观坍塌了。因此,《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只能把他和特丽莎的宿命爱恋归结为六个偶然。某种意义上,《窥视者》正是这种现代主义荒原感在情爱领域的投射。现代人有奋不顾身的爱,却很难有无可置疑的信。在相互的试探、猜忌甚至窥视监控中,爱被放逐了,只有在性的海洋聊以靠岸又永远无岸。小说中,讲述故事的70后小说家和80后评论家之间何尝不是另一场相互保留的刺探攻防的开始。就此而言,《窥视者》事实上通过一个一地鸡毛的现代情爱镜像透视了现代心灵的价值变异,或可视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类现代主义情爱小说的后现代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