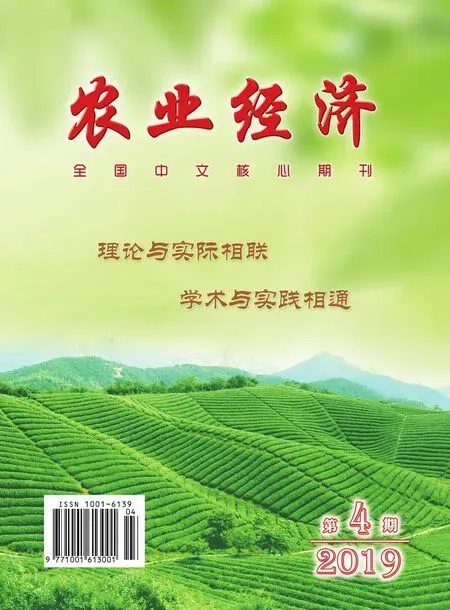少数民族乡村节庆视角下的地方品牌建构*
——以林芝嘎拉村为例
◎桑森垚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均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该背景下,乡村旅游作为可以有效保护乡村生态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案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而西藏作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和唯一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乡村旅游更是被作为提振乡村经济、实现全面脱贫的战略方案。而地方品牌化作为构建地方符号价值的过程,其不止有利于促进乡村内生发展,最大化地方资源特色,强化地方市场竞争优势,提升区域产品的原产地效应;而且有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乡村旅游内外部顾客的价值感知。
地方品牌化是地方品牌开发者根据地方特色构建地方品牌并进行社会化传播以获得社会经济利益的过程,地方品牌的传播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载体。节庆作为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文化的特殊载体,其在传播地方形象,强化游客地方本真感知,以及促进本地居民文化自信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节庆所具有的仪式化效果和经济溢出效果有助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节庆作为有效的地方品牌传播和脱贫手段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青睐。但现有的研究中缺少对节庆影响地方品牌形成过程框架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林芝嘎拉村为案例地,以嘎拉村桃花节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节庆如何影响地方品牌化形成。
二、地方品牌
地方品牌的本质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对某地方的特定解读。解读者包括地方品牌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部门,如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如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游客,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如本地居民;而形成可供解读对象的过程即是地方品牌化的过程。据此,地方品牌的概念核心是被赋予了意义的空间领域。地方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将商谈所得的地方意义赋予地方素材,并通过一定方式的沟通,获取社会或经济利益,该过程即被定义为地方品牌化。由此可见,地方品牌是可供传播的社会符号,其承载了地方品牌化过程中所赋予地方的社会意义。
地方文化是地方品牌符号的对象,地方形象是地方品牌符号的解释项,地方认同则可被视作地方品牌符号的表征。地方文化、地方形象和地方认同共同构成地方品牌,而其中地方认同是地方文化和地方形象的映射,地方文化和地方形象则分别被地方认同所嵌入,由此,地方文化、地方认同及地方形象间循环影响,该动态过程即是地方品牌化的过程。该过程中,地方文化是地方传统、价值观以及仪式、自然生态的综合,是以本地居民为主体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对地方固有意义的阐释;地方形象则是地方品牌开发者籍以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同时满足本地居民认同延续的传播主体;地方认同则是地方品牌开发者协调基于地方形象认知的外部社会需求以及基于文化传承的内部社会需求的产物。
三、林芝嘎拉村桃花节
嘎拉村位于318国道沿线,西距林芝县城16公里,东距林芝镇6公里,平均海拔2900米。该村2005年由真巴自然村和嘎拉自然村两村合并而成。全村共有32户,153人。其中,一般贫困户1户,低保户2户,劳动力68人。嘎拉村属于半农半牧村,其山野桃林是远近闻名的“桃花沟”,总面积约286亩,有野桃树1253棵,享有了“桃花村”之美誉。该村作为“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举办地,自2002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过14届。“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的成功举办,促进了全村走向乡村旅游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全村16户办起了农家乐,2户家庭旅馆。
此外,政府投资了860万元建设嘎拉小康示范村建设和投资150万元改造升级嘎拉“桃花园”工程,打造了嘎拉桃花村“四个功能”(“林芝市桃花旅游文化节举办地”、“林芝市城市公园”、“林芝市婚纱摄影基地”、“大学师生实习写生地”)。2017年,在“第十五届桃花文化旅游节”期间,共接待游客73900多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00万元,其中门票收入195余万元,游客接待中心,广告牌等租赁收入18.9万余元,家庭旅馆、农家乐及摊位等经营性收入12多万元,同比增长88%,相比2013年翻了38倍,是西藏自治区发展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以实现旅游扶贫的经典案例。
2018年林芝桃花节再次在林芝嘎拉村举办,并借西藏自治区推出“冬游西藏”项目之机面向游客开放,本次桃花节包括桃花盛景、民俗体育、文化桃源、桃花爱情等板块,将自然、文化、社会、美食相结合打造藏族乡村节庆品牌。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收集的资料反复整理,梳理出林芝嘎拉村桃花节作用于嘎拉村地方品牌形成的过程框架。
四、分析结果
(一)桃花节的嘎拉村文化重塑功能
嘎拉村是典型的藏族村落,桃花节举办之前,保持着较为原始的农牧文明。2014年,广东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针对嘎拉村提出了“整合资源、整村推进、村景合一、发展旅游、增加村民收入”的整体扶贫工作思路,将以桃源为核心的自然资源融入藏族村落,开发嘎拉村桃花节,对嘎拉村的地方文化进行重新塑造。自然和传统文化共同融入至桃花节节庆品牌中,桃花节节庆文化进而反馈至地方文化,其本质是地方符号正当化过程中的道德价值观嵌入过程,而其结果则对嘎拉村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由藏式原始村落变成了嵌入地方自然资源的“桃花村”。该文化的重构被本地村民所解读,对其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由于桃花节的地方文化重构过程嵌入了传统文化和地理标识,重构结果所产生的本地居民感知地方变迁呈现积极面,具体表现在本地村民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的提升。
(二)桃花节的嘎拉村形象传播功能
桃花节作为节庆品牌,其核心功能之一是地方形象的“叙事者”。一方面,桃花节作为地方文化的重塑主体,其通过一系列仪式行为将嘎拉村地方符号意义传播给节庆参与者。这些仪式行为包括展现传统文化的民俗体育体验活动以及民族服饰摄影活动;也包括展现自然特色的“桃源盛景”,游客通过文化和自然体验共建,解读桃花节作为地方形象传播者所传达的符号意义,以体验地方本真。另一方面,桃花节本身作为塑造嘎拉村地方品牌的IP,其社会宣传过程本质上是嘎拉村地方形象间接传播的过程。而类似“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社会化符号,则为桃花节的社会化传播提供了解读的“伴随文本”,进而为嘎拉村地方品牌形象赋予了“神话”色彩。
(三)桃花节的地方认同表征功能
桃花节重塑地方文化的过程是其通过影响本地村民的地方认同进而影响地方文化变化的过程。而桃花节作为地方形象传播的载体,其传播的本质是桃花节发挥地方认同表征作用的过程。地方认同是地方实践者(包括本地居民、游客等所有利益相关者)感知地方符号意义,并将自我与地方意义相链接的过程。一方面,嘎拉村村民作为局内人,其通过参与桃花节决策间接参与桃花节的地方品牌文化重塑,其地方认同伴随着对嘎拉村地方文化进化的认知而发生改变,而桃花节作为地方文化进化的引导主体,桃花节事实上是村民地方认同的表象。另一方面,桃花节所代表的嘎拉村地方形象被作为局外人的游客所感知,桃花节本身成为了嘎拉村地方形象的符号呈现。而桃花节所呈现的社会化符号意义被游客所接收,通过与游客的自我相链接,在游客感知自我存在本真的过程中,完成游客的地方认同感。该地方认同的形成既出现在游客未抵达桃花节前,通过桃花节的社会化符号传播(如媒体宣传)而形成期待的过程中;又出现在游客参与桃花节活动的仪式互动过程中;还表现在游客结束桃花节活动,通过社会化文本(如照片)进行回忆的过程中。而无论哪个阶段,桃花节既是地方形象的“叙事者”,又是游客形成地方认同的“媒介”。
五、结论
地方品牌化是地方文化、地方形象、地方认同三要素间循环影响的过程。将地方品牌视作地方品牌管理者制造的可供传播的社会符号的话,地方文化、形象和认同则分别是社会符号三要素中的对象、解释项和表征。而地方品牌的传播必须依靠承载地方形象的载体。节庆作为承载地方形象的“叙事者”,其在地方品牌化的全过程中作用显著。本研究以林芝嘎拉村为案例地,构建“桃花节”促进地方品牌形成的框架。
研究结果显示,桃花节通过重塑地方文化、传播地方形象、呈现地方认同来影响嘎拉村的地方品牌化。同时以少数民族乡村节庆为例,梳理了节庆影响地方品牌化的框架,有助于乡村旅游`地方品牌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地方品牌开发者可以通过节庆旅游方式塑造地方形象,同时通过在地方节庆影响地方品牌化的不同阶段实行针对性的策略引导整体地方品牌化过程,如已知地方认同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通过加强本地居民赋权感知强化节庆重塑地方文化效果,则可以渐进地改变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感,而不会引起居民的认同丧失,从而整体上带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