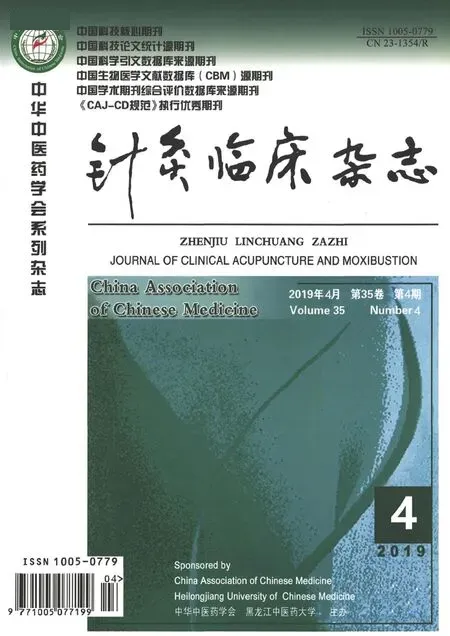试论出针补泻的临床意义*
程德均,黄 伟,2△
(1.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治未病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 武汉 430061; 2.湖北省中医院,湖北 武汉 430061)
出针,又称起针、退针等,是针刺治疗过程中继进针、运针、留针后的最后一步,即当针刺达到所要求的治疗目的后,将针缓退至皮下然后拔出的过程[1]。针刺补泻是针刺产生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经云:“虚则实之,满则泻之”“补泻反则病益笃”,故而正确掌握针刺补泻方法的意义不言而喻[2]。出针的补泻法源于《内经》中的有关记载,《灵枢·九针十二原》曰:“按而引针, 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可见古代医家十分重视出针的补泻,而现代临床忽视了出针在针刺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导致对出针补泻的质疑。笔者拟从出针的临床现状、出针在补泻手法中作用以及后世医家对出针可以影响补泻的研究三个方面来论证出针补泻的重要性。
1 出针的临床现状
1.1 临床出针方法
李靖等[3]在制定针刺基本手法操作行为量表时,对出针的描述是:押手取干棉球轻按穴位处皮肤,刺手轻柔地捻转并上提针至皮下,刺手迅速将针拔出,押手迅速用干棉球按压穴位片刻防止出血。临床具体运用时,医生大多受患者的感受、安全性、时间等因素影响,或取针前后不配合押手按压,或一味追求快速出针,或针对不同的患者,出针操作无法达到因人而异[4]。由此可见,以上出针操作忽视了补泻这一关键因素。
1.2 忽视出针补泻的原因
临床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大多重视行针的补泻手法,而忽视了出针的补泻手法[1]。造成这一现状原因大致有以下4点:一是出针常因看似简单而往往由实习医生完成[2],实习医生难以把握患者病情,很难实现出针补泻;二是为了保证出针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出针时多以立即按闭针孔为主;三是临床工作量大,加之时间紧迫,故难以兼顾出针的补泻;四是出针涉及补泻时往往操作复杂而影响临床应用。
1.3 出针中所涉及的补泻手法
有文献表明,出针是影响针刺疗效的关键一步,如果处理不当或不施行正确的补泻手法,往往达不到相应的治疗效果[2]。出针补泻与针刺疗效密切相关,临床上应重视出针补泻。与出针相关的补泻手法丰富,譬如,教材常以开阖补泻为例论出针补泻,部分学者在论述出针补泻时,亦引用了徐疾补泻、呼吸补泻、烧山火、透天凉等手法中出针的操作过程[5-7]。
2 出针在补泻手法中作用
临床上,单式补泻手法中涉及到出针这一步骤的有徐疾补泻、开阖补泻、呼吸补泻三种方法,为考证出针过程在各补泻手法中的重要作用,现论述如下。
2.1 出针在徐疾补泻法中的作用
徐疾补泻法首载于《内经》,如《灵枢·小针解》曰:“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缓慢进针配合快速出针可以达到补益的作用,快速进针配合缓慢出针可以达到泻实之目的,可见出针快慢是徐疾补泻操作中的关键步骤。明代徐凤对徐疾补泻亦有记载,如《金针赋》曰:“补者一退三飞,真气自归;泻者一飞三退,邪气自避”。新中国时期,各版本《刺法灸法学》[8-12]对徐疾补泻的定义包括进针与出针的配合,进一步论证了出针是徐疾补泻法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2.2 出针在开阖补泻法中的作用
开阖补泻法源于《内经》相关论述,《素问·刺志论》中提出:“入实者,左手开针空也;入虚者,左手闭针空也”。治疗实证,不按闭针孔或出针时摇大针孔,此为腠理“开”;而治疗虚证,在出针后立即按闭针孔,此为腠理“阖”,可见出针后是否按闭针孔为开阖补泻法的关键。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曰:“此法非止推于十干之穴,但凡针入皮肤之间,当阳气舒发之分谓之开。针至肉分间,当阴气封固之分谓之阖。”杨氏引入阴阳来分析开阖补泻,阳气舒发为开,阴气固藏为阖。新中国时期,各版本《刺法灸法学》[8-12]指出,开阖补泻的依据为出针时是否配合按闭针孔,进一步肯定了出针后是否按闭针孔为开阖补泻的关键。
2.3 出针在呼吸补泻法中的作用
呼吸补泻法来源于《内经》的相关记载,《素问·离合真邪论》曰:“呼尽内针……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故命曰补。吸则内针……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故命曰泻”。操作上强调出针时配合呼吸是呼吸补泻的重要步骤。晋代皇甫谧亦论述了出针在呼吸补泻中有重要作用,如《针灸甲乙经》记载:“泻者,……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补者,……,复以吸排针也”。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曰:“呼者因阳出,吸者随阴入,……补之时,气出针入,气入针出,欲泻之时,气入入针,气出出针”。杨氏肯定了出针在呼吸补泻的重要性,并引入“阴阳”来分析呼吸补泻的机理。新中国时期,各版本教材[8-12]对呼吸补泻法的主要描述均是呼气入针、吸气出针为补,吸气入针、呼气出针为泻,进一步肯定了出针配合呼吸是呼吸补泻的关键步骤。
3 后世医家对出针可以影响补泻的研究
3.1 单一手法的研究
崔明慧等[13]将缓慢进针而快速出针理解为重在徐入,这是徐疾补泻的补法;对于泻法,将快速进针而缓慢出针理解为重在徐出。故而,若仅仅考虑快速进针,而脱离缓慢出针这一步骤,这不能体现泻法重在徐出的思想。郑灿磊等[14]通过设计随机对照试验,观察徐疾补泻手法针刺腰夹脊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规定了徐疾进出针具体时间,如泻法为疾速进针(2 s)配合徐徐退针(6 s),补法则相反,结果显示,徐疾补泻手法治疗效果优于常规针刺,反映了出针的补泻在针刺疗效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刘阳[15]通过设计随机对照试验,观察头针徐疾补泻法对恢复期脑卒中的影响,规定徐出针是让皮肤隆起呈丘状而出针,疾出针无此动作,结果显示,徐疾补泻疗效优势显著,进一步说明出针补泻的作用。
龚启华[16]发现,开阖补泻泻法操作中,摇大针孔会在针刺所及的范围内使大气不断渗入组织间隙,提高其压力,迫使间隙液向压力较低处流动、疏散,而起到化瘀消散的作用,这是对开阖补泻法泻法的现代解释。乔红伟等[17]在探讨针刺开阖补泻的量效关系时提出,研究补法量效时以按压时间、按压力度这两点为控制变量,泻法以摇动时间、摇动幅度及摇动方向这三点作为控制变量,强调了应用开阖补泻的补法时应注重按压时间、按压力度,应用泻法时应注意摇动的时间、幅度和方向等因素。笔者以为,开阖补泻中摇大针孔以利气出为泻法,可以类比放血疗法为泻法的思想,一个是无形之气,一个是有形之血。
梁丽珠根据《难经》演绎出呼吸补泻其实是在调整阳气[18],根据呼属阳、吸属阴,候吸出针可以泻阴进而补阳,候呼出针可以泻阳,论证了出针配合呼吸可以补泻阳气。此外,蔡通[19]对《内经》中的呼吸补泻有新的理解,他认为候呼出针以令邪气出故为泻,侯吸出针则真气不得出故为补。景丹丹等[20]在治疗左侧三叉神经痛患者时,取右侧合谷穴,嘱患者深吸气的同时进针,得气后,让患者呼气的同时将针提至皮下出针, 如此进行强刺激数次, 患者诉左侧面部已无疼痛。蒋帅等[21]在治疗偏头痛患者时,取双侧阳辅穴,嘱患者深吸气的同时进针,并行捻转泻法,待患者出现酸麻胀感后,嘱其呼气的同时将针提至皮下出针,患者诉疼痛较前好转。景丹丹与蒋帅等通过临床实践研究,发现呼吸补泻的疗效确切,论证了出针配合呼吸在针刺疗效中的重要性。
3.2 综合手法的研究
开阖补泻与徐疾补泻亦经常配合使用,蔡通[19]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开阖补泻可从属于徐疾补泻,在十五第1版[9]、十一五第2版[10]《刺法灸法学》中对徐疾补泻在出针的描述是,快速出针配合疾按针孔为补法,缓慢出针配合徐按针孔为泻法。
开阖补泻常与呼吸补泻法配合使用以增强出针补泻,如复式补泻手法烧山火、透天凉,吸气时退针、出针后迅速按闭针孔为烧山火的出针方法,呼气时退针、出针时摇大针孔,不扪其穴为透天凉的出针方法。杨景柱[22]运用透天凉手法针刺曲池、合谷以治疗发烧患儿,结果显示,针刺组降温效果优于对照组,从侧面论证了呼气时退针、出针时摇大针孔具有重要意义。
4 小结
出针不是简单的将针起出,它同样也是影响针刺疗效的关键一步,出针过程施行相应的补泻手法,不仅可以补虚泻实,而且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如蔡曦庆[23]认为,出针配合一定的呼吸,不仅可以减轻针刺疼痛,还能促进针刺感应的传导,进而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综上可知,从《内经》时期到晋代《针灸甲乙经》、明代《针灸大成》、再到新中国时期各版本《刺法灸法学》教材中,在论述徐疾补泻、开阖补泻、呼吸补泻时,均有出针时的手法要求。即在针刺过程中欲达到补虚泻实的目的,仅仅在进针、行针过程上运用补泻手法是不够的,还应配合出针时的手法才能达到相应补泻效果。快速出针、出针后疾按针孔、出针时配合吸气均可以达到补虚之目的,且以上补益手法相互配合可加强补虚;缓慢出针、摇大针孔并且出针后不按针孔、出针时配合呼气均可以达到泻实之作用,各种泻实手法组合亦可增强泻实之作用。
出针补泻与机体机能状态、腧穴相对特异性、针刺手法密切相关[15]。笔者认为,临床出针欲通过针刺手法达补泻之目的,还应考虑患者机能状态和特定腧穴。①患者机能状态是针刺效应的决定因素,比如针刺疗法对虚证患者有补虚的作用,对实证患者有泻实的作用,这是针刺的主要效应。故而,出针过程应视患者病症虚实行相应补泻手法。②特殊腧穴的选择是影响补泻效果的基础条件,譬如关元、气海、命门、膏肓、背俞穴、募穴及原穴等多用以补虚,人中、委中、太阳、大椎、十宣、八风、八邪、十二井穴、荥穴和郄穴等多用来泻实。故而,出针过程还应注重在特殊腧穴上行补泻手法。
当然,临床出针的补泻方法很多,某些补泻手法的补泻作用仍有异议。李志道[24]认为,出针后针感遗留为阳性出针法,此法可以泻实,出针后无遗留针感为阴性出针法,此法可以补虚。袁军等[25]对遗留针感的理解刚好相反,即出针后针感遗留可以补虚,实证患者出针时不要求出现后遗感。不管争论如何,以上均注重出针在针刺过程中的作用,且都肯定了出针补泻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