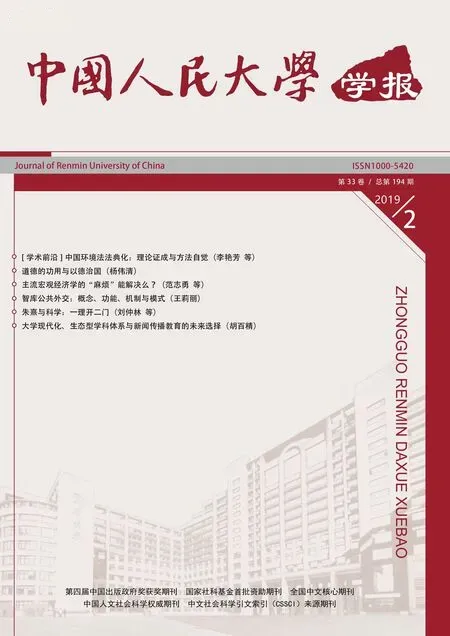论《水浒传》的“忠义”冲突及其近代意义
王 昕
古代小说作为认识与阐释民族历史的一个形象化线索,其隐秘的内涵是随着人们对历史认知的深入而不断显露的。作为古代小说的经典,《水浒传》的“忠义”主题一直是历代的读者和研究者称扬、模仿和解读的关键。明清时代发生的无数“教匪”、秘密结社,文学中产生的许多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都带有大同小异之梁山泊式的忠义问题与倾向。在《水浒传》的成书与流传过程中,“忠义”是一个逐渐突出的词语,一部部《忠义水浒传》《忠义水浒全传》的名称就是这一过程的物化体现,最终形成了“忠义而水浒,水浒而忠义”的结果。人们习惯于将“忠义”主题视为一体的儒家伦理范畴,即“忠于君,事于友”,“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注]① 袁无涯:《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载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无论是忠,是义,还是忠义,大体都是同样的意义”[注]② 井坂锦江:《水浒传新考证》,3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今人的研究认为《水浒传》是以“忠义”思想为内容、伦理判断为主体,[注]③ 宋克夫:《乱世忠义的悲歌》,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6)。无论是将“忠义”视为梁山好汉的“颂歌”或者“悲歌”,人们大都将“忠义”视为一体进行论述。[注]④ 张锦池:《“乱世忠义”的颂歌》,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4)。即使是论述“忠义”伦理悖论的研究,亦将“忠义”视为一个词语或者道德观念内在的逻辑悖论[注]⑤ 宋铮:《〈水浒传〉忠义伦理的悲剧精神》,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尚不及明清评点者那样,将“忠”“义”视为一个两种意涵与道德的连接。
“忠”与“义”的矛盾是解读《水浒传》文学价值与近代意义的关键。明人模糊地意识到“忠义”的不同面向,如大涤余人的“亦知《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注]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载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20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是用“人”与“言”的不同,来解释《水浒传》之所以得到官方认可与民间欢迎的原因。金圣叹的“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注]金人瑞:《水浒传序二》,载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21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指出“忠”和“义”具有不同的道德含义与现实功用。近年来,研究者日益关注到忠义主题的复杂性以及“忠”“义”的区别[注]参见刘上生:《三国演义“义”文化心理结构之系统考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2);赵敬鹏:《论水浒传主题的图像传播——以“义”为中心》,载《明清小说研究》,2017(4);王丽娟:《文人之“忠”与民间之“义”——桃园结义故事两种叙事的比较分析》,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1),文章讨论了元明时期不同“桃园结义”故事中,文人叙事与民间故事对“忠”与“义”的各有侧重,但未讨论“忠”与“义”矛盾所造成的主题性质。,但人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义”是“忠义”,还是“侠义”这样的问题,盖“忠义就包含着对朝廷的尽忠,义字却只强调朋友间的友情”[注]池田大作、金庸:《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67页,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1998。。而除了传统的“侠义”之外,《水浒传》的“义”还有更丰富的内涵与类型。《中庸》云“义者,宜也”,孔颖达据此认为“义”乃适宜性。《水浒传》受到宋明以来一代代民众的喜爱,是因为“忠”与“义”的背离,使得水浒故事具有包含不同时代、不同阶层规则与道德的弹性。尤其是“义”这个词语,在明清文化语境中,具有了新的质素,可以将之概括为近代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意义,代表了新的平民精神。这种近代价值使得《水浒传》主题的悲剧性,超越了小说的文本,形象地表达了蕴含在明清社会中,新兴庶民阶层与专制伦理的深层的矛盾,这样的“忠义”悲剧才是史诗级的英雄的悲剧。
《水浒传》的“忠”与“义”,其实是两条不同的伦理道德维度。本文试图梳理“忠义”观念的表述历史以及《水浒传》所蕴含的新的“义”的产生过程,以挖掘“义”的近代精神价值和意义。
一、“忠义”而在庙堂
“忠”“义”二字本自经史,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本质是纵向和横向的两种社会约束力量。忠是自下而上的依附与归属的关系;义,则是横向的个体的情感与义务的连接。在中古之前,“忠”与“义”两者相关,又各自独立。对于“义”,经学更讲礼义、仁义、君臣之义。《礼记》有言:所谓礼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所谓仁义,《中庸》云:“仁者人也,亲者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所谓君臣之义,“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孟子》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首先,在儒家经典中,“义”,具有“仪”的成分,是礼的一种体现,所谓“礼义由贤者出”,即《左传桓公》“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的意思。《论语》中的“信近于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个“义”都含有礼义之意思。
在君臣之义上,孟子主张相等的对待“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注]孟轲:《孟子注疏》,2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在后来的逐渐引申中,“义”被进一步赋予相宜、规范、善等更概括的抽象内涵。
最早将“忠”“义”连缀在一起的是汉代苏武的《报李陵书》。在这封信中,苏武自表心迹,言其“忍困强存,徒念忠义,虽诱仆以隆爵厚宠,万金之利,不以滑其虑也”[注]苏武:《报李陵书》,载严可均辑:《全汉文》,2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这封书信或为后人伪托[注]李陵、苏武间的往还书信从唐代就受到怀疑,如刘知几、苏轼等。王重民认为,《报李陵书》作者当为晚唐人,“作者托苏李以摛文,殆有无限感慨滋于其中”,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但《汉书·苏武传》中,李陵劝降时,苏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苏武为报君主之恩,推孝尽忠的言辞,道出了“忠义”的本质。在东汉之后,“忠义”作为一个词语就频频出现了。
其次,先秦时代,儒家的“忠”“义”观本是相对的,孔孟荀子都主张贵民。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孟轲:《孟子注疏》,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可见,“忠”是有前提的,对为君者也有道德要求,并非绝对地服从与效忠。“义,理也”[注]荀况:《荀子集解篇》,504、4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是具体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孔子多次提到“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义以为上”;孟子则说:“仁,人心;义,人路”;“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义”在原儒经典当中,兼具道德与情感的意涵,同“忠”一样,都是相对的。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董仲舒将“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视为《春秋》大义[注]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至此,儒家以“礼”为核心的等级人学逐渐固化。在王权支配的社会中,“忠义”成为政治的品格,进入史传书写。
唐代房玄龄于《晋书》“列传”中首设“忠义传”,表彰杀身以成仁,“捐躯若得其所”的“蹈节轻生之士”、君臣忠义之节。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卷187设“忠义传”上下,所录为杀身成仁,舍生而取义的“德行君子”。所谓忠义者,为死国事的臣子。“忠义传”上,为李唐开国时出生入死的大将,如夏侯端、罗士信等;下篇则是天宝之乱及其后的殉国之将。欧阳修、宋祁等撰的《新唐书》“忠义传”从列传116至118,增至三卷。《新唐书》在“忠义传”中增加了朋友之义这一类型。如“吴保安”,吴保安的朋友郭仲翔被蛮民俘虏,为营救赎买朋友,吴保安“力居货十年,得缣七百”,弃家不顾,终于赎出朋友。郭仲翔也以义报之,保安死,“丧不克归。仲翔为服缞绖,囊其骨,徒跣负之,归葬魏州,庐墓三年乃去。后为岚州长史,迎保安子,为娶而让以官”。这个故事,在“三言”中被改编为《吴保安弃家赎友》,受到读者的喜爱。
元代脱脱所作《宋史》“忠义传”大大扩充了“忠义”范围,从列传205至214,有“忠义传”十卷,近二百人,为历代史书之最,并区分了忠义的情境与等级:
奉诏修三史,集儒臣议凡例,前代忠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然死节、死事,宜有别矣:若敌王所忾,勇往无前,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寓官闲居,感激赴义,虽所处不同,论其捐躯徇节,之死靡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若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审义自裁,斯为次矣;若苍黄遇难,霣命乱兵,虽疑伤勇,终异苟免,况于国破家亡,主辱臣死,功虽无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变沦胥,毁迹冥遁,能以贞厉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欤!至于布衣危言,婴鳞触讳,志在卫国,遑恤厥躬,及夫乡曲之英,方外之杰,贾勇蹈义,厥死惟钧。以类附从,定为等差,作《忠义传》。
出于个人主动选择的捐躯殉节,被视为“忠义之上者”;被俘而死或者苍黄遇难则等而次之。那些平民百姓中的布衣之士、乡曲之英、方外之杰,也得以“以类附从,定为差等”。这是宋代“忠义军”历史事实的反映,显示了宋代庶民阶层的影响力。
明代宋濂等所作《元史》卷193至卷196,有“忠义”4卷。《明史》卷289至卷295,共7卷为“忠义传”,也是博采旁搜“有明一代死义死事之臣,”近三百人,汇次成篇。正史所录的忠义之士,即是“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注]李希仲:《蓟门行》,载彭定求等校点:《全唐诗》,3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忠义”之所以在各朝正史的列传中成为不断扩大的一部分,是由于“忠”对“义”的定义和笼罩。而朋友之间的“信义”、个人行为中的任侠并不能成为列传中的一类。如曹子建《三良诗》所称颂的那样:“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所言忠义者,是秦国三良,以身殉穆公事。这个“忠”是无条件的、抹去个人价值感的殉葬般的牺牲。如此的“忠义”是一个单纯的“忠”的意涵,是“忠”对“义”的定义与收编。
总之,从先秦至唐宋,“忠义”一词的话语权就存乎庙堂。如欧阳修所谓秉“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注]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载刘扬忠编选:《欧阳修集》,276页,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14。,特指对朝廷、对君主的忠诚、节义,不存私利和自我的士大夫才能称为忠臣义士。同时,庙堂之外的下层士人,为国家和君父复仇的事迹也存乎史册,成为美谈。如萧齐谢脁的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是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宋代以来平民社会的兴起,平民阶层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使“忠义在草莽”[注]王冕:《寓意三首次敬助韵》,载钱谦益辑:《列朝诗集》,3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民间成为社会的理想与寄托。这是明代书商将《水浒传》冠名为《忠义水浒传》的背景与意义所在,它显示了近代的庶民意识和新的道德观念。但是,平民阶层的“义”的观念,不只是“忠义先国家”,而是包含了丰富的驳杂的内涵和欲求。通过分辨与体察“忠”与“义”的冲突,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水浒传》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二、“忠义”而在《水浒传》
“忠义”一词,在《水浒传》中是“忠”与“义”的联合。“忠”在大部分梁山好汉口中,是贯在“义”前面的修饰词,是一个陪衬。在早期的英雄故事里,“忠”是被迫害、摧折的对象,所谓“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杨志被劫去了生辰纲,“花石纲原没纪纲,奸邪到底困忠良。早知廊庙当权重,不若山林聚义长”。一般打家劫舍的好汉的自称“忠义”,重点在好汉间的“义”,而非对朝廷的“忠”。如第十七回,亡命的杨志和鲁智深相见,被形容为“人逢忠义情偏洽,事到颠危策愈全”。第二十回晁盖、吴用等打劫了生辰纲的大盗和林冲等人,在梁山上落草,说书人称为:“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岁寒心”。第四十九回,母大虫顾大嫂要劫牢救解珍解宝,“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注]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6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下文引文凡出自100回本,文中标明,不再注。。此处之“忠良慷慨”,用来形容最好赌钱的闲汉,与朝廷史册之中的“忠义”“忠良”之意,相距不啻霄壤之距。
那些好汉口里的“忠”,还有谐谑之意。如第十九回,何观察带兵捉拿阮小五,往“阮小五打鱼庄上来。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听得芦苇中间有人嘲歌。众人且住了船听时,那歌道: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刚刚劫了生辰纲,声言杀掉朝廷官吏,偏要说“忠心报答赵官家”。说书人把这种谐谑解读为:“忠为君主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水浒传》120回本,第55回)这是对“忠义”的一种自主的发挥性的解释,是民间的,在下者眼中的政治正确与道德高尚。
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两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当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忠义”的悲剧主题,其背后的原因和时代意义值得深入探讨和阐释。
“忠”“义”的矛盾,在于一个属于政治伦理,另一个属于新的民间道德,两者的背离不可避免。章学诚《丙辰札记》斥责了小说中的各类结义行为:“‘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似《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注]章学诚:《丙辰札记》,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章学诚看到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无君臣而直称兄弟,是一种新的超越等级的关系。《三国演义》的蜀刘一方,集圣君、贤相与良将于一体。小说开篇就是刘关张“桃园结义”,三人既是君臣又是兄弟,在“忠”与“义”两个方面都成为道德的典型,义气干云、忠心无二,却落得同赴黄泉,在三国角逐中提前出局的结果。作者越是将同情的笔墨、正义的油彩倾向蜀刘一方,越是渲染出刘关张的兄弟义气、上下同心,则“忠”与“义”的冲突与背离越是明显。“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让赤壁之战的胜局大打折扣;刘备急于兄弟义气,不听诸葛亮劝阻,执意起兵为关羽张飞报仇,而兵败身死。很显然, “义”既是加固蜀刘一方君臣关系的黏合剂,也是瓦解其秩序和图谋的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国演义》的“忠”“义”处于一种紧张冲突之中。从政治理性上讲,兄弟义气对传统的“忠义”具有破坏性,作者将大传统系列中那些死王事的忠臣义士和民间小传统中的任侠使气,以及具有破坏性的江湖义气弥合在一起,显露出某种困惑和悲情。
《水浒传》把皇权神圣的神话故事,下降到一群盗寇身上。小说的开篇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天上的星宿下凡历劫的故事,将水浒英雄的平凡人生神圣化,这种戏仿古代帝王将相的神话,本身就是消解神圣化。出现在这些新兴的长篇小说中的“忠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作品的架构模式。但作为民间道德理想的“义”,已不同于史传叙述中的国家伦理道德,而是显露出民间性与复杂性的新的道德内涵与价值观念,这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受到喜爱的更为内在的原因。
《水浒传》的“义”并非儒家传统中的“义”,也非宋江个人的“忠义”所能涵盖,而是同道互助的江湖义气。在梁山好汉,这个“义”是“一个滑溜溜的字”,意思不定,标准不一:既包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也包括仗义疏财的慷慨,互相救助、义气深时共生死的牺牲;更有不顾道德的知恩图报(如武松为施恩抢生意而拳打蒋门神等),残忍的杀戮报复等等。这个“义”是出自梁山道德的应然,也合乎其语源学的本意。《周易干卦》所云:“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唐代孔颖达《疏》云:“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义”训为“宜”,“宜”的意思为“适宜”“应该”,这种“义”属于下层的百姓和被社会排挤的边缘人群。
关于“义气”的双重标准性质,研究者将之归纳为小圈子之内的“牺牲精神”,是亡命心态——“杀掠之认可、求生的焦虑、迫害感”的体现[注]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在相等的对待这个方面,“义”倒是和原儒经典中对情谊的强调有相通之处。《水浒传》的绿林好汉故事凝结了宋代以来普遍的民间态度和价值观。那些英雄好汉大多具有相同的经历和故事;如宋江杀阎婆惜和卢俊义杀妻故事的类似;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的遥遥相对;李逵杀四虎与武松打虎之类。类似的人物、相近的故事,表明了它们的半独立性——都是可以移之他人、更名换姓的举动。李贽、金圣叹等明清接受者对水浒忠义的阐扬,更合乎小说的大众文化本质,也更易于从中发现小说的意义与价值。这个“义”的新质素大致包括三方面。
首先,“义”是对等的,是相互间的道德与行为的约束。“义”类似于一种投资,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宋江“舍着条性命来救”晁盖,晁盖、吴用在梁山上立住了脚以后,马上想到“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以报答他的搭救之恩;因为“结义”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不论什么原因,不管哪个人落难,好汉们都会舍命相救。《全相平话三国志》的刘关张结义,“共破黄巾,图名于后”;到了《三国演义》当中,刘关张的誓词虽然以国家大义代替了个人的追求:“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但兄弟三人是以平等的个体结成一个互利的小团体,这个性质是没有变化的。在刘关张的几次危急关头,他们强调的是“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的情意。所谓弟兄结义,为的是“他时富贵无相忘”。同辈间结成利益联盟,获得某种安全与利益的保障,在乱世共同博取富贵荣华。黄巢与朱温等结义,“指天说誓道:‘富贵时,无相忘’”[注]《五代梁史平话》,载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如刘关张桃园结义,乃张飞和关羽看到刘备“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而刘备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状貌非俗”是英豪的物化的标志,三人乃“桃园结义,共破黄巾,图名于后”[注]《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载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7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在民间说书人那里,桃园结义绝非盲目的博爱,而是以相近的实力(状貌非俗)为基础、以三人结义抗击黄巾军为手段,以谋求身后名为目的。
“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注]这种民间英雄间的义气,是个人对个人间的、直接的人际关系上的忠诚,而非对神圣的王权的忠诚,有用和功利乃是这种“义气”的本质。
其次,这种相对等的,“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的“报”的观念,破坏了君权的绝对性。在民间文化里,“忠义”一词产生了分化与背离。忠臣义士本是儒家所标榜的道德伦理准则。在古代中国,君权被赋予类似宗教的神圣性质,是最高的终极价值的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义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义务与立身根本。但在唐宋之际的转变中,近代市民社会开始形成,世俗化是这一转变的最大特征。这对于王权的神圣性也是一种削弱。在宋代勾栏瓦舍里,京师老郎流传着“说五代史”这一门,还有话本小说中的“发迹变泰”,也多有“五十三年更五姓”的五代君王,如刘知远、郭威、史弘肇混迹市井的故事。频繁的君权转替,大大削弱了其神圣性。
所谓乱世,是指王权不稳,权力出现真空,各种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占有发生了大的变化,社会骚动,底层的人们可以通过个人的能力攫取权力与财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英雄“结义”,是觊觎权力者联合互助,以博得更大的胜面、得到不可尽述的“富贵荣华”的手段。宋元明的通俗话本、小说里,那些追求功名富贵、发迹变泰的好汉故事,固然不知“忠君”为何物,而“仁义”“信义”之“义”,也脱开了儒家的原始意义,具有了以个人情感与欲求为中心的近代特征。
在《水浒传》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中,“义”具有更多平民间的互助性质。宋元以来,民间社会中的交友结义成为普遍的现象。但小说所推重的“义”,多为平民间互相帮困扶持的温情与道德。“义”的缔结往往是萍水相逢的双方而非地缘、血缘,抑或等级上下的关系。如张劭在行旅之中,因救助身患瘟病的范巨卿而耽误科举考试,“以义气为重,功名富贵,乃微末耳”[注]冯梦龙:《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载《喻世明言》,140、14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3。。《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流落在燕山的杨思温,历经辛苦帮助义兄韩思厚取回妻子郑义娘的骨匣。《宣和遗事》的水浒故事,就是从“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被派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开始的。杨志杀了人,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其余人救出杨志,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注]《宣和遗事》,载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3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水浒传》中第一对结义的好汉是林冲与鲁智深,那个场面似乎是对“桃园结义”场景的模仿。林冲在墙外看鲁智深耍弄“头尾长五尺,重六十二斤”的浑铁禅杖,口里道:“这个师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而鲁智深所见的林冲则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非俗相貌。当下大喜,两人结为兄弟。林冲被高俅陷害,发配沧州,鲁智深放不下,一路跟随直送到沧州。袁无涯评“放不下朋友便成信人义士”[注]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1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隋唐演义》中秦叔宝秉持的“有恩必报”的民间的温情,也属于此类“义”的范畴。
其三、民间的“义”,不只是道德准则,还包括日常生活方式:大方的金钱观、个人性格的豪爽直率等等。不同于史传中的忠义人物,在梁山好汉的传奇故事中,银子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江湖好汉以对待金钱的态度判断地位、品质与关系的亲疏。宋江之所以成为折服梁山好汉的首领,是因为有“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他所仗的“义”的内核主要是金钱。那宋江“处处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武松落魄中得宋江温情拂煦,临行把手依依,又以十两银子相送。武松寻思道:“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果然不虚,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第23回)靠着“及时雨”的慷慨美名,宋江收服了众多江湖好汉,在历次危局中获救,并最终坐上了梁山泊头把交椅的位置。
鲁达救济金翠莲父女,向史进、李忠借银子,史进拿出十两银子,说“直甚么,要哥哥还”。李忠只摸出二两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将银子丢还李忠(第3回)。检验好汉与否的主要标准就是能否仗义疏财,吝啬无钱者自然受到鄙视。毕竟梁山聚义最具诱惑力的招徕便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这种和金钱观、享受欲交缠在一起的“义”,与原儒之“忠义”“仁义”间的差距不可不辨。也正是“义”所具有的近世社会的个体化的物欲性质,使它与排除个人性的极端化的“忠”,成为两个时代、两个阶层的话语,其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忠义”主题更广泛的悲剧意义。
三、“忠”“义”冲突本质与时代意义
一部作品最能动人心魄的力量,在于它与时代精神的共振,它对历史趋势把握阐扬的深刻程度,更在于它对时代局限与困顿的形象化体现。“忠”与“义”的背离与冲突构成了《水浒传》悲剧主题的复杂性、必然性和深刻性。
(一)复杂性
研究者注意到了《水浒传》中“义”的复杂性,“义”并非只是传统道德中的合宜、正理,友谊与牺牲。夏志清称之为“匪党的道德”;孙述宇称之为“同道中人之间水平的忠”,是他们之间的“互相撑腰”[注]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2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梁山好汉所表现的多种层面的“义”,产生自宋代以来平民社会的发展,是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由金钱运转支配着的新的伦理道德。具体说来,盛行在江湖道路与市井里巷间的“义”,体现了宋代以来的民间社会所具有的,平民的发展与政治重要性的衰退这两个根本特征[注]内藤湖南:《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转引自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它和官方史书中的“忠义”观念以及驯服于王权的“忠”,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与龃龉。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具有启发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在宋元时代,下层市井社会流行的“义”,其本质是庶民间自律、自助的行为。洪迈(1123—1202年)《容斋随笔》卷八“人物以义为名者”,归纳了六类“以义为名”的人和物。其中有“仗正道曰义”“至行过人曰义”,这个“义”出于每一个个体的自主性、公共性的活动。孟子曾说“义,外也,非内也”,在正直、仗义之外,还有从外来而非从内生的意思。在宋明以来,具备了开放性、流动性和弹性的庶民社会中,“义”——公义、仗义、正义的道德准则开始流行。“义”这种行为,不但在“游民”这种脱离了乡土与社会秩序的阶层中存在[注]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在“社会中间阶层”——“跨农村与新兴城镇的中产阶级”当中,也多有公心好义之士。[注]斯波义信:《南宋时期“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载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10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意识中形成的利益交换准则的延伸。无论是水浒英雄酷虐的“有仇必报”,还是《隋唐遗文》中秦叔宝温情忠厚的“有恩必报”,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践行着民间的道德——对等的“报”。而“忠”则要求放弃自我,没有理性的绝对服从。所以“忠义”一词,虽然被一体地概括成为梁山好汉的政治纲领、道德标签,但在宋明时代,“忠”与“义”已经是两种道德和价值观。
这种趋势也表现在其他文学样式当中。如明清戏曲中的“忠义”虽然大多延续着庙堂话语,像李开先《宝剑记》、冯梦龙的《精忠旗》、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歌咏的林冲、岳飞、左良玉之“忠义”,与庙堂之“忠义”区别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的市井戏曲家李玉《清忠谱》里,则将“忠义”许之市井里的颜佩韦,市井中人因为他“听见不平,忿忿大怒,道他是个义士”,赞其“怀公愤,是忠义俦”,则此“忠义”,同样表达的是民间道德观念的“义”。
一般的理解中,“义”主要指公正合宜的道理和理论。在市井人物口中的“义”,是出自自我立场与视角上的公平,这就有了丰富的意涵与声音。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要玉帝搬出天宫让给自己,李逵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都是要求权力平等;西门庆说:“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是要求的金钱平等;潘金莲看到自己和武大郎在容貌上不够敌体登对:“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注]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一奇书本),3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这种自傲与自信,在这个哪管天高地厚的小妇人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合宜之论。
白话的叙事文学将这些累累不休的“盗贼之言与事”[注]潘德舆:《读水浒传题后一》,载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32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细细道来,自高自信的盗贼与市井妇人形象,反映了民间伦理对国家伦理的质疑与漠视。“忠”与“义”的背离,可以说是宋元以来社会问题与时代精神的本质。在《水浒传》《金瓶梅》等英雄、庶民的一路“倡乱”“诲淫”小说中,下层社会的男男女女,日常的暴力与物质欲望,腐蚀着儒家所定义的“忠孝节义”一类国家伦理。梁山好汉以他们的活力洋溢的形象,展示了民间的欲望与伦理的鲜活生命力,但他们左突右冲,终究在专制的国家伦理的压制下消弭。《水浒传》“忠义”悲剧的本质是平民伦理的“义”与国家伦理的“忠”的冲突与对抗,所以它的影响十分深远。
从“水浒”故事世代累积与传播的历史来看,宋代以来的说书、戏曲等的民间作者循着平民伦理的“义”,创造了一个个平民英雄的个人传奇。“义”成为草泽人物最绚丽的油彩,将他们擢拔出凡俗的众庶,成为英雄人物。水浒英雄的“义”,包含了多个方面,其核心则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对等。“忠”,作为国家伦理,始终是以不对等的服从与牺牲为根本的。一个属于民间的温情与道德,一个属于庙堂统治理性。研究者将这些属于民间小传统的故事,称为“小水浒”。“‘小水浒’是表现个体冤情乃至反抗的局部性叙事,其中包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江湖行径。”盗贼强盗受招安,担当起匡时济世之责,重新“瞻依廊庙”,纳入王权的秩序体系就是“大水浒”。[注]李庆西:《大水浒与小水浒》,载《读书》,2018(1)《水浒传》70回之前的英雄聚义,代表着民间的道德理念的凝聚发扬,所以热热闹闹、畅快淋漓;70回之后则是国家伦理对民间伦理的绞杀毒害,最终形成了悲剧的结局。
(二)必然性
很多明清文人都指出了《水浒传》的悲剧的必然性,并从这个盗寇故事读出了社会寓言的意味。《水浒传》之所以产生并广泛流传是因为:首先,庶民阶层的兴起,使民间出现了“大力大贤”的强者社会;其次,自尊自爱,强调自我价值和尊严感的个体,通过新的社会伦理“义”作新的连接,聚集在民间的智力、伦理、荣誉感已经形成规模化的市场,却无处施展;再次,民间文艺的发展,催生了《水浒传》《金瓶梅》一类市井传奇,主人公从孤高超绝的先贤、大丈夫下降为平民中人,人欲人情成为依循的行为准则。
“水浒故事”风行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在《水浒传》成书前后,梁山好汉故事就在民间大量流传。南宋时宋江事就见于街谈巷语,话本中的水浒英雄如“青面兽”“花和尚”“石头孙立”等;元明两代盛行着“水浒戏”,李逵、燕青、林冲等英雄的故事在瓦舍村巷中传唱;胡应麟认为《宣和遗事》为元代作品,称之为“胜国时闾阎俗说”,即《水浒传》成书所本,是宋元流行的说书,他的根据是《宣和遗事》“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馀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43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用他们心中的美德、理想打扮着这些起自草莽的英雄,使之熠熠生辉,渐渐脱离了他们自身,重新走入了王权和政治伦理的序列,并招致了自我的毁灭。
在70回之前的《水浒传》,主要内容是梁山聚义,“聚义”既是故事框架,也是主题的伦理核心。这些由好汉的个人故事组成的一连串传奇故事是《水浒传》最精彩的部分。盖“义”,在民间被赋予新的道德内涵,成为世俗平民理想的寄托,散发着新的道德馨香与温度,正呼应了近代民间的欲求,反映了当时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具体生存感受和心理状态,故格外具有感染力和影响性。宋代以来的庶民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关系的重建的问题,庶民的伦理核心是平等、利己,个人独立,这些都要挣脱传统的忠孝,以构建一个新型的意义系统。
《水浒传》作为里巷鄙说,既能生动地捕捉新的社会动态,又面临着自我合法化的生存问题。因而“忠”与“义”的缀合,是其政治正确性的保障,它使那些个强盗故事具有了政治伦理的合法性。“义”的主题,在本质上昭示了社会公义的缺失,结义是平民阶层的自保,民间之“忠义”所指在“义”。《水浒传》中好汉结义“可以彼此帮助,免受人欺”。从以《水浒》和“三国”结义为榜样的民间帮会宗旨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水浒传》之“义”的本质和必然性。
民间帮会结盟时往往以“忠义”为标榜。清嘉庆年间天地会花帖称:
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溯其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啻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弃,似等仰尊帝忠义,窃劳名聚会。[注]
此处 “忠义”显然侧重于对关羽与结义兄弟福祸共当的“义 ”的强调,而无“忠”的意涵。
帮会是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集结、组织方式。近代都市化运动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便是它生长的起点。帮会一类都市“共同利益社团”,“掌握了个人适应新环境和群体生存的关键”[注]郭莹:《帮会意识初论》,载《社会学研究》,1993(2)。。个体生存与发展受到外部社会的巨大压力,更促进了帮会内部的凝聚力,造成帮会成员特殊的心理契约,以“义”为核心的帮派伦理便在此基础上产生。帮会是一种非制度性的社会组织,它的维系和发展得不到制度上的保障,而必依赖于全体成员奋不顾身和精诚团结。所以“义”是帮会的最高生活原则,自四面八方本无血缘关系的帮会成员就会建立起仿血缘的兄弟关系,会为帮会的利益义无反顾地献身,这种运作机制和伦理核心同梁山好汉之“义”若合符契。
宋代,随着专制集权的极端化,忠君被极端道德化;另一方面,民间社会滋生出世俗化的社会。民间社会对于君权神授,真龙天子一类的故事十分艳羡,造反者又怀揣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觊觎。“忠”是建立在王权神圣的基础上的信仰,市井阶层的“义”则是一种富于包容和弹性的世俗精神。宋明时代的世俗化,主要是王权信仰的衰落与市民精神的多元化,表现为个人对自我利益的捍卫、自我声名的追求。这就意味着对君权神圣信仰的怀疑,意味着王权在水泊梁山的空间中失去了神圣性。梁山近乎一个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空间中取代了山下身份等级约束严苛的社会,这个意气相投的小社会是由自由平等的个体组成的新的联合体。
(三)悲剧的深刻性
唐君毅称赞“《水浒》乃中国文学中之悲剧而又超悲剧之一的作品”。有李逵、武松、鲁智深诸人,皆顶天立地、至情至性汉子,不思前、不想后,生死患难一切直下承担。却“在天地之滨,在水之浒,在望招安之宋江之下,即可悲也”[注]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259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水浒传》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有一篇单道梁山泊好处的“言语”,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联合体。怎见得: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注]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892页,上海,中华书局,1961。
这个从身份等级严苛的山下社会中奋力挣脱出来的乌托邦,它的道德根源是“义气”,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它和宋江的“忠”两者在本质上是矛盾的。
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极赞宋江“识性超卓”, 尤强调其“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注]周密:《癸辛杂识》,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识性超卓”是他具有与普通好汉不同的见识和主张,这显然将宋江视为一个特殊造反者。宋江上山之前,梁山的核心是“聚义厅”,宋江上山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宋江以“忠”收服凌驾在众好汉的江湖义气之上,将之作为政治理想和施政纲领,一步步改造着水浒好汉。乐蘅军认为有“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代表宋江个人权力意志对梁山集团命运的成功驾驭。第70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噩梦”,坐稳梁山泊头把交椅的宋江,让众好汉一起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患难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这段誓言,实质是宋江用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对梁山好汉平等的兄弟之义的替换与改造。
宋江身上既集合着一层新的民间道德与平民精神,又逃脱不了浸入骨髓的奴性人格。从这个刀笔吏身上,体现了秦汉以来王权社会的浸淫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奴性的忠诚。在父系社会中君父权威下,忠是自上至下的道德伦常要求,是带有强制性的、绝对的道德规范。民间把这种伦常义务形象地概括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自不得不亡。”忠是孝的类比与扩大,死忠死孝,都是缺乏自主选择的一种义务与责任,缺少温情与弹性的空间。
在宋明时代,能使宋江这样一位下层的刀笔吏,博得声名和权力的,恰恰是那群不为王权所容的强盗。宋江曾对武松发感慨:“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32回)靠着发自民间的“义”才使他具有了“团圆百八人”“忠义心如一”的能力与筹码,他企望的却是用“忠”来收服泯灭好汉中“义”的平等精神。“忠”与“义”两者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影响与扭曲。“忠”既是绝对的、盲目的服从,“义”亦有盲目性。梁山好汉对宋江的“忠义”与招安之举,既不思前,又不想后,在性命攸关的抉择面前,放弃反思和诘难,就是出于“义气”的盲从与信任,只在寂天寞地中“谈笑如平日”地走向悲剧宿命,这就使“忠”“义”的冲突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