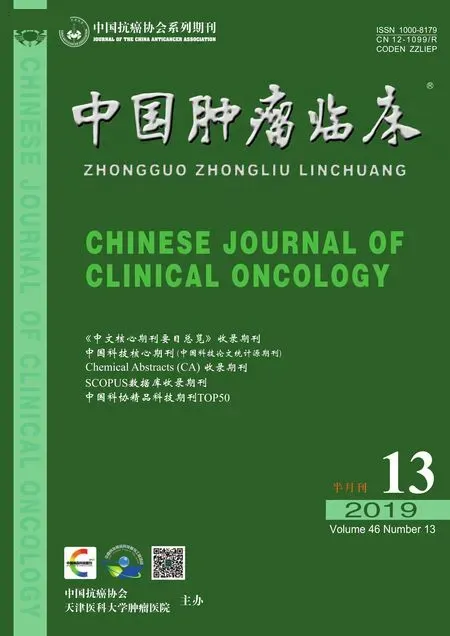肝内胆管细胞癌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研究现状*
张荷月 金添强 综述 戴朝六 徐锋 审校
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仅次于肝细胞癌的第二大原发性肝癌,发病率约占原发性肝癌的5%~30%[1]。近40年来,全球ICC 发病率不断上升,其中亚洲发病率位居首位[2]。ICC 恶性程度高,大部分患者发病时病情已处于晚期不可切除状态。对于可切除ICC,手术切除仍是首选的治疗方法,肝移植也可作为早期ICC的治疗选择[3],但是术后复发率高达60%~70%,5年生存率仅为30%[4]。目前对于能手术切除的ICC 采取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晚期ICC 采取以局部治疗联合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5]。近年来,免疫治疗和分子靶向治疗已成为ICC治疗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本文就此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的原理是利用自身免疫系统来控制并消除癌细胞。目前主要分为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和肿瘤疫苗。免疫分子检查点是免疫系统的调节器,是一类表达于肿瘤细胞和免疫效应细胞上的蛋白分子。肿瘤细胞可以通过上调抑制性检查点分子配体的表达水平来逃避免疫系统对其灭活作用。目前已经开发出针对免疫检查点分子的抗体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和纳武单抗(nivolumab),以及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T-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抑制剂替西利姆单抗(tremelimumab)和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等用于治疗肺癌、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研究显示可以延长此类患者生存期,改善预后[6]。肿瘤疫苗则是借助疫苗的辅助作用激发自身免疫反应来灭活肿瘤细胞,目前临床试验主要以树突状细胞疫苗为主,个体化肿瘤疫苗也逐渐得到重视。
1.1 免疫检查点疗法
1.1.1 PD-1/PD-L1抑制剂 PD-1是CD28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共抑制分子,是T 细胞应答的强抑制剂。PD-L1 和PD-L2 是PD-1 的配体,与PD-1 结合可抑制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增殖和免疫相关细胞因子的产生[7]。有研究发现,72.2%的ICC 患者肿瘤前缘细胞表达PD-L1,而且PD-L1 阳性者存活率下降60%[8]。
PD-1 抑制剂已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但目前暂缺乏单药用于ICC的病例,更多的是与化疗药物联合的病例报道。2 例ICC 术后复发患者采用pembrolizumab 联合替加氟化疗,其中1例化疗3个周期后使用了15 个周期pembrolizumab,另一例化疗5个周期后使用了6个周期pembrolizumab。复查CT和磁共振显示病灶均明显缩小,腹腔内肿大的转移淋巴结均消失,疾病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16 个月和13个月,治疗期间均未出现pembrolizumab 相关不良反应[9]。Mou 等[10]报道1 例pembrolizumab 联合奥沙利铂与替加氟治疗PD-L1 阳性的晚期胆管癌患者,治疗4个周期后增强CT显示转移至大网膜和右下腹腔的病灶明显缩小;因第5个治疗周期中出现中性粒细胞降低伴发热,停用奥沙利铂与替加氟,改为pembrolizumab 单药继续治疗6 个月后体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上述研究结果均提示,PD-1/PD-L1 抑制剂联合化疗治疗ICC 是可行的。1 例pembrolizumab 单药治疗高肿瘤突变负荷的术后复发ICC,注射6 次后复查磁共振显示肝内病灶及腹膜后肿大淋巴结完全消失,目前疾病完全缓解,无进展生存期大于6个月[11]。这一试验结果使PD-1抑制剂单药治疗ICC 的可行性得到极大支持。未来有必要将联合治疗方案和单药治疗应用到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中,对比两种方案治疗ICC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1.2 CTLA-4 抑制剂 CTLA-4 主要在活化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中表达,阻止CTLA-4与其受体B7-1和B7-2的结合可促进T细胞的活化[12]。一项CTLA-4抑制剂tremelimumab 联合微波消融治疗16例晚期胆管细胞癌(包括ICC)的研究结果显示,7 例患者病情得到控制,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3.4 个月,总生存期为6个月,提示tremelimumab 联合局部消融治疗晚期胆管细胞癌是可行性的[13]。另一项tremelimumab 联合消融治疗丙型肝炎相关肝癌的研究结果显示,肿瘤微环境中CD8+T细胞数量明显增加,6个月和12个月的疾病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7.1%和33.1%,总生存期为12.3 个月[14]。尽管目前尚缺乏大宗病例的tremelimumab 单药或联合用药治疗ICC 的相关研究报道,鉴于丙型肝炎是ICC 的危险因素之一[15],由此可以推测CTLA-4 抑制剂可能对丙型肝炎相关ICC也有类似效果。
1.2 肿瘤疫苗
一项自体树突状细胞疫苗与活化T 细胞联合治疗ICC的研究中,36例手术后接受辅助治疗者疾病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分别为18.3 个月和31.9 个月,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同期26例单纯手术切除者,后者疾病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分别仅为7.7 个月和17.4个月,而且疫苗注射部位皮肤反应在3cm以上者预后更好[16]。另一项树突状细胞疫苗联合吉西他滨治疗65例胆管细胞癌(其中34例为ICC)的研究显示,第1次疫苗注射后3个月按照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标准评估,全部患者中部分缓解4 例、疾病稳定15例,1年生存率为69%,2年生存率为31%[17]。另外,细胞因子诱导杀伤(cytokine induced killer,CIK)细胞也有机会作为肿瘤疫苗治疗ICC。有研究[18]表明,人CIK 细胞能够减少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小鼠体内ICC细胞的增殖。针对肿瘤特征研制的个体化肽疫苗也能诱发抗肿瘤免疫反应,延长无瘤生存时间。Löffler等[19]使用这种疫苗治疗1例ICC伴肺转移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生存期为5年。因此,肿瘤疫苗尤其是个体化疫苗有望在ICC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分子靶向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通过抑制肿瘤细胞膜表面分子从而抑制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来控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黏附和运动。ICC中主要存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FGFR)、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表皮细胞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R)、乳腺癌1型易感蛋白相关蛋白-1(breast cancer type 1 susceptible proteinassociated protein-1,BAP1)等分子突变[20]。目前有多种分子靶向药物正处在临床研究阶段,部分药物已在ICC治疗中取得进展。
2.1 FGFR抑制剂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信号可调节细胞增殖、分化,促进伤口修复,血管生成和迁移[20]。一项选择性泛FGFR 激酶抑制剂BGJ398 治疗FGFR 突变的胆管细胞癌的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总体缓解率为14.8%,疾病控制率为75.4%,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期为5.8 个月[21]。另外,非选择性FGFR 抑制剂帕纳替尼(ponatinib)和帕唑帕尼(pazopanib)也对FGFR2 基因突变的晚期ICC患者有效。1例FGFR2-MGEA5突变的晚期ICC 患者接受吉西他滨和顺铂治疗6 个月后病情恶化,改用ponatinib 单药作为补救治疗,6 周后发现肝尾状叶处肿瘤坏死,转移淋巴结明显缩小,CA19-9 由1 408 U/mL 降至142 U/mL[22]。另外6 例ICC 患者早期接受pazopanib 单药治疗,疾病得到控制,随后疾病进展改用ponatinib 治疗,疾病再次得到控制[22]。这也提示ponatinib可以作为对pazopanib耐药者的二线治疗药物。另外,一项关于BGJ398(口服选择性FGFR激酶抑制剂)的Ⅱ期临床研究中期分析结果显示,该药对胆管细胞癌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疾病控制率达82%[21]。近日,FGFR 抑制剂厄达替尼(erdafitinib)已被FDA批准用于晚期尿路上皮癌的治疗。鉴于之前erdafitinib(JNJ-42756493)针对晚期或难治性实体肿瘤的Ⅰ期研究结果,尿路上皮癌和胆管癌对erdafitinib 的应答率最高,分别达46.2%(12/26)和27.3%(3/11)[23]。因此,erdafitinib 有望在ICC 治疗上发挥重要作用。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FGFR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化疗均可以作为ICC治疗的可选项。
2.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受体抑制剂
VEGF是调控肿瘤血管生成的主要细胞因子,在肿瘤内皮细胞和肿瘤细胞中过度表达,VEGF受体抑制剂旨在抑制肿瘤新血管形成[24]。据报道,VEGF在53.8%的ICC患者中过度表达,表达水平与不良预后呈正相关[4]。由于VEGF 受体抑制剂可以修复肿瘤微血管平滑肌,从而改善微血管功能,提高化疗药物输送效率,促进其吸收,进而抑制肿瘤生长[25]。故VEGF受体抑制剂联合化疗药物可作为改善ICC预后的治疗方法。
索拉非尼(sorafenib)是一种多激酶抑制剂,能够靶向抑制包括VEGF 受体在内的多种酪氨酸蛋白激酶,目前已作为肝细胞癌和肾细胞癌的一线治疗药物。临床前实验表明,sorafenib在体外和体内均可抑制ICC 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26]。Sorafenib 单药治疗晚期ICC的单中心临床研究也显示,15例患者中4例病情缓解,7例病情稳定,疾病控制率高达73.3%,中位总生存期达5.7 个月,疾病无进展生存期达5.5个月[27]。有1例ICC患者经sorafenib治疗后生存时间将近4年[28]。1例混合型肝细胞-胆管细胞癌患者,手术切除后3个月出现淋巴结和骨髓多发转移,连续服用2年sorafenib,因出现不良反应停药,一年后仍无转移复发迹象[29]。这些研究都表明sorafenib 对ICC 有效,可以作为晚期ICC的靶向治疗药物。
阿帕替尼(apatinib)是一种高选择性VEGF 受体2拮抗剂,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介导的细胞迁移和侵袭,降低转移相关蛋白表达水平,来抑制ICC发生发展,是ICC 治疗的一种潜在有效的靶向药物[30]。Apatinib 联合替吉奥治疗23 例晚期ICC 的结果显示,疾病缓解率为34.78%,疾病控制率为78.26%,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期为5.2 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7.8个月[31]。不良反应主要有蛋白尿、高血压、手足综合征等,发生率高达70%,停药后均可获得缓解[31]。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吉西他滨和顺铂联合VEGF抑制剂西地拉尼(cediranib)或安慰剂治疗ICC 患者的疾病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8.0 个月和7.4 个月[32]。尽管apatinib、cediranib等VEGF受体抑制剂单药对ICC患者是否有效目前尚不明确,但也证明这些抑制剂联合化疗治疗ICC是有效的,更加优化的方案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2.3 EGFR抑制剂
EGFR 是由原癌基因编码的细胞膜受体酪氨酸激酶。有表皮生长因子、肝素结合因子和双向调节因子等多种配体,这些配体与EGFR 在胞外区域偶联,启动细胞内信号级联,增加细胞增殖、运动和侵袭的能力[33]。有研究显示,28.6%的胆管细胞癌患者表达EGFR,且Ⅲ和Ⅳ期患者表达水平更高。EGFR表达阳性的患者12、24、36 和48 个月生存率分别为100%、75%、50%和0,阴性者分别为100%、87.5%、65.6%和65.6%。这表明EGFR 表达与ICC 的不良预后有密切相关性[34]。一项体外研究显示,EGFR抑制剂afatinib 通过阻断EGFR-STAT 3 信号通路可抑制ICC 细胞增殖[35]。然而,也有EGFR 抑制剂单独治疗ICC的临床试验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可能与肿瘤细胞耐药有关,具体机制尚不清楚[36]。ICC 的高度耐药性,为分子靶向治疗增加了难度。有研究表明,与单独接受Gemox(吉西他滨与奥沙利铂)化疗的晚期胆管癌患者相比,EGFR 抑制剂联合Gemox 治疗可提高疾病的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无进展生存期,但总生存期并未得到延长[37]。这为EGFR 抑制剂联合化疗治疗ICC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以后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了思路。
2.4 IDH抑制剂
IDH 催化异柠檬酸转化为α-酮戊二酸,由IDH基因突变编码的异常IDH使α-酮戊二酸的代谢产物2-羟基戊二酸水平增高,这种突变与DNA 甲基化相关并可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瘤体血管生成[38]。15%~22%的ICC 患者存在IDH1 和IDH2 突变[39]。一项根据影像学预测IDH 基因突变的研究结果表明,ICC 患者的肝脏增强CT 中IDH 突变的肿瘤内血管较多,边缘和中心均有多发强化灶,进一步证明了IDH 突变对肿瘤血管生成的促进作用[40]。已有研究证明IDH1 抑制剂AG-120 和IDH2 抑制剂AG-221 对IDH 突变的ICC 具有暂时性控制作用[41-42]。IDH 抑制剂dasatinib 针对ICC 的Ⅱ期试验正在进行中,目前尚未有明确结果。
3 其他靶向分子
多种促进或抑制ICC 发生发展的相关分子仍在研究过程中,虽然目前尚未开发出针对性靶向药物,但可为治疗ICC提供线索。
3.1 BAP1
研究表明,BAP1 表达水平降低或基因突变可加速肿瘤的发生、侵袭、复发和转移[43]。73.3%的ICC患者肿瘤组织中BAP1 相关信使RNA 和蛋白质分子水平显著降低,BAP1通过抑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ERK1/2)和c-Jun N 端激酶/c-Jun 通路,从而在ICC中发挥抑癌作用[44]。生存分析显示,在卵巢性脊髓间质瘤、肺癌、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BAP1 低水平表达或突变可使总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降低[45]。目前认为BAP1 是ICC 的抑癌因子,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和潜在的治疗靶点。
3.2 巨噬细胞调节因子CD47
最近研究发现,阻断CD47 与其信号调节蛋白SIRPα相互作用可加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从而抑制ICC 的生长和转移[46]。CD47 抗体抑制分子B6H12.2能特异性增强巨噬细胞吞噬活性,提示抗CD47分子和SIRPα 阻滞剂的潜在作用[47]。因此,CD47 可作为调节巨噬细胞途径的改善ICC预后的分子。
3.3 微小RNAs(miRNAs)
miRNA 在肿瘤微环境中调节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和侵袭,可促进或抑制肿瘤的发生发展。ICC细胞中的miR-21 分子可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其致癌作用与抑制CTLA-4和金属肽酶抑制剂TIMP-3的表达有关[48]。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ICC 患者体内循环中miR-21水平下降,而在姑息性切除患者中没有下降,提示血浆miR-21 水平可作为评估预后的指标[48]。ICC 中miR-26a、miR-191 和miR-181 的高表达与临床分期、远处转移、分化状态及患者预后不良密切相关[49-50]。miR-145分子可能通过抑制新式激酶家族1通路从而抑制ICC 细胞增殖,可作为ICC 的抑癌分子[51]。这些起到抑癌或促癌基因作用的miRNA分子均有望成为治疗ICC的靶点。
4 结语
尽管目前ICC 免疫治疗和分子靶向治疗的进展有限,多数研究尚处于Ⅰ、Ⅱ期临床试验,Ⅲ期临床试验数量较少且未取得明确成果,但有些已让部分患者获益,提高了生存率。随着对ICC肿瘤微环境和免疫微环境的逐渐重视,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值得不断深入挖掘,也将会给这种高度恶性肿瘤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此外,在不断推进ICC临床试验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患者的耐受性、耐药性及药物不良反应等。总之,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ICC的方法仍需不断地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