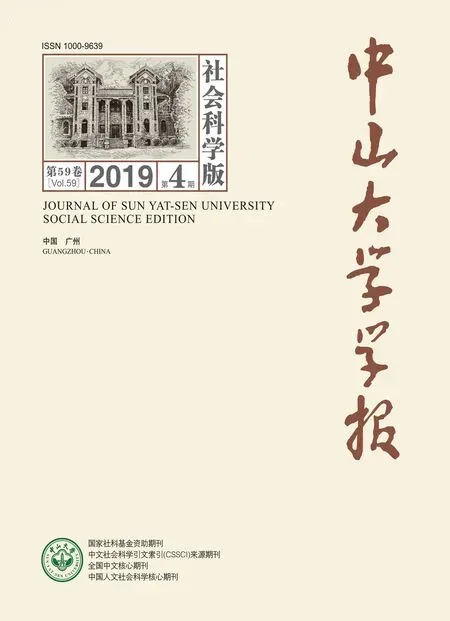融合与断裂*
——对美国波士顿“在家教育”学习网络的人类学分析
尚 文 鹏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人?康德指出:教育是人性塑造的核心因素①康德在《论教育学》中有这样两句论断:“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人只有通过人,通过同样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教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则关涉教育的目的、场所和实施者等。参见[德]康德著,赵鹏等译:《论教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但由谁充当教育的实施者,在现代性背景下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学校教育是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与人类自古有之的家庭教育始终处于张力之中。在关于教育理想的主流论述中,自由是一个关键字眼,一个自由的人是具有理性反思能力和自主支配能力的个体,但到底是家庭还是学校更有利于培育自由?经由怎样的途径才能实现自由?是靠保护和顺应人内在的自然,还是靠理性的力量来施加外部的限制?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构成了教育哲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维度。
洛克和卢梭在自由教育上所诉求的对象都是家庭,洛克强调通过习惯的培养来达到理性自主,只有家庭才能帮助孩子培养好的习惯,成为合格的绅士。卢梭认为自由教育就是自然教育,这不是诉诸于理性的意识,而是尽可能以自然为限度来存留人的自然成分,家庭最贴近人的自然,经由自然自由,进而到达道德自由,最后实现政治自由②参见渠敬东、王楠:《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33、177—180页。。但在涂尔干看来,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年轻一代的社会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单纯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知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注][法]爱弥儿·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8,43页。,因此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必须通过外在规则的灌输才能培育社会人。但是说涂尔干完全忽视个体也不公平,他说:“通过道德规范的实践,我们养成了一种能够支配和规定我们自身的能力,这才是自由的全部实在。”②[法]爱弥儿·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8,43页。他坚定地认为学校是连结个体与社会的最好的中介组织,只有在学校里,道德个人主义的建构才成为可能,亦即,学校教育在孩子身上加诸社会存在,而成功的社会化必然使孩子成为自主的理性主体。与涂尔干的观点针锋相对,福柯揭露了学校教育反自由、非人性的一面。在他看来,学校如同监狱、医院等一样,是一种规训机构:通过奖励好的行为、惩罚坏的行为来达到支配学生的目的[注]参见Nick Stevenson. 2011.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SAGE Publications Ltd., p.104。。遗憾的是,福柯对学校的反思止于批判,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建设性构想。
纵观历史,现代性的发展同时也是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节节败退的过程,学校教育完全压倒家庭教育,成为现代社会支配性的教育形式,生产并塑造了一个社会的集体生存心态。而家作为私领域,承担了更多的情感功能。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在家教育[注]2016年,美国在家上学的学生人数为170万,占5—17岁学龄人口的3%。参见McQuiggan, M. and Megra, M. (2017). Parent and Family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Household Education Surveys Program of 2016 (NCES 2017-102).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近年来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也不断出现。在家教育原本就是人类的传统,只是在进入现代性的时空之后,在学校教育成为主流的语境下,在家教育才区别于一般的家庭教育。只有作为一种反传统和替代性的教育形式,它的兴起和实践才在学理上具有了研究的意义。
本文探究的是在家教育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探讨的问题包括:在家教育奉行怎样的教育理念?其对教育理想的践行有哪些特征?在家教育是否如其名称所示,在与学校相对的家庭领域内实施?如若不止如此,它在哪些方面挑战了学校—家庭二元对立的观念?这种“另类”教育形式对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培育和人性塑造又有哪些意义?
笔者曾于2013—2014年对美国波士顿的在家教育做过一年的田野调查,访谈了38个家庭,每次时间从一小时到五六个小时不等,经受访人同意,采用录音与笔记结合的非结构性方法。2018年6月,笔者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继续进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家教育”的研究,对其中的8位以邮件和Skype方式进行了回访。所有受访的家长都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4人有硕士或以上学位,大多全职在家,或者从事的工作允许有相当多的时间在家。
二、重估“学习”
在对家长的访谈中,“学习”是被反思最多也是讨论最多的话题。在许多人看来,学习是自然而然或者在无意中发生的。它被描绘为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正如在家教育的倡导者和核心人物约翰·霍特(John Holt)所说:“鸟会飞,鱼会游,人会学。”[注]Holt, John. 1981. Teach your Own: A Hopeful Path for Education.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既然是一种天赋,那么任何形式的强迫都是不必要也是不可取的。这样的学习如何进行呢?好奇心是在家教育的核心概念,以孩子的好奇心为学习的唯一指向,因此,什么样的知识更有价值,应该什么时候学,都取决于孩子的兴趣。
如卢梭所言,根据孩子所处的年龄阶段,人的教育必须以自然的内在要求为主导,用否定性的方式,保护内在自然免受社会的侵害[注]参见梁敬东、王楠:《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棱的教育哲学》,第168—169页。。由此,教育的重心不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灌输,而是如奥古斯丁所说的“唤醒”。他的论述中有一个关键的“内在人”意象,即每个人有一个内在的自我,所谓的教诲是教师通过符号游戏而把学生内在的知识激发出来的过程。这种唤醒式的教育,强调的不是教师输送,而是把学生“内在的人”照亮,启发他的自然,“学”才是更为根本的目标。“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教”的手段不是强行灌输,而是着眼于如何创造条件,使学生内在的自我一点点显现[注]李猛:《指向事情本身的教育:奥古斯丁的〈论教师〉》,《教育与现代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6—33页。。
相信并强调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这种观念突出地体现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学说中,他谓之为“自发性”、“直觉”或人的自然天性[注][美]拉尔夫·瓦尔多· 爱默生著,蒲隆译:《自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2页。。自我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在与外界互动中不断向内探索和创造的思想过程。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孩子实现对自我的探索,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显然,对许多父母来说,学校的标准化倾向无法满足不同个体的需要,这是促使他们选择在家教育的重要原因。
在对“学习”的反思和重估下,孩子的教育被重新安排。学习的范围突破了学校所规定的书本内容,进而囊括整个生活世界,打破了生活与学习之间人为的界限。好几位家长都提到在当今社会,信息触手可及,“还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有规规矩矩坐在课堂里才能学到知识,就太落后了”。
Tina 的个案比较有代表性。她的家是一栋三层小楼,客厅显眼处摆着一架钢琴,饭桌上有一本《新闻周刊》, Tina说那是他们家订的唯一一本杂志,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还有一本日历,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顺便学一个单词,墙角的沙发上散放着几本书。三楼书更多,Tina在那里放了几排书架,俨然一个家庭图书馆。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后院,被辟成一块块小小的菜地。她的女儿Anna跑过来展示她的“蔬菜生长”笔记本,她与爸爸是笔记本的主人,一起分门别类记录蔬菜的长势和特性等。
Tina介绍:相较于学校的“备用学习”(just-in-case learning),她实践的是“即时学习”(just-in-time learning)。“播撒(strewing)指的是在家里到处摆上我们事先选好的书、碟、游戏,等着孩子自然地去发现,想读什么看她的兴趣。” 正如一位妈妈在访谈伊始所声明的:“一般人老以为在家上学就是固定在厨房桌子边学习,我们可不是这样,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家里复制学校。”
三、重新审视“社会化”
“社会化”常常被认为是在家教育的最大缺陷,很多学者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担忧。在这些阐述中,在家上学的孩子被想象成孤立于大众人群之外,自缚于“茧”(cocoon)[注]Michael W. Apple. 2000. Away with all teacher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ome school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0(1): 61-80.,在社交场合是不合时宜的另类。但也有学者调查发现,在家上学的孩子无论在学业成绩、自我意识、公民参与以及成年后的生活各方面,都不比学校教育的孩子差,甚至很多数据显示要优于后者[注]Brian D. Ray. 2013. Homescchooling Associated with Beneficial Learner and Societal Outcomes but Educators Do Not Promote It,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iton. 88(3): 324-341; Richard G. Medlin. 2013. Homeschooling and the Question of Socialization Revisited,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iton 88(3): 284-297.。
Cathy跟我讲起第一次接触这个群体时的情景:“几年前我去阿灵顿艺术中心参加一个活动,正好碰上十几家在家教育的家庭聚餐(potluck),我问起让我担忧的社会化问题,结果每个人都笑起来,他们说,在家上学的最大优势恰恰是社会化!学校的社会化过程才奇怪,在家上学能够更好地有机地进行社会交往,所谓有机,指的是顺其自然,我们的孩子可以与大人,与各种不同年龄的人交往,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这些话打动了Cathy,她只有一个女儿,正觉得她太孤单,于是也开始在家教育了。
“真实”、“开放”,是他们认为在家教育“社会化”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特征。Zoe这样对我表示学校模式下“社会化”的虚假和封闭:“学校是一个如此刻意的环境,外面的世界那么大那么复杂,而我们却在同一栋大楼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跟和我们相似的同一拨人在一起,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困在一个密封的细菌培养液容器里面。并不是说我的老师和同学不好,没有,只是这种设计样式根本就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谁会把40岁的人跟同样年龄的人放在一间屋子里,说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只能你们在一起交往?”Fiona以在Cathy家上写作课的例子来阐述在家上学社会化的有机性:“你看,这4个孩子最大的14岁,接下来是12、11和9岁,他们相处得很好,大的懂得顾及小的孩子的节奏,小的会尊重大的,没有等级之分,大家互相尊重容忍,而学校才是一个人为制造出的机构,同样的年龄,学习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进度,而且孩子对这些丝毫没有发言权。”
围绕着“什么是真实的社会化”、“哪一种教育才能更好地适应真实的社会”,在家教育的父母们创造了一套与学校模式相对抗的话语。如同对“学习”的重新定义,“自然”、“有机”被标榜为社会化的特点,以表明在家上学的社会化并不是遮蔽而是更富有人性和情感。这并不是说父母不需要给孩子建立规范,但他们普遍认为,相比学校,父母们在道德教育方面更能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性,更能保护孩子的内在自然。但另一方面,没有了学校围墙的限制,这些孩子又进入另一片往往是由父母选择的天地中,尽管范围可能更广阔,但更趋于阶层性的聚集。
四、重构学习网络
在家教育可以被想象成一个类似同心圆的动态统一体,它是由父母发起的,以家庭为核心,向更大的社区和社会扩展的过程。当教育回归家庭,教育并没有被人为地分割为一项单独的事务,而是成为抚育(parenting)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原则,学习渗透进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波士顿有各式各样优质的教育文化资源,父母们连接并整合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社区大学等社会机构,为孩子创建了一个绵密的学习网络。
(一)“城市学校”
经常有父母表达对“homeschool”这一称谓的质疑,他们认为自己的教育行为多数不发生在家里,即使在家也不是对学校的复制,怎么能是“家庭学校”呢?Katy说:“我们经常拿这个词开玩笑,因为我们真的是难得在家。”
Ben用“城市学校”来代替“在家上学”:
“homeschooling”只是一个统称,在文件上是这么写,我们自己家是说“city school”。我一直觉得学校在学业上的挑战不够,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周末去参观博物馆和各种展览,去看城市的排水系统如何运作等等。八年级向剑桥学区递交了在家教育申请之后,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我们带着三个孩子到处旅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教室。我们去了康涅狄格州的飞机制造厂,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华尔街。旅行是以学习为导向的,回来后让她们就某一题目写文章。
对在家教育的家庭而言,旅行模糊了常规生活中固有的分类范畴,如学习和玩耍、理论和实践,甚至不同时空的界线和亲子之间的权威关系都趋于消弭。“在旅行中学习”被塑造为一种优于学校模式的方式:它是自然有机的,在与外界的广泛接触中可以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正如一位妈妈所说,在家上学有这样的好处,可以避开人多的公众假期,经济上也更为划算。Tina向我介绍的“即时学习”理念,除了“播撒”之外,另一种是“serendipity”(意外发现珍宝的运气),尤其适用于旅行中:
比如说当孩子在路上碰到一只蜗牛,她想知道蜗牛吃什么,就去查资料,但在学校的话,可能到六年级,才正式学到蜗牛是什么纲什么属的知识。上次我们去参观殖民地时期的威廉斯堡,住在现代化的度假村里,却在那些重建的殖民地房屋里发现了类似我们家的生活方式,Anna为此兴奋不已,对那个时期的美国历史充满了探索的兴趣。
除了旅行,波士顿众多的文化机构是这些家庭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其中图书馆是最常被提及的。每一个市镇都有几个图书馆,对居民完全免费开放。各种博物馆和展览也是这些家庭频频光顾的场所。每个城市的图书馆都为市民提供一定限额的免费票券,在家上学的孩子更可以利用非周末时间申请这些免费票或者办理优惠年票。有一位妈妈这样表达她的感受:“孩子上学的时候,天天忙着上课和作业,那时候就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却没办法充分利用,好可惜。”比起不得不周末使用这些资源的上学的孩子,这些家庭认为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权。正如Tina所说:“我们不用跟他们挤周末啊,周末我们什么都不安排,那是我们的家庭时间。”
(二)教育内包
除了由父母亲自实施的教育之外,还有家庭之间的资源整合。相比把孩子送到托儿机构的“教育外包”,“教育内包”现象既有赢利的因素,又混合了情感和合作性质。
有一些已经“退休”的家长,孩子长大不再在家上学了,就为其他的孩子上课。如Carey在波士顿城区就为许多人知晓。她住在剑桥,每周去牛顿、沃瑟姆、阿灵顿给8个不同的班上文学课,每次课收10到15美元。有些曾经在家上学、现在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也会回来辅导小孩子。Daphne的两个女儿就以这种形式上了一年的数学和物理课,“因为他们也是在家上学长大的,大家的学习理念和方式都很相近,很好沟通,而且他们也曾经在学习或成长中遇到相似的问题,辅导起孩子来有说服力和针对性。再说,这些大孩子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知根知底。收费不贵,就是给这些大孩子一个兼职的机会,对大家都好”。
几个家庭的家长还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组织不同的活动小组,如文学、历史、数学、逻辑等等。这些合作社性质的联合对孩子有明显的教育功能,整个家庭作为交往的单位,也可以更深地彼此了解,生活交叉在一起。Tony的女儿Jodie的教育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家庭之间的资源共享:“我们有几家人总是一起做事情,典型的一周是这样的:周一,去一个人家里学数学,周二来我家学写作,周五参与一个科学项目。很幸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社区,很多父母愿意说:‘嗨,我是作家,我可以给孩子们上写作课。’有一个朋友是厨师,愿意教孩子们烹饪。”
1999年,几个在家教育的家庭一起在麻州的阿克顿(Acton) 创建了“航海者”(Voyagers)合作社,这意味着在家教育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开辟了家庭之外的专属物理空间。“航海者”发展至今,已有70多个家庭。它是家庭互助小组模式的延伸,共同之处在于知识技能互惠,不同之处在于空间的固定性以及来源于但又超越于个体家庭的权力运作。它是一个志愿性的非营利组织,由在家教育家庭共同管理并提供资金支持。在家教育的家庭可以选择每周固定的一天聚会,收费以家庭为单位,也就是说,有4个孩子的家庭与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缴纳相同的费用。这项规定既能减轻多子女家庭的财务负担,又能确保家庭的集体参与,实在有经济困难的家庭可享有助学金,也可以选择承担更多的清洁工作,以抵消一定数额的保洁费。每天的课程和活动由当天的几个家庭共同商议决定,是否参加取决于孩子的兴趣和能力,而不是年龄。一般来说,老师由当天的父母或者家里年龄较大的孩子充当,本质上是一种技能互惠。有时候也会请外面的老师,有一些家长若不提供课程,也被期望以别的方式来参与合作社的管理,如看管那些父母去上班的孩子,维持合作社的卫生和秩序等等。因此,每位家长都不会闲着,对合作社的日常运作都负有责任。每天有一位家长作为义务管理员,负责当天的日常管理。
尽管合作社与学校同样有实体的物理空间,但本质上不是学校,它不对孩子的表现打分,没有固定的课程,上什么课完全由个体自主决定。合作社也不是托管机构,所有的家长都必须和孩子在一起,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负有完全的责任。它的运作摒弃了学校的等级制权威结构,而是人人平等参与的民主组织形式,个体有权利参与决定与自身有关的事务,同时对他人和合作社有相应的职责,活动的安排等事宜也有赖于相互的协商。在将合作社建构成道德共同体的过程中,互相依赖、共同合作的共同体意识很自然地生长出来。合作社的情感色彩已经对它的成员们产生了切实的吸引力。晚上7点是合作社关门的时间,草地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家长和孩子在谈话玩耍,Fiona的大女儿Eva告诉我,她每周最盼望的日子就是星期三,因为可以去合作社。
(三)哈佛继续教育学院
有组织的结构化学习在在家上学的孩子中也极为普遍,尤其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龄,社区大学和哈佛继续教育学院是非常普遍的选择。这里我将以哈佛继续教育学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以下简称哈佛教育)为例,分析在这些父母的逻辑里,以好奇心为导向的学习是如何与制度化的学习相容的。
Ben在学区为3个女儿申请在家上学后,除了“城市学校”,另外就是在哈佛教育上课。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并数次向我提及对哈佛教育的感激之情:
孩子从十年级开始就在哈佛教育修生物和拉丁语,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在这条路上走得特别远:高中四年,每个孩子在这里修了20多门课。我心里特别感谢哈佛教育,真正是一所极好的完美的机构。波士顿大学也有这样的项目,向高中生提供大学课程,但我觉得哈佛教育的优点在于高中生也与其他人一样受到平等对待。
在Ben看来,哈佛教育的价值在于其卓越的师资和打破年龄的界线。显然,对于高中生来说,哈佛教育的老师在资质上要优于剑桥高中。我参加了哈佛教育2014年春季宣讲会(Information Session),招生的老师告诉我:这里的课程适合各种水平的学习者,没有入学门槛,只需要有学习的热情。学生最小的才12岁,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所以一个课堂的学生什么年龄都有。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高中生选择哈佛教育,其中在家上学的孩子也显著增多。非学分课程每门1 250美元,学分课程每门2 500美元,高中学生可享受50%的优惠,因此与社区大学差不多(社区大学对高中生也有优惠,每门课是650美元)。
为什么从学校机构出来,却又进入另一种机构呢?难道那不是封闭的环境、统一的内容吗?家长们不约而同地诉诸“让孩子选择”的话语。如Ben所言:“那不一样,重要的是孩子可以选择上什么课,如果她不喜欢,比如说老师,或同学,或者别的什么,可以离开,而在学校则不可以。”
(四)市场的参与
除了充分利用公共社会资源,家长们越来越多使用的是一种叫做“自主学习中心”(self-directed learning center,以下简称中心)的商业性教育机构。它是私有化教育大潮下的产物,近年来纷纷涌现。Zoe说起这一趋势显得有些气愤又无奈:
真的是层出不穷啊(mushrooming)!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反对这些机构,但是有一点要搞清楚,这不是在家教育。既然你们接收孩子,那就去申请执照啊!像现在这样,打着“在家教育”的旗号,我感觉他们在利用“在家教育”。他们自称“替代性的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拜托,那是“替代性的学校”(alternative schools)好不好!他们希望的就是家长每天都把孩子送到那里。那不是学校是什么呢?没错,社会应该提供多种教育选择,教育不应该被标准化。但我关心的是独立的在家教育,而不是被虚拟学校或是这种中心所破坏。这是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在家教育俨然已成了一个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Zoe的不安是有道理的。考察在家教育的动机,许多家长不甘于由学校控制孩子的教育,不甘于标准化的教育,意在寻求父母在孩子教育上的主导作用,并依据孩子的内在自然,培育有个性的人;而且她们遵循的自然教育也表现为对消费主义的抵制,如今将孩子送到“中心”,岂不是一种悖论吗?
事实上,围绕着这种市场化趋势,在家教育群体已开始出现分化。Lydia和Zoe等20年前就开始在家教育的家长,感慨如今丰富的资源削弱了父母探索的主动性,让他们变得疲于奔命。Lydia感慨道:“花上几十美元报班,在众多活动中驱车来往,这中间会失去什么呢?比如穿着睡衣跟孩子拥在一起读书,在一个无事可做的下午无意中有了惊喜的发现,或者当别的孩子都困(cooped up)在学校的时候,几家人在秋天的瓦尔登湖边消磨掉半天的时间,直到日落才散。”Lydia认为,市场对“在家教育”的影响在于把这个群体变成一个个网络(networks),貌似热闹温暖,实际上,她引用盖图在Dumbing us down中的话,让人有种城市居民所熟悉的“明明身处人群之中,却感觉孤独的奇怪感受”。
与这些资深在家教育父母不同的是,许多人对中心持支持和欢迎的态度。Daniel说他知道这些机构没有申请执照,“但那又怎么样?有执照就可以更具效力吗?你看看许多政府机构倒是正式批准成立的,还不一样办事效率低下?我觉得这些中心的存在对于那些单亲家庭,和不得不工作的父母有很大帮助,这样他们就能实现‘在家教育’了”。
尽管中心也奉行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但正如Lydia等资深在家教育家长所指出的,问题的关键是教育的主导权在谁手中。将孩子送到“中心”,父母表面上仍享有主导权,但实际上却减少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以及在不知不觉中传递文化资本的机会。这便是市场给“在家教育”出的难题。
结论与讨论
培育自由是现代教育在个体身上开展的目标,在家教育本质上是以“自由”为指归的教育实践。换言之,在一部分中产阶级家庭看来,正是因为“自由”的教育理想不能在学校体制下很好地实现,所以才诉诸这种反传统的教育形式。在中国,对学校教育的不满亦是选择在家教育的主要原因[注]任杰慧:《中国式在家上学:R学堂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0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卢梭意义上的教育试验,即相信并保护孩子的内在自然,根据环境创造适宜的条件,顺应内在自然的发展,使孩子获得精神自由和自主支配能力。而在家教育之所以近年来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当归“家长主义”的盛行。这是新自由主义逻辑支配下的产物,强调家长的自主选择权,家长介入教育的比重得以增大[注]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南京社会科学》 2015年第2期。。从实践来看,在家教育并非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单一和封闭,而是一种以融合及弹性为特点的学习网络。
首先,在家教育并没有局限于家庭领域,而是整合资源,构建多种形式的学习网络:从家庭内部延伸至广阔社会的学习网络,打破了固有的边界。相当一部分人从自己孩子的利益出发,并不完全排斥学校的活动,如加入学校的合唱团、足球队或者使用图书馆,甚至经过协商,有些孩子在公立高中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课。范·杰内普发现,所有的仪式过程都有着标示性的三个阶段:分离阶段、阈限阶段以及聚合阶段。其中阈限阶段处于两种结构的中间地带,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注][美]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等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阈限没有明确的类别归属,它既是边缘的、无力的,却也孕育着产生新的结构的力量。在家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有阈限性的特征,它所建构的社会空间穿越于家和外界之间,使两种不同属性(私领域和公领域)的空间界线变得稀薄和可穿透。随着国家和市场对在家教育的进一步接纳和介入,越来越多的混合教育形式出现了,在家教育变得越发难以归类了。这种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内在的关联性,非常契合我们这个社会的流动性逻辑。
其次,在家教育的逻辑不乏前后脱节之处,这种混乱也导致了这一群体内部的分化。他们遵循自然教育,反对外部强加,却又用新自由主义流行的“选择自由”来为哈佛继续学院制度化的学习形式辩护。他们主张由父母主导教育,对消费主义充满警惕,却对私有化教育机构态度模棱两可。在家教育的父母虽然反对学校的“标准化的人”,致力于培育“特殊的人(有个性的人)”,但在国家和市场的干预下,似乎正在陷入新的标准化。
回到文章开头,涂尔干将学校视为建构道德个人主义的唯一希望,笔者认为,在家教育的实践对现代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现代社会存在包括学校在内的多种中间组织,对其进行有效的整合,也许能够更大程度地使孩子成长为社会人。正如查尔斯·格伦在“在家教育全球大会”上指出的那样,政府不应该垄断教育,而应让公民社会的第三种力量参与进来,如家庭、宗教组织、志愿性团体等社会的“中间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s)[注]Charles L. Glenn. 2012. “Can families be trusted?” Keynote address at Global Home Education Conference, Berlin.。现代社会存在着包括学校在内的多种中间组织,对其进行有效整合,也许能够更大程度地使孩子成长为具有自主支配能力的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