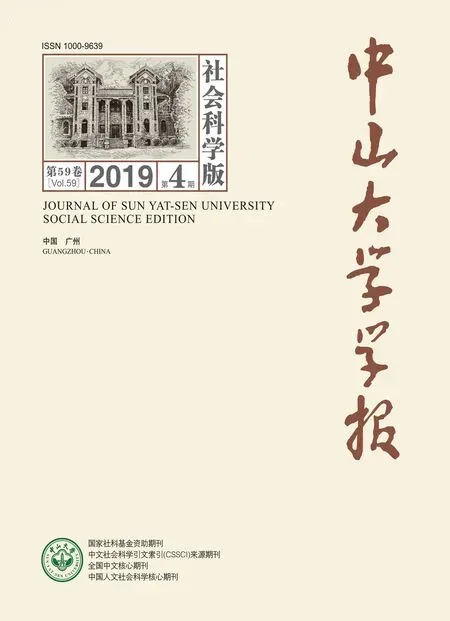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
李 义 琼
白银财政体制的建立,是明代国家与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①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第19页;《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专栏解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66页。,明代盐法的变革,便属此趋势中的重要领域的重大变化②黄国信:《盐法变革、商业繁荣与国家和市场新型关系研究——基于明代财政体系演变的考察》,《海屋集——黄启臣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5—326页。。明代盐法有开中法、在司纳银制和纲盐法,以纲盐法尤为学界关注③开中法为明朝管控盐业产、运、销,利用商人在边纳粮、附场支盐的管理体制,在司纳银制为明中叶出现的盐商在运司纳银开中或交纳余盐银的管理制度,纲盐法则是明末户部强制佥派固定盐商交税服役的制度。参见[日]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87年。藤井宏:《明代盐场の研究》下,《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54年。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第4期。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志“纲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明代的公共资本市场:以两淮盐引为中心》,《明代研究》第十期,2007年;《盐引·公债·资本市场:以十五、十六世纪两淮盐政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汪崇筼:《明万历淮盐疏理中的两个问题和利润分析》,《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4期;《明万历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2期。,但因其本身的复杂性或分析视角多集中于盐业本身之局限,以往的盐法研究多侧重两淮而少论及两浙,本文将淮浙联系起来考察④淮浙皆为国家盐法重地,所行盐制一致,且给国家交纳的盐课银位居前两位。例如万历间两淮两浙交给户部太仓银库的盐课银,据万历《大明会典》和《太仓考》的记载,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74%或75%。,以晚明盐课银分配的三大去向——库价、京解和帑银为主线,探究户部在白银需求驱动下主动调整盐法的做法,认为:在司纳银制确立后,又出现了盐商到司领银的制度;为保障中央财政的盐课收入,户部加强对内商中资本雄厚者的身份性管控;明代盐法从官专卖走向商专卖的标志,是比两淮纲盐法更早的两浙纲纪制度。
一、库价:从边中场支到在边纳粮、在司支银
开中法为明朝管控盐业产、运、销,利用商人以物(粮草)易物(盐)、边中场支的盐业管理体制。从明中叶到明末,开中法出现了系列变化:弘治以后,边方纳粮开中和运司纳银开中并存[注][日]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第281页。;同时,白银支付越来越广泛成为开中运行的主要手段,边商除了赴运司纳银取代在边纳粮外,还出现了到司支银而非赴场支盐的情况。晚明边商在运司所支白银,时称库价、给商银或给客银等,主要在两浙两淮实行[注]徐泓曾在其论文中提及库价,但未展开研究。参见其文《明代的盐法》上,台北:台湾大学197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8页。。库价出现于盐课折银之后,两浙库价多为盐场灶户交纳的灶课银,也有州县代盐场交纳的盐课银[注]李义琼:《明代嘉万间盐课银收支与盐法体制变迁》表1、2、3,《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79—83页。,而两淮库价则主要为内商预交的商课银。二者皆贮于运司,用来支付纳过边粮拿到仓钞勘合后来到运司的边商,代替本应赴场指令的实物盐。
根据明人王圻的介绍,两浙库价出现于嘉靖二十七年,本来是从盐场征收来的用以支付给边商的“给客银”,大概每盐引扣除纸价三厘,“实给银二钱一分五厘”;而此盐引则是用于开中的正盐引,起初“仍听边商自行赴场买盐掣销”,即制度允许边商从运司领得库价后,仍然可凭一正盐引附带一余盐引的余盐政策,向盐场灶户购买盐; “后因边商赴场不便,将引转拨内商赴场买补,价归边商以补边价不敷之数”[注]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8《各场额征下·库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562,562,563页。。
领到库价后的边商很少赴场买补盐斤的原因,除向灶户购买盐斤需要大量资本外,还有两点:其一,两浙边商领取库价时,不仅未能补足其在边纳粮之全部成本,而且还需长时间守候。“边价每引三钱五分,及领库价,每引二钱一分五厘,实亏银一钱三分五厘。又须守候二年,方缠得领。全赖空引分拨内商,得价以补不足。”⑤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8《各场额征下·库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562,562,563页。可见,两浙边商所领库价不足额,而且还无法及时获得,“须守候二年”,甚至5年⑥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8《各场额征下·库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562,562,563页。。其二,余盐课银比正盐课银要高,这在嘉靖间余盐政策走向规范时便已确定。嘉靖十四年,两淮盐斤每包中的正盐一引(285斤)收税0.5两,余盐一引(265斤)淮南盐收税0.65两,淮北盐为0.5两,两浙每正盐一引(250斤)收税0.35两,余盐一引(200斤)所收税银,嘉兴、杭州、绍兴和温州批验所各不相同,分别为0.5、0.45、0.4、0.2两[注]嘉靖《盐法条例》卷12,上海图书馆藏古籍善本。需说明的是,淮浙正盐课银属于货币估算,并非开中实态,户部仍然强调边商在边上纳本色粮草。。总体上看,两淮两浙余盐斤数比正盐的略少,但余盐课银却比正盐课银要高。
以上两点对于资本不丰的边商来讲十分不利,所以边商很可能不愿赴场买盐,并完成交纳余盐银税收等后续环节。嘉靖二十六年的盐制规定:“边商有不愿赴场者,方许内商、牙店三面赴司告拨,即于边商名下注记明白,以杜冒领之弊。”[注]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9《边仓引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576—577页。于是,边商便将盐引转让给资本更为雄厚的内商,转让方式便是“空引分拨内商,得价以补不足”。所谓“空引”,应指尚未买盐运销的正盐引。边商同内商交易之盐引价格,根据边商是否愿意守候以领取库价,可审慎推测,正引价格在一钱三分五厘或三钱五分以上。更进一步来讲,边商转卖给内商的,其实是一种叫做小票(或左券)的凭证,只有即将轮到内商称掣时,才“将小票投换单引,赴场买盐运掣”[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1《边商·派场印挂单票》,《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这样,成本得到补足的边商才能边返回边方,准备应付下一轮开中。
万历时期两浙库价(给商银)约有89,952两,主要来自灶课银,约占灶课银总数(122,905)的73%,灶课银中解入户部太仓库的白银约15,555两,占灶课银总数的13%[注]李义琼:《明代嘉万间盐课银收支与盐法体制变迁》表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84页。。即政府从灶户(包括州县)征收的灶课银,绝大部分不是解入户部充作军费等,而是用来支付边商的价银。这与明初开中法下,运司系统从灶户手中征收实物盐,贮于盐仓,候商支领,程序上是一致的。随着在白银财政体制逐渐取代实物劳力体制,盐课领域也出现了白银税收“总收分解”趋势[注]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页。,导致白银解运时,不再区分它来自何种名目,也不按照原有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的规定去开支,常被挪作他用。如万历时期两浙的大部分灶课银,本应以库价形式支付给在边纳过粮草但到司支不到盐的盐商,然而户部在应对边饷压力时,对白银收支控制加强,一方面将白银运至京师的银库而非存放在各地运库,另一方面,有意挪解地方运库中的白银,以增加京师银库的收入,出现下文要探讨的京解挤占库价的现象。
两淮运司的库价比两浙的稍晚出现,户部尚书毕自严认为,库价由盐法疏理道袁世振创立,出于运司为优恤边商保持开中法的正常运转之目的,而且,库价是运司动用运库所贮白银预先支付给边商的,后来再从内商应交的引价银中扣除[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15《题遵奉圣谕议修盐政疏·重边商以维祖制》,《续修四库全书》第4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64页。。据袁世振本人奏云:“边商携仓钞到淮,倘即有引目填给分卖固善,恐一时引目未即关到,则运司先将库银给发,边商早得回边,速办下次盐粮,断不可以引目未到,使之需次穷旅,致悮(误)国课。”[注]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475《袁世振·盐法议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6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0页。可见他在两淮运司设置库价的意图,既是为了疏引行盐,充实边防粮草和户部银库,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边、内二商私下交易,边商受到内商“不肯预买”之苦,无法返回边镇继续纳粮开中之弊。
两淮库价与两浙库价的异同,简言之,二者都是户部下辖运司为了体恤边商,以维持在边纳粮的开中法的继续运行而设置的,但两淮库价主要来自运司向内商预征的引价银。“法今初行,或边商未必即到该司。查明四十五年应该行引内商的名,预征引价贮库,俟边商随到随给,不必与内商亲手贸易可也。”[注]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474《袁世振·盐法议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662册,第361页。两浙库价已于上文分析过,主要来自灶课银。两淮库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商拖延交纳价银,而两浙库价的主要问题,则是运司挪借库价,用来支付京解,即“奈两淮内商巧于拖延而日久不补,两浙那(挪)作京解而急彼缓此,斯库价之所以仅成具文而不能如期给发也”[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6《覆宁镇条议见给边商引价并清厘盐法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88,88页。。可见淮浙虽然皆有库价,但来源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稍有不同。
不过,从具体边镇来看,其所需盐粮所开中的盐引,可能既有来自两浙运司的,也有来自两淮运司的。以宁夏镇的盐粮为例,宁夏镇每年开中两淮盐引84,980引,两浙盐引112,014引[注]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39《盐法》“两淮盐运司”和“两浙盐运司”,《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69、1273页。。故崇祯间的宁夏镇巡抚耿好仁“谆谆为边商请命,议将崇祯四年以前仓勘径投运司,全给引价,以苏商困”,而两淮两浙的引价中,淮引中有库价二钱五分,浙引中有库价二钱一分[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6《覆宁镇条议见给边商引价并清厘盐法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88,88页。。
晚明两淮库价主要来源于商课银的事实,反映了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在盐法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户部通过盐课折银,将明初实物劳力为主的财政体制下本应由两淮运司负担的支付边商盐斤(征自灶户)的责任,转嫁到内商的身上。自明中叶盐商分化为三商——边商、内商、水商后,内商的主要任务便是接买边商的正盐引,下场支取正盐,买补余盐,并在批验所称掣后缴纳余盐银。这些余盐银,基本由运司解进户部太仓银库。也就是说,内商要为运司设置的偿付边商开中成本的库价提供白银,同时,还要给京师户部交纳余盐银。所以,内商在户部建立的白银财政体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晚明白银财政体制下,户部与内商的关系的问题,将在文章第三部分继续探讨。要明白这一改变对明代盐制的影响,还需要了解边商发生了什么变化。
库价乃户部下辖运司支付边商开中纳粮成本之白银,这体现了国家对边商的重视。那么,晚明的边商究竟是什么人充当呢?是否像内商那样,多由徽商、山陕商人充当呢?[注][日] 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第288—289页。据隆庆间(1567—1572)庞尚鹏的疏文可知,至少在隆庆年间,充当边商之人不再是远道而来的客商,而是本地商人,而且,本地商人并非自愿充当盐商,而是被政府佥派的,具有劳役性质[注]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4《清理宁夏屯盐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24页。。到万历间和崇祯初,边商的情况可在崇祯初年宁夏巡抚耿好仁的奏疏中得以窥见。他指出:宁夏镇的边商非资本雄厚的富商大贾,他们被政府强制佥派而非自愿充当盐商,“不过就山陕客民强派而应盐商”,带有商人应役之意;边商有小利可获时,尚能勉强支撑宁夏镇的粮草开中,但到晚明尤其是明末开中无利的情况下,资本不丰的他们已无法单独承担纳粮开中之役,甚至“听各商扳报土著务农稍足之家以协纳”[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6《覆宁镇条议见给边商引价并清厘盐法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85页。。也就是说,到明末,边商不一定就是商人,很可能就是务农之编民。
晚明宁夏镇的边商已是土著的情况,并非特例,毕自严提到: “看得延镇盐粮……远商既逐,势必佥报土商,辗转扳连,倾家荡产。”[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5《覆陕西按院李应期条陈屯盐鼓铸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31页。此外,他在谈到库价和边商关系时还指出:“惟得复设库价,少拯边商之苦,亦足以示招徕之意。查得各镇边商皆系土著小民,原无两副资本,必卖得本年引价,始纳得次年盐粮。”[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15《题遵奉圣谕议修盐政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3册,第663—664页。他认为“各镇边商”都是没有什么资本的土著小民。所以,明末边商由当地土著小民充当的情况,并不局限于宁夏镇,可能是北边的普遍情况。
综上所述,晚明两浙两淮先后设立的库价表明,在白银介入盐法后,户部管辖的运司积极利用白银货币来调整盐法,处理其与盐商的关系。于是,在明中叶的盐商在司纳银制之后,晚明运司又有了新的创举,即主动体恤被政府佥派、财力不丰的边商,向已在边镇纳过粮草而来到运司的他们尽快支付库价,以免他们因久候或被内商勒索而破产,从而影响下一年的开中。不过,下文京解挤占库价的现象表明,两浙两淮的库价制度,并未如其设计的那样运作。
二、京解:从在司纳银到在部纳银
盐课银中的京解,又称解京银,意为运司解往户部的税银,主要来源为余盐银,亦有少部分灶课银。京解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对库价的挤占,意味着盐商在司纳银制向在部纳银转变,反映了户部对白银的强烈渴求。淮浙的京解,即《万历会计录》《太仓考》等记载的定额余盐银,两淮为60万两,两浙为14万两。由于两淮的京解挤占库价的问题没有两浙那么突出,故本文重点分析两浙的情况。
在户部看来,两浙的京解为余盐银,然从运司的角度看,京解虽以余盐银为主,但构成要更为复杂。两浙京解中的余盐银由内商在运司交纳,再由运司解入户部银库。而京解中还有灶课银,既有来自盐场灶户交纳的部分,也有来自州县代盐场交纳的部分。万历间,两浙盐场与州县交纳的灶课银约为15,555两。两浙运司灶课中,大约73%为库价(给商银),用来支付边商,约13%为解京银,解往户部太仓银库,约3%为帑税银,乃皇帝内库的收入,最后约2%才是存留运司的收入,用来充当公费、赈济费和兵饷[注]李义琼:《明代嘉万间的盐课折银与盐法体制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84页。。
余盐银是京解的主要来源,各运司交纳的余盐银数量,至迟在嘉靖间已实现定额。之后,除非国家爆发战事等特殊情况,基本维持定额。据《万历会计录》《太仓考》和万历《大明会典》等的记载,全国各运司交纳的盐课银总数约为100万两,类项有五种,但其中数量最多的仍属余盐银,按数额大小排列,依次是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运司,总数高达932,200两,占《太仓考》所计户部银库总数1,001,664两的93%。在五大运司的余盐银中,两淮、两浙余盐银加起来为740,000两,占户部余盐银收入的79%。可见,两淮两浙之所以为明王朝之盐法重地,与两大盐区的财政地位紧密相关[注]数据出自刘斯洁:《太仓考》卷9之4《岁入·山东布政司》,《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42页;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39《盐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268—1288页;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32《课程一·盐法一》和卷33《课程二·盐法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0—586页。。
值得注意的是,余盐银之名目下,有时还包含了其他项目。以两浙运司交纳户部银库的余盐银为例,虽然额数为14万两,且记载之名目只为余盐银,但这14万两的余盐银中,实际上还包括两浙的水乡灶课银、没官银、票税银、买补银等名目。
两浙的京解除余盐银外,还有各州县缴纳的水乡银、草荡银和包补银。而两浙的库价,主要来自盐场灶户缴纳的灶课银,以及州县代为缴纳的各色盐课银。前者解送至户部太仓银库,后者支付给边商。京解挤压库价,意味着户部盐课银的保障优于边商的引价银,户部盐课银缺乏时,甚至可以挪借边商的库价。
万历后期,京解严重挤压库价,使得库价逋负长达四五年,严重影响了边商的开中[注]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11《余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609页。。启祯间,辽东战事紧张,军费开支加增,户部的财政压力更大。于是,京解挤压库价的现象日益严重,盐法愈发遭到破坏。对万历到崇祯间京解挤占库价的问题,两浙巡盐监察御史李宗著有着系统清晰的认识。崇祯五年,他上奏道:两浙京解、库价各有定额,前者为14万两,外加赃罚银7,000两,后者额数约为96,900两;从主要来源上看,京解主要来自盐商所纳之余盐银和引纸银,库价则来源于各县和盐场的灶课银、草荡银等;至于用途,京解在解入京师的户部银库后,用作边费,而库价则用来支给边商,维持开中法;京解主要分春、秋两季解运户部,但战事、水旱之灾、海啸风潮、大工等因素常常导致京解挤占库价;战事愈发紧急、中央军事、财政管理能力愈发衰退,则两浙京解挤占库价愈发变本加厉,竟高达50余万两[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7《题覆两浙盐院李宗著整饬盐政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138页。。如此,边商得不到边引价银,其在边开中盐粮的资本日益匮乏,开中动力便逐渐消失。
毕自严在论及淮浙盐法弊端时曾指出:“边商之苦边臣非不屡有控呼,恤商之法臣部非不时有申饬,乃运司毎视边、腹为两途,痛痒不关,即盐臣亦谓苟完岁额,便足了任内事,而不复为永远之计。虽经臣部议定,给过库价年终造册奏报,亦竟漫灭不行,此盐法之所以愈坏也。”[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6《覆宁镇条议见给边商引价并清厘盐法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89页。他认为盐法愈加衰败的原因之一,是运司“视边、腹为两途”,没有处理好边、内商的关系,在库价与京解方面,优先完纳户部所需岁额,而不惜侵蚀给边商的库价。
在这样的情势下,随着盐商不再只于盐运司交纳盐课银,而是绕过盐运司直接到户部交纳盐课银,盐商的身份角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部商、额商等新的名目。在明后期白银财政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随着户部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尽可能快速有效地获得白银,加强财政上的中央集权,是户部的现实选择。然而,这可能严重冲击盐法的正常运转,户部越来越难理顺它与盐商之间以及边商与内商之间的关系等。
作为盐商的专称,明末的部商是从内商分化而来,即在京师户部上纳余盐银等盐课的内商[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1《题覆御史张养条陈两淮盐法疏·部商宜酌》,《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7,566,567,567页。。部商较多地出现在毕自严[注]于崇祯元年五月至六年三月任户部尚书。的《度支奏议》中。据载,大约在天启五年(1625),因辽饷匮乏,户部尚书李起元[注]于天启四年十一月至六年七月任户部尚书。便利用袁世振的纲法,“议将积引纲窝,每年续行积引二十二万,每引照例纳余盐银八钱,辽饷一钱,割没一钱,共岁增银二十二万两”④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1《题覆御史张养条陈两淮盐法疏·部商宜酌》,《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7,566,567,567页。。而这些余盐银、辽饷和割没银的交纳之地,是在京师户部而非各地运司。户部直接在京师招商纳银,凡是有能力在京预纳户部盐课银的商人(部商),户部便特许其行盐权利。
以盐商刘国祚为例,他在户部预纳过崇祯元年、二年的余盐银,占窝淮盐11万引,这引起在两淮运司上纳余盐银的内商不满,故淮商与部商起了争执⑤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1《题覆御史张养条陈两淮盐法疏·部商宜酌》,《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7,566,567,567页。。于是,崇祯元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养建议,“其实总是淮商,而部商之名委不必设也”⑥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1《题覆御史张养条陈两淮盐法疏·部商宜酌》,《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7,566,567,567页。。自后,部商之名虽未设置,但内商赴部纳银中盐的行为却得以持续。崇祯二年,山东道监察御史邓启隆议论盐法时,将部商斥为奸商,认为其行为对盐法的破坏太大,要求禁绝此举,“自臣受事以来,凡商人有赴部告增盐引者,一切屏斥”[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2《题覆两淮新盐院邓启隆条陈三款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616页。。这说明崇祯初年仍存在内商赴部中盐的现象。
崇祯四年,户部尚书毕自严指出:“据称,所销辽镇六万三千九百二引,虽系天启七年并崇祯元、二两年停中之引,实已附销纲外,而正纲三年毎岁犹然缺额六万三千九百二引,仍听臣部召商开中。”[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4《题覆辽镇淮引征课行盐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707页。户部在京招商纳银开中的行为得到明确认可。
为满足对白银的渴求,户部实施在部召商政策的同时,还新设了额商。额商与季商[注]额商的解释详见下文。季商,就是手持正、余盐引(又叫季引),分四季到批验所称掣的盐商。四季称掣之法,参见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21《奏议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812页。是一对经常一起出现的概念,与二商相对应的盐引分别是额引和季引。“在季引则先期纳课,挨年掣盐,候久而利微。额引则当时纳课,当时掣行,途捷而利厚,且又无抵告包补之课。”[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5《题覆浙商方俊条陈清厘额引大票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17,14—16,15页。虽此材料在讲浙江归安、乌程二县额商侵占季商利益之事,但奏疏前面提到在其他地方,如宜兴县、长兴县等地,也出现盐引改季为额之事。显然,在获引、掣盐和纳课方面,额商比季商享有更多优惠。那何为额商?为何额商能够获得优惠?这与户部增加辽饷有关。
在户部看来,额商是承纳本部或运司之增课,协佐辽饷,从而获得本部给予优惠条件的商人,但在季商看来,额商是投机分子,是侵占了盐法常态运转时他人利益的人[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6《覆两浙盐院李宗著查奏厘革额引大票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99,98页。。 而且,二商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况借额为由,而侵占上则之地,强据额内之引,扼吭而夺之食,是季固仇额,而所深仇者,尤创增之额也”。虽然这是崇祯四年,在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要求下,杭州盐法道右参议兼佥事薛邦瑞,会同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庭梅以及按察司按察使陈良训一起做出的分析,但这的确体现出了季商与额商的矛盾症结所在。
崇祯四年七月,毕自严题覆两浙运司季商方俊时,提到了方俊指名陈奏的奸商叶文芳,便是额商。关于方俊与叶文芳的矛盾,毕自严认为应当查实后再议。崇祯五年四月,户部认为叶文芳行额引之事已查清,是叶文芳利用户部增课之机,以多纳8,000两盐课银的条件,获得了增引3万道。所增额引,其实并非额外之引,而是侵占了季商在盐法规定下的正引。虽然表面上叶文芳给户部增课8,000两,但实际却亏损了本该纳给盐司的4,700余两包补银,而且导致叶文芳利用额引做窝,卖窝肥己等问题的出现。故户部决定让叶文芳补缴包补银4,700余两,并罚卖窝银2,000两,且改额引为季引。但是,户部所增的8,000两盐课银,仍然予以保留[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6《覆两浙盐院李宗著查奏厘革额引大票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101—102页。。
可见,不论是京解挤占库价,还是盐商在部纳银,皆表明户部在变更盐法中的逻辑已经清晰,即崇祯间户部对白银的需求非常强烈,甚至都等不及各地运司解送盐课银,而直接在京师招商纳课,以获得盐商的课银。为此,户部不惜变乱已有的盐法秩序,就连后来对额商叶文芳的惩罚,也可视作基于获得税收之考虑。
三、帑银:从势要占窝到户部佥派纲纪商人和纲商
帑银是晚明运司管辖下的开支项目,指被皇帝分割并试图制度化的盐课银。虽然各色势要一直破坏盐法,但户部仍是明代制度规定的唯一掌管盐法的部门。在户部的应对下,势要占窝并未成为制度。然而万历间,皇帝不仅插手盐法,而且试图从制度上分割户部的部分盐利(帑银),给户部专管的盐法带来极大挑战,同时也为清朝皇室获得盐法管理权和制度性盐课收入提供了先例[注]明代掌管盐法的部门是户部,但清代盐法由户部与皇帝共管,清代帑银为内务府向盐商放贷并获取利息收入的资本。参见李克毅:《清代盐商与帑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9—24页。。
中山八郎曾提出疑问,明代盐法如何从明中叶的势要占窝发展为明末的商人占窝[注][日]中山八郎:《开中法和占窝》,《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第243页;[日]藤井宏:《“占窝”的意义及其起源》,第347—367页。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11页。。或许在探究明末势要干预盐法的情况后,通过分析户部反对势要占窝而允许商人占窝的应对措施——编佥纲纪商人和纲商,我们可获解答。
皇帝和内官是势要中处于权力顶层的势力,一旦干预,将带来盐法的重大变化。明代皇帝、内官虽一直干预盐法,但在两浙帑银出现之前,他们多停留在偶尔干预的层面,但到万历后期出现了新特点,他们则直接插手盐课分配并试图将既得利益制度化,即两浙出现帑银。
帑银是万历末财政分配中属于皇室的盐课收入。它约起于万历二十七年,总数约为37,000两。当时,万历皇帝为搜刮钱粮充实内库,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税使。浙江税使为太监刘成,百户高时夏为讨好他,诓骗说两浙和福建有多余盐斤和壅滞引目,如果召商发卖,每年可多得盐课银约30万两,后虽经巡按、运使和地方官等共同查证高时夏之议为虚言,但仍加增两浙盐税银约37,000两[注]周昌晋:《鹾政全书》卷下《盐疏》,《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37页。万斯同:《明史》卷101《食货七·盐法》,《续修四库全书》第3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45—646页。。帑银共征了15年,始于万历二十八年秋,至万历四十二年大部分获得蠲免[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1《征收钱粮总额》,《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365页。。
万历末,两浙运司解入内府库的帑税银为37,548两,分别来自内商、边商、盐场、票商、州县牙铺、店户等交纳的税银,涉及到产、运、销和缉私等各个环节的税目,而且,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费用[注]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8《各场额征下·盐税加额》,第560页。其中,内商引税18,188两、总额37,548两皆为笔者计算,文献记载分别为18,181和37,000两。。其中,铺垫费便是一种费。它表明这些帑银是皇室收入,因为铺垫是交给皇帝内府库宦官的管理费[注]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1—52页。李园:《明代铺垫研究——以内库的物料监收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可见,皇帝、内官对晚明盐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各个环节、各色人群。
王圻的记载可助我们窥见票商所纳票税银的具体组成:其一,两浙盐票有大、中、小票,县有上、中、下三则,新加帑税一般加在上、中则县份的中票上;其二,每票加税的税率不等,可能与所属之府有关,其中,杭州府的票税税率最高,松江府、苏州府次之,其他三府同;其三,两浙行票之盐,一般称作中津桥票盐,此外,还有贫难军民离场较近范围内售卖的肩挑小票盐;其四,万历间两浙共解税盐票帑税总计2,970两[注]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12《票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621—626页。据笔者计算,两浙共解票税帑税约2,631两,与文献记载稍有不同。。虽然票税帑银才有两千多两,但在古代中国,税收负担的轻重不仅与税收数额大小有关,更与征税者身份以及征收交纳过程密切相关。譬如交给内库的白粮,虽数额有限,但不仅运输成本十分高昂,而且常在入库环节出问题,原因便是入库时会遭遇各色人等的盘剥,或因手续十分复杂,或因对管库内官打点不够等,常致江南交纳白粮之民倾家荡产[注]鲍彦邦:《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暨南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第37—47页。。
由于票盐行盐地一般离盐场较远,交通不便,多在内地山区,因此票税上所加增的帑银表明,万历间皇室和内官对盐法的干预之手,已经深入东南沿海的山区。不过,至万历四十二年,因其生母李太后去世前之请,万历皇帝应允蠲免浮课,其中包括两浙3万多两的帑银。然因关涉内库宦官收入,太监刘成瞒骗皇帝,试图只减三分之二,引起盐臣反对并上疏抗辩,过程甚是激烈曲折[注]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21《奏议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821、815页。。势要对两淮和两浙盐法的干预,在天启崇祯年间仍在继续。
继万历间太监鲁保破坏两淮盐法后,天启间,两淮盐法又遭到太监魏忠贤的严重破坏。崇祯元年,兵部尚书王在晋上奏指出,天启间,受魏忠贤指挥的太监刘文耀和胡良辅[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3《题议两淮旧逋分年征解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669页;又见《度支奏议》山东司卷4《题覆两淮未完盐课应速补解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697页;以及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44《人物列传·苏茂相》,《中国地方志集成》之《福建府县志集》第23辑,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445页:“扬州老库久不会珰。一旦借大工为名,搜括二百万,而属运司且八十万。遣珰胡良辅、刘文耀守解。”可知刘、胡二监指的是天启末的太监刘文耀和胡良辅。之所以说刘、胡二人是受魏忠贤指使的,是因为刘若愚揭露了他们的紧密关系。参见刘若愚:《酌中志》卷10《逆贤乱政纪略》,《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73—475页。,从两淮运司搜刮80余万两白银。这些白银既包括属于户部的余盐银,又包括内商缴纳的支付边商的库价,从而导致边储国课俱受损[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1《题覆诸臣条议盐政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56页。。魏忠贤的搜刮,是通过派出太监,与当地奸商合作而实现的[注]谈迁:《国榷》不分卷,崇祯元年十一月,《续修四库全书》第3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国家兴建大工也会告借两淮的盐课银,甚至挪用两淮边商的库价。“天启六年,大工紧急,尽将库价搜括助工,以致边商守候经年,资本无归,故将盐粮告停告减,渐至压欠经年,而亏损边储甚矣。”[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15《题遵奉圣谕议修盐政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3册,第664页。工部也会通过增加两淮盐斤收取课银,获得本部完成工程的银两。例如天启六年,工部因修建陵墓需要,向两淮商人增加盐斤,获得白银2万两,至崇祯二年题免[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7《题两淮运司助饷盐课勿误解助工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149页。。
此外,淮浙运司皆有“袍价”,此乃织造太监李实利用织造之名,侵夺两淮、两浙盐利的表现。“两淮运司原无袍价,旧额始于天启五年,织监李实题准:两淮动支余盐银三万,又两浙动支余盐银二万,每年二、八月解交织监以充袍价。维时两淮、两浙俱经如数支解,后两淮盐臣陆世科以余盐银两系解部正额,难以分解,议于和、含等州县,改行食盐二万九千余引,征课三万两,以抵袍价,是亦不得已而为之区处耳。”[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1《题覆御史张养条陈盐法疏·袍价宜蠲》,《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6,566页。后经勘查,崇祯元年,皇帝准许两淮袍价从此停免[注]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1《题覆御史张养条陈盐法疏·袍价宜蠲》,《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6,566页。。
虽然帑银仅是在万历二十七至四十四年间存在的税目,但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整个明代皇帝、内官等凭借特权干预盐法、分割盐利,从而导致盐引壅滞、商灶受害、国课受损的事实。因此,我们将在两浙推行纲纪制度和在两淮实行纲盐法,编佥纲纪商人和纲商,视为户部保障盐课银收入的举措,以及其应对势要干预盐法包括皇帝强取帑银等的措施。
在两淮纲盐法下的纲商出现之前,两浙已存在另一种“纲商”,即纲纪商人。嘉万间,户部管辖的两浙运司编佥纲纪商人的做法,类似州县为了交纳赋役而编定的里甲组织,可视作户部维护盐法秩序的努力。虽然卜永坚探讨了白银进入中国后,明政府管制商人的模式反而强化,例如对盐商的实行商业里甲制进行管理,不过其论证仅以两淮为例,没有用到两浙纲纪制度的资料,故缺乏商业里甲制的直接史料和论证,也忽略了比两淮纲法更早的两浙纲纪制度的重要性[注]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志“纲法”》,第14—21,18页。。
关于两浙纲纪制度的创立和纲纪商人的编佥,据《两浙订正鹾规》记载:其一,两浙运司编定纲纪商人,在嘉靖三十八年之后,本意是维护开中法下的边商和余盐制下的内商二者的利益,维护盐法秩序的正常运转[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4《招徕·定立边内引商纲纪》,《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63,563,563页。,即盐臣们希望边商在边纳粮后,能赴司支银或从内商处得偿价银,而内商的正余盐引皆得疏通,回收资本,赚得利润;其二,从资格来看,入编纲纪之商应符合守法且资本雄厚的基本条件;其三,从数额和区域来讲,两浙运司编定的纲商共九名,纪商共四十二名,他们在浙东、浙西、徽州府、江西、山西皆有分布;其四,具体组织方式,为纲商管理纪商,纲纪下再编甲,纪商管理甲商;最后,材料虽提到,边、内二商皆入纲纪,但未明列二者各自数额和来自的区域[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4《招徕·定立边内引商纲纪》,《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63,563,563页。。
明代两浙地区是较早实行票盐法之地。在票盐法推行后,两浙运司也于票商中编定了纲纪商人。票商中的纲商编于万历九年,最初仅在华亭、上海两县,每县纲商一名,纪商一名,共计四名,而且,纲商纪商之间互相保结,“后有坏法,定行连坐”[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4《招徕·票商纲纪》,《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63页。。这意味着,编定纲纪商人的目的是在维护盐法正常秩序的同时,对盐商实行连坐追责管理。票商如此,引商(边、内商)亦如此。可见,晚明两浙盐商,即便是票商,亦绝非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那些身份自由的商人。
两淮推行纲盐法在万历四十五年,在两浙推行纲纪制度的58年之后。虽然两淮编定纲商晚了两浙佥定纲纪商人半个世纪之久,但两大盐司对盐商的管理方式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政策出台的背景、实效、目的与影响等方面。
两淮纲盐法的核心内容,集中在袁世振的“纲册凡例”和毕自严的“覆两淮盐台张养更纲疏”中[注]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477《袁世振·纲册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662册,第396、385—386页。该册中的袁世振的盐法奏议有串页现象,《纲册凡例》部分内容被前置于第385—386页的《盐法议八》之后。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3《覆两淮盐台张养更纲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636页。,是指两淮为保障每年收到盐课银将盐业专卖权让渡给了盐商,让登记在册的纲商世代行盐⑥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志“纲法”》,第14—21,18页。。而这些纲商,正是袁世振初期认定的破坏盐法但资本雄厚的囤户[注]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制度的建立》,第309页。。这样,户部不仅能疏通盐法,而且至少保证能顺利收到盐课银,或者至少在盐课逋负时,能向财力相对雄厚的大盐商追偿。
两浙两淮的纲纪制度和纲盐法,在出台的背景方面皆与盐引壅滞、浮课盛行有关。两浙编定纲纪商人,始于嘉靖三十八年[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4《招徕·定立边内引商纲纪》,《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63,563,563页。,时值“抗倭”,盐法紊乱,户部盐课遭到总督浙直福建军务都御史胡宗宪截留,充作地方军费[注]《明世宗实录》卷471,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1年,第7922页。,故可推测,编定纲纪商人也有稳定盐法保障盐课收入的目的。关于两浙盐引在嘉靖末年至万历间的壅滞情况,时任户部侍郎的李汝华约于万历四十一年指出,两浙盐引壅滞问题在两浙纲纪制度出台前后都存在,“后因嘉靖末年倭警,万历初年水荒,内商流徙,积引壅滞,加以二十七年奸弁高时夏之诬奏,不得已行废引一十五万。废引一行,正引愈壅,以致积有一百五十余万”[注]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8《艺文二·酌议带销旧引以疏新引疏》,《续修四库全书》第8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46页。因李汝华在该疏中提到“今盐臣崔尔进”,而崔尔进任两浙巡盐御史是在万历四十一年,故推测李汝华写该疏的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任职户部左侍郎时。另参见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21《奏议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811—812页。。其中的“奸弁高时夏之诬奏”所加增的盐课银,正是前文37,000余两的帑银[注]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21《奏议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第813页。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2《票商·行票定额》,《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422—423页。。可见,盐引壅滞盐课无着的确是嘉万间两浙盐政的显要问题。而两淮地区在纲法前的壅滞盐引已达200多万引[注]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474《袁世振·盐法议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62册,第359—360页。,万历四十一至四十四年逋负的盐课银约200余万两,如从万历三十四至四十四年以十年计之,约达700余万两[注]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474《袁世振·附户部题行十议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662册,第354、355页。。
而两浙两淮盐引壅滞盐课征收困难的问题,与私盐问题紧密相关。事实上,两浙编定纲纪商人要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私盐,故两浙明确要求纲纪商人在盐业缉私方面发挥作用。两浙对运销阶段的私盐,将责任算在纲纪商人头上,“……□带管贩私盐,责在纲纪”[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4《巡辑□法禁□私盐》,《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30页。。两淮的袁世振纲盐法改革,一度以杜绝私贩为首要工作,包括整顿盐场的盐务机构、试图恢复灶户团煎法和清理囤户等[注]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第307—308,310页。。虽然袁世振初期的计划或是不够切合实际,或是阻力太大颇为不顺,并未很好贯彻,但这至少表明,两淮两浙盐政面临的问题基本相似,都是私盐问题突出,导致引积课壅。
在晚明盐法疏理的实效上,两浙的纲纪商人制度与两淮的纲盐法,虽因明末各种问题例如兵制调整、财政危机等交织在一起,导致崇祯期间的推行实效颇微[注]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第311页指出,至崇祯六年(1633),两淮累年新旧两饷积欠已达2,069,245两之多。,但在制度推行初期,确有一定实效。两浙纲纪商人主动参与稽查,将那些存在较大走私隐患的煎盐场所拆除,“万历二十年,纲纪商众条陈,孔家湾地方□□煎□□舍,乞行拆毁……该宁绍分司会同萧山县查得,各舍离场甚远,难以稽查,尽行拆毁”[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2《场灶·钱清场过海煎办》,《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03页。。此外,他们还召集商众,给盐务机构提建议或与其协商,以改善盐务管理的某些环节。例如,万历后期青浦盐商争夺华亭县行盐市镇,紊乱引、票盐之行销区域,运司便采取将往两县行盐之纲纪商人请出来进行协商的办法,暂时平息了争端[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3《票商·行票境界因革》,《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437页。。两淮纲盐法推行后,初期也取得一些实效,不仅一些逃亡之盐商复业,而且新旧之引疏通,盐课增收不少[注]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第307—308,310页。。
两浙两淮的纲纪制度和纲盐法在推行初期具有一定成效,这与两个制度本身的严格规定和推行目的有关,譬如二者都强调一定要将纲商的姓名登记在册。两浙“本司遵将所招商人总登其名数,边、内商人各有纲以统纪,纪以统甲”,而且,“纲纪必于众商中推其行已端庄,与谙□□法者为之体统,比众稍优实”[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4《招徕·定立边内引商纲纪》,《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63页。。目的在于要让纲纪商人之间“总撒互结”,“如无保结者,不许收册。后有坏法,定行连坐”[注]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4《招徕·票商纲纪》,《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563页。。袁世振在进行两淮纲法的制度设计时,明确要求“此十字纲册自今刊定以后,即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其册上无名者又谁得钻入而与之争骛哉?”[注]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477《袁世振·纲册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662册,第385页。可见,两浙两淮的纲纪制度和纲盐法,通过将商人姓名登记在册,目的不仅是将专卖权特许给在册之商,而且方便在盐课银收不上来时对盐商进行连坐追责之管理。
晚明两浙两淮的纲纪制度和纲盐法为清代沿袭,并且上升到了国家制度的层面。康熙时(1662—1722)还有关于两浙纲纪商人和纲纪册的记载[注]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15《条约一》,《续修四库全书》第841册,第302页。。而两淮的纲盐法,在明末就已得到推广,例如明末山东的纲商共有14纲,到清代雍正时期仍保留了明末的11纲[注]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287—293页。。
综上所述,两浙两淮的纲纪制度、纲盐法具有高度一致性,基本可视作一种制度的不同称呼。它们皆是户部为了应对私盐问题导致的引壅课逋而制定的政策,皆起到一定的疏理积引保障国课之实效,且皆为明末乃至清前期的盐法所沿袭。至此,中山八郎所提问题已获部分解答,明代盐法从明中叶的势要占窝发展为明末的商人占窝,主要在于掌管盐法的唯一部门户部在白银财政分配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为打击干预盐法的势要和盐业走私以保障盐课银的收入,主动调整其对盐商的管理政策,强制佥派边内二商中财力丰厚者承接政府颁发的盐业专卖权,于是便有了部商、额商以及两浙纲纪商人、两淮纲商等。
结 论
与明代财政体制演变的大势一致,明代盐法经历了从盐商灶户应役向盐课纳银的转变。通过对晚明盐课银分配的三个去向库价、京解与帑银,以及两浙纲纪制度和两淮纲盐法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建立过程中,盐法调整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明初开中法下的户部,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和维持政策运转,边防粮草供应交由盐商等,控制好灶户所产之盐以偿付盐商,指定特定区域以掌控盐的销售;但明中叶以后,户部为稳定获得盐课银,主动采取设置库价、允许盐商在部纳银,以及编佥两浙纲纪商人、两淮纲商等举措,调整盐法。随着在司纳银制和晚明纲纪制度、纲盐法的确立,户部不仅要保证其本身银库和下辖运司银库有定额足额的盐课银贮藏,而且要支付边防年例银。为此,它在盐商中设立了额商、部商等名目,进一步分化盐商群体,同时,在两浙编佥纲纪商人,在两淮更是不惜与它曾打击的破坏盐法的势要(明末称囤户)合作,推行纲法。
其二,晚明开中法虽已变质,但其制仍维持下来,出现新的特点,边商在司支银而非盐,内商赴部纳银而非在司纳银,而户部对白银收入的需求引起京解严重挪用库价,导致其对维持开中法的边商的管理失控。随着边防白银开支需求压力的加大,户部对两浙两淮盐商的管理,尤其在两淮采取了抛弃资本较小之边商,而与资本雄厚的内商合作的政策,故边商在清朝基本消失,而内商以及不法商人囤户则被纳入纲法的管理。
其三,一般认为,明代财政体系的演变大势,是从主要依靠徭役体制到白银赋税化的转变,但本文对盐商的研究表明,明代盐商则在盐课纳银的转变中,逐渐成为一种役。开中法下的盐商,是那些有一定资本和能力且愿为潜在的巨大盐利甘冒风险的人,他们尚未被户部固定姓名,强行佥派。但明后期至明末两浙两淮盐区的在边纳粮在司支银的边商以及纲纪商人和纲商,皆是户部为获得稳定收入,强制佥派须固定充当之人。这些盐商,被户部实行连坐追责管理,虽然他们参与到盐业的生产、缉私等环节,但说到底,晚明的盐商是一种具有劳役性身份的役。这种役,虽使盐商在经营环节采用了市场的手段,但最终还是揭示了古代中国经济为贡赋经济的本质。
其四,晚明两浙的纲纪制度是明代盐法从官专卖制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以往学界对明代盐法的研究,多侧重于两淮,故认为明代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转变的标志,是万历四十五年两淮实施的纲盐法。但两浙于嘉靖三十八年开始推行的,与两淮纲盐法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纲纪制度表明,它可能才是明代盐法从官专卖制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
——盐业古籍整理新成果《河东盐法备览合集简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