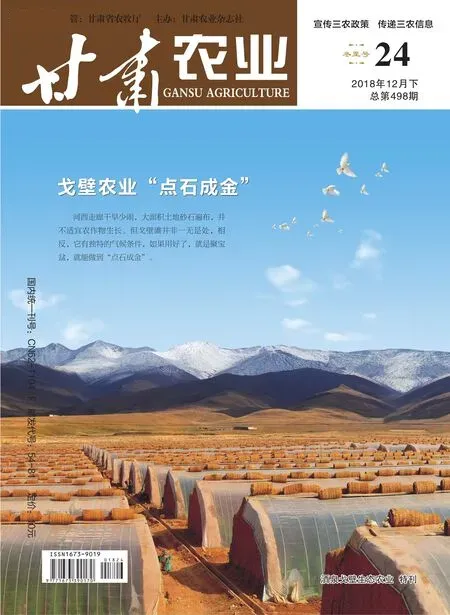难忘八角城
八角城,藏语叫卡儿囊。在夏河县东北约35公里处,在辽阔甘加草原的最东端。1970年,我曾经在那里教学半年多,虽然时间不算长,但给我留下了极为美好难忘的印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首先,令人难忘的是它是一座神秘的令人向往的古城,而且建筑构造十分奇特。全国的古城我也见过不少,一般都是四方四正的,有四个角。但八角城却不是这样,它不是四方四正的,本应有八个角,但因为建城者又裁去了城垣上的八个角,结果形成了20个面16个角的古城。如果你站到高处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原来它的整个城是呈“十”字型的。据有关专家介绍,八角城的这种特殊建筑结构,不容易形成射击死角。八角城城外有城,这在古代叫做“廓”。内城和外廓之间还有护城河。南城门外尚有瓮城,面积约为150多平方米。
八角城地形非常雄奇险要。它坐落在一个高高的台地上,东北面紧靠巍峨连绵削壁千仞常年云雾缭绕的大力加山;南面濒临滚滚的央曲河,真正易守难攻。其地形不禁使人联想到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的诗句:“一片孤城万仞山”。用这句诗来形容八角城所处的地形,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1981年9月,甘南历史学家李振翼曾仔细勘察过八角城。他认为:“(八角城)凭山依水,踞高临下,内城外廓,层层设防,引水护城,壕沟纵横,八角呼应,首尾相顾,成为一座防御性甚强的城堡。特别是内城20个面和16个角,互相呼应,克服了一般城堡在防御上不可避免的死角。”至于这个城的建筑年代,说法不一。有的说,这里就是汉代的白石县,原来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后来突然遭到鼠疫的传播,原有居民全部死光了。才留下这座空城。1938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到过八角城。他起初认为这是汉代白石县,后来又认为可能是明清时代所建之城。但李振翼1981年9月勘察后认为,八角城是一个被废弃的唐代军事堡垒。至于具体叫什么名称,他也没有说清楚。现在,如果你漫步在八角城外,在附近山上还可看到清清楚楚的梯田的痕迹,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确曾经非常繁华过,曾有许多人居住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八角城还是一座空城。甚至被认为是一座闹鬼的废城。美国探险家哈里森·弗尔曼曾到过该城,据他观察,城内除了几堆破碎的陶片堆,没有其他人类居住的痕迹。据此可知,城内现有居民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陆续迁入的。这一切给古老的八角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旅游者前来考察游览。
八角城1981年被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经成了甘南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了。但我认为,八角城极高的文物和旅游价值,现在还远没有挖掘出来。我多次游览过举世闻名的嘉峪关,两相比较,我认为八角城在以下五个方面都远胜嘉峪关:
第一,它的历史更悠久。八角城如果按照李振翼认定的唐代军事堡垒算,那么它距今已有1 200多年的历史。而嘉峪关始建于明代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距今不过600多年。
第二,它的建设规模更巨大。八角城由内城和外廓组成,不算外廓,其内城周长就有1960米,面积达169600平方米。而嘉峪关没有外廓,内城周长才640米,面积仅有25000平方米,再加上它的东西二瓮城各500平方米,总计也不过26000平方米。八角城仅内城面积约为嘉峪关内城的6.5倍。
第三,它的结构更独特。如前所述,八角城内城呈“十”字形,实际有20个面和16个角,这在国内外古城中是独一无二的,而嘉峪关为一般常见的四方形古城。
第四,它的地形更险要。如前所述八角城依绝壁千仞陡峭的大力加山而建,濒临央曲河,依山临水,地形十分险要。而嘉峪关建在一个不高的嘉峪山上,实际地处茫茫戈壁滩上,其险要程度远逊于八角城。
第五,它现在是一座有藏族群众居住的活古城。嘉峪关没有任何居民居住,仅为一座古建筑。只是由于八角城所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再加上过去很长时期宣传不够,才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我相信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进一步重视,有关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我国旅游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古老的八角城,其文物价值将一定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和青睐。
难忘八角城!对我来说,更令人难忘的是生活在八角城的淳朴善良憨厚勤劳的藏族人民。当时城内生活着数十户人家,绝大多数是藏族。城中间有一所小学,虽为公办小学,但十分破烂,条件极差。不大的校园,几栋又破又旧又小的土木结构教室,两三间连窗户都是纸糊的很小的教师宿舍,这便是学校全部财产。师生冬天烧的都是牛羊粪。学生只有四五十人,分四个年级。我被派到该校任教时,教师只有我一个人。我既是校长、教员,又是学校勤杂工。虽然我当时的工作几乎完全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但出于对那些贫苦的失学的藏族儿童的同情,工作得十分卖力,干劲大得惊人。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学生。精力不够怎么办?我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将三四年级学生合为一个班,由我进行复式教学,又上语文又上数学。一二年级学生抽派四年级学生给他们轮流上课。而这些小先生耽误的课,由我再给他们补。这样做,当然教学质量难以保障,但避免了低年级学生失学现象。这种教学是很累的,一节课刚教完三级,又要教四年级,每天教得口干舌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的嗓子全哑了,讲话都很困难。晚上,我又一度给那些满是泥土,身穿破旧皮袄的藏族群众开办夜校。没有课本,就用《毛主席语录》作教材,选择简单的话句给他们教,目的主要是为了识字。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挤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家学习热情非常高涨。整个校园内熙熙攘攘,书声琅琅。我在八角城小学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取暖做饭烧羊粪,菜,在这里绝对是奢侈品,几乎没有。肉、酥油,当地买不上。我吃光了从夏河县带来的不多的一点肉及酥油后,不是吃干糌粑,就是吃开水下面。我做包谷面疙瘩的水平就是在那里迅速得到提高的。最困难的是水,冬春季节要到山下央曲河去挑,每向上走一步都很吃力,有时碰到刮风天,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八角城的藏族群众是我见过的天下最好的群众。他们给了我许多关心和热情帮助。我刚到该校时,举目无亲,生活困难,他们看到这种情况,纷纷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有的给我送来糌粑,有的给我送来酥油,有的给我送来当地产的一种蔬菜——圆根。我几乎成了全村的客人,包括大队主任贡保、公社干部尕卜藏在内的许多当地藏族群众,多次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皮薄、肉多、油多,美味可口的著名的藏族包子;品尝了他们风干的又酥又香的牛肉干,品尝了他们常年悬挂保存的腊肉和过年时油炸的像门扣一样的油馍。有一次,我去夏河县城打面,一位名叫华布加的中年藏族男子陪我同行,他给我备好马鞍,扶我上马,并一路打狗为我开路,一路上穿过了许多牧场狗群,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我肯定成为成群藏獒的美餐了。为了便于交流,我在藏族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开始学习藏语,狗叫“其偶”,喝茶叫“加唐”,我很快粗通了日常生活藏语,能简单地用藏语跟群众对话。我发现一旦我使用藏语同他们对话,我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一下子缩短了,后来我的藏语水平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藏族群众讲的一些家事我似乎都能听懂。

最让人难忘的是八角城的“西毛”(姑娘)们。她们由于常年在阳光下不避风雨辛勤劳作,一个个体魄强健,面色红润,跟大城市的黄豆芽般的姑娘截然两样。虽然这里自然环境非常严酷,她们穿着简陋,甚至有些破烂;吃的呢,一年四季几乎全是糌粑,而且每天放牧种地十分辛劳,但一个个都显得非常开朗乐观,全没有红楼梦所描写的林黛玉那样的忸怩伤感哭啼之态。也许是藏族姑娘从未受过像汉族姑娘那样的封建礼教束缚的原因吧,她们喜欢游戏打闹,特别喜欢同青年男子摔跤。只要是劳作间隙,往往能看到她们主动同青年男子摔跤的场面,地点不局,田地、草场、院子,甚至牛棚都可以成为摔跤的地方。我刚到八角城小学的下午,就在校园中经历过一次,我正跟贫下中农住校代表谈话,后面一位藏族姑娘突然给我脖子里浇了一勺凉水,我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另一位姑娘已上来将我拦腰抱住摔倒在地上,我大为惊讶。但一副更使我惊讶的场面出现在我的眼前,又有几位姑娘正同几位学生摔得难解难分。由于她们体魄强健,一般男子很难摔过她们,有几次,她们邀请我同她们摔跤,我总是被她们很快摔倒在地上,而且死死压住不放,这时只有用藏语告饶,她们才放我起来。其中有几位“西毛”见到我从山下担水很吃力,还主动帮我背水。我也多次接受过她们递给我的用拾过牛粪的手拌的糌粑,吃起来感到格外香甜。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最熟悉的一些“西毛”的名字:卡巴、日巴、格日,桑老、大卡老、尕卡劳。
就这样,半年时间一晃而过。说实话,尽管这里条件比较艰苦,但我还是想留在八角城小学,不想回县城任教。后来只是因为上级领导怕我赖着不走,先派人悄悄地把我行李带走了,我才不得不服从组织调动离开了八角城。
时光荏苒,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但神奇壮丽的八角城,还有居住在这里的淳朴善良的藏族群众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有时这种怀念反而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