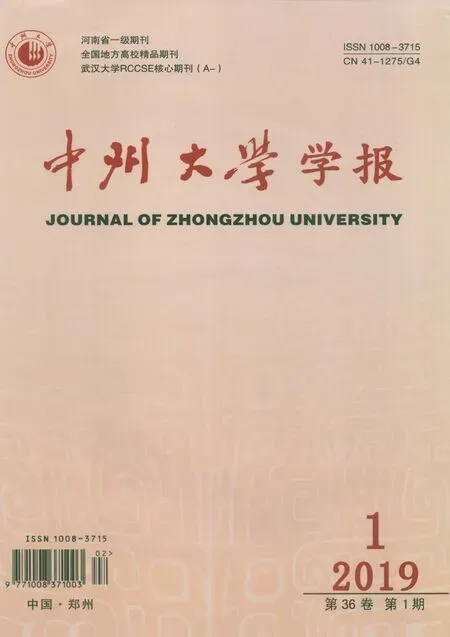关于中西方生态文化思想的对话
鲁枢元,张嘉如
(黄河科技学院 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6)
张嘉如(2018-06-18): 关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如何能够解决生态危机?
张红军老师的文章的一个命题是鲁老师(和其他生态学者如曾繁仁老师)认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思想和本源思想可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中国古代和西方的辩证思想异同在哪里?为什么要凸显中国古代的辩证思想?为什么中国的辩证思维可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些问题,目前我正在寻找答案。
如果红军老师命题无误,西方学者会很有兴趣学习的。
他也提到“本源”思想。我从禅宗的角度可以稍微理解为什么此本源思想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至于辩证思维这一块,我还不太清楚,原因在于它与西方有何异同?如果一样的话,那么中国的辩证思维又有何独到之处?如果不同,它如何看待生态危机问题?
您不用花太多时间回复,若能指出哪一本书(或文章)的章节让我看,就可以。
鲁枢元(2018-06-19):我似乎不曾讲过“古代辩证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恐怕还须红军自己来阐释。
辩证法属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我和曾老师更看重的是存在论。
我还特别看重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这在我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有专节论及。
张嘉如(2018-06-20):您说没提过“古代辩证思想”,我当然就不会在文章里提到。我一直以为辩证思想是典型的西方思维,和《易经》或阴阳哲学里的二元互动是非常不同的,后者本质上不算是辩证,而是一个“有机能量流动说” (我自己胡扯出来的词)。
您说:“我还特看重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这在我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有专节论及。” 那么,中国哲学(除了陶渊明的道家诗意的存在之外),还有哪些影响了您的生态文艺学观?
我真心希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够介绍您在1980、1990年代对中国生态人文领域的贡献。除了比较文学的视野(如提及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对您的影响),我想让西方学者知道中国古代智慧如何影响、重塑当代文人的文学观和哲学观。
西方生态批评家在读我们的文章时,对西方的东西如何影响我们并不感兴趣。他们想学习中国人独特的思维,可以帮助他们思考如何解救当代生态危机问题。
鲁枢元(2018-06-21):我用了一天时间回答你的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对我学术生涯的影响。
你提出的这一问题,逼迫我对自己以往治学的历程做一个回顾与思考,这对我来说很有益处,但也不无困难。
困难在于:按照西方学界的通常看法,中国古代就没有“哲学”,而我又从来缺少正规的学术训练,做学问的随意性很大,也不擅长西方学界正统的“概念逻辑思维”。
在中国当代学界,我是个不入主流的人。
好在我热爱读书,读书还算多,而且多是“杂书”。即使中国古代没有西方人所谓的“哲学”(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总也还有丰富的“思想”与“智慧”吧!侯外庐、赵纪彬诸位先贤撰著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就是我早年的启蒙读物。
我在前期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后期从事生态文艺学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受中国古代“道家哲学”影响较多。
比如“宇宙观”,我认同老子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大有讲究,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空无一有”中的“涵容万有”,是“无限”,是“无极”,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道可道非常道”。这个“无”,有点类似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中的“在”。这样,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接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尤其是玻尔、海森伯的量子物理学后,就很容易将其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论联系起来。据说,玻尔也很热衷于老子的宇宙图景,对中国的“太极图”极感兴趣。
我在研究文艺心理学时,尤其是在研究文学语言时,将这种外在的宇宙图景运用到人的心灵世界,即人的“内宇宙”,也曾促使我产生诸多灵感。具体可参见我在1990年出版的《超越语言》一书。2002年我在《文艺研究》第5期上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一文中,也较多地涉及古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宇宙观。
正是这样,我就不再把牛顿物理学的时空观以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本质论”当作绝对真理。而这些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存在基础,也是当代生态灾难的源头。我反而更看重“前现代的思想遗存”与“后现代的思想萌芽”联手,以救治200多年来的现代社会酿下的生态灾难。这是我始终坚持的一个治学的思路。
在道家哲学中,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是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的,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但“天人合一”,而且天人之间还可以相互“感应”。人和自然是在同一个系统之中的,这个系统又是运动变化着的,这就很类似现代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我在我的那篇《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中,就试图将“风的语义场”解释成一个张力充盈的生态系统。
老子的道家思想,根子在更早的《易经》中。《周易》源于自然,源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环运动变化。变化的能量和动力是“阴阳”两极的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的物质和轨迹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相克相生。“生生之谓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这里的“生”,是“生命”“生长”,也是“生存”“生活”。一方面体现了生命个体的生长发育、生命群体的化生繁衍,同时也包含有生命个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讲,有人说中国古代哲学就是生态学,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李约瑟博士把中国古代哲学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也是顺理成章的。
朱熹说的“天即人,人即天”,天心即人心,天心、人心皆以仁为心。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人心顺应了天心,人类社会就清明昌盛;人心背离了天心,社会就纷争堕落。我的前期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文心”,即刘勰《文心雕龙》所指的“文心”,侧重于个体人的人心;后期的研究对象是生态文化,可以说是侧重于天心、自然之心、生物圈的心。就刘勰而言,“文心”“人心”“天心”三者之间是重叠的、相互关联的。你或许应该留意,我的生态文艺学研究,包括随之而来的对于生态文化的关注,都是在前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在面对“天心”即“自然”时,不忘“人心”,不忘人的精神,即人的生存理念、价值取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改善现代社会中自然生态的状况,首先,或曰从根本上要改变人类自身的精神状况,这也就是我强调的“精神生态”。
这当然与具体社会、具体时代背景下作为个体人的观念、行为有关。
《易经》在生命个体层面上的具体应用,则体现为中国的“中医学”上。“中医学”里的身心是一体的,不但强调医病,也强调医心,心理健康才是身体健康的根本。中医学不仅强调身心是一体的,而且强调人的身心与其存在的环境也是一体的,与其家族的历史也是一体的。1985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为“中医学”概括出以下几点现代哲学的含义:中医学在“现象学的学科形态”“系统论的整体观念”“直觉意会的思维方法”,以及范畴与概念的组合、论著的主观风格等方面,这些曾为我的文艺学心理学科建设提供许多启示,现在看来依然可以运用到生态文艺学研究中来。(注意:中医学讲“辨证论治”,其中的“辨证”是不同于“辩证法”中的“辩证”的,不是同一个词。)
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思想,如儒家、道家的某些对待历史的态度都对我产生过某些影响。儒家、道家都不是“社会发展进步论者”,他们都认为社会的最好的境界在很早以前,其理由是那时的人们更贴近自然,自然是“神”,能够更贴近“神”的社会当然是幸运的。这恰恰与欧洲早期的浪漫主义思潮是一致的,对此,我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有较多的论述。此前我曾特写过一篇题为《关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反思》的文章,记得好像《新华文摘》也转载了。当然,我并不认为美好的“伊甸园”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也并不存在一个总是“进步”的社会发展规律。纵观人类历史,有些地方是进步了,比如科学技术;有些地方没有进步,比如人的伦理道德;有些地方显然是退步了、堕落了,那就是地球的生态!
我出生在中国腹地一个古老城市的底层社会,就生活哲学来说,也更多地坚守了传统的道德伦理。比如,做人要“诚信”,待人要“友善”;做人要看重内心的丰富、内在的涵养,“藏愚守拙”“被褐怀玉”“重于外者而内拙”,不让“心为形役”;生活中“见素抱朴”“知白守黑”“清净自守”“忧道不忧贫”。有时我会对朋友自我炫耀:“我生活能力很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很少。”我的生态理想是:“低物质损耗下的高品位生活。”这里的“高品位”,指的是“拥有丰富的、内在的精神内涵的生活”,也是“充满诗意的生活”。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我看来是违背自然的,人也应当像水一样往“低处走”才好,这就是《老子》一书中说的“水利万物而不争”,善处下也。“处下”,即降低自己的身段,虚怀待人、待物,也是和谐社会必须的。其实按照道家哲学,“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高与低、上与下、得与失都是相辅相成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这里不存在“二元对立”,这显然也是生态哲学的认识论。这些内在的生活伦理、生活哲学,或许也是我之所以选择生态文化研究的内在原因。
可以说,我在整个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型的,“老庄哲学”与“孔孟之道”是我的精神基因,就像我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但我赶上一个开放的时代,当我一开始接触西方世界的哲人、哲思,就发现其中的某些人似乎早就在那里等候着我,他们也已在久久地张望着东方、张望着古老的中国。这其中就有:卢梭、海德格尔、舍勒、西美尔、梭罗、怀特海、荣格、玻尔、贝塔朗菲、德日进、利奥波德、汤因比、柯布、罗尔斯顿、斯洛维克、塔克、杜赞奇等等。其中有些人已经作古,有些人依然健在,而且我有机会与他们握手言欢,我发现即使中间橫隔着语言的大山,我与他们的沟通并非过于艰难,这就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是幸运的。
嘉如,你提出的问题很大,匆忙作答,我不知是否已经说清楚。此信中提到的一些文章,在网上不难查到,你可以参考。
我年事已高,一生治学虽然乐此不疲,但成就甚微,况且已经到了收尾时期,再进一步也难。
张嘉如(2018-06-22):非常感恩您这么费心思地回答我的问题,也谢谢提供相关资料,这样大大帮助了我的写作过程。
也许哪一天我对您和曾老师的研究(尤其是对西方哲学的部分)熟稔了,我可以用英文写一本书来详加介绍。我对海德格的哲学理解得很少。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因为他与纳粹的关系,往往把他边缘化,所以提到他时,政治正确上多半以负面的评价来对待,至少,在提到他时必须提到他和纳粹的关系。这也是中西方的不同之处。所以我在提到他对中国生态批评、美学的影响时,也必须面对这个在西方学术界非常敏感的问题。(对不起,也许您信里没提到他)
(2018-07-10)现在开始写关于您的章节。昨天把您寄给我的访谈读完了。对您的成长过程以及学术的传承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我早期也对荣格心理学、坎伯的神话诠释有兴趣,直到看到荣格说东方的直观是走火入魔的时刻,我就不再对他感兴趣了。
我想重写这一篇文章,比较完整谈您(也扩大到包括曾老师的生态美学)的研究。我觉得一篇把您们两位介绍到西方的文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尤其谈到您近年来做的东西(万衫寺和梵净山),让西方学者知道您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社区营造的参与。
现在在读您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对您的知识量非常佩服。
(2018-07-09 ):有两个问题想跟您厘清一下:
(1)海德格尔对老子/中国文化的研究,您是从哪里得知?据我所知,海德格尔与日本东京学派学者(禅宗)有直接交流,但我不知道他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系。我想在文章里提及。若有引用书目就更好。我问过德国生态批评学者,他说他没听说过海德格尔受到中国哲学影响的事实。(52、64-65页最下面)
(2)中国环境历史学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环境破坏在汉朝以前就非常严重,老庄学说其实是一个对自然破坏的反动,并非中国人的民族天性比西方人更亲近自然,也并不是马克思学说进入后中国人丧失天人合一的本性,把对自然的破坏推到极端。我想知道您如何回应这样的批评。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在提出陶渊明、老庄精神时,我们必须回应环境历史学家的反驳。
(2018-07-10):我上封信提到的环境历史学者是伊懋可,书名是《大象的退却》,第十章。他对陶渊明以及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是负面的看法。我想听听您(作为陶渊明专家)如何回应他的“生态批评”(分别对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评价。
鲁枢元(2018-07-10):嘉如:我和张平去了一趟日本,今晚才回到苏州。你三次来信中提到的问题,我很感兴趣,我可以做出较为周详的回答。等我稍微静一静心,再给你写信。
张嘉如(2018-07-11):很高兴您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农业起家的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这些传统的具有生态内涵的东西没有办法抵挡现代化与历史进程(现代化、经济发展、环境破坏等)?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物质诱惑下这么不堪一击?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污染这么严重?”也许这只是少数精英的论述,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对自然的态度(人类中心主义)。当然,许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精神的必要性。我只是觉得在当前中国环境污染这么严重的时刻,我发现我很难说服西方学者(甚至我自己)认同中国的自然观可以为目前环境危机提出一个解决的途径。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还有许多比较细节的部分的子问题我就不多麻烦您。
也许您的陶渊明一书里有解答。我这星期会开始读。
鲁枢元(2018-07-17):嘉如:难得你对我的学术思考花费如此多的气力,我很感动!
你提出的某些知识性问题倒还好回答,其中一些学术评价、社会走向问题很严峻,也是我的心结,很难得出完满的结论。
综合此前你的几封来函,我梳理出以下六个问题并尝试着加以回答:
一、早期也曾对荣格心理学、坎伯的神话诠释有兴趣,直到看到荣格说东方的直观是走火入魔的时刻,我就不再对他感兴趣了。
荣格尽管是学术大师,也不是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正确。就整体看,荣格的学术倾向以及他为人的风格,与东方哲思都比较接近。他的文学心理思想有时也走极端,但我仍然喜欢,包括他的神秘主义倾向。以前我在课堂上曾讲过:弗洛伊德是“现代主义”(理性主义、决定论),荣格是属于后现代的。
二、谈谈您近年来对万衫寺和梵净山的关注,让西方学者知道您的生态批评对生态社区营造的参与。
我做的这些仅仅是开始,很不够。精力与人手都不足。
但这两个地方(你所说的社区),都是绝佳的。
我现在倾力帮助万衫寺能行大法师实现营造“生态寺院”的理想。7月22—24日,我和张平将陪同美国过程哲学研究院的几位学者到万衫寺来,与大法师作一交流。
三、海德格尔对老子/中国文化的研究,您是从哪里得知的?
我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第二章(纸本)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拥有丰富的生态意蕴。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有一位留德的青年学者宋祖良,为此写过一本专著:《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我的生态思想颇受此书影响。而此书被当时中国学界的某些人认为是浅陋之见(当时中国哲学界还在漠视生态)。
海德格尔是个颇有争议的人,连他最亲近的学生也不肯原谅纳粹时期他犯下的罪过。我将其归为读书人误入“政途”,是决计要蒙辱的。但这并不否定他的某些深刻的学术观念。就像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当过汉奸,散文仍然是极品。
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且资料甚多。我在《陶渊明的幽灵》82页(纸本)提到当年海德格尔与中国留学生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的事,萧师毅本人有长篇回忆文章(见附件),我在台湾曾遇到中大的一位教授,他说与萧师毅曾经同事。
我书中引用的莱因哈德·梅依的《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一书中,也曾说到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另有中国当代哲学家张祥龙先生的文章,对此也有论证,我都将其放在了附件里,供你参考。
四、关于某位中国环境历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负面评价问题。
我不知道这是哪位“中国环境历史学者”?
“中国的环境破坏在汉朝以前就非常严重”,要看是与什么对象相比较?如果是与同时代的北美洲相比,那时的北美洲还是一片荒原、原始的自然,汉朝的环境破坏当然要严重得多,但这样的比较有意义吗?如果是与当下的中国、当下的美国相比,不要说汉朝,看一看一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老残游记》,山东泰山附近还常有老虎出没。我在吉林长白山下,一位老人告诉我,他年轻时,院子后边的山林里就能看到老虎。京剧《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唱段也正应了这些。如今,踏遍中国国土,哪里还有老虎的踪影!
环境的严重破坏,当然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世界性的生态恶化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脚步(消费主义的大脚的脚印)纷至沓来,这是常识。对于英国,是在“伦敦毒雾”时代;对于日本,是“脱亚入欧”之后;对于中国台湾,始于日本殖民时期;严重的环境破坏对于中国大陆,则是在“改革开放、经济起飞”之际。
我小时候,即20世纪50年代,我家在开封市(那可曾是省会城市啊)居住的那条小街,不但有蝴蝶、蜻蜓,还可以见到黄鹂、画眉、刺猬和蛇,甚至黄鼬、狗獾。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那是因为城市现代化了。
将环境危机与现代性、现代化联系起来,这才是一个问题,才是一个拥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至于东方与西方谁更亲近自然?不好一概而论。
我是主张东方(中国、印度、明治以前的日本)更亲近自然的。
原因之一,在于思维方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一种“理性的”“抽象的”“概念的”“逻各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容易使人与自然间隔起来、对立起来,容易将人置于自然之上进而认识自然、掌控自然、开发自然、掠夺自然。所以,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最终走向笛卡尔,走向牛顿,走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而中国不行,从老子、庄子无论如何也走不出个培根、牛顿、爱迪生来!东方式的思维是一种模糊的、直觉的、不脱离感性因此也就与自然融为一团的混沌型思维,这样的思维方式容易产生诗歌,却很难发展起科学,于是中国就成了诗的国度;《庄子》一书说是古代哲学,更像是寓言故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必须并入西方哲学思维的轨道,不必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
原因之二,在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已经数百年,而中国几千年来长期驻留在农业社会:“土里刨食儿”“靠天吃饭”,所以必须怀着对“天空”与“大地”的崇拜与敬畏之心;西方科学技术凭的是人自己的智慧、技能,信奉的是人的理性,所以容易以人类自己为主体、为中心。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是的,中国早就已经有人(如荀子、王充)提出“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一直不入主流;只是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进步论传入现代中国后,这些观点才火了一阵,王充更是被哄抬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古代学者代表,也恰恰是因为这些投合了现代性思维的门径。
五、关于环境历史学者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对陶渊明的负面评价问题。
我不知道这位学者,也没有看过他的书。
不过,你看看我的《陶》书第4章第4、5、6节,就会看到,在近代,随着启蒙理念渐渐传入中国,随着中国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步步趋近,对陶渊明的批判也就愈来愈强烈。日本有一位叫冈村繁的大学者,批判起陶渊明来更是不遗余力,陶渊明差不多成了一个消极保守、言行不一的反面人物,竟至让我得出在现代中国“陶渊明的精神也已经死去”的结论。
关于陶渊明与谢灵运的比较,《陶》书第197页(纸本),有过一大段论述,你或可参考。无论“人品”“文品”,谢比起陶都要低不止一个档次!
六、关于“为什么农业起家的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没有办法抵挡现代化与历史进程中的环境破坏”等相关话题。
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犹如一台超大马力、超大体量的隆隆战车,自其在欧洲启动以来,一直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古老的中华帝国曾经顽固地抵制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以惨败告终。
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蒙培元先生出版的《人与自然》一书,将中国古代文明概括为“生态文明”,有一定的道理。
如今,希望以“生态文明”遏制这台战车的运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否能够成功,我自己是悲观的,我接触的一些西方学者反倒比我乐观。说下个世纪是中国哲学的天下,有些自吹自擂,我不相信。说下个世纪是中西思想相融合的时代,东方精神将为生态时代的演进贡献自己的价值,此话当不会有误。
我将陶渊明视为中国古代“自然主义的”思想家与践行者,并致力于在国际论坛上积极加以推介。正如我在《陶》书“题记”中声明的:希望它能够为营造人类的下一个新的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产生积极的效应。总还是应该得到同情的吧?
但一个陶渊明就可以改变世界吗?
或者,一个梭罗就可以改变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吗?
或许不能。
但你看到人们对于梭罗、陶渊明的渐渐认可,总觉得还是有一丝希望在。
况且,根据中国传统伦理学的说法:难能可贵,难行能行才可贵,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人的精神之所在。
陶渊明以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当然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历史长河不会倒流,即使流错了方向也不会再倒流过去。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温故而知新”,借鉴古代人的生存智慧,“调整”“矫正”时代的走向。这也正是我在《陶》书结尾引用的列奥·施特劳斯的话:“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
你说:“我很难说服西方学者(甚至我自己)认同中国的自然观可以为目前环境危机提出一个解决的途径。”如果把这句话改为:“中国的自然观可以为解救目前环境危机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途径。”你是否同意呢?
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大约是前年,乐黛云先生为她主编的《跨文化对话》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新维度、新路向》的长文,也寄你一阅,你从中不难看出我的疑虑与彷徨。
以上只是我临下笔时的一些想法,仅供你参考,并希望得到你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