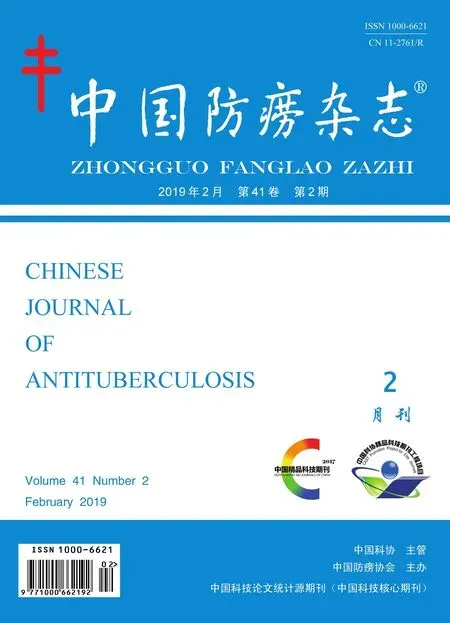间充质干细胞在结核病治疗中的应用与问题
吴蓓蓓 黄薇 王志敏
目前,针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的治疗原则主要是采取多种二线抗结核药物联合使用的治疗方案,但联合化疗的药物不良反应大,患者耐受不佳,甚至还可能使患者产生新的耐药风险[1]。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寻找新的方法治疗MDR-TB。疫苗是科学家们首先想到并且进行开发的治疗手段。1921年,Albert Calmette和Camille Guérin经过13年的努力共同研制成功了预防MTB感染的人工疫苗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érin,BCG)[2]。BCG自从面世以来,全球约有40亿人接种[3]。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由于环境、人群基因,以及MTB基因不同其对于成人保护效果差异很大。因此,人们开始尝试对BCG进行基因重组改造以提高其免疫效果[4],以及过表达BCG保护性抗原Ag85B,减少免疫系统对BCG的干扰等[5]。
细胞免疫在抵抗MTB的感染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巨噬细胞是人类抗击MTB的第一道防线,MTB在进入到人体内后,巨噬细胞先识别MTB,再和MTB相连,最后将其吞噬消灭[6]。另一方面T淋巴细胞分泌的γ干扰素(IFN-γ)可以激活巨噬细胞产生活性一氧化氮(NO)和相关的氮元素中间产物(reactive nitrogen intermediates,RNI),这些细胞因子可以通过底物左旋精氨酸(L-arginine)产生一些抗生素[7]。但是研究表明,MTB可以通过阻止被感染的细胞被免疫系统识别,以及抵抗巨噬细胞的消灭病菌的功能使得其自身可以同宿主细胞共存[8]。随着细胞治疗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的深入探究,科学家们看到了新的曙光。
一、MSC生物学特性
MSC是来源于发育早期中胚层的多能干细胞,主要分布于骨髓、骨、软骨、脂肪等多种组织的细胞,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分化为骨、软骨、脂肪等多种细胞。原代的MSC呈长梭性,形态类似于成纤维细胞,易黏附在塑料的培养器皿壁上生长。2006年,国际细胞治疗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ellular Therapy,ISCT)发布了鉴定MSC的标准,即MSC是一类可黏附于塑料的培养器皿壁上,具有成骨、成软骨、成脂的分化潜能,并且CD105、CD73、CD90表达量在95%以上,而CD45、CD34、CD14 或者CD11b、CD79a或者CD19 以及 HLA-DR表达量在2%以下[9]。
二、MSC参与结核病的免疫调节
近些年由于科学家发现MSC能参与免疫调控等作用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10]。2010年, Mei等[11]发现经过MSC静脉注射处理的患有败血症小鼠,炎症相关因子白细胞介素(IL)-10、IL-6基因等明显下调,而一些促进吞噬作用进而杀死细菌的基因明显上调。此后,Malek等[12]发现将MSC静脉注射到被MTB感染的小鼠后,小鼠肺部的大量细胞均能检测到干细胞抗原1(stem cells antigen-1,SCA-1), 即小鼠干细胞的特征,这些细胞表达CD29、CD44、FLK-1,但不表达CD34、CD45、CD11b和GR1,从而进一步证实MSC渗入到MTB感染的小鼠肺部。通过组织学分析,MSC浸润到肺部以后,在MTB周围形成了肉芽肿,建立了免疫抑制的区域,并且限制了MTB的播散[13]。研究表明,免疫反应太弱不利于抑制MTB的生长繁殖,然而免疫反应太强又会损伤机体自身[14]。随后,Kim等[15]将MSC注射到被MTB感染的小鼠中发现,其不仅提高了被感染小鼠的存活率,也促进了肺和脾脏内MTB的裂解,并且还能抑制MTB在骨髓巨噬细胞中的生长。此外,MSC分泌的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通过上调NF-кB信号增加了巨噬细胞NO的分泌[16],NO的分泌抑制了CD4+、CD8+T淋巴细胞的反应,从而使得免疫系统在防御病原体及其避免自身免疫反应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并且MSC促进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等细胞因子分泌,而这些细胞因子诱导MSC高表达NO合成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巨噬细胞NO的分泌[17]。而当细胞免疫过于低下时,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会分泌微量的IFN-γ,从而促使MSC增加的趋化因子配体-2(the chemokine C-C motif ligand 2,CCL2)/单核细胞化学引诱物蛋白质-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的合成,而CCL2/MCP-1在连通IL-12和IL-18后会促使NK细胞大量合成IFN-γ,形成了反馈循环,增强了NK细胞的免疫杀伤作用[18]。
三、MSC的趋化特性
MSC除了参与到免疫调节过程中,还具有特殊的趋化性来帮助炎症部位的恢复。趋化因子是一类相对分子质量为8000~10 000的小分子物质,主要有CC、CXC、C、CX3C这几类[19]。2004年,Abbott等[20]分析了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1,SDF-1)在MSC归巢现象中的作用。科学家们通过腺病毒转染提高心肌梗死小鼠梗死部位SDF-1的表达量,发现会明显增加MSC向梗死部位迁移的数量;而对照组无心肌梗死损伤的情况下,并不会增加MSC的募集数量。 而Wang等[21]发现MCP-1、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a(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1a,MIP-1a)和IL-8在大鼠缺血脑组织中均有表达,静脉注射MSC后,MSC在这三种趋化因子的协同作用下向损伤的脑组织迁移,并且修复脑组织损伤[22]。2013年,Wang等[23]证实外源性的MSC在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协同作用下向肺损伤部位聚集,并且进一步分化为肺泡细胞及其血管内皮细胞等修复损伤组织。2017年,Nenasheva等[24]用荧光染料羟基荧光素二醋酸盐琥珀酰亚胺脂(CFSE)对MSC标记后,静脉注射入结核病小鼠体内,3 h后其中(12.63±10.24) %的细胞被发现进入到小鼠肺部,也进一步证实了MSC的趋化特性。
四、MSC疗法的探索
近些年,科学家们在细胞和动物水平上均证实了MSC能参与到肺部疾病治疗上。Yudintceva等[25]将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的新西兰兔的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提取后,用超顺磁氧化铁纳米粒子(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SPION)进行标记后回输到兔体内以治疗泌尿生殖系统结核。经过观察,发现兔膀胱的变形和炎症反应明显下降,并且纤维化程度也明显降低。2015年,Zuo等[26]首次在支气管上皮基底层位置鉴定到了具有肺再生功能的p63+/Krt5+双阳性远端气管干细胞(distal airway stem cells,DASC),在流行性感冒病毒诱导的小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模型中,内源的DASC能迅速地扩增并分化成微支气管和肺泡细胞等具有各种功能的细胞,从而重建整个肺结构,制造出了首个“换肺”的小鼠模型。随后,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对肺纤维化患者开展了临床试验[27]。而对于结核病患者科学家们也已经开展了相关的临床实验。2005年开始,Erokhin等[28]对15例MDR-TB和12例XDR-TB患者分别进行了自体MSCs全身性辅助化疗,发现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均得到了改善,其中20例患者在治疗3~4个月以后痰菌明显降低;在治疗1.5~2年以后,有9例患者长期随访中无复发。从2009年开始,Skrahina等[29]用患者自体的MSC全身移植治疗MDR-TB,而后观察到患者的肺部空洞逐渐缩小。 2014年,Skrahin等[30]报道了一项临床试验,将60例患者(年龄范围21~65岁)随机分为2组,其中30例经标准抗结核药物治疗4周后接受单剂量的MSC注射治疗(试验组),而另外30例只接受标准抗结核药物治疗(对照组)。18个月后,试验组的治愈率(53.33%)是对照组(16.67%)的近3倍,并且安全性良好,无药物不良反应。这些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了MSC治疗结核病的可行性。
五、MSC治疗结核病存在的问题
MSC治疗疾病的机制尚未明确,并且对于不同的疾病和个体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由于MSC低免疫原性及参与免疫调节等作用,让人们在很多疑难杂症(包括结核病,特别是MDR-TB)的治疗上都看到了曙光。尽管如此,世界范围内目前批准的干细胞药物依然有限,这项技术依然需要完善。
首先,由于受到传代次数的限制,无论是自体还是异体的移植,年轻而又足量MSC的来源一直是移植上需要解决的问题[31]。其次,即使治疗成功的结核病患者,依然可以从自体的MSC中检测到MTB,而生长因子CD271+可长期潜伏于骨髓MSC并且可长时间在宿主细胞内提供保护[32]。因此,移植MSC时是否需要去除CD271+ MSC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而Raghuvanshi 等[13]和Ramakrishnan[33]都发现, MSC形成的肉芽肿限制了MTB的活动,但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T淋巴细胞的免疫活性,协助了MTB的免疫逃逸,使MTB可长期潜伏于患者体内。
六、总结和展望
尽管MSC治疗结核病尚存在一些问题,但依然给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目前,仍需要大量的机制研究和临床试验以进一步评价MSC治疗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此外,根据人群个体的差异,MSC治疗的剂量、时间,以及运输过程中的储存、冻存、复苏等问题都尚未完全解决。随着再生医学的不断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MSC的这些问题会逐步解决,真正帮助到结核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