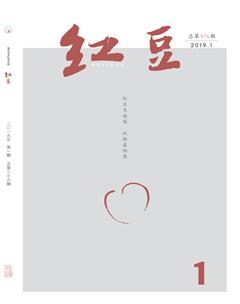人物卷子之一
胡竹峰
茅盾
参加拍卖会,看见一幅茅盾书法立轴,清癯入骨,秀气里藏不住傲骨,儒雅得仿佛柳公权附体给董其昌了,或者欧阳修附体给杨凝式了。茅盾晚年和老朋友在信上闲聊,说他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代临过董美人碑,后来乱写,老了手抖,目力又衰弱,“写字如腾云,殊可笑也”。老先生谦卑矜持,不显山露水。
印象中,茅盾给不少杂志题过刊名,一律精瘦精瘦的样子,筋道,有钢丝气。字很潇洒,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有功夫,比书法家多了文人气书卷气风雅气。徐调孚说:“茅盾书法好,写稿虽然清楚,字并不好,瘦削琐小,笔画常不齐全,排字一走神会排错。”我倒是愿意做一回茅盾文稿的排字工,苦点累点没关系,写在原稿纸上的笔墨养心养眼也怡人。
上次出去开会,偶遇茅盾任职《人民文学》时期的同事。老人家八十多岁,谈起茅盾来,赞不绝口,开口沈先生如何如何,闭口沈先生如何如何。说茅盾为人随和,去他家里,要多随便有多随便。说沈先生脾气好极了,永远温文尔雅,放手让他们去组稿、编辑,关心杂志社小同志的生活。说沈先生的手稿啊,清清爽爽,改字用笔涂掉然后画一根线牵着替换的内容,像穿了西服打了领带一样漂亮雅致。这些我信。
茅盾,原名沈雁冰。
茅盾作品看了很多,小说里,真要说,一些短篇比《子夜》要好。偶尔翻翻他的《春蚕》《秋收》《寒冬》,一笔一画勾画悲伤,怎么爬都爬不起来的描写太深刻,读得人心中浮现一缕缕心酸。
有年在旧书摊买到两本茅盾的文学评论集,熬夜读完,他的如椽大笔,大开大合,让人心怀敬意。萧红《呼兰河传》,书前有茅盾先生一九四六年八月写的序,有识见、有性情、有体温。茅盾诗意地评价《呼兰河传》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结论性的定评,很准确,很恰当。近人文章里很少能看见结论,更不要说定评。王顾左右,东拉西扯,客客气气,几乎成了当下的文风。过去不是这样,茅盾先生的文学评论,枪挑脓疮处很多,需要一针见血,绝不点到为止。一来是文风性情使然,二来也是见识问题。
一九三二年,阳翰笙小说《地泉》三部曲再版,特意请茅盾写序。茅盾事先就说,你的《地泉》是用革命的文学公式写成的,要写我就毫不留情地批评它:“《地泉》在描写人物时用了脸谱主义手法,在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出现了公式化现象,在语言上用标语口号式的言辞来表达感情。从整个作品来讲,《地泉》是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
民国很多作家写文章,敢下结论。现在人之所以不敢下结论,主要还是怕献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几十个字交代一本书,所谓艺高人胆大,评《三国演义》如此论述:“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这样的才气这样的胆气这样的语气让人神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是主编。他执掌后的《小说月报》,成为新文艺最大阵营之一。
茅盾一生条理分明:做人第一,读书第二,写作是游艺,从来没有颠倒过。他当编辑,体贴作者,笼络了一批优秀作家,在文坛上地位高、人缘好。一九四五年,茅盾五十大寿,重庆《新华日报》为其祝寿,文化界由郭沫若、老舍、叶圣陶、洪深、陈白尘、巴金等十四人发起,声势浩大,成为四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坛大事之一。各路英雄人马纷纷写文章祝寿、祝福,情形如《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夜宴,与《隋唐演义》各路好汉给秦琼母亲做寿有一比。
看《子夜》,就知道人家多么了解上海社会,对金融市场尤其熟悉。当年《良友》杂志想要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编辑请茅盾操刀,他一口答应,很快写出一篇香粉弄華商交易所的素描文章,经纪、散户都写活了。
前些时候准备重读《子夜》,几乎读不下去。有报纸副刊编辑老友骂我,说那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瞿秋白都称赞。瞿秋白称赞我知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口味趣味,读小说是闲事雅事乐事,给自己找不快我不干。
但我知道茅盾的功力,也知道《子夜》了不起。书中人物饱满,构架宏大,开篇知大手笔,心理描写糅合着诸多细节,让人感叹时代变迁,人情冷漠。茅盾单用一年的起落,道尽中国百年风雨飘摇。
三十岁后,巴金、老舍、赵树理的很多小说都读不下去了。他们的创作谈回忆录倒经常翻翻,翻出沧桑也翻出很多陈旧故事、陈旧人物,也不乏旧文人趣味,跟他们穿长衫的照片一样斯文。
茅盾去世,巴金写悼念文章,怀念之意且不去说,忆旧之情也不去说,一些小细节、小场景有意思: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
据说茅盾记忆力不错。一九二六年的一天下午,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茅盾、郑振铎、夏丏尊及周予同等人吃饭。酒至半酣,章锡琛对茅盾说:“听说你会背《红楼梦》,来一段怎么样?”郑振铎拿过书来点回目,茅盾随点随背,一口气背了半个多小时,一字不差。但我总感觉这一类笔墨多是小说家言,可以聊充饭桌茶楼间的谈资,不能当真。
茅盾的散文底色太红,格调上不如巴金、老舍,但气息够足,常常有抑制不住的情感,力量巨大,一腔绝望又充满希望地滚滚而来。茅盾的小品文,《白杨礼赞》之类不论,不少篇章写得摇曳多情,读来口舌生香。茅盾的很多小品文有鲁迅《野草》的风格,只是隽永不及,激情有余,损了文格。
茅盾旧体诗写得不坏,手头一册上海古籍版的《茅盾诗词集》,精装本、竖排版,天地开阔,红色的八行笺里印着古典一脉的春风杨柳,虽嫌做作,但气度清华疏旷,雅致又风流。茅盾那批老民国,偶然写点旧诗词,格调不低,说白了还是旧学底子好。
老舍
梅兰芳演《晴雯撕扇》,必定亲笔画张扇面,装上扇骨登台表演,然后撕掉。画一次,演一次,撕一次。琴师徐芝源看了心疼,有回散戏后,偷偷把梅先生撕掉的扇子捡回来,重新裱装送给老舍。
老舍钟情名伶的扇子,梅、程、尚、荀四位以及王瑶卿、汪桂芬、奚啸伯、裘盛戎、叶盛兰、钱金福、俞振飞等人书画扇,藏了不少。老舍也喜欢玩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缝,买来摆在家里。有一次,郑振铎仔细看了那些藏品之后轻轻说:“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我看着舒服。”相顾大笑。此乃真“风雅”也。舒乙著文回忆,老舍收藏了一只康熙年的蓝花碗,质地细腻光滑,底釉蓝花色泽纯正;另有一只通体孔雀蓝的小水罐,也是绝品。
老舍一生爱画,爱看、爱买、爱玩、爱藏,也喜欢和画家交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许地山向齐白石买了幅《雏鸡图》,精裱成轴,兴奋莫名。和画家来往渐多,老舍藏品日益丰富,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陈师曾、吴昌硕、李可染、于非闇、沈周,他在北京家里的客厅西墙换着挂,文朋诗友誉之为老舍画墙。
老舍爱画也爱花,北京寓所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当当,按季更换。老舍说花在人养。天气晴和,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家客厅桌子上两样东西必不可缺。一是果盘,时令鲜果轮流展出;二是花瓶,各种鲜花四季不断。老舍本人不能吃生冷,但对北京产的各种水果有深厚的感情,买最好的回来摆在桌子上看看闻闻。
老舍爱画爱花的故事让人听了心里欢喜,这是真正的舒庆春。老舍的面目、茅盾的面目、鲁迅的面目,几十年来,涂脂抹粉,早已不见本相。
大陆有人在乡间小学当校役,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文笔却好得惊人。亦舒说从来没有兴趣拜读此人大作,觉得这样的人难有独特的生活经验和观点意见,她认为文坛才子是要讲些条件的,像读过万卷书,行走万里路,懂得生活情趣,擅琴棋书画,走出来风度翩翩,具涵养气质。老太太说话锐利了一点,却有道理。文章品位得自文化熏陶,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乃至朱买臣负薪读书,求的还只是基本功,未必能成大器。钱谦益说: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与山水近,与市朝远;与异石古木哀吟清唳近,与尘埃远;与钟鼎彝器法书名画近,与时俗玩好远。故风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余世,其积习使然也。”
钱谦益读的书多,气节上暂且不论,见识不差。文行出处,此四字不能忘。古玩字画、吹拉弹唱,读书人懂一点不差,笔下体验会多一些。
这些年见过老舍不少的书法对联,还有尺幅见方的诗稿、书信,一手沉稳的楷書,清雅可人。他的大字书法,取自北碑,线条凝练厚实,用笔起伏开张,并非一路重按到底,略有《石门铭》之气象。老舍的尺幅楷书,楷隶结合,波磔灵动,有《爨宝子》《爨龙颜》的味道,古拙,大有意趣,比大字更见韵味。
老舍早年入私塾,写字素有训练。在拍卖会上见过一幅老舍的书法长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手书,内容是毛泽东诗词。凑近看,笔墨自然蕴藉,浑朴有味,线条看似端凝清腴,柔中有刚,布局虽略有拘谨,但气息清清静静,落不得一丝尘垢,看得见宁死不屈的个性,看得出忠厚人家的本色。
老舍手稿我也见过,谈不上出色,比不上鲁迅比不上知堂,也没有胡适那么文雅,但好在工整。前些年有人将《四世同堂》手稿影印出版,书我虽早已读过,但还是买了一套,放在家里多一份文气,“我看着舒服”。
课堂文学史上的老舍从来就不如时人笔墨中的老舍有情有趣。住在重庆北碚时,有一次,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晚会,老舍自告奋勇垫一段对口相声,让梁实秋搭档。梁先生面嫩,怕办不了,老舍嘱咐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部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作‘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这样有趣的人下笔才有真情、真性、真气,才写得了《赵子曰》,写得了《老张的哲学》,写得了《骆驼祥子》。
少年时在安庆乡下读老舍的小说,平实而达真实。大夏天,暑气正热,天天不睡午觉,洗个澡在厢房的凉床上躺着细细观赏老舍的文采。
围墙外蝉鸣不断,太阳渐渐西斜,农人从水塘里牵出水牛,牛声哞哞,蜻蜓在院子里低飞,飞过老舍笔下一群民国学生的故事。小说是借来的,保存了民国面目,原汁原味是老舍味道。只有一本旧书摊买来的《骆驼祥子》,字里行间的气息偶尔有《半夜鸡叫》的影子,读来读去,像一杯清茶中夹杂了一朵茉莉花,不是我熟悉的老舍,后来才知道那是五十年代的修改本。
老舍的作品向来偏爱,祥子、虎妞、刘四是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的人物。后来读到民国旧版《骆驼祥子》,真是满纸辛酸。最后,祥子不拉洋车了,也不再愿意循规蹈矩地生活,把组织洋车夫反对电车运动的阮明出卖给了警察,阮明被公开处决了。小说结尾写祥子在一个送葬的行列中持绋,无望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调子是灰色的,但充满血性,是我喜欢的味道。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故事在一连串对比鲜明的形容词中结束。似乎每一个好的故事都是一场生命的陨落,从美好的开始到阴晦的结束,历经一场场挣扎,渐渐灰了心。
都说老舍幽默,这太简单也太脸谱。“幽默”二字不过是老舍的引子,概括不了他的风格。《赵子曰》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逼真动人,轻松微妙,读来畅快得很。写到后半部,严肃的叙述多了,幽默的轻松少了,和《骆驼祥子》一样,最后以一个牺牲者的故事作结,使人有无穷的感喟。老舍的小说,令人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而悲愤,悲愤才是老舍的底色本色。湖水从来太冷,钱谦益跳不进去,老舍跳得进去。
汪曾祺在沈從文家里说起老舍自尽的后事,沈先生听了非常难过,拿下眼镜拭泪水。沈从文向来感谢老舍,之前老舍在琉璃厂看到盖了沈从文藏书印的书,一定买下来亲自送到沈家。
二十年后,汪曾祺先生想到老舍,写散文写小说表示牵挂怀念。《八月骄阳》写老舍投湖:骄阳似火,蝉鸣蝶飞,湖水不兴,几位老人闲聚一起,谈文说戏,议论时势。穿着整齐的老舍,默默地进园,静静地思考,投湖而逝。井上靖一九七0年写了篇题为《壶》的文章怀念老舍,感慨他宁为玉碎。玉碎了还是玉,瓦全了不过是瓦。
巴金
快十年了,在郑州古玩城旧书店搜书。百十家古旧书店,在那里买过不少新文学旧文学著作,也买过不少作家签名送人的文集,有汪曾祺、冰心、巴金。有回见到老舍的手稿、巴金的信笺,没能买下,现在想来后悔。旧书店的老板用宣纸仔细包了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翻开,说从笔迹上看,老舍、巴金一手字四平八稳,是个忠厚人。
巴金信笺上的字写得认真,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像学生体。晚年手抖,笔力虚浮,越发像学生体。巴金的签名有意思,潦草又认真,有说不出的味道,偶尔签名赠书友朋辈,落款后盖一枚小指头盖大的印章,阳文“巴金”二字,红彤彤、鲜艳艳比樱桃好看。我见过几枚巴金的印文,不知何人操刀,件件都是奇品:生机勃勃,一纳须弥。
巴金本姓李,是西化人,巴金的笔名也是西化的,取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名字首尾二字。还据说巴字是纪念法国亡友巴恩波,金字和其译作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有关。李家人相信西医,巴金的母亲和几个英国女医师做朋友,她们送李母《新旧约全书》,西洋封面、西洋装帧、西洋排版,巴金很喜欢。后来在家自学外语,进外国语学校读书。这是巴金的底色,巴金的基因。
巴金早年认为线装书统统都应该扔进废纸堆,批评郑振铎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旧物。看见巴金晚年用印章,送线装书给人,我心里高兴,这才是中国读书人的面目。巴金九旬大寿时,出版界朋友想送给他一件有意义的礼物,精制一批《随想录》线装本,老人家很是赞赏。
《家》的开头写大雪,十几岁读过,有些句子竟然背得下来。很多年过去,风散了,雪化了,书中戴金丝眼镜的十八岁青年也成了旧人。十五六岁时,第一次读《家》《春》《秋》,觉新、觉民、觉慧真好,梅表姐也好,鸣凤也好,都好看,不像张恨水笔下的人物那么新潮、那么儒雅、那么深情,灰长袍配白围巾黑皮鞋自有一股斯文通透。
巴金小说暌违经年,今春读《寒夜》,六十年前的故事,平平常常波澜不惊。三十年前的老书,深蓝色的封面一钩残月,素到不能再素。开始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树生,结尾是树生在寒夜中回到旧居。情节是寒夜的故事,意境也染上寒夜的悲凉,读来感叹不已,有冷月葬诗魂的凄清美。巴金有一颗敏感的心,善于察觉各种极微小的细节并引发内心的波动。
年少时候读《寒夜》觉得压抑难耐,心被揉成一团不忍读下去。那种剑拔弩张、极其细微的悲凉一点点爬进了身体每个角落。理想毁灭,挚爱离去,分别前夜偷偷地哭泣一直到最后的病逝,全部都绝望,巴金不留一点出路。
《寒夜》之后,巴金的创作也进入寒夜了。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作家思维跟不上执政家手腕。小说也在写,散文随笔特写,书一本本地出,但不是老巴金,而是戴了面具的执笔人。后来,文章的面具也不让戴了,巴金被安排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法国几位作家不知巴金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肩膀上的两百斤终于放下,巴金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巴金的翻译不硬译、不死抠,流畅、自然、传神,富于感情,和他的创作风格统一。草婴喜欢巴金的译文,说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高莽说巴金译文“语言很美”,表现出“原著的韵味”。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我读过,至今还记得那句:“风一吹,芦苇就行着最动人的屈膝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上海笼罩在初冬的微寒中,七十多岁的巴金颤巍巍写下一篇《谈〈望乡〉》。自此正式启动了《随想录》的写作,直至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
我读到《随想录》已经是巴金写完之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了。黄昏萧瑟,暮气笼罩着北方的城市。暖气不够热,坐在椅子上需要铺个毛毯。看巴金怀念萧珊、怀念老舍,有真情有真意有真气,是地道的白话文,白如雪如棉如絮,但分量不轻,一个个字灌满铅,沉甸甸的。胡适先生看了一定会喜欢。
《随想录》的重点是随想,但归根是录,记录。《广雅》云:录,记之具也。《后汉书》云: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这个录是总领的意思。《世说新语》说陶侃在做荆州刺史期间“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这里的录指的是收集、收藏。《孔雀东南飞》里说: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里的录却是惦记了。过去的旧人旧事忘不掉,这里有一份眷恋。
巴金写旧人旧事,是文人之叹也是史家之思,还有对人性之美的向往,一篇篇文章平白沉郁,又清秀又智慧,严明深切。《随想录》虽为实录,不少篇章亦为旧梦重温,其中生死离别,自然情切,有无量悲欣。数百则随笔几乎全用白描,又诚实又坦白,不回避、不矫饰,每个字都是修辞立其诚的注脚。
《随想录》时期的巴金,是智者,是仁者,也是长者、尊者。写自身日常的冷暖,怎样的麻木,怎样的怯懦,怎样的后悔,还有失落、逃逸,笔锋正而直,丝毫不带斜风细雨。世人写巴金,往往仰视惊叹,巴金偏偏以平常之心平常之情平常之笔写世俗中的人和事,这样的文章读了受用终生。
二00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金去世。人走烟消,民国余脉快飘散净了。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