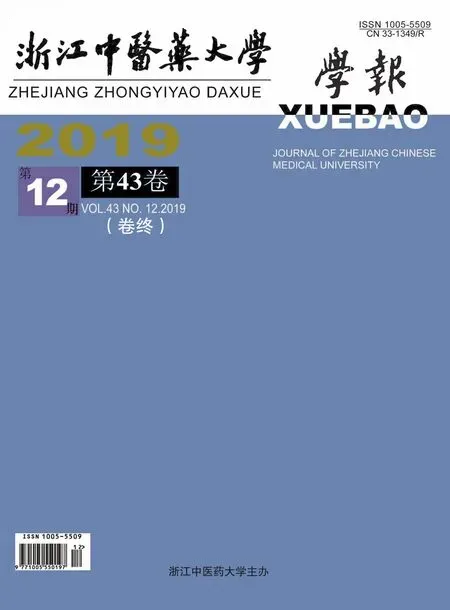影响针灸疗效的时间因素研究概况
1.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针灸疗法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一种,适用于临床常见的多种疾病,具有疗效显著、操作简便、医疗费用低廉、不良反应较少等特点。临床上,患者心理状态、疾病本身、针灸处方以及医者手法等均可影响针灸疗效,其中时间因素作为针灸处方的重要方面,包括针刺介入时机、针刺时辰、留针时间、行针时间、治疗间隔时间、疗程等诸多方面,现从实验和临床研究两个方面就影响针灸疗效的时间因素进行简要综述。
1 实验研究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时间因素对针灸疗效的影响,针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相关的动物实验研究。例如刘勇等[1]研究认为,针刺能够降低模型大鼠缺血脑组织中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deleted on chromosometen,PTEN)蛋白表达,提高缺血脑组织中磷酸化蛋白激酶B(phosphorylated protein kinase B,p-AKT/PKB)、磷酸化糖原合酶激酶-3(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pGSK-3)表达,且造模后2h针刺介入的效果明显优于72h和168h,由此推测针刺越早介入,对缺血神经元损伤的修复、再生和保护作用越明显。谢感共等[2]研究发现,灵龟八法开穴针刺可提高健康豚鼠机体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性,降低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其中卯时针刺SOD活性增幅最大,MDA含量午时降低幅度最大,亥时降低幅度最小。此外,崔建美等[3]认为针刺小鼠“后三里”留针时间不同则镇痛效果有差异:留针30min内,针刺镇痛效应呈升高-降低-再升高-再降低的波浪形曲线,留针20min针刺镇痛效应达到最大。赵仓焕等[4]研究中发现,电针可显著增强炎症疼痛大鼠局部前阿黑皮素(pro-opiomelanocortin,POMC)和前脑啡肽原(preproenkephalin,PENK)mRNA 的表达,从而产生镇痛效果,而每天电针治疗1次镇痛效果最好。李晓宁等[5]研究认为,夹脊电针可显著改善急性脊髓损伤大鼠的运动功能和神经凋亡情况,且与治疗3d组比较,治疗14d组大鼠细胞凋亡数量降低更显著。以上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针刺介入时机、针刺时辰、留针时间、治疗间隔时间以及疗程的不同对于实验动物均可产生不同的生物学效应。
2 临床研究
2.1 针灸时间
2.1.1 针灸介入时机 针刺介入时机的选择与疾病的进展与转归密切相关,以下就中风、面瘫、痛经等针灸科常见病的针刺介入时机进行综述。相关学者认为,脑梗塞患者急性期针灸介入比恢复期疗效更佳,而恢复期开始介入比后遗症期疗效更佳[6]。早期有学者认为,面瘫急性期机体处于正虚邪盛状态,此时介入针灸不仅无效,反而可能加重病情[7]。也有学者就此提出异议,认为周围性面瘫发病5~7d达到病情的高峰期,是疾病的自然发展规律,此期治疗主要目的在于控制病情继续发展,而非缓解症状[8]。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针灸治疗最佳时机在急性期,如于学平等[9]认为,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7d内行针灸介入效果最佳。王韵等[10]则认为急性面神经炎及早介入针刺,可减缓面神经损伤的进展,提高疗效、缩短疗程,从而减轻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冯蕾等[11]等研究发现,周围性面瘫急性期4~7d内治疗效果最佳。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早期针灸介入可提高疗效。杨欢等[12]总结了国内外近二十年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对照试验,得出在行经前针刺介入通常疗效更好的结论。卜彦青[13]则认为,经前针灸介入和行经期间发作疼痛即时针灸都有显著效果,两组对比无显著差异。综合以上研究结果,笔者认为针灸介入的时机影响针灸效果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学者们对具体的最佳介入时机各持不同观点,但大多认为越早介入则疗效越好。
2.1.2 针刺时辰 关于针刺时辰理论,目前以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研究较多。该项理论强调时间对针刺疗效的影响,其以阴阳五行理论的生克制化来推算人体经脉气血的流注盛衰和经脉穴位的开阖,根据气血流注旺盛选择出最佳针刺时辰,从而获得最佳治疗效果[14]。同时“择时治疗”也体现了针灸“三因制宜”的治疗原则。《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第四十四》有云:“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说明上午人体阳气长,病气衰,故针灸治疗时间一般在上午[15]。张慧玲等[16]运用“子午流注理论”研究辰巳时与不定时针刺治疗脑卒中患者,观察临床疗效及患者血脂、血凝指标,结果表明辰巳时针刺治疗脑卒中的效果更明显。宋立中等[17]认为,酉时和辰时针刺均能明显影响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血栓素B2(thromboxane B2,TXB2)/6-酮前列环素F1a(6-keto-prostacycline F1a,6-keto-PGF1a) 的比值,但酉时针刺调节作用效果优于辰时。国兰琴等[18]研究按时取穴治疗失眠发现,申时(15点至17点)针灸与走罐治疗失眠的疗效优于上午,取穴以膀胱经俞穴为主,因为此时膀胱经最旺,针刺五脏背俞穴可使全身气血调和、阴平阳秘,从而改善睡眠。以上研究说明择时针刺较随到随针疗效更好,但实际情况下,因医者门诊时间固定、门诊量大,导致患者针灸时间多不固定,往往随到随针。
2.2 留针时间 针灸治疗过程中常根据病情需要,选择是否留针及不同留针时间来提高临床疗效。留针时间从古至今都是针灸医者关注的焦点,《灵枢·五十营》曰:“呼吸定息,气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一刻相当于14min24s,则经气循环一周的时间为28min48s,是现行临床普遍留针20~30min的依据[19]。现代针灸研究多以30min为参照进行对比,例如何扬子等[20]对比了留针20、40和60min治疗缺血性中风患者的疗效差异,结果显示60min组疗效最优,其次为40min组。姚肖君等[21]观察针刺得气后留针20、30、45、60min治疗急性疼痛(主要是急性腰扭伤、落枕等病症)的即时镇痛效果,结果发现留针45min即时镇痛效果最好,30min组次之。陈少宗[22]认为,留针时间应以针刺作用的最佳诱导期为依据,即针刺开始到达到最大效应所需的时间为留针时间,而留针时间明显长于或短于最佳诱导期都达不到最佳疗效。韩明娟等[23]整理文献总结认为,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留针时间越长,可以实现最大刺激量,疗效越好;此外,周围系统神经疾病中以面神经炎为例,留针20min的疗效较好,与30min的疗效相当。上述研究结果比较具体地评估了最佳留针时间,比如60、45、30min,但临床实际操作中评估是否需要留针以及留针时间长短,除综合患者具体病症以外,还需考虑患者的依从性和耐受性等多方面。
2.3 治疗间隔时间 《灵枢·终始》有“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的论述,这是古代文献首次论述针刺间隔时间[24]。当代也有不少有关针刺治疗间隔时间的临床研究,如周桂桐[25]认为急性病、实热性病证需缩短间隔时间,增加针灸次数,如对于发热、急性泄泻或急性疼痛,可以3~4次/d,一般痛证应2次/d;对于慢性病证,可1次/d或隔日1次;有的病证如甲亢,每周针刺2~3次即可。卞金玲等[26]对石学敏院士针刺手法量学进行了总结,石学敏院士认为,针灸治疗两次施术间隔时间的最佳参数为3~6h,例如针刺治疗脑血管疾病应该间隔6h,而针刺治疗哮喘应间隔3~4h。有学者研究不同针刺频次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疗效的影响,认为针灸每日2次治疗脑梗死恢复期疗效优于每日1次[27]。杨帆等[28]对照研究每日1次和隔日1次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结果表明治疗7d后每日1次组的疗效优于隔日1次组,而治疗14d后两组的疗效没有明显差异。针灸效应的持续时间有限,大多疾病需要重复治疗。治疗间隔时间影响针灸效应的累积,因此确定最佳治疗间隔时间能有效提高针灸疗效[29]。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疾病、不同证型所需的治疗间隔时间不同,即使是针对同一种疾病的研究结果也有较大差异,这可能与相关临床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者选取的参照时间不同、样本量偏小等因素有关。
2.4 疗程 患者的病种、病程、体质以及针刺耐受性不同,故治疗所需的疗程也有差异,临床医生多根据诊治经验和疾病发展确定疗程。关于最佳疗效所需的疗程,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唐华生[30]进行了针灸治疗单纯性肥胖的研究,经过4~6个月的治疗和观察,发现疗程越长疗效越好。张昶等[31]通过检索针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相关文献发现,支气管哮喘发作急性期针灸治疗比缓解期所需疗程短,急性期治疗1个疗程即可,缓解期则需1~4个疗程。薛晓等[32]将90例原发性痛经患者随机分成3组,分别治疗1、2、3个疗程,以研究不同疗程对针灸疗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治疗2个和3个疗程的疗效优于1个疗程。河恩惠等[33]研究结果表明,电针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有明显疗效,且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加,疗效变化更明显,尤其以第6周为甚,提示针刺疗程增多可加强中髎及会阳深层神经所支配的膀胱逼尿肌与尿道括约肌的功能,从此能够加强患者自控排尿能力。以上临床研究表明,随着针灸次数的增加,疗效增强。但疗程与针灸疗效并不呈绝对正相关关系,疗程太短则治疗无效,疗程过长也达不到预期效果,刺激时间超过一定限度,有效刺激反而会转变恶性刺激[34]。因此判断疗程长短时应及时评估患者病情、病性及疾病转归,同时综合考虑针灸后效应、患者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治疗太过或不及。
3 小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时间因素对针灸疗效影响的研究近年来多集中在中风和周围性面瘫这两大类针灸疗法优势病种,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针对失眠、肥胖、各种痛症等常见病的研究。针对每个具体时间因素都有相关的研究,其中留针时间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多,而行针时间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仍然很难总结出每一病种的具体时间标准。现代关于针灸时间因素的相关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经各种临床及实验研究证实,上述时间因素与针灸疗效之间确有关系,但其中因时间因素产生疗效差异的具体机制却很少有学者提及。(2)单个时间因素与针灸疗效的相关研究不少,但多个时间因素同时参与的研究设计方案鲜有,各时间因素之间有无交互影响很少涉及,例如针刺时辰对留针时间、介入时机对疗程的影响等。(3)相关术语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也是文献研究中的一大问题,例如在文献中“针刺时间”可指“针刺介入时机”,亦可指“治疗总疗程”等,导致研究缺乏标准化。(4)相对临床研究,实验研究比较单薄,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针刺量学标准的研究一直是针灸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针灸疗法传承发展和推进针灸国际化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推进研究进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临床研究往往因主观因素过多,而限制和影响了数据结果,为探讨针灸治疗过程中时间因素的规律性,临床学者应尽可能把主观因素转变为可控因素,保证操作的规范化,同时增大样本量以减小统计学误差。(2)实验研究相对较少,而阐明时间因素影响针灸疗效的生物学机制主要依赖实验研究,实验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单个时间因素,亦要关注多个时间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3)现在的临床操作多来源于古籍,因此文献研究不可少,其中统一文献中的时间因素相关术语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