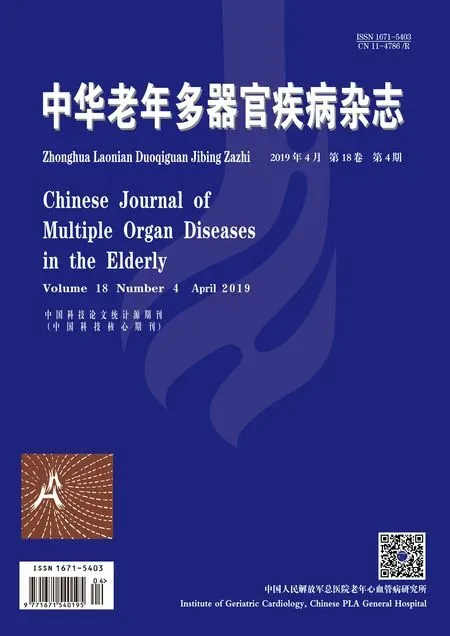双膦酸盐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疗程的研究进展
曹海玲,张一娜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老年病科,哈尔滨 150001)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多见于绝经后女性和老年男性[1]。髋部骨折是最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或称脆性骨折),亦是所有骨折中致死、致残的最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髋部骨折的发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导致患者生命质量明显下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1]。因此骨质疏松症及其引起的脆性骨折已成为日益瞩目的公共健康问题。
双膦酸盐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一线抗骨质疏松症药物。主要包括阿仑膦酸钠、唑来膦酸、利塞膦酸钠、伊班膦酸钠。这类药物不仅能特异性地结合到骨转换活跃的骨表面、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减少骨吸收,而且可促进钙在骨骼中的沉积,提高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进而降低椎体、髋部和其他部位骨折的风险[2,3]。尽管在降低骨折风险方面发挥作用,但双膦酸盐与不良结局相关。最常见的不良结局包括胃肠道副作用、急性期反应、肾毒性和心房颤动等[4]。此外,有研究表明颌骨坏死(osteonecrosis of the jaw,ONJ)和不典型股骨骨折(atypical femur fracture,AFF)的发生似乎与长期使用双膦酸盐有关[5-7],因此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1 双膦酸盐类药物治疗骨质疏松引起的不良反应
1.1 ONJ
ONJ被定义为口腔内暴露的骨头,在诊断后8周内不能愈合,有使用抗吸收剂(双膦酸盐或丹诺单抗)进行治疗的病史, 无颅面放射病史[8]。ONJ最初是在接受高剂量静脉注射双膦酸盐的晚期癌症患者中描述的。据计算,接受口服双膦酸盐的患者中ONJ的发生率从1∶250 000到1∶10 000[9,10]。ONJ的风险随着暴露于双膦酸盐的持续时间而增加;非癌症患者的风险在使用5年后显著增加[11]。
1.2 AFF
AFF即在低暴力下发生在股骨小转子以下到股骨髁上之间的骨折。研究表明双膦酸盐使用超过5年后,AFF风险会增加(4~5例/1 000例)[12,13]。国外一项队列研究发现,患者在使用双膦酸盐1~2年后,AFF年发病率为1.8/10万;8年后,增加到113/10万[14]。
研究表明双膦酸盐可能对骨量有长期的残余作用。因此有人提出“药物假期”作为降低ONJ和AFF风险的手段。虽然其他因素可能导致ONJ和AFF的发生(如口腔健康差、侵袭性牙科手术及AFF的下肢和臀部几何形状),但双膦酸盐持续应用引起的骨转换抑制似乎起着重要作用[15]。研究显示,尽管双膦酸盐在骨骼中有长期残留效应,但一旦撤出后AFF的风险也会显著降低[16,17]。双膦酸盐停用对ONJ风险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2 “药物假期”对长期双膦酸盐治疗骨质疏松患者疗效的影响
2.1 阿仑膦酸钠
“阿仑膦酸钠假期”的标志性研究是骨折干预试验延长(FLEX)研究,1 099名绝经后妇女应用阿仑膦酸钠治疗5年后被随机分成5 mg/d组、10 mg/d组和安慰剂组(药物假期组),为期5年。结果显示:持续用药组相较药物假期组,临床意义上(有症状)的椎体骨折的风险显著降低(分别为2.4%和5.3%),但影像学上椎体骨折的风险没有明显差异(分别为9.8%和11.3%)。非椎体骨折的累积危险性在持续治疗组(19.0%)和药物假期组(18.9%)无显著差异[18]。此外,持续用药组髋部BMD并未随着阿仑膦酸钠的继续使用而进一步增加。同时药物假期组患者髋部BMD虽有所下降 (2.4%),但仍高于10年前未治疗时的基线水平。类似的, 药物假期组骨转换标志物 (bone turnover markers,BTMs)虽有缓慢升高,却仍低于治疗前水平[19]。Bauer等[20]发现应用阿仑膦酸钠5年后停药的妇女,停用时年龄大和髋关节BMD低与骨折风险增加显著相关,且基线时股骨颈T评分与阿仑膦酸钠疗效之间相互关联。在FLEX基线没有椎体骨折的妇女中,阿仑膦酸钠的继续治疗减少了股骨颈T值≤-2.5的妇女的非典型椎体骨折发生风险,但不会减少T值≥-2.5妇女的非椎体骨折风险。在上述所有的阿仑膦酸钠扩展试验中, 没有出现ONJ或AFF的病例。
2.2 唑来磷酸钠
在HORIZON-PFT延伸试验中,比较唑来膦酸6年组 (n=616) 与唑来膦酸3年组(n=617)发现:与基线股骨颈BMD值相比,持续用药组BMD基本保持不变(4.5%), 药物假期组略有下降(3.1%),但仍较治疗前水平高。药物假期组BTMs略有增加, 但低于基线值。在椎体骨折发生率方面,持续用药组优于药物假期组,但在非椎体骨折发生率方面2组并无差异[21,22]。随后,Black等[22]对HORIZON-PFT延伸试验进行了为期9年的第2次延伸,发现持续用药9年组和6年组髋部BMD、BTMs及骨折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异;相比之下, 9年组少量增加了严重和非严重心律不齐。因此,他们认为,对于股骨颈处BMD低(T值≤-2.5)的患者,经过3~5年的治疗后发生椎体骨折的风险仍最高。Cosman等[23]研究亦证实了上述结论。值得重视的是,唑来膦酸6年组和3年组均无AFF报告,6年组仅有1例ONJ记录[21]。9年组和6年组均无ONJ和AFF确诊[22]。
2.3 利塞膦酸钠
在利塞膦酸钠临床试验 (VERT-MN)中, 一组应用利塞膦酸钠治疗(5 mg/d,n=398),3年后停药1年, 对照组接受安慰剂治疗(n=361)。与对照组相比,利塞膦酸钠组股骨颈BMD明显增加 (2.32%),影像学上椎体骨折发生率下降46%。未增加非椎体骨折风险。BTMs比治疗前水平增加, 与对照组没有区别[24]。在VERT-MN的延伸试验中, 利塞膦酸钠治疗7年(n=31),对照组先使用安慰剂5年、 然后利塞膦酸钠2年(n=30),中止利塞膦酸钠治疗1年后, 2组股骨颈BMD均保持或轻度增加, 然而全髋和大转子BMD下降。2组骨吸收增加程度类似, 接近安慰剂组5年时水平。该研究表明利塞膦酸钠累积效果较小, 可能是因其骨亲和力较弱。该研究没有椎体骨折报告, 亦没有ONJ和AFF报告[25]。
因此,对于绝大部分患者来说,阿仑膦酸钠5年、唑来膦酸3年后停药不会明显增加骨折的风险。而那些高骨折风险的患者(如股骨颈T值≤-2.5且高龄)可能受益于继续治疗,应用唑来膦酸者可在治疗6年后酌情进入药物假期。对于应用利塞膦酸钠治疗的患者,应考虑更短的药物假期,因为停药超过1年可能导致高骨折风险发生[24,25]。
3 长期使用双膦酸盐治疗后哪些患者可进入“药物假期”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无明确共识。欧洲女性与男性更年期协会发布声明:对于使用阿仑膦酸盐、利塞膦酸盐或唑来膦酸治疗超过5年的患者,应考虑停用双膦酸盐。对伊班膦酸盐则没有任何建议。如果患者在治疗前或治疗期间未出现骨折且骨折风险较低,则可推荐“药物假期”。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建议使用利塞膦酸盐1~2年、阿仑膦酸盐3~5年、唑来膦酸3~6年[26]。美国骨质疏松防治委员会推荐:对已接受双膦酸盐初始治疗3~5年的患者进行综合评估,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停用[4]。Villa等[27]按照骨折风险高低对患者进行分层,提出如下建议:对于中低等骨折风险的患者 (BMD T值≥-2.5、无骨折危险因素、无脊柱或髋部骨折史且BTMs水平较低),接受3~5年双膦酸盐治疗后可进入药物假期,但停药期间需每1~3年进行评估,包括测定BMD、BTMs以及骨折风险的再评估等,而对于高骨折风险的患者 (BMD T值<-2.5、有骨折史、BTMs水平较高或正在接受大剂量激素治疗),至少需维持10年(口服)或者6年(注射)之后,经评估酌情进入药物假期。
4 何时再启动治疗
目前对于何时再启动治疗没有明确专家共识或指南推荐。 孔西建[9]指出,药物假期中每年应对患者的年龄、跌倒史、是否有新的骨折、可能危险因素、BMD和BTMs进行评估。如果BTMs(高于正常非更年期水平)增加,则可考虑恢复治疗,尽管停止阿仑膦酸盐治疗后1年的BTMs变化与骨折的风险无关[20]。如果出现任何新的骨折或BMD降低(股骨颈T值≤-2.5),可以恢复抗骨质疏松治疗[4]。
5 小结
双膦酸盐是临床一线抗骨质疏松症药物,疗效确切,但由于其长期使用可能存在的风险,药物假期的概念应运而生。笔者认为:对于年龄<70岁、股骨颈BMD T值≥-2.5、无骨折危险因素、之前无脊柱或髋部骨折史且BTMs水平较低的中低骨折风险患者, 连续应用阿仑膦酸钠治疗超过5年、唑来膦酸盐超过3年、利塞膦酸钠2~3年可考虑停药;对于高骨折风险的患者(如股骨颈T值≤-2.5且年龄≥70岁),应当坚持用药6~10年后酌情进入药物假期。我国尚无最新指南或专家共识对药物假期的时间长短提出建议说明,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患者的病史和骨折再发风险的高低制定个性化区间。国外相关研究表明2~3年是一个合理的停工期,有待进一步证实。在药物假期期间,应监测患者BMD、BTMs等指标,如有BMD明显降低 (T值<-2.5) 或新发骨折, 即应立刻重启治疗或换用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