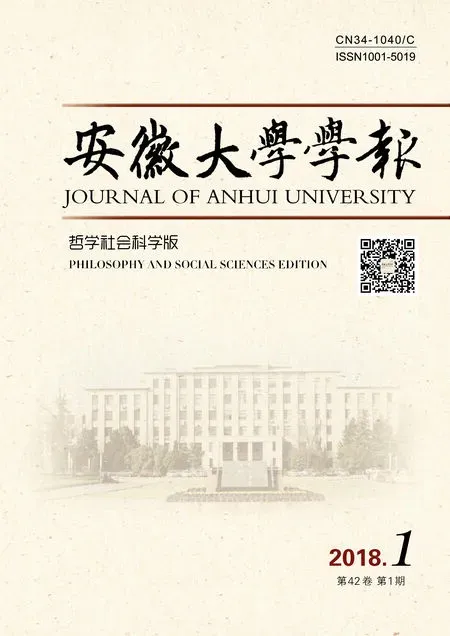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
王振忠
一
新安故郡,古歙新城,山明水秀,人杰地灵。
履黄山而登白岳,然(?)登画阁朱棂;游练水以玩秀溪,不少茂林修竹。
试看一村一落,咸居万户人烟;某里某村,慕千年宗族。
素称胜地,宿号名区,居是邦者,不亦乐乎?
奈无良田万顷,空余大厦千间;虽生居于故国,常作客于他邦。
别堂上高年父母,泪自涟涟;抛闺中弱质妻儿,心犹悒悒。
仆仆风尘,别故乡而竟去;依依杨柳,向异地以驰驱。
将见下渔滩,过箬岭,淼淼兮烟波,苍苍兮云影。
或四海以寄萍踪,或三次而投市井。
夕阳古道,谁怜帽影鞭丝;海角天涯,自叹桥霜店月。……
这篇《新安赋》,未见于此前的任何传世文献,写作年代不详,作者更不知姓甚名谁,但其文字却颇为雅致,对黄山白岳间风俗民情之刻画亦极其生动,从中可见:在传统时代,吃苦耐劳的徽州人,或沿着新安江的三百六十滩,或顺着先人在徽杭古道上铺砌的石板小路,前仆后继地外出务工经商,开行设铺。他们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顽强拼搏,创造出长江中下游各地“无徽不成镇”的奇迹……此类的文字描摹,可谓徽州研究之第一等的好材料。
类似于此的民间文献,我在近二十年来百余次的实地考察中曾收集到许许多多……
徽州文书是指在皖南旧徽州府一域发现、由徽州人手写的各类文献。从数量上看,徽州遗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献,其规模在迄今发现的各类地域文书中首屈一指。而从内容上看,除了狭义的契约文书之外,徽州民间文献还包含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或亦称“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案卷等。由于徽州“贾而好儒”的传统,因商业发达滋生出极为浓厚的契约意识,以及凡事必记、有闻必录的日常生活习惯,使得徽州文书的种类繁多,内容具体而微,此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他地域的现存文书所望尘莫及。从形式上看,徽州文书既有单张的散件,又有成本的簿册。而从其涉及的范围来看,徽州文书反映的地域范围极为广阔,这与明清时代徽商之无远弗届以及徽州文化极强的辐射能力密切相关。可以说,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特别是南中国的社会历史,徽州文书之重要性难以忽视。
迄今为止的徽州文书之收集、整理和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徽州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现,徽州文书已由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珍稀文献,一变而为明清史学工作者案头常备的一般史料。不过,就目前徽州文书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来看,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
其一,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公藏机构还是私人收藏家,都积累了相当多的徽州文书。而迄今为止出版的徽州文书,则以公藏机构的土地契约占绝大多数。虽然说“百年无废纸”,尚存天壤的所有故纸,都自有其相应的价值,但在汗牛充栋的田土买卖契约文书之外,反映其他纷繁社会生活的各类文献也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有时一册上好的稿本、抄本,就能解决一个较大的历史问题,而这可能是成千上万份制式化的土地契约(即使它很成规模,也都归属于一家一户)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不过,目前对徽州文书稿本、抄本的披露和出版仍极为有限。
其二,徽州文书的数量相当庞大,但因其分散于各类公藏机构以及私人收藏家手头,迄今得以披露者仍然只占冰山一角。许多公藏机构(特别是博物馆、档案馆)庋藏有不少珍稀文献,但囿于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学界开放的程度颇为有限。而私人收藏家中的不少人,或因其非专业研究者,或因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诸多珍稀文献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些,都造成了学术资源的闲置乃至浪费。
有鉴于此,笔者联合一批民间收藏家,并得到个别公藏机构的部分支持,决定出版《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希望化私为公,让祖先传下的故纸化身千百。根据最初的设计,本丛书在原则上不收录此前常见的土地契约,主要辑录徽州日记、商书(商业书和商人书)、书信尺牍、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杂录和启蒙读物等,所收文献皆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献的现存形态既有稿本、抄本,又包括具有徽州特色的刊本、富有学术价值的印刷品等,以及一些成规模的抄件*全书计30册,每册由提供文献者独立编辑及署名,分别撰写简单提要,文责自负。全书由王振忠主编,将于近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
本人的此一倡议,得到不少同好的积极回应。目前征集到的文献多达数百种,我们从中遴选了一部分,出版《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此一丛书受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基金申报过程中,曾得到唐力行教授、周振鹤教授的鼎力推荐,特此谨申谢忱!,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以下简要分类论述。
(一)商业史研究
徽商是明清时代的商界巨擘,历来备受关注。1947年,傅衣凌发表《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一文,多侧面论述了徽商之发展及其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开创了徽州研究的新天地。在海外,首先系统研究徽商的是日本学者藤井宏,他于1953年发表长文《新安商人的研究》。此后,徽商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叶显恩、张海鹏、王廷元、唐力行、王振忠、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冯剑辉以及日本的臼井佐知子等,都先后出版专著详加探讨。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从事徽商研究,受到学界愈来愈多的关注*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拙著《徽学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特别是在宏观描述已几近饱和的背景下,新史料之开掘和细致的深度探讨,显然是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途径。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收录的文献中,包含有多种珍稀的徽商史料。在徽商研究中,盐商(特别是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商)一向是相关研究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出现了多种全新的史料。例如,清代佚名抄录的《扬州徽商与各地往来书信》1册,收录有徽商书信180余封,内容主要是两淮盐商之间的鱼雁往还。《盐商汪氏汉、扬两地书信》誊稿1册,为清嘉庆年间坐镇汉口的徽州盐商汪某与其委派在扬州的执事之间的往返信札。在彼此的嘘寒问暖、互诉衷肠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两淮盐务的商业规范以及口岸之销盐状况,而且还能看到一些著名的盐商(如鲍有恒、鲍方陶、尉跻美、程俭德、王允涛、吴公和、萧怡茂等徽商西贾)之活动身影。《志徽在邗寄里家书底稿》一书,则是休宁蓝田人誊录的信底,反映了嘉庆十八年至二十四年(1813—1819年)扬州盐商与桑梓故里的通信。上述三种与扬州盐商相关的信函底稿,对于清代前期徽商与两淮盐政史的研究,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类似的资料,还有《淮北盐商程德中公文汇抄》1册。该书收录了徽州籍盐务总商程俭德属下的淮北盐商程德中盐店之公文汇抄,其时间跨度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迄至嘉庆初年,涉及的地域包括皖、豫二省的六安州、光州和光山县等地,其内容则收录了百余件原、被告的禀帖、答辩、甘结以及州县、盐院、巡抚和总督有关盐业经营的公文,并抄录了嘉庆皇帝的相关上谕。此书的价值在于:在18世纪,因复杂的自然及人文环境,淮北引岸长期是两淮盐务中的“疲岸”,但以往所见的史料,除了少量官方奏疏和个别碑刻中的只言片语偶有涉及之外,相关的史料较少。而《淮北盐商程德中公文汇抄》的内容极为细致、翔实,为研究盛清时代淮北盐务之实态,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新史料。此外,同治年间《淮盐总局按照花名、引数售盐付课总账》,记录了商家“豫隆祥”的淮盐销售及盐课状况,是清代两淮盐务的珍稀史料。对于此类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无疑会将相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清代,扬州的八大盐务总商家族之中,除了程氏之外,还有歙县的其他一些商人。《二房赀产清簿》抄本1册,收录了清咸丰八年(1858年)歙县盐商江仲馨的分赀产簿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房江繁禧的赀产清簿。江仲馨系歙县江村人,曾代理扬州总商领销和州引盐3776引达四十余载。为此,他在和州置下大批田地、房产。道、咸之际,因淮南盐政改革及随后的兵燹战乱,江氏盐商遭受到严重打击。此一文献,对于考察19世纪徽州盐商之盛衰递嬗极具史料价值*周晓光:《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赀产清簿〉剖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前述江村江氏是扬州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而歙县许村许氏也是类似的另一总商家族。《许村许氏诉讼文书抄本》1册,收录了乾隆、嘉庆年间的四份房地契抄件以及道光十年(1830年)的十余份诉讼文书。当事人许恒吉、许安吉皆为歙县许村人,他们分别在扬州东台县和安徽定远县北炉桥镇经商。抄本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歙县许村的房产诉讼,从中反映了中小盐商彼此之间的纠纷。《疏文誓章稿》抄本1册,收录了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歙县盐商“锡”与二弟“钟”(字伊黄)为财产纠纷而写下的相关文字。其中的一份信稿,详细开列出自康熙三十九年至康熙五十五年(1700—1716年)间安庆盐店的收支账目,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参见江巧珍、孙承平《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徽州姚继泽《尺牍(全)》抄本,主要誊录徽商的书信底稿,内容聚焦于清代道光中叶淮北盐务改革时期的票运、票贩及盐场状况。除盐业之外,少量信底亦涉及典当业。该书的主体部分是研究徽州盐商与道光年间淮北票盐改革的珍贵文献,颇为少见。上述各种文书,对于研究徽州盐商的社会生活、经营状况以及诉讼纠纷等,都提供了相当翔实的史料。
以往,我们对于盐商中的运商了解较多,但对于场商(垣商)则所知甚少。上述的多种文书,都是有关运商的珍稀文献。不过,在《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中,我们还是幸运地收录了三种反映场商活动的文书资料。其一为《盐业文契遗存》,内容是有关清康熙、乾隆、嘉庆等时代淮盐买卖和盐业方面的租约合同契纸。其二是《亭灶呈报清册留存》,内容主要是清嘉庆年间淮盐垣商张振隆等11家盐店各自属下的亭灶及灶户口数呈报之清册底稿(含禀帖1件)。其三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月的《盐业傢伙账》。这三种资料,都是乾嘉时代与歙人张振隆店号相关的文书,对于细致探讨徽州盐商在盐场之经营活动和两淮的生产关系等颇多助益,是相当罕见的珍稀文献。
在传统时代,盐商与酱商往往是二位一体,但有关徽州酱商的材料一向颇为少见,以至于迄今为止尚未有专门的学术论文加以探讨。《祁门吉春永记盐酱店文书存底》抄本1册,收录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吉春永”盐酱店的顶受约据、酱园租约和新立合同等,这对于研究太平天国战后盐酱店的经营,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除了盐商、酱商的经营史料之外,还有不少盐商宗族方面的文书。清乾隆《岑山渡程氏支谱》抄本6册,前五册分别标有“壹”“贰”“叁”“四”“五”,另有未标明册数的合订本一册,此合订本的前一部分为“程氏天下统宗源流宗谱”,后一部分标作“岑山渡派转迁于外略辑以备查考”(从中可见岑山渡程氏外迁各地的情形)。另一册《岑山合族置产簿》抄本,收录了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众议条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第五房管年邀仝族众并经收人诰茔言》和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祠产清单等。上述两份文书中的“岑山”即歙县岑山渡,此处位于新安江畔的水南乡,是清代扬州盐务总商程氏家族的桑梓故里。揆诸史实,岑山渡程氏是清初最早出现盐务总商的一个家族,国内现存的多种《岑山渡程氏支谱》皆为刊本,而此处收录的抄本则为目前所仅见。书中对于淮扬盐商的记载尤为详细,故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岑山合族置产簿》中收录的祠产清单和宗族管理条例等,可以与《岑山渡程氏支谱》以及前揭的《淮北盐商程德中公文汇抄》等资料比照而观,对于研究大徽州(旅外徽商活动的范围,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小徽州(徽州一府六县)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颇为翔实的新史料。
在传统时代,盐业、典当和木材是徽商最具特色的经营领域。在《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中,有关木材、典当的文献也多有收录。例如,雍正年间婺源木商俞氏的《长江放排札记》,内容包括途经湖口、芜湖、赣州等关的量排钱粮,以及婺源木材商人之诉状和放排承揽凭单,等等。《道光许惇大号典规文约簿册》抄本,为同治年间歙县岩寺夏官第许氏辑录,该书的内容即与“徽典”有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衢州府龙游县城内河西街余、程两家合开有惠和典。及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因资本不敷,该典产出顶于许用先名下,为此,书中收录有典规章程、典帖执照和出顶典契等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关的还有咸丰年间的《妆奁汇记》和同治年间的《古董汇记》,这些,对于探讨徽州典当业之运作以及徽州典商的家庭生活*与之相关的还有《祖考显考墓地营造始末暨费用账》1册,由同治年间岩寺夏官第许绍曾所抄,其内容包括记事和费用账两个部分,提及卜葬祖考、显考两地风水始末根由,详细记录了相地、买山业、营造墓穴、安葬、上坟、祭礼、祀例、进主及费用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研究徽州的丧葬习俗颇有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明代,“钻天龙游遍地徽州”之谚一度为世人耳熟能详。及至清代,即使是在龙游商帮的桑梓故里,徽商的活动仍然极为活跃。一些徽商往往是多种经营并举,上述歙县岩寺夏官第许氏,不仅在浙江龙游县从事典当业经营,而且还在当地广置田产,经营粮食生产,并开设“许春和号”酿酒作坊。关于这一点,《龙游许春和号酿酒登记簿》一书,就反映了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日酿造传统米酒的流水账,内容包括酿造的工序、方法、配方、成本核算和包装方式等。这些,不仅是探讨徽商酒业经营的珍贵史料,而且,对于徽州名酒“甲酒”之研究,亦提供了颇为稀见的史料。
明清时代,徽州是目前所知商书编纂最多的地区。作为商贾之乡,徽州的商书编纂蔚然成风,而商书的大批出现,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中收录了不少新的文献。例如,由郑紫琳抄录的《商贾便览》,推测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抄本,主要内容是逐日风暴日期、天时占验、各路地头所产米粮、各处粮食、商贾十则要言和士商十则要言。在传统文献学领域,以“商贾便览”为题的商书,最为著名的首推乾隆时代吴中孚所编的刊本,一向为中外经济史研究者所瞩目。而目前所见郑紫琳抄录的《商贾便览》,则是徽商根据个人经商的实际需要编辑而成,故而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清代姚继泽《尺牍》一书,虽然主体部分是尺牍体例和尺牍活套,但书中亦收录有“立身处事大略”,具体则包括“本业宜勤”“用度宜俭”“出门宜慎”“交友宜择”“口过宜防”“教子宜严”“大节宜审”“心田宜正”和“性气宜平”数则,是有关商业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方面的规训,属于明清商书中商人书的范畴。1905年抄录的《生意经》,记录了初学生意的“小官”进店之规矩,对于待客、习字、算盘、站柜台、说价钱、戥秤银两、收发货物和送客等都有详细的解说。佚名编纂的《商贾格言》,内容包括商贾格言十三条和商贾十则,并摘录了天下土产。类似于此的各类商书,以往颇有所见,可供进一步的相互比较研究。与此相近的资料,还见有施氏所编的《京业必读》抄本,其中除了“办货要知大概、识物务须小心”“八珍之名称”之外,亦缕述了各种货物的产地和等第。此外,民国年间歙县人刘福生曾在苏州的“丰泰银炉”做“学生”(学徒)。当时,他抄录有经商所需的相关知识,其中的“各路条叶饰金”一节,详细记录了上海、苏州、无锡、琴川(常熟)、常州、宁波、杭州、南京、扬州、镇江、松江、新仓、通州、宜兴、鸳湖(嘉兴)、海门、如皋、北京、天津、盛京、四川、陕西、广东、广西、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福建、河南、云南、贵州、江西、安徽、徐州、牛庄、清江、沙头、平望、昆山、平湖、青岛和湖州等地所设银楼的数量、字号名称及产品之成色。此一文献,无疑是近代商业史研究方面的珍贵史料。
明清以来,徽商在其从事的各行各业中,都根据实际经验编纂了相关的商人书和商业书。例如,在传统时代,桐油有着多方面的用途。“频年川广运桐油,篾篓重重载满舟,储入栈中招客买,分销漆作饰崇楼”*(清)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桐油栈”诗,见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此一诗歌,状摹了晚清时期四川和湖广桐油东下运销江南各地的盛况。而此次收录的《洪油要诀暨往来信函》,就具体反映了以湖南洪江为中心的桐油运销。该书是清光绪年间往来于两湖、江西等地的徽州休宁商人王松泉所抄录,书中的主要内容包括“论洪油要诀”“洪江售洪油章程”“从家十五里至长沙”“常德水陆路程”及往来信函等,既有商业书对于从业技巧的细节描述,又有反映实际操作的书信底稿,这使得我们可以将此商书放在具体的商业运作中加以分析。
在明清商书中,商人书和商业书的数量都相当不少。大致说来,商人书强调的是商人的道德修养和经商的行为规范,商业书则主要涉及技术层面的操作,反映的是商品类型、来源、技术标准和经营规矩等。当然,上述两类亦并非截然分开,有的稿本、抄本中,既有商人书的内容,又有商业书之描述。在商业书中,算术素来自成一体。早在明万历年间,程大位编纂的《算法统宗》就曾“风行寓内……海内握算持筹之士,莫不家藏一编,若业制举者之于四子书、五经义,翕然奉以为宗”*(明)程大位著,李培业校释:《算法纂要校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页。。可见,《算法统宗》一书对于商人而言,就像是四书五经之于读书人一样重要。明代以还,算法一脉不绝如缕,不仅有《算法统宗》的各种变异形式,而且,近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算法教材。前者如抄录于咸丰九年(1859年)的徽州《算法》抄本,主要内容除了“九九上法总论”“九九退法总论”等之外,另有“丈量田地歌诀”,与《算法统宗》卷3中的《丈量田地总歌》大同小异,反映了《算法统宗》对后世的影响。类似的算法资料,在徽州民间文献中所见颇多。此外,宣统元年(1909年)绩溪县的《植基学校教材》(印本1册),设计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百道算术应用题,其中有不少反映了徽州(特别是绩溪)商业方面的内容。此一新式教材,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算盘”的流风余韵。
在明清时代,征信录是一种公开财务收支、以昭信实的档案,其中的徽州征信录也包含了不少商业史方面的讯息。现存的“徽州征信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徽商在侨寓地的征信录,另一种则是在徽州本土形成的征信录。以徽商征信录为例,同一名目的征信录,因时代的不同有的多达数种乃至十数种,自成系列,前后可以相互比较。例如,上海的徽宁思恭堂是由徽州府和宁国府商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创置,《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在道光年间可能是一年一刻,后改三年一刻,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又改为一年一刻。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徽宁思恭堂征信录》计有十数种,而此次收入本丛书的两种,分别为同治七年(1868年)和宣统三年(1911年)的《徽宁思恭堂征信录》。管见所及,同治七年的第十七刻《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应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种;而宣统三年的《徽宁思恭堂征信录》,亦为迄今所仅见。此外,清宣统《婺源商务分会征信录》和民国《婺源商务会征信录》,分别将县内商号分为城厢、东乡、西乡、南乡和北乡五个部分,以营业状况将其列为特班、甲班、乙班、丙班和丁班征收公费,并将各项开支分门别类地造具清册。上述二册虽分别仅有寥寥十数页且流传未广,但对于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婺源县的商业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历史地理研究
近十数年来,徽州民间文献的大批发现,为历史地理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新史料的层出叠见,使得明清交通地理、村落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可望有诸多新的推进*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见拙著《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序,“六零学人文丛”,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以历史交通地理为例,早在199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由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 天下路程图引 客商一览醒迷》,其中的《天下水陆路程》和《天下路程图引》,都是徽人著作。此外,杨正泰另编著《明代驿站考(附: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1994年版,2006年修订再版)。1997年,陈学文亦利用他在日本收集到的相关文献,写成《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一书。除了上述代表性的作品之外,海内外学者还有不少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不过,以往此一领域的绝大部分成果,多是利用散落海内外(尤其是日本)的刊本。以商编路程为例,从史料来源上看,上述著作显然是参照各种原始路程图记编纂而成,然而,此前见诸著录、由徽商所编的“路程”原件,学界所知者还相当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广泛收集、整理民间文献中的徽州商编路程,并将此类路程放在具体的商业环境中加以考察,显然有助于推进明清交通、商业与社会地理的综合性研究。
此次出版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收录有多种商编路程:
(1)《长江路程图》稿本1册,道光年间休宁渠口佚名商人所编,内容包括“长江水运总图”“湖广湖南湘潭县由大江至镇江府水路程歌”以及自休宁县前往汉口镇、襄阳府等长江中下游各地的水陆路程等。
(2)《江湖绘图路程》稿本1册,同治年间休宁渠口佚名商人绘编,内容包括“士商规略”“士商拾要”“镇江盐船上楚水路歌”“湘潭至镇江路程歌”以及渠口村至九江、安庆、汉口等地的水陆路程。
(3)《广东路程》抄本1册,道光四年(1824年)黟县西乡郑圣扶抄,记录了徽州祁门县由江西进广东的水陆路程,分为“祁门县至景(德)镇二百八十里”“景镇至饶州府一百八十里”等,另附珠江潮水涨退时刻日程表、广州八景名录、广东省属一州十六县之名称等。
(4)《路程编歌》抄本1册,编者汪玉衡系清末休宁旅杭商人,全文计370多句,具体描述了自钱塘江—新安江溯流而上抵达屯溪的沿途所见。
上述《长江路程图》为彩图稿本,在商编路程中别具一格,为目前所仅见。除了成册的抄本之外,还有的是见诸文书抄本中的路程记录。如清乾隆年间歙县岩镇(今岩寺)《谢凤鸣家记事簿》中,就抄录了“徽州府至严州府水路程”“江口三十里至北新关”“杭州至苏州水路程”和“苏州府至扬州府水路程”等,与一般习见的明清商编路程之记载稍有区别。此外,还有一些单张的印刷品,这是以往较少发现的新资料。如清末印刷品《杭州至徽州旱路路程表》,其路程的终点为休宁的上溪口。其中,除了地名和里程的记载之外,还有简明的特别提示,如“起旱”“远”“右手走”“过桥”“远路崎岖上岭”“无店”“有巡检司”等。另外一张商编路程,则是从余杭县起旱,经昌化县入昱岭关、老竹岭、杞梓里、大佛(今大阜)、章祈(今瞻淇)、稠木岭到徽州府,过河西桥,经岩寺镇、万安街、休宁县和渔亭,最后到达祁门县及黟县*此件为孙承平收藏。。值得注意的是,该路程系印刷品,而且末尾有一段说明:“板在泳丰茶漆铺刊刻敬送。”这说明当时的商店(茶漆铺)也刊印此类简易的路程,并可能是随其他商品之购买而零星派送,供外出务工经商之人利用。此一例子反映出其时在徽州外出经商之人为数众多,以至于像休宁上溪口以及黟县的泳丰茶漆铺,都以本地为中心印刷相关的路程*刊本《摽船规戒》一书,是以歙县岑山渡为中心编纂、刊刻的商编路程。参见王振忠《新安江流域交通、商业与社会的综合性研究——以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为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研究》第3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商编路程对于徽商研究、交通地理以及地图史的研究,都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徽商研究为例,上述路程,反映了徽州人外出经商最为重要的几条商路,即徽商在长江流域、新安江流域以及赣江—大庾岭商路的活动轨迹。《长江路程图》和《江湖绘图路程》,是徽商在长江中下游从事盐业贸易的实物见证;《广东路程》与此前所知的诸多入粤路程一样,都与徽商“漂广东”、从事洋庄茶叶贸易有关*参见王振忠《従内陸山区到口岸都市——明清以来広州貿易中的徽商活動》,日本都市研究会编《年报都市史研究》,东京:山川出版社,2011年。;而徽杭之间的水陆路程,则与皖南及长江三角洲的沟通和交流息息相关,其中,尤其是新安江水道更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顺便应当提及的是,明清以来在商路上奔波的信客也相当值得探讨。所谓信客,是指民间从事书信传递、货物携带等业务的那些人。在徽州,有关信客的活动,以往所见的资料较少。孙承平制作的邮集《徽州民信局》,曾于1997年在全国集邮展览上荣获银奖。此次,他所提供的资料中就有不少有关信客的资料。个中,除了民信局实寄信封和汇款单据之外,引人瞩目的还有《歙休送信簿》和徽州信客的名片,极为罕见。从中可见,信客与徽商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些资料,使得我们对于徽州信客的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此类资料与过塘(载)行签订的运输合同——船票、合同单据等,对于进一步探究交通地理、邮政史和商业史,均有颇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除了交通地理之外,与村落研究相关的文献亦颇值得关注。如所周知,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大批市镇兴起,再加上县区的频繁分割,亦使得乡镇志的编纂呈现出颇为繁盛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共编纂乡镇志50余种,清代各地共编成乡镇志300余种。而在近400种明清乡镇志中,绝大多数反映的内容均集中在南方各省,尤其是在太湖流域、宁绍平原、闽南滨海平原、珠江三角洲和皖南徽州地区这五个区域,该五区的乡镇志占明清乡镇志总数的90%*褚赣生:《明清乡镇志发展的历史地理考察》,《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迄今所知的多种徽州村落、乡镇志,此前已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此外,我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了数种村落志或准村志的稿本、抄本。此次收入本丛书的计有三种:一是清康熙年间《上溪源志》抄本,二是嘉庆六年(1801年)《磻溪纪事》稿本,三是《绩溪乡土地理表说(续)》抄本(光绪年间汪子青撰)。《上溪源志》抄本辑录了自明代中叶迄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有关婺源县上溪源村落的文书资料,生动、翔实地反映了15至17世纪徽州基层的社会实态,是极为珍稀的孤本史料。磻溪村位于今歙县杞梓里镇,《磻溪纪事》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人物考》,下卷为《诗律》,某种程度上看,可以视作一种准村志的史料*与此相关的资料,除了下文的《詹[澹]斋集稿》外,还见有以下两种:一是嘉庆歙县下磻溪方庆的《澹斋文集》8卷,二是嘉庆年间方庆所辑的《下磻溪纪事集律诗四十八景》。方澹斋之名,亦时见于道咸年间的《会约序文集》稿本。。至于《绩溪乡土地理表说(续)》(内页作“绩溪全图表说”),其内容包括概论、山脉、水道、道路、要隘和县治以及各都情况之详细描述(位置、界域、广袤、乡村、交通、山岭、桥梁和圳堨),为我们探讨县以下的微观地理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
(三)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是近数十年来中国史研究领域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分支,相关研究的议题颇为广泛,此处先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为例。
在明清社会史研究中,民众信仰及相关习俗是颇为重要的课题。不过,囿于史料的限制,以往我们很难从普通民众的角度作细致的观察。所幸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许多从田野调查获得的新见文献,被纳入社会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这为以民间文献书写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在具有悠久商业传统和契约意识的徽州社会,具体而微的众多民间文献,在某种程度上看,其精密程度有时甚至不亚于现当代的社会调查资料,这使得我们可以从史料的角度“较近距离”地观察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侧面,观察一地社会经济、文化、民间信仰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勾勒出更为全面的日常生活图景。
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民间日用类书是相当重要的一类资料。例如,歙县南乡的《会约序文集》稿本1册,辑录了康熙至咸丰年间的议约、会约、文约及序文等各类民间文献,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清末歙县胡楚才抄录的《文约》《应酬文约有备》和《阴事写疏总款》等,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应酬,都详细列举了相关的文书活套,从中,我们可以颇为具体地了解民间日常的生活规范。例如,《文约》中的“做台议约”“做戏台批捐”“做戏批捐”“许戏文”和“写戏关书”等*胡楚才《应酬文约有备》中也有“写戏关书式”,对戏班演出的程式、报酬等,有颇为具体的规定。更为详细的资料,可见民国休宁南乡和化里璜川《三宝会戏清账》抄本,其中有1921年“揽戏关”以及筹措演戏的详细账目、迎神赛会过程和相关的神台匾联。,反映了民间戏剧演出之兴盛及与茶叶贸易的关系。而“邀十保启”(4份)和“具保状”(2份),则是明代以来在长江中下游各地普遍流行的“十保福”信俗之生动史料。其时,在徽州各地,若有人生病且医药未能奏效,病家就会延请道士做十保福,由十人出面,各出钱若干,向东岳求寿。“告阴状式”反映了民众因遭受冤屈而无处可诉时,则求助于冥界的神明。此外,“菩萨腹内札咐[付]”*胡楚才《应酬文约有备》中,亦见有“菩萨腹内札咐[付]式”。、“安葬坟墓地契”等,也印证了歙县民间菩萨开光、风水丧葬方面的惯例。而《阴事写疏总款》一书,收入了“求雨疏”“九华疏”“齐云疏”“观音疏”“三官疏”“诵经疏”“送火疏”“白虎疏”“开光犒猖疏”“蒙山疏”“善会许神疏”“追魂牒”“地狱牒”“安山疏”“血湖牒”和“礼七疏”等数十种疏文格式,反映了民间信仰及迎神赛会的诸多侧面。民国歙县大洲源日用类书抄本,也生动地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新安江上游大洲源沿岸村落管理、日常生活以及民众的应酬交往。此一抄本因其细致入微,为我们以文本为线索展开实地调查,从事村落社区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上述各种日用类书中,也有不少反映商人外出贸易的内容。如胡楚才《应酬文约有备》中的“合本生意合墨式”、“合同大意式”(2份)、“期票式”、“雇船票式”、“雇脚夫、轿夫、驼夫、车夫相同(票式)”、“租市房据”、“生财顶首契”、“合伙议据”、“抵押借券式”、“借票式”、“荐伙保单式”和“荐保学徒关约”等,都与旅外商业密切相关。
此外,与民间日用类书接近的资料还有各类的杂抄。清同治年间歙县南乡私塾先生方华安的《詹[澹]斋集稿》,分门别类地收入“略”“传”“行状”“疏”“引”“跋”“论”“序”“祭文”“记”“阄书”“帖”“联扁”和“约”,其中颇多反映歙南民间社会生活的生动史料。而《开检可观》稿本,则是晚清监生李邦福杂抄各类资料而成,书中记录了祁门西乡云村的会社、祭祀、扫墓、求雨、演戏和诉讼等方面的活动,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乡村管理与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中可见,在晚清、民国,徽州乡村社会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市场规制亦颇为成熟。与此同时,土客关系、主佃关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逐渐接纳棚民融入地方社会,一些佃仆也得以开豁为良,这些,都显示出徽州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弹性与包容。
在一些杂抄中,誊录的书信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如清光绪年间的歙县杂抄,主要部分就收录了书信底稿,其中颇多涉及旅京贸易、茶叶经营、齐云进香以及日常应酬等方面的内容。民国佚名无题徽州杂抄,除了誊录一些活套之外,还抄录了不少信底。特别是书中辑录的一份妻寄夫书,内容是因旅外徽商金屋藏娇,引发故土正妻之不满,后者软硬兼施,勒令他即刻返归故里……书信内容一波三折,此虽系游戏笔墨,却是对传统时代徽商家庭生活的一种提炼,在徽州民间抄本中亦并非孤例*参见王振忠《两地书:从敦煌到徽州》(上、下),载《读书》2007年第2期、第3期,“日出而作”专栏;《鱼雁留痕:传统时代的情感档案》,载拙著《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97页。。
书信不仅是研究旅外商人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亦颇具价值。歙县昌溪人吴炽甫(1847—1929),是清末民初徽州的著名茶商。他出生于徽商世家,初营砖茶,销往内蒙古等地,后逐步形成茶叶收购、加工、窨制、批发和销售的一条龙,其经营范围遍及皖、浙、赣、苏、闽、鄂、冀、辽、京、津诸省市。全盛时期的吴炽甫,在北京、汉口、扬州和福州等地都有产业和投资,是歙县南乡的巨富之家。近十数年来,有关吴炽甫的相关资料不断地从徽州流出,为私人收藏家以及当地的档案馆和个别大学机构所收藏。《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收入的往来信件多达二百余封,属其中最富学术价值的精品。信函的内容是吴炽甫亲人写给他的书信,大多作于吴炽甫最后30年的商业顶峰时期,从中可见其人的茶业经营状况,以及晚清歙南首富家族内部的管理。此类的资料,为我们探讨徽商的商业经营与社会生活实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特别是书中涉及徽州茶商在北方的贸易活动,为以往史料所少见。除了大商人之外,徽州还有更多的中小商人。例如,歙县岔口佚名抄录的《歙县深渡乾裕号信底录稿》,收录了1903—1913年的信底68封,主要内容是新安江流域各埠以及长江三角洲商人之间的鱼雁往还,其中除了家庭事务,还涉及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对徽州商界的影响等。歙县漳潭乡漳坑人吴义荫在汉口从商,留下的《延陵退思氏信底稿录(1923年)》和《延陵退思氏信底稿录(1943年)》,主要收录其人与亲戚朋友的往来信件100余封,从中可以颇为细致地分析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歙县当地的社会生活。信中除了记录徽人外出,上海、汉口等地的商业行情、物价涨跌之外,还提及桑梓故里长辈祝寿及女子缠足、教育等方面的状况。其中较为特别的是民国时期的妇女生活,关于这一点,吴义荫在给妻子汪氏的信中曾提及:“春花缠足一事,予意雅不欲为,盖一包裹,将来皮肉必致受苦,予为悯之,是否必行,仍请吾卿裁夺。惟开年入学,是不能游移者也。”其后的另一信还指出:“丽云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读完时,可再读《最新国文教科书》。”而在《禀父》信中,吴义荫亦重申:“丽云孙女《千》《三》《百》读完时,男意欲其读《女子国文教科书》,里中函已述及,既买《女儿经》,待其读完篇,再读《教科书》可也。”其后,妻子汪氏在其来信中,也表示将遵从这样的意见。此类的书信讨论,都反映了徽商对于女子教育的重视。
有些书信,还反映了一些典型人物的独特心态。例如,《节妇汪宝瑜往来书信》收录了清末民初歙县西溪人汪宝瑜(1897—1943)与亲人的往来通信,从中可以从诸多侧面考察新安理学影响下徽州妇女的社会生活。此一书信散件,亦涉及扬州等地的盐业经营,颇具史料价值。再如,《歙县瀹潭士绅方子韬往来书信》400多封,包括方子韬与同族著名商绅方晓之和徽州名流汪己文、江粹青等的来往通信。这批书信,为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士绅与徽州社会的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民国婺源黄氏之《信》,为旅外务工者与家乡亲人的来往信函。抄本除了迎神祈雨等乡族琐事之外,还提及外埠布匹、粮食、茶叶之物价涨落等商业讯息,特别是江西乐平的粮食经营、上海的红茶行情等,尤为详细。歙县少雁方记《信稿》,收录商业书信底稿,其书写者来自歙县南乡的磻溪、鸿飞、洪琴、阳川(三羊坑,即今三阳坑)一带,务工经商的中心主要是在江南的娄县和木渎。此外,与上海、杭州、临安、湖州、南浔、宁波、苏州和营口等地亦有往来。各信涉及的商业贸易主要是茶叶、烟和茧等,尤以红茶居多,生动地反映了外出务工者的社会生活。徽州佚名无题尺牍1册,书中既有活套,又有对少量书信原件的誊录。诸信内容所涉地域较广,但其部分当事人应主要围绕着浙东绍兴一带活动。另外,书中涉及的行当相当不少,但以典当和盐业居多,尤其是典当业,有多封书信与之相关。歙县尺牍活套,当系活跃于兰溪、杭州一线的歙县徽商所抄录。光绪绩溪上川胡氏《信实通商》,主要收录在外务工经商者的来往书信底稿,涉及的商埠有芜湖、汉口、上海、九江、金陵和阜阳等地。特别是书中有不少绩溪人从事徽馆业(徽面馆、徽菜馆)以及相关的招股、合股信函,在目前所见的徽州信底中较为罕见。此外,有些书信还涉及海内外的商业交流。如民国曹楚芝《信笺》,为1928年前后的活套和信底,其中抄录了某人的世界游历旅程及相关见闻,涉及国内商号与欧洲、美洲的国际贸易。
在社会史研究中,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各类日记更是不可或缺。同治年间的《迪祥里胡氏谱局韵枫氏日记》稿本,撰著人为休宁县周村石田迪祥里生员胡光瑍,该书详细记述了谱局四年中外联、筹资、编撰、印谱、接谱和祭仪等活动经历。特别是其后的《胡光瑍年纪》,逐年追述了胡氏的生平往事,内容翔实、生动,从中可见太平天国时期徽商在本土以及侨寓地汉口的经历,对于考察宗族社会亦极具史料价值。《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暨粤难避乱实迹附叙生平碎事》稿本,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歙县毕体仁所作。该书备述道光以来薛坑口茶行屋业始末根由,其中涉及家世、生平、生计、茶市、乡俗以及民事纠纷等,是一册极为珍贵的文书。乡村教师的《江氏日记》稿本,作于民国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1932—1933年),内容除了介绍作者任教的日常生活外,还涉及不少歙县当地的时事,如壬申七月二十九日记提及:“稠木岭数十家,十有七八家养珠兰。”珠兰花是窨制花茶的重要原料之一,此一史料颇为珍贵。根据方志的记载,从民国初年开始,歙县就窨制珠兰花茶,天津、山东和通州等北方茶商纷至沓来,收购茶叶。该条日记,直观地反映了稠木岭附近培养珠兰的实态。同月三十日记族人洪珠由郡城返里,诉及其人“因讼事已用去二百余洋,胜负尚未可卜”。此后数日,皆记此一讼事,涉及打官司中的诸多细节。另外,书中还提及歙南大阜、北岸借接李王菩萨聚众赌博等,反映了徽州民间纷繁多样的社会生活。
此外,一些因特别兴作留下的相关文献,亦颇值得关注。例如,《新安吴氏大宗祠锡类堂肇建记》,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吴氏休宁临溪支裔汇编,记录了肇建新安吴氏大宗祠“锡类堂”以及相关的祠事条规。除了修建祠堂,清明会也是宗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余氏三门宗祠清明会簿》一书,由民国时期徽州婺源县余氏敦叙堂族人余胡荣(字得振)抄录,该书根据祠约、账目及清明祠祀活动实录和财产实物登记等资料集录而成。除了宗祠兴建之外,地方事务还涉及基层社会的诸多方面。例如,历口位于祁门县西乡,地属交通要道。当地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起建有石桥(原名集福桥,后改名利济桥),因迭经洪灾,屡建屡圮。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再次因蛟波肆虐而冲塌无存。光绪五年(1879年)春,同人挨村劝捐,募得洋银18800余圆,鸠工再建。关于利济桥,常见的史料主要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重建利济桥征信录》。此次,吴敏新提供的相关资料计有两种:一是《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手记》稿本1册,作者系祁门县闪里人(生于1830年),是位具有生员身份的商人。光绪五年(1879年)历口重建利济桥,他兼任桥局局董。《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手记》一书,保存有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8—1882年)的手记,记录了桥局公事、家庭琐事以及乡间要闻等,从诸多侧面反映出当地农村社会的生活面貌、风俗民情。此外,与之相关的还有《重建历口利济桥众善捐输芳名册》刊本1册,内容包括《重建祁西历口利济桥启》《劝捐重建历口利济桥启》《凡例》和《众善芳名捐资排序》等,对于研究光绪年间历口利济桥之兴修以及当地的人名、商号等,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民间信仰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明清以来,徽商遍布于全国各地,其中的不少人在经商致富之余,关心桑梓,力行慈善。婺源虹关的镜心堂,便是当地极为著名的一个乩坛。由婺源虹关镜心堂刊行的《镜心甲子宝诰》,系由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出版,该书是以扶鸾形式写成的“新型善书”。除了《镜心甲子宝诰》之外,与虹关镜心堂相关的文献还有《闺门宝训》《徽州婺北镜心堂重修浙岭征信录》和《济祖临坛诗集》等。此外,吴敏提供的《镜心坛扶鸾乩语日录》稿本1册,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至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之间的扶鸾记录,其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太平天国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此一文献,对于研究徽州民间的慈善组织,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除了扶乩之外,其他的民间信仰活动亦颇值得关注。前述《会约序文集》中,有专门的“神会序”和“祀会序”,收录了“地藏王佛会序”“观音大士会序”“新邀观音会序”“上帝神会序”“敬奉三官神会序”“重订上帝神会序”“新立上帝会序”“观音三官上帝诸神会谱总序”“准提神会序”“礼地藏小引”“张仙神会序”“新立观音神会簿序”“皇富社会重雕神牌序”“清平东社会序”“和兴社会谱序”“丰和社会序”“仁义大社会序”“义兴社会序”“新宁小社会序”“新宁大社会序”“仁义小社会序”“重兴新宁小社会序”“重兴新宁大社会序”“文昌帝君会序”“关圣帝君会序”“汪公神会谱序”“汪公神会序”“正月十八朝汪公及关公、九公、十王、玄坛、土地、社稷诸神会序”“八相公神会谱序”“九相公神会谱序”“九公贺衣神会谱序”“正月十三日九公灯会序”“正月十四日及八月十五日灯会、中秋九公会序”“正月十五日九公灯会序”“土地会序”“玄坛会重立序”“正月十六朝九公灯会序”“正月十七朝中立九公灯会序”“虎坝庙玄坛老神会序”“虎坝庙玄坛新神会序”“洽河社庙玄坛神会序”“虎坝庙重订玄坛新神会序”“睢阳公神会谱序”“灵山会序”“春福会谱序”“聚星会序”“三元会序”“蒙山会序”“度孤会簿序”“盂兰盆支序”和“赈孤会序”等,涉及徽州民间大大小小的神明祭祀。其中的“灵山会序”曰:
我徽僻处万山,山深多疫,疫盛于夏,若有物凭焉,禳之则释,诚灾患之大者。御之、捍之无术,里人忧之,爰采方士言,每岁于春夏交,设龙舟送之,放乎中流,而位神于上,以主厥事,行之辄验。由是城隅内外,互相角胜,各奉所祀之神,饰以冠裳,坐以虎辇,导以旗鼓,四月八日,登诸人之堂,呵而走焉,如周方相逐疫,礼虽近于戏,亦犹行古之道也。
类似于此送龙舟驱瘟的仪式,在徽州一府六县皆相当盛行。道光年间倪伟人《新安竹枝词》有:“梅城五月出神船,十二船神相比肩,小拍齐歌啰嗊曲,大家结得喜欢缘。”“梅城”亦即祁门县城之别称,至于“神船”的做法,以前所见都只有简单的只言片语。而《合邑船福会规则》稿本1册,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汪、王、吴三户同订,记录了当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初五日祁门县城的船福会事,对于迎神赛会时的各类开支、所办器物以及工食脚力等,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为我们细致了解祁门的神船福会,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史料。
除了日常生活史之外,徽州文献还展示了极为多样的社会生活内涵。例如,近年来社会史的发展日新月异,出现了不少新的分支,在这方面,第一手史料的支撑必不可少。《王仲奇先生医案》抄本1册,由郑村分院唐梦芝于1957年5月抄誊,内题“缑山仙馆医案”,其作者王仲奇(1881—1943)系歙县人,为现代著名的新安医家。此抄本汇集了王氏于民国年间在沪行医时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来自歙县、上海以及毗邻省、市、县(如苏州、南通、宁波、溧阳、平湖、嘉兴、松江和兰溪等地)128位病家的医案。与此相关的资料还有民国《歙县中医公会会员录(附休宁籍)》,系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歙县中医公会汇编,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科、喉科、眼科和痳痘科等,总共170人。末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休宁县中医师公会会员册”油印一纸,录有医师名单39人。此类文献,对于时下方兴未艾的医疗社会史之研究或有助益。
(四)赋役田土史料与地方社会研究
根据最初的设想,《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不收录此前常见的田土买卖契约。不过,该丛书仍汇集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相关文献。
清僧玉山《佛堂庵香灯田地字号谱据》抄本1册,记录了嘉庆三年(1798年)前后及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佛堂庵户官则完纳钱粮并南米”的详细清单。对金兰、仁义二社,地藏神会与佛堂庵的相互关系,敬神设醮之规例,会友及庵僧各自所占的份额,寺庙传承之源流脉络,每年正月元旦出行拜贺新禧的顺序路线,以及佛堂庵户头名下的关帝会、关公会等完纳钱粮的惯例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张韩俊的《崇仁庄田图》和《崇本堂浮南各处条段田图》二种,是有关婺源甲道张氏宗族的相关文书。该家族于光绪甲午(1894年)续修宗谱,遂将所余款项,在江西浮南大路埕等处购置庄屋,置有崇本、崇仁两庄,其田共计百十亩。由于田亩分布比较零散,收租不便,故而于1908年开始一一临田摹绘、说明。由于徽州人稠地狭,粮食供应不足,特别是婺源和祁门等县,多仰赖于江西的粮食输入,在此背景下,也有一些徽州人在江西各地购置田产,从事粮食的生产和运销。二书对于徽人在江西求田问舍的经营与生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地方社会。例如,晚清民初休宁南乡和化里璜川《本甲经办会议十排清账》*与此相关的还有民国休宁南乡和化里璜川《三宝会戏清账》,系当地历次举行“三宝慈尊”迎神赛会的清账誊正,反映了地方社会的运作。,为休宁二十八都十图和化里璜川陈吉诜所订立。该书誊录了同治九年(1870年)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本甲9次轮值排年会议经理的收支清账,相当细致、生动。光绪五年(1879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反映了清代徽州山区的保甲编制、族际关系、人口家庭和户籍职业等诸多侧面,据此,我们可以洞悉村落社会纷繁复杂的生活实态,对于宗族社会背景下徽州佃仆、棚民的社会生活等,亦有了诸多新的认识。迄今为止,类似的文献所见极少,相关的研究也颇为有限。对于此类珍稀文献的解读,可以大大推进县以下地方组织、村落社区的探讨,对于人口史研究之深入亦不无助益。
(五)法制史研究
自宋代以来,徽州就以“健讼”著称于世。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曾指出:“(歙州)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61,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3页。是文作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特别是明代以来,诉讼案卷的留存极为丰富,仅笔者收集到的诉讼案卷即有数百册之多,这是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目前收入《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的抄本计有数种,其中有的是作为诉讼教科书的抄本。如《歙县南乡讼案诉状集》抄本1册,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歙人彩淀抄录,内容包括清代前期歙南一带的各类诉状46件,反映了民间社会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其中有不少内容,对于徽州佃仆制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此外,绝大多数抄本皆是具体的诉讼案卷。例如,《詹氏瑞环堂族人互争讼案》抄本1册,为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1776年、1777年)詹嘉士所抄,主要内容是有关宗族内部的纠纷。此一资料是婺源庆源詹氏宗族的相关文书,对于著名的《畏斋日记》之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相关史料。佚名所抄《淳安县截阻运徽米船诉讼案卷附嘉庆年旧案》抄本1冊,收录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年(1899年)淳安县阻米讼案的公私原始文件。这些资料,对于探讨新安江流域的粮食供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贵溪胡氏积善堂祠前地诉讼案卷》,是祁门南乡十二都贵溪胡氏积善堂的公匣存底,汇集了民国七年(1918年)7月17日至民国十年(1921年)12月24日的相关诉讼文书,其中还提到村董胡元龙(红茶创始人之一)的居间调解,颇具史料价值。
除了在徽州本土的这些诉讼案卷之外,还有一些是旅外徽商与土著的冲突记录。如《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抄本1册,系光绪年间佚名抄录。这是有关黟县商人控告安庆府潜山县当地七社扁担会抬价强挑的诉讼案卷,收录了相关的知单、议约、呈词、禀帖和布告等,反映了旅外徽商利用官府的权威,殚精竭虑地确立市场规则的努力。
上述诉讼案卷,对于诉讼各方的角色、诉讼过程中的各类开支,多有颇为清晰的记录。此类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可以在诸多侧面推动明清以来法制史研究的拓展。
(六)其他
藉由《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刊布的徽州文献,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研究价值。
以传统文化与遗产保护为例,《休宁县黄村荫余堂黄子植接收的信札》就有颇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该批信札的主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先后在江西饶州和兴典、乐平县永和布号谋生。书信计170封,反映的时间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涉及在湖北武昌、上海、江西景德镇、江苏邵伯和窑湾等地典当、纱厂的徽州人与休宁桑梓故里之信函往来。1997年,休宁黄村荫余堂被整体拆迁至美国马萨诸塞州赛伦市(Salem)碧波地·益石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此一异地重建的荫余堂,成了北美学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该批信函也更成为引人注目的一批珍稀文献,这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资料涉及近代名人的研究。如清末民国的韬庐文献资料,为著名学者汪宗沂的家信等。汪宗沂(1837—1906)字仲伊、咏村,号韬庐,素有“江南大儒”之称,黄宾虹、许承尧等均出其门下。此次披露的书信,有助于我们了解皖派汉学传人汪宗沂之生平经历、为人及其家教等,为研究徽州的文化世家提供了极好的个案资料。汪宗沂为王茂荫之婿,在这批书信中,就有他写给王茂荫的信函,其中提及曾国藩及其幕僚程尚斋(桓生,两淮盐运使)等人的相关事迹。
汪宗沂的弟子许承尧(1874—1946),字际唐(霁唐),号疑庵,歙县唐模人(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是现代著名的方志学家、诗人、书法家和收藏家。此次收录的文献中,就有与之相关的《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该书系家印本,为国民党将领唐式遵私刊。抗战期间,唐式遵率部驻扎在歙县唐模,他曾就收集到的一些书画精品礼请许承尧题跋,后又结集印出。该书前有许承尧短序一篇,介绍了此书编辑、印制之由来。从中可见抗战期间徽州书画流传的一些侧面,间及少量敦煌文书之解题,对于了解许承尧的书画收藏见解颇有助益。另外,1933年3月24日至12月15日的《许承尧日记》,内容相当翔实。例如,当年3月29日到5月6日,许承尧在上海一个多月,其间,与张大千、张善子、李拔可、陈柱尊等文化名人以及徽州同乡颇多往来。此外,《许承尧日记》还提及徽州当地的书画收藏状况,这对于我们了解其时的书画价格及其传承、许承尧之书画交易等,都提供了新的史料。在《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中,还收录了民国年间家刊的《潜德录》,所存极少,为许承尧已故亲人之传记资料,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许氏的家世背景。
汪宗沂的另一弟子黄宾虹,为歙县潭渡人,现代著名画家。此次收录的文献就有黄朴存(即黄宾虹)户籍所在地的《保安善会籍帐》,是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946—1948年)歙西潭渡村保安善会经理数年“打平安醮”活动的收支清账,如实反映了当地住户人口及民生状况,是研究画家黄宾虹及其故里民俗的第一手资料。
除了上述数种资料外,《祭文附祭草》是清末民初绩溪县旺川村“自在轩主人”曹诚瑾所辑,该书共辑录散佚哀吊与祭祀文稿40篇,其中所录,有一些涉及绩溪名人胡祥木(近仁)和胡适之父胡传的文献*与此相关的资料还有咸丰绩溪墨庄主人辑《旺川节烈文集》。。
在《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中,还收录了一批通讯录,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徽州府学休宁籍《(21年岁试)同登录》、民国五年(1916年)《旅汉安徽同乡会第一期调查同乡录》、民国十五年(1926年)休宁万安《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职员学生通讯录》、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休宁隆阜《安徽省立徽州女子初级中学校友录》、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休宁万安《安徽学院皖南分院员生通讯录》、民国休宁万安《省立二师校刊登载历届职员学生通讯录》等,这些通讯录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徽宁旅沪同乡会章程》等,除了较为系统地展示了徽人在本土与外埠生活、经营状况之外,也有不少反映了一些徽州名人的活动轨迹。
除了历史名人研究之外,有的文献也从一些独特的角度反映了大的社会历史变动。抄本《粤逆匪谋叛原由等》,抄录的内容皆与太平天国史事相关。其中的《新安纪事略》和《节略新安难民词》,反映了咸丰兵燹对徽州的破坏,以及民众惨遭劫难的状况。《记事珠》为日记稿本,内容是咸丰庚申和辛酉年间(1860—1861年)的日记。日记作者程秉钊(1838—1893),自号“臧拜轩主人”,是出自绩溪县的典当商子弟,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了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并成为著名的学者。《记事珠》记录了太平天国战前徽商子弟在杭州诗酒陶情、琴书养志的悠闲生活,以及咸同兵燹期间杭城民众流离于干戈之间的惨状。这些,都为研究侨寓徽商及东南地区的社会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民国时期的一批苏州典商书信抄件,是1931年至1932年间旅居苏州的徽州典商与歙县亲朋好友之来往信函底稿。写信者为歙县南乡人,各信中除了记录诞育、修屋、租契手续、寿庆贺礼、齐云进香、水灾等乡邦琐事之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外埠与徽州的货物流通,苏州、杭州、上海一带的商业经营状况、物价涨落等。特别是不少信函涉及“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上海民众流离失所的惨状,以及长江三角洲各地在战争阴霾下紧张的气氛和对商业的负面影响等,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亦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此外,颇值得一提的还有民国年间屯溪的《青帮海底》,该书是民间会道门方面的史料,可能与徽人大批外出颇有关系。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目前已发现有数种,值得进一步关注。
三
近三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不少民间文献,其中,徽州文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历史学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细节,理清原本面貌模糊的问题,细致地展现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实态。
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书而言,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体系,而且,各类文书又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因此,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下手的许多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明清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此前,笔者曾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徽州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现,称为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亦即除了文书数量的增加之外,还将对狭义的文书(契约)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文献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参见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此一“再发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其他区域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中,清水江文书的再度大规模发掘,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上述这批资料,大多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民间收藏家经精心挑选而得到的珍稀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近年来,在民间文书收集与研究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动辄以数十万件土地契约收藏引以自傲的机构不只一二家。不过,土地契约在皖南民间随处可见,最便于收集且易成规模,但这并不是徽州文书的全部。总体上看,汗牛充栋、制式化的土地契约,就其内容的丰富性而言,远不足以与这些文书抄本、稿本相提并论。在徽州,各类史料相互印证,有很好的“史料环境”。近年来不少人反复强调的所谓归户性,并不是判定具体文书价值高低之唯一标准。在目前,我们利用徽州文书从事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一些高质量的关键性史料。另外,就史料的收集情况来看,由于收藏市场的升温,明清史料之大规模发现,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不加紧收集、整理和刊布,许多珍贵的文书将会很快散佚。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花多大的力气去收集,应当都不过分。而整理和出版此类的珍稀文献,对于学术研究之推进作用不言而喻。
最后还应当指出,除了私人收藏家之外,全国不少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乃至近十数年来闻风而起的一些科研机构,也或多或少地庋藏有一些重要的徽州文献。在这里,也衷心希望公藏机构能以博大的胸襟,为学界开放各类珍稀文献,以共同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