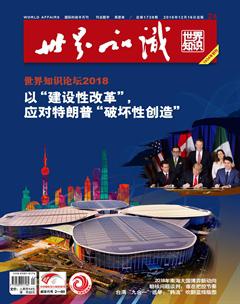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现状、导向和成因
袁鹏
美国的内外环境事实上也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浩浩汤汤,是大势所趋,受到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普遍支持,而美国作为老牌霸权国却害怕这种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西方世界的整体性低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美国虽仍是“一超”,却再难“独霸”,这也是奥巴马、特朗普两任总统都寻求战略收缩的根本原因所在。“特朗普们”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不那么情愿承担领导责任了,转而强调所谓“美国优先”。从国际秩序角度看,二战后确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新旧秩序转换对霸权国的挑战比对新兴大国还要大,美国是首当其冲的。从国际安全角度看,威胁的多元化成为当今世界的新现实,美国拼命想聚焦应对来自中俄等传统大国的挑战,却无法摆脱形形色色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威胁。
这三大变化全方位冲击着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意识到,美国对这样一个世界继续无休止无节制地投入下去将掉入无底洞,所以强调“美国优先”,不太想管外面的事,这反映了美国很多人的心声。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9日在哈德逊学院发表的针对中国的演讲,既体现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面对中国崛起的反制,其中充满无端的指责、偏执的傲慢和和无知的狂妄,同时也反映出美国的幾分无奈,更像是一声叹息。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的大变局带给美国莫名的焦虑感和无力感。最近特朗普、彭斯等人在谈及中国时总要求中国“尊重美国”,反复强调说美中要“相互尊重”,殊不知这正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对美国的基本诉求。美国似乎已经意识到,它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美国了,中国也不是过去那个中国了。所以我们在观察美国咄咄逼人的一面时,也要看到其背后的恐慌情绪,看到其色厉内荏的一面。
美国国内也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独立以来,美国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赢得独立战争、颁布宪法、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为标志,美国对内“韬光养晦”、聚焦国土拓展和经济发展,对外奉行孤立主义和有限参与国际事务信条,实现了初步的崛起。
第二个阶段从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从国家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型,成功捍卫了国家统一,形成东西南北贯通的交通网和统一市场,并且经济总量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开始满怀信心地登上国际舞台中央。
第三个阶段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冷战,这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走向完善、定型和成熟的时期,美国实现了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实现了从经济实力全球第一到综合国力全面增强的转型,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并最终在冷战的大比拼中笑到了最后。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发展进入第四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地位从“两极”到“一超”,美国的国家体制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理论上本应再实现一次体制性转型以适应新变局。然而,转型没能展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信心爆棚,没有自我变革的紧迫感。小布什时期因9·11事件突发,忙于反恐无暇他顾。其实那个时候美国人已经深刻意识到不转型不行了,不改革美国可能就不是美国了,这才使得“黑马”奥巴马有机会上台执政。奥巴马以“多伙伴世界”的观念迎接多极化,以注重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迎接变化了的地球,改革路径本是顺应世界潮流,无奈他政治根基浅、动员力有限,加上国内政治极化现象严重,各项改革都不彻底,美国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更加严重。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时代,特朗普才得以上台。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曾说:“特朗普总统想的不是未来四年,也不是四十年,而是四百年!”这话似乎不全是玩笑话。
特朗普真能创造影响延及百年的变革吗?恐怕不能。因为尽管特朗普个人比较强势,有魄力,懂营商,施政强调美国优先、实力至上、经济优先、结果导向、价值回归,还夹杂着从总统到家人再到核心团队成员的强烈个人偏好,决策相当高效,现在又开始抓执行力,但却没有做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外政策调整,而且美国国内政治日益分化。所以,目前的美国,对外没有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这“五化”,而是用各种办法抵触它们,走回到挑起大国竞争的老路上去;对内没有系统把握贫富矛盾、族裔矛盾、代际矛盾、地域矛盾、性别矛盾这“五大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复合性、结构性难题。特朗普处理问题的方式特别简单化,他的改革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因而成不了百年一遇的理性、伟大领导人。
再进一步讲,特朗普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但路径是错误的——“美国优先”。当代美国之所以一度伟大,就在于它既服务自己也服务世界,现在美国搞“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只顾自己不顾世界了,实际上是过于现实主义了,再这么下去就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至上和危险的民粹主义了,很难有好下场。而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之所以短期内看起来成功,是因为他依托着仍然强大的美国国力。换言之,他是在以消耗美国的国力、消费美国的影响力来达致自己并不正确的目的,长期看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将最终加速美国的衰落。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似乎可以概括为:以“让美国重新伟大”为目标,以“美国优先”为路径,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针,以实力为后盾、高压为手段、经贸为重点、军事为保障,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军事—经济“轮辐体系”。依然重视同盟关系,但强调投入收益,同时不因军事同盟弱化经济打压。依然重视伊朗和朝鲜的“核导威胁”,但更倾向于“极限施压”,重威逼轻利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强化地缘对手中俄的威胁性,淡化伊斯兰极端主义等恐怖威胁,融合“里根主义”和“尼克松主义”,既重实力霸权,又重谋略攻防。依然视“亚太”为地缘战略重点,将其扩展为“印太”,既利于将防御空间扩大为自己赢得安全距离,又可以拉拢日澳印对中国进行战略挤压。将经贸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采取双边谈判各个击破的策略,辅以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压政策,寻求利益最大化,同时谋求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