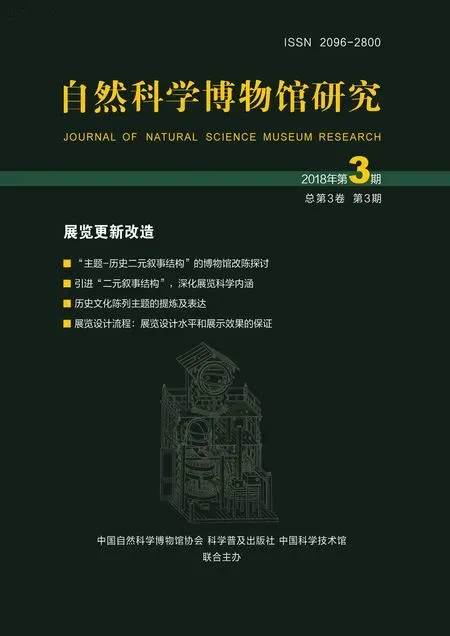德日进与北疆博物院
崔冠瑜
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5.1-1955.4.10),中文名德日进,是享誉国际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也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他在中国工作多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德日进的哲学思想也对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从法国奥弗涅到中国天津的命运之旅
德日进出生在法国中部奥弗涅的克莱蒙费朗市(见图1)。奥弗涅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出过许多像赫伯特和帕斯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德日进是家中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四,他的母亲是伏尔泰妹妹的曾孙女,父亲是当地农场主兼博物学爱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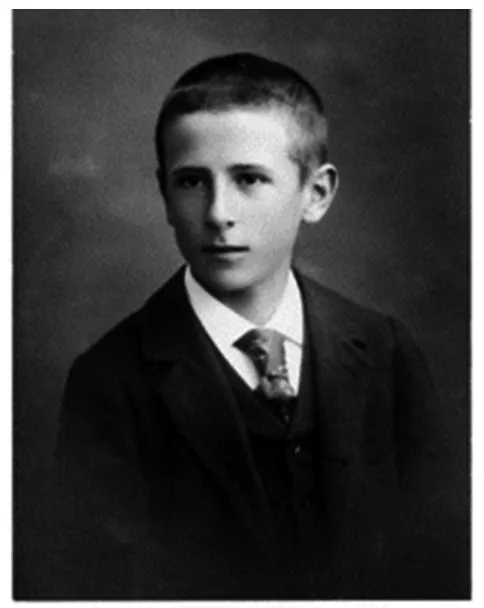
图1 12岁的德日进
德日进自孩提时代就醉心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德日进12岁进入由耶稣会经营的蒙格雷圣母学院学习,并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和数学学士学位。1899年加入耶稣会成为修士。1902年德日进决定到普罗旺斯省艾克斯市耶稣会初修院学习哲学史,希望通过哲学研究的学习,使他能够继续探索科学奥秘,并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1905年德日进被委派到埃及开罗圣家中学担任化学和物理实习教师,1908年又到英国进修四年神学,1911年晋铎为神父。1912年,德日进进入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在这里他遇到了法国人类起源学说和考古学权威玛瑟兰·布勒(Marcellin Boule)教授,受他的影响,德日进开始对古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德日进的科学事业,他被迫停止考古研究,应召入伍,成为了一名担架兵(见图2)。战后,戴着军功章、年近40岁的德日进重新回到巴黎,自此开始致力于他所钟爱的古生物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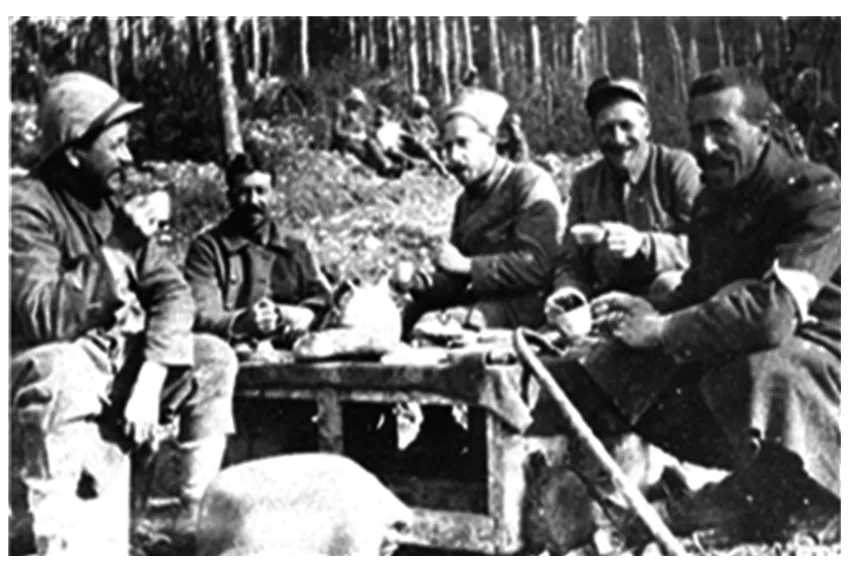
图2 德日进(右1)在凡尔登的战壕里
1922年德日进以题为《法国始新世早期的哺乳动物及其沉积层》的论文完成了他的地质学答辩,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地质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在巴黎天主教学院任职,教授地质学。此时的德日进是耶稣会士,博学多识,前程一片光明。但他的一篇关于原罪的论文,质疑了圣经叙事的史实性,并且表现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好感,使得他与天主教会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了避免同罗马教廷关系的恶化,法国耶稣会只好派德日进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1923年4月10日,德日进在马赛港启程前往天津,就是这次旅程成为了他科学生涯的重大转折点。
二、在北疆博物院的工作
德日进与北疆博物院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踏上中国大地之前。1920年,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法国神父桑志华(Emile Licent)在甘肃庆阳发掘了一大批古哺乳动物化石。桑志华本人并不是地质古生物专家,为了探究这些化石的科学价值,他将一部分化石寄回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交由德日进做鉴定研究。1922年11月,德日进在《巴黎科学院述评》发表了题为《在中国西部蓬蒂期出土的动物群》的论文,开启了他与东方远古生命的首次科学联系。
1923年4月10日,受桑志华的邀请,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又名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派出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与桑志华联合组成“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考察团首先在位于宁夏银川60公里外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水洞沟。一个月后,他们又在350公里之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谷找到了一处埋藏丰富的化石地点,一大批化石和打磨石器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化石涉及了奇蹄类、偶蹄类、食肉类、啮齿类等共33个属种,其中包括3副披毛犀的完整骨架和300多件羚羊标本,数量之多、保存程度之好都是十分难得的。
1924年,考察团又考察了内蒙东部哈达(乌兰哈达,今赤峰)、林西、达里诺尔(克什克腾旗西部)、戈壁、喇嘛庙和张家口,在林西考察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后,考察团又在赴河北省桑干河的旅途中,在泥河湾找到了富含化石的层位。
与此同时,在鄂尔多斯的沙漠里,德日进写下了他诸多神秘主义色彩作品中的一篇《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
1924年10月德日进返回法国,但他的科学思想仍旧不被罗马教廷所接纳,教会以散布异端邪说为由禁止了他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受益于同德日进的合作而名声大噪的北疆博物院和桑志华,后者得知了德日进在法国的处境,便亲自返回法国请求教会并邀请德日进来北疆博物院为他进行研究工作。1926年,德日进第二次来华,他跟随桑志华走遍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土地。从1926-1929年的三年时间里,德日进与桑志华一起赴山西及泥河湾做野外考察,与桑志华一起首次考察了周口店,与安德生讨论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与桑志华一起赴东北扎赉诺尔做野外工作,德日进对中国地质古生物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地质学论述和古生物化石鉴定报告,为北疆博物院在国际学术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借助于德日进杰出的研究成果和工作业绩,桑志华获得了1927年法国铁十字骑士勋章。
1927年,在翁文灏和步达生领导的周口店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化石500箱,包括一颗人类牙齿。原本计划两个月完成的工作,经过实际发掘后发现,这是一座几年也清理不完的化石宝库。同年,德日进、桑志华特地来到这个发掘现场,二人都被现场的景象震惊,不同的是桑志华看到的是化石出土量之大,而德日进则是预见将有如此之多的研究工作等待人们去完成。所以,当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在北京正式成立后,聘请德日进为顾问兼研究员时,桑志华也许可德日进赴京工作。
1934年,德日进与汤道平(M.Trassaert)对山西榆社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由于化石出土地点密布整个榆社盆地,其地质年代延续之长、种类数量之多世所罕见,于是发掘工作在1935-1936年间,连冬季也没有中断过。这是一批由第三纪上新世到第四纪更新世构成的非常完整的系列化石标本。其中大部分化石标本都收藏在北疆博物院中,成为研究亚洲大陆新生代第三纪晚期哺乳动物演化极为重要的化石证据。
1929年到1937年是新生代研究室和中国古生物学的黄金时期,德日进以极高的效率配合野外发掘工作,兼顾新生代研究室对华北、内蒙古、西北以至新疆的探查工作(见图3)。同时,德日进仍然承担着北疆博物院的研究工作,德日进自来到北疆博物院工作后,先后对桑志华历年来采集的脊椎动物化石和石器进行了研究,并在北疆博物院出版的刊物和各类馆外刊物发表了共计48篇关于北疆博物院藏品的专著和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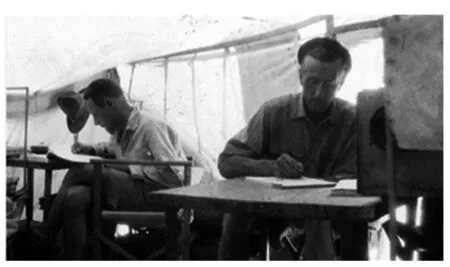
图3 德日进(右1)在乌鲁木齐野外考察时的工作照
三、北疆博物院的守护者
如果说桑志华是北疆博物院的创建者,那么德日进才是北疆博物院能够保存至今的守护者。1937年平津沦陷,天津的英法租界被日军封锁。1939年天津遭受洪灾,北疆博物院被淹,水深超过1米。大水过后,日本人解除了封锁并不断“光顾”北疆博物院。而这时,桑志华已趁欧洲战场尚未全面铺开的时候返回法国。为了拯救北疆博物院的藏品免于骚扰和水灾风险,德日进和北疆博物院代理院长罗学宾(Pierre Leroy)决定以建立“北平地质生物研究所” (Institute de Géo-Biologie, Pékin)为名,把北疆博物院重要的化石、图书资料、实验室设备等转移到北平东交民巷台基厂三条三号,德日进任名誉所长,罗学宾任所长。德日进在建所启事中声明该所是天津北疆博物院为研究工作而设,并停止了天津博物院的一切活动,派法籍耶稣会会士盖斯杰(Albert Ghesquieres)留守。
1945年抗战胜利,法国教会下令召回德日进和罗学宾,而对北疆博物院转移到北平地质生物研究所的那批重要藏品如何处置只字未提。回国前,德日进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其中11775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标本存放在刚刚恢复建制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其中史前史学藏品5329件、脊柱动物化石5237件、地质研矿760件、现生哺乳类骨骼449件,委托裴文中代管,直到德日进、罗学宾重返中国时为止——这种行为的背后饱含了德日进对中国的感情、对北疆博物院的感情,也反映了德日进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纯粹性。
1950年,年近古稀的德日进成为了法兰西学术院院士。1955年4月10日,德日进在纽约溘然长逝。然而德日进还有大量的随笔、演讲稿和论文未能在其生前发表,直到1976年才先后将他的240余篇文章收入《德日进著作全集》出版。其中《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论人类动物群》就是德日进在北疆博物院工作期间,于博物院旁桑志华、德日进的居所中撰写的。可以说德日进的科学思想是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和成熟,同时他也为中国博物馆事业、为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
2016年1月22日,修缮一新的北疆博物院北楼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重新向公众开放。2018年3月,经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多方协调,北疆博物院终于拿到了原址南楼的钥匙,开始着手对南楼进行修缮和布展,并将于10月正式对外开放,逐步实现北疆博物院以及紧邻的桑志华、德日进故居和神甫楼结合,成立博物馆聚落的设想。相信北疆博物院这座开启了德日进在华科研生涯的百年博物馆,能够在新的百年里继续他的辉煌。
——军旅写生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