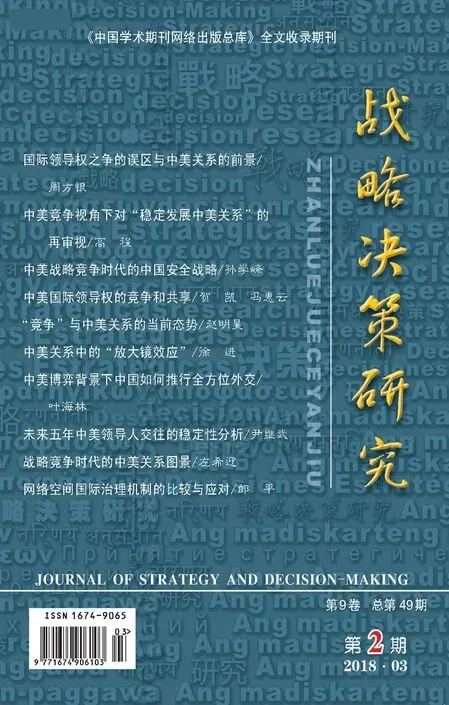国际领导权之争的误区与中美关系的前景
周方银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上升,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未来中国在国际上将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特别是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激烈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领导权之争,就成为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重要现实价值的问题。
一些现实主义者对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持零和博弈的看法,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之间的竞争将变得更为激烈。双方之间的冲突,既可能是由于崛起国对现状不满意而挑起,也可能是霸主国出于对未来国际地位的担心而采取的预防性行动的结果。①关于这种权力转移的视角,可以参考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些学者试图在权力转移与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之间寻找确定性的联系,近年来,这种讨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名义下进行。②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Bos⁃ton:Houghton Mifflin,2017).反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可以参考:D.A.Welch,“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9(3)2003:301-319.
总体上,我们认为,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为了获取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有些大的战争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发生,但并不是说权力转移本身自动引发了战争,而是由于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没有有效地管理好利益关系,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包括意外因素、第三方因素等等的作用,而导致了战争。
毋庸置疑,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分工,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度的相互依存关系。面对诸多全球问题的挑战,中美也有着很大的共同利益。同时,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它们也存在很大的利益不一致的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内容,包括安全利益的竞争,经济利益的竞争,以及可能出现的国际领导权竞争。
大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利益竞争是否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中国实力的进一步上升,中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是否必然带来中美之间高强度的紧张?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重点从中美利益不一致的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利益、安全利益,还是国际领导权的争夺?
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哪一个方面的利益争夺更加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更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激烈冲突,是经济利益的竞争,安全利益的竞争,还是国际领导权的竞争?
当前,经济问题正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因素。在特朗普执政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特朗普的政治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从国际上看,中国是让美国不再伟大的关键因素,而中国对美国的冲击当前更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层面。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曾宣称,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犯下的最大错误。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18年1月提交国会的报告称,美国当初“错误地”支持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③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January 2018,p.2.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促进美国繁荣”列为四项核心利益的第二位,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因为强大的经济支撑着美国的权力。④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 2017,p.17.在美国舆论场中,则充斥着“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中国通过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了美国经济”等等论调。
特朗普政府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极端强调,一定程度上把中美在某些经济领域的摩擦转变成经济对抗,甚至赋予战略对抗的含义,中美经济议题事实上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未来一个时期,中美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会继续有所发展。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非常真实,这种相互信赖很难摆脱和出现根本性逆转。中美之间即使展开有限程度的经济战,其代价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它对美国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对于特朗普念念不忘的振兴美国经济的目标来说,对外关系固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更根本的方面在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包括鼓励技术创新,改善基础设施,培育人力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通过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推动制造业的振兴,等等。另外,如果国内经济政策手段不能奏效,那么使用战争与冲突的手段也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特别是,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
总体来说,即使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美国的推动下有所激化,经济问题终归是可以协商和妥协的,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也表现出务实的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态度。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实质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其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对代价和收益颇为敏感。其一些颇为高调的言辞和做法,可能既是为了显示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从中长期看,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可以用经济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和处理,中美不会因为经济竞争而引发无法调和的冲突。
其次,是中美安全利益关系的性质。当前,从美国的角度,中美安全关系似乎越来越具有零和的性质。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战后世界的秩序和繁荣有赖于美国的领导作用和主导性的军事实力。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俄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重塑地区秩序。⑤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 2017,p.25.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公开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念,它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认为对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中心挑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长期复兴和战略竞争,认为中国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未来则寻求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优势地位。⑥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 2018,p.2.
这种认为中国试图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并最终取代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的观点,对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即使那些并不持这样观点的美国观察家,也相信维持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是美国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好保证。这潜在的要求是,美国要确保有能力在任何涉及中国的重大军事政治突发事件中占据优势。⑦史文:《超越美国西太平洋主导地位:稳定中美均势的必要》,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61-77页。而要实现这一点,很容易导致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正当要求的压制,从而提升中美安全关系上的紧张。
总体上,从中国人的角度,美国方面显著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在中美关系中,实际上是中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并有着较高的不安全感。在军事安全领域,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无疑都是处于明显力量劣势的一方。中国在安全上的目标总体上是防御性的。当然,中国从策略、手段上进行了某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但中美安全关系的基本战略态势并未因此发生质的改变。
当前,中国的军事实力确实在稳步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影响力确实在扩大,但这并不构成对美国本身的安全威胁。从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的角度,美国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国家,它是世界大国中最安全的。中国也积极寻求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的军事安全关系。在中国具有较为可信的基本的核报复能力,中国完全没有主动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动机的情况下,中美两国之间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事情。2018年1月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也指出,该国防战略的最深远的目标是把中美军事关系确立在透明和互不进攻的轨道上。⑧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2.
中美之间安全利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安全影响力的竞争。中美两国的军事建设,并不是直接为双方之间的战争做准备的,并不是以双方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这样一种想象为基础的。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当前推动的以印太为框架的军事安全合作,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抑制中国在亚洲、亚太地区安全影响力的扩大,而不是应对某一种具体的、可解决掉的安全问题上的威胁。
近一两年来,从美国的视角,中美竞争的激烈程度出现明显上升,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也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视中国为一个具有中心性的长期威胁。经济上,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的绝对经济实力仍在继续上升,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给美国经济也带来了很大益处。美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不满,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冲击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影响了美国经济模式在国际上的吸引力。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降低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的。
从安全的角度,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不构成现实和紧迫的威胁,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由此影响美国亚太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信心和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地区安全影响力的竞争。
如果中美竞争主要是经济竞争,或者主要是安全竞争,那么不容易解释为什么在近两年美国对于中美竞争的看法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毕竟,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是一个较为长期和平稳的过程,而且自2012年以来,中国虽然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但GDP的增速从2011年的9.5%下降到8%以下,近两年都稳定在6.5%~7%之间。
如果把中美竞争理解为国际影响力的竞争,美国政策的这一变化就比较容易理解。从这个角度,“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的快速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和成立、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作用的提升,以及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努力,都被美国一些人士理解为对美国的挑战。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过程中,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国如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的态度,在一些人看来具有标志性的意义。⑨David Dollar,“China’s rise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The AIIB and the‘one belt,one road,”2015年7月15日,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ise-as-a-regional-and-globalpower-the-aiib-and-the-one-belt-one-road/.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本身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利益。⑩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 2017,pp.4,37-42.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崛起难以接受的方面,并不在于中国经济实力的绝对增长,也不是中国实际上对美国形成了什么样的安全威胁,而是因为感到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受到了冲击。现实的或者想象中的中美领导权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美关系紧张程度的上升。
二、具有误导性的中美国际领导权之争
当前,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在中美之间存在国际领导权的争夺。美国不少人士认为,中国崛起最根本的挑战,就是中国要获取国际领导权,⑪特朗普的中国政策顾问白邦瑞宣称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战略欺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New York:St.Martin's Griffin,2015).或者换一种相对委婉的说法,认为中国试图凭借自身的力量优势,建立一种中国主导的与当前不同的国际秩序。⑫这样的观点不仅在美国较为普遍,也在美国的一些盟国中有较大的市场。澳大利亚政府2017年11月发布的新版《外交白皮书》明确认为,澳大利亚从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显著受益,但当前这个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见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p.21.那些把中国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挑战看得十分严重的人士,一方面夸大了中国试图获取国际领导权的迫切程度,另一方面则是用高度零和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领导权的性质。但是,国际领导权竞争真的如此激烈、如此重要、如此不可调和,以至于中美两国需要通过高强度竞争、包括可能需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吗?我们认为,中美国际领导权竞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误导性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领导权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国际领导权竞争是否对于其他利益具有压倒性?还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的考虑?国家是为了追求国际领导权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计较经济成本、安全代价,还是国家从服务于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出发而追求国际领导权?如果是后者,那么,国际领导权本身的重要性就不具有根本性。这样的话,美国在二战前对国际领导权不太热衷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同样,在“英国治下的和平”下,也不是所有其他大国都试图取代英国获取国际领导权,也成为比较好理解的事情。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美在国际上追求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对中国来说,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通过两个阶段的努力,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⑬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居于中国政府确定的长期目标的核心位置。早在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中,中国政府就做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其中的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未来三十年发展目标的设定,并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但对于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压倒性重视则是一脉相承的。
对美国来说,其所拥有的国际领导权是与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密切联系的,这包括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安排、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所带来的金融等方面的利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增进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等等。同时,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也涉及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是否需要从长期保持国际领导权是一个涉及成本收益权衡的问题。国际领导权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压倒性的目标。⑭不要说支持美国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进行战略收缩的学者,即使反对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学者,也往往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论证。参考Stephen Brooks,G.John Ikenberry,Wil⁃liam Wohlforth,“Don't Come Home,America: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3(Winter 2012/13),pp.7-51.即使对于已经长期习惯于国际领导地位的美国来说,国际领导权就其本身的重要性而言,远远不足以压倒现实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后者。这在当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调整中已经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总体来说,中美都是体量巨大的国家,从宏观的角度,其内部事务的重要性都要优先于外交事务,它们都不太可能为了国际影响力目标,而过于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否则,由此损害的不仅是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且会带来较为麻烦的社会和内部政治问题。
其次,国际领导权竞争,是否是直接在中美之间展开的?领导权是一个可见的、直接可争夺的东西,还是它是在领导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建构起来的东西?
如果领导权是一个实体性的物质,它放在谁手里,谁就有了领导权,那么,对它的争夺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如果领导权不是这样的东西,而是一个需要通过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在潜在领导国和潜在被领导国之间建构的东西,那么抛开其他国家,直接在两个大国之间展开领导权的争夺,这件事情本身就变得有些虚幻。
中美国际领导权竞争是一个颇为具有误导性的说法。这个说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就是国际领导权是一个放在那里的东西,美国拿到了,就在美国的手中,这个东西,也可以被中国从美国的手中夺走。这种看法是对国际领导权的一种十分简单化、但并不很符合事实的理解。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是不是没有中国的竞争,美国就一定拥有国际领导权?或者,只要美国不努力阻止,中国就一定能获得国际领导权?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不必然是肯定的。国际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领导国家与承认其领导地位的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相互关系。这个领导权并不是固定存在的,也不是可以轻易地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移交的。
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国际领导权的交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些人预期中的中美之间和平的权力转移,即使发生了,也主要只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就其本身而言并不代表国际领导权转移的实现。
第三,领导权是领导国家与承认其领导地位的国家之间一种稳定的关系建构,拥有体系中最强大的实力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有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要获得和维持稳定的国际领导权,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获得一定数量国家所提供的稳定的国际支持。⑮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可参考Stefan A.Schirm,“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6(2),2010,pp.197-221.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这往往需要大国能够可信地包容和维护追随国的利益,适当地支持其政策理念,在国际场合代表其发声、维护其立场,缓解其承受的国际压力,获得他们的理解、接受和尊重。同时,大国需展现一定程度的自我战略克制,以便其他国家可以放心地追随,而不是把该国视为需重点防范的威胁。此外,国际领导行为也不等同于国际领导地位,后者建立在一种稳定的关系结构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
如果中国试图做有效的国际领导者,需要得到的是大多数国家的认可,需要得到的是相当数量国家的稳定支持。对一个大国来说,只要能够获得足够多国家的支持,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领导者。只是有强大的实力,但得不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自愿追随,就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中的领导者。
在这个方面,一个多少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当前美国政府对于维护其国际地位的意愿有所下降,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特别是发展美国经济方面时,部分美国的盟国在其官方政策表态中,明确表示希望美国继续领导国际和地区秩序,这在澳大利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体现美国过去在建立其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在建构领导国与追随国关系方面有其颇为成功的地方。
第四,国际领导权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绝对零和性质的事物,而是有着颇为丰富和复杂的体现。
在当前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可以有不同的领导者。领导者可以是单一国家,也可以是若干个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在有些领域,领导者的身份可能并不是很清晰,而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过去几年,中国在综合实力处于世界第二的情况下,以和平的、建设性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广泛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等国际合作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都体现了较强的国际领导力。过去几年的实践也说明,仅仅聚焦于中美两国来探讨国际领导权问题,本身是一种颇具误导性的做法。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从乐观的角度来估计,未来中国也很难成为冷战后前二十年那种美国式的领导。美国获得当时那样一种领导地位是诸多有利条件的结果。这样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复制。未来的国际格局不会是单极体系,而会呈现出复杂的特性,这会对大国的国际作用构成强有力的制约。
在中国的国际作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未来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可能更多是功能性的、领域性的,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发展、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某些挑战方面,是一种对他国干预程度很低的、总体具有非强制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非机制性的、某种意义上是服务型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地位,对于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来说其吸引力无疑会明显下降,但可能更为其他国家所欢迎,并对整个国际体系来说更具有建设性。
未来国际领导权所具有的上述性质,对中美关系本身来说有其积极的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从长期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前景可以抱有相对乐观的预期。⑯这种对长期前景的预期,并不排除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有所恶化,双边关系竞争性增强的可能性,这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关于未来几年中美安全压力增大的分析,可以参考孙学峰:《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