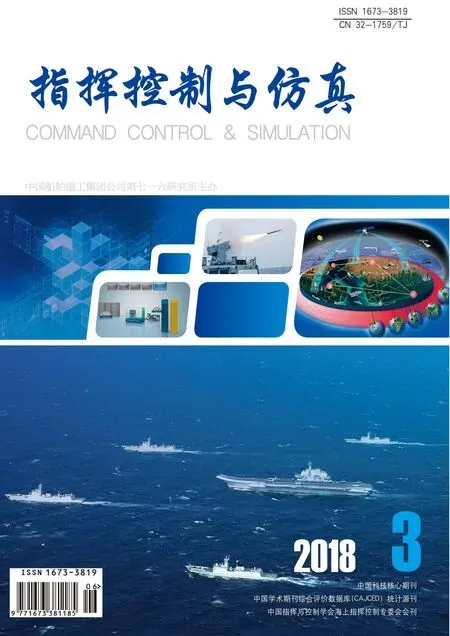美军联合作战规划发展历史及启示
于鸿源, 叶雄兵, 刘成刚
(1. 军事科学院, 北京 100091;2. 解放军31002部队, 北京 100094)
联合作战规划是指,联合作战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在规划保障人员的辅助下,依托信息化工具,运用科学化方法,以作战任务为牵引、作战程序为驱动,在指挥程序框架下制定作战计划,进而生成作战命令的过程[1-6]。作战计划是指挥员决心的具体体现,是组织与实施作战行动的依据,作战命令是实施指挥和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的基本依据[7],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都是作战规划活动的产物。依托信息化工具,科学地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并生成作战命令,是达成联合作战目的,准确实现上级和联合作战指挥员意图,将战略和作战策略转化为军事行动的必须途径。因此,联合作战规划是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合作战指挥行为的重要环节,对于真正形成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构建具有我军特色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军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刚刚建立,联合作战规划事业正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需要充分吸收借鉴外军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美军十分重视联合作战规划问题,已经在此方面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且屡经实战检验,在组织机制、实施准则、作业工具上均已发展成熟。对美军联合作战规划发展历程进行探究、对其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攫取其中精华为我所用,对我军联合作战规划事业必有促进和启迪作用。为此,本文梳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军规范化联合作战规划发展历程,总结其前进的主要动因,梳理各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成果和存在问题,提出对发展我军联合作战规划的启示,为建设我军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提供参考。
1 美军联合作战规划发展历史
美军施行规范化联合作战规划始于20世纪60年代[8],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历史。分析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起步发展、成熟运用和改革探索3个阶段。
1.1 起步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是美军规范化联合作战规划的起步发展阶段。美军在联合作战体制改革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在国防系统管理和规划改革的大背景下,着眼提高作战计划拟制效率和对部队行动的控制能力,开发并应用了统一的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和联合部署系统,解决了联合作战规划起步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美军联合作战机制的建立和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为美军联合作战规划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和技术基础。为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军联合作战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美国国会于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1958年通过《国防部改组法》,使得军种脱离作战指挥体系,实现军政与军令分离,美军联合作战机制初步建立[9],为联合作战规划提供体制基础。20世纪50~60年代,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并应用于军事活动,计算机软件系统改变了美军使用“铅笔头”制定作战计划的方式,为联合作战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10]。
其次,开发统一规范的联合作战规划系统解决初期存在的军兵种作战规划系统冲突问题。随着各作战司令部和军兵种各自建设作战规划计算机作业系统,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各作战规划系统相互冲突,数据存储格式不相统一,信息交换困难;各单位部门的规划流程不同、成果格式互异,联合部队指挥机构各自为战,难以有效支撑战区司令部的联合作战规划,联合作战规划作业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时至1966年,美时任防长麦克纳马拉关注到上述问题,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统一的联合作战规划流程,开发标准化的数据处理系统,即联合作战规划系统(Joint Operation Planning System,JOPS),该系统于1970年批准立项、1973年进入研发、1975年投入使用。JOPS系统能够支持平时和战时的作战计划制定,具备危机情况下快速依托作战计划生成作战命令的功能,统一了联合作战计划制定、审核和执行流程,规范了简洁的作战计划格式,使得联合作战规划软件程序及其数据格式标准化,便于信息快速流转和处理[8,10]。
再次,开发联合部署系统解决联合作战规划部署与实施方面的不足。1978年10月,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Nifty Nugget”指挥所和实兵演习,检验美军整体动员部署能力。演习暴露出JOPS系统在兵力部署规划与实施方面的不足,主要是系统不具备监控作战命令执行的能力,不能依时间节点规划兵力行动。为解决上述问题,美军于1979年3月成立联合兵力部署局,着手研发联合部署系统(Joint Deployment System,JDS)。新研的JDS系统能够按照时间节点规划兵力行动,实时监控作战命令执行过程中的兵力部署动态,与JOPS系统共同支撑起美军的联合作战规划活动[11]。
1.2 成熟运用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前几年,美军改良联合作战体制,建立专业化联合作战规划执行机构,整合开发新一代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出版联合作战规划相关准则,将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系统应用到实战之中,联合作战规划发展进入成熟运用阶段。具体有3个方面体现。
第一,改良联合作战体制,明确联合作战规划责任主体。为改善军职、文职指挥权混乱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功能不彰的现象,1986年里根总统签署《高尼法案》。该法案确立了美军联合作战指挥权责与指挥关系,赋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作战规划权责,明确平时和战时联合作战计划制定均由战区司令部负责[12]。在《高尼法案》基础上,美军建成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成员、联合参谋部、各军种部门及军种司令部、战区及下属司令部、作战支援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共同体[13],专司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工作。
第二,整合研发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系统(Joint Operation Planning and Execution System, JOPES),并应用到实战之中。尽管JDS系统对JOPS系统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作为各自存在缺点的两个独立系统,使用过程中的频繁切换十分影响工作效率。1981年5月,美国防部长办公室会同联合参谋部共同评估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过程,查找联合作战规划在各级指挥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整合JDS和JOPS系统功能,研发一套能够完整支持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的系统。1982年6月,联合参谋部组成联合作战规划指导组,指导开发JOPES系统[14]。
JOPES系统的自动数据处理软件具备生成兵力部署需求、评估后勤补给和输送需求、审定输送计划可行性,优选兵力部署计划、跟踪兵力部署执行状态等功能[15]。除软件程序,JOPES还囊括了作战计划制定流程和系列指导性和规范性文档,指导作战计划和命令的拟制,规范作战计划的制定步骤、种类和格式。JOPES系统发布后不断改进完善,首次在海湾战争中用于实战[15],并在台海导弹危机[16]、伊拉克战争[17]等美军历次作战计划制定和兵力部署中使用。这是美军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三,发布系列联合作战规划指导原则。随着JOPES系统发展成熟并投入使用,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94年8月发布第一版第5-0号联合出版物《联合作战规划准则》[18],以法规文件形式规定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制定的格式、程序、内容、分类、审批和修订等内容[19]。此后美军根据训练和实战经验,不断修改和完善联合作战规划准则,于1995年、2006年、2011年[20]和2017年[21]更新发布第5-0号联合出版物,持续为美军制定合理的联合作战计划提供权威性指导。
1.3 改革探索阶段
21世纪初至今,是美军联合作战规划的改革探索阶段。随着作战形态的不断发展,美军联合作战规划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美军正试图通过一系列适应性规划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运用JOPES系统制定了1003V号“伊拉克自由行动”计划,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该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均不满意[17,22],认为JOPES系统存在多个方面缺陷。一是作战计划的制定周期过长(通常为24个月);二是作战计划根据初始的战略环境、情报及判断结论制定,经过较长制定周期所得的计划与迅速变化的外在环境往往不再相符;三是制定的作战计划没有充分吸纳相关军地部门意见;四是作战计划成果修改调整十分困难(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总统和防长在危机时刻面对提交的作战计划,除了签署执行没有更多选择。为此,2005年11月,拉姆斯菲尔德签署适应性规划改革路线图,开启了美军对联合作战规划的适应性改革[23]。
适应性规划改革期望能够紧贴不断变化的战略和战场环境,快速、系统性地制定和修改作战计划。为此,改革要点包括:一是引入“过程审查”机制,在作战规划过程中防长与战区司令按阶段进行多轮讨论,以确保制定的联合作战计划与高层战略意图相符;二是引入跨部门协作机制,计划制定全过程军地各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充分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达成战略目标;三是制定多分支的作战计划,在预想多种可能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多种行动方案,以使作战计划能够适应多种危机情况,供上层决策者选择,便于快速调整作战计划;四是压缩作战计划制定周期,通过提高规划人员素质、优化规划流程、改进作业工具等多种方法压缩作战计划拟制周期,力求在6个月内完成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17,22,24]。以上改革思想落实到新一代的适应性规划与实施系统(Adaptiv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Enterprise,APEX)中。
参谋长联席会议2011年出版的第5-0号联合出版物体现了美军从JOPES系统到APEX系统的改革,明确“联合作战规划活动通常通过APEX系统完成”[13],2017年第5-0号出版物修订版明确“APEX系统整合联合作战规划共同体的规划活动,辅助计划制定向实施转换”[21],权威性地规定了相关单位应运用APEX系统进行联合作战规划作业。可见,适应性规划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近年不断出现关于美军适应性规划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的文献报道[17,22,25],主要列举改革后的复杂作战计划制定过程使得计划制定周期没有缩短反而拖长,繁多的过程审查需求堆积在国防部高层而得不到回应,新的作战计划制定流程使得参谋机构不堪重负等问题。据文献报道[17],2016年1月战区司令部在作战计划制定过程中摒弃了“过程审查”。由此可见,美军适应性规划改革依然在探索之中。
2 美军联合作战规划主要技术沿革
信息技术是联合作战规划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联合作战规划的发展过程中,美军不断将新技术方法应用到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建设中,创新解决实际作业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在其联合作战规划发展的各个阶段均有体现。
2.1 起步发展阶段应用的主要技术
在起步发展阶段,美军应用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Auto Data Processing,ADP),解决手工制定作战计划耗时费力,作战计划修改烦琐等问题,实现给定约束条件下兵力运用和部署的科学性,主要依托JOPS ADP软件系统实现。
一是计算作战计划相关兵力和保障需求,包括作战兵力需求、支援保障兵力需求、装备物资需求、作战轮换人员需求等,由JOPS软件系统的兵力需求生成器(Force Requirement Generator,FRG)和机动需求生成器(Movement Requirement Generator,MRG)实现[10]。其中,FRG软件由当时的后备司令部设计,用于生成作战兵力需求,实现作战兵力的选择、组合等功能;MRG软件由太平洋司令部设计,用于生成支援保障需求,实现作战保障装备、物资及替代兵力需求计算和选择[10]。
二是建立兵力和保障装备、物资向作战地域开进的机动序列,评估兵力、装备和物资的投送可行性,由JOPS软件系统的输送可行性评估软件(Transportation Feasibility Estimator,TFE)和时序兵力部署数据库(Time-Phase Force and Deployment Data,TPFDD)实现[10]。JOPS系统的FRG软件和MRG软件生成的兵力和保障需求,经过进一步地数据处理,生成按时序划分的部署数据,存储到TPFDD数据库中,作为生成作战计划的基础数据;TFE软件读取时序的部署数据,生成兵力、装备和物资海空投送需求,并模拟投送过程,评估计算投送并到达作战地域所需时间,生成投送可行性报告。
以上运用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实现的作战需求计算、兵力规划、行动可行性分析等功能,是联合作战规划的核心功能,在后续的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建设中得以持续发展。
2.2 成熟运用阶段应用的主要技术
美军联合作战规划发展到成熟运用阶段,联合作战规划系统不再限于作战计划和指令制定的基本功能,而是发展成为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囊括联合作战行动的规划、监控和实施功能[26]。这要求联合作战规划系统能够支持计划和指令数据、兵力行动数据的远程、高效、准确传输,多源数据的实时同步等。网络技术(Web Technology)、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技术(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和数据库同步技术(Database Synchronization)等分别用于数据远程传输、规划系统与网络间数据交换以及数据存储过程中,由JOPES IT软件系统实现。
一是应用网络技术。JOPES IT系统架设在美军保密IP路由网络(SIPRNET)上,通过GCCS-J指挥控制系统终端为用户提供Web访问服务,其后台由数据库服务器(Database Server)、应用服务器(Application Server)、网络服务器(Web Server)、管理服务器(Enclave Management Server)、域名服务器(Domain Name Server)等提供功能支撑。为确保冗余度和安全性,每个网络节点由主副两条网络线路与SIPRNET相连接,能够在高负载、有限带宽条件下准确、高效地传输数据,为用户提供健全、稳定的联合作战规划相关功能[26]。
二是设计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JOPES IT系统规范数据交换(Data Exchange)格式,配合使用数据网络服务(JOPES Data Network Services)和数据订阅服务(JOPES Subscription)技术,在JOPES Database数据库和外部网络间提供可靠、高效的数据交换接口[26]。
三是通过架设固定式数据服务器(FSSD Database Server)和迁移式数据/应用服务器(DSSE Database/Application Server),JOPES IT较好地解决了多用户并行操作带来的数据同步问题。
2.3 改革探索阶段应用的主要技术
在改革探索阶段,美军力求通过联合作战规划适应性改革,促进各部门和单位在作战计划制定过程中的沟通协作,制定能够适应快速变幻的作战环境之作战计划。由此,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到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建设中,以期能够在分布、动态、多源、异构的网络数据环境下,提高作战规划的作业效率。应用的主要技术包括虚拟化数据层技术(Data Virtualization Layer, DVL)、简单对象访问协议技术(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基于属性的数据访问控制机制技术(Attribute-Based Access Control, ABAC)等[27],调整优化数据源、数据交换协议和数据访问控制机制,将在新研的联合规划与实施框架中实现(Join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Service Framework, JFW)。
DVL技术旨在建立一个基于内存的高效共享的联合作战规划数据源,统一多源、异构、多所有者的联合作战规划数据,将数据集成管理并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实现多用户对数据的远程高效读写访问,有效解决数据同步问题。
SOAP技术提供了轻量、简单、基于XML的网络协议,服务于分布式指挥控制网络环境中的联合作战规划数据交换,使得结构化、固化的联合作战规划数据高效、准确地在各用户之间传输交换。
ABAC是基于实体属性的数据访问控制机制,通过定义属性之间的关系,控制复杂的授权和访问控制约束,解决联合作战规划数据的细颗粒度访问控制和大规模访问用户动态授权问题,将增强数据访问地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根据美国信息系统局信息[27],集成以上技术功能的新版联合规划与实施服务框架(Join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Services)将于2018年3季度前研发完成,并于2020年底前取代JOPES系统的相关软件程序。
3 美军联合作战规划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研究美军联合作战规划发展历史能够为我军联合作战规划建设发展带来如下启示。
一是研发全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规划作业平台,为协同作业提供基础。美军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发并应用了统一的联合作战规划作业工具,适应性改革推行以来,将军地相关部门广泛纳入联合作战规划体系,共同在APEX系统框架内参与作战计划制定。统一的作业工具是联合作战规划相关单位密切协作的基础,能够避免“烟囱”现象导致的资源浪费,便于作业过程中的上下沟通、横向联动,促进作业成果交流,力求联合作战规划活动高效可靠。
二是依托指挥信息系统搭建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形成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的闭环。美军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JOPS系统没有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建设[10],在实兵演习中暴露出无法通过JOPS系统监控作战计划实施过程的缺点,而后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建成JDS系统弥补这一缺点,导致在一段时间内陷入需要2个系统配合完成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功能的窘境。随后建成一体化的JOPES系统依托WWMCCS指挥控制系统建设,并随着系统升级迁移到GCCS指挥信息系统上。我军在建设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系统的过程中要避开美军走过的这条弯路,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建成计划制定-计划评估-计划实施-实施监控-计划修订的联合作战规划与实施闭环,确保能够随着战场态势变化调整作战计划,避免作战计划脱离执行实际。
三是联合作战规划要科学谋算,不能搞短时突击。21世纪初的适应性规划改革推行以来,美军为压缩作战计划制定周期不断寻求突破。然而,尽管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作支撑,美军至今未能实现半年至一年时间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的目标。可见,有效管用的作战计划不是依靠几天或几周的快速突击就能制定的,联合作战规划要对作战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情况作充分预想,对各作战因素精算细算,对规划成果常态推演。由此才能制定出对国家利益负责、对官兵生命负责、经得起实战检验的作战计划。
四是制定联合作战规划准则,提供标准规范。联合准则是指导美军联合运用各军兵种力量、协同行动以达成共同目标的基本原则,具有权威性[20]。美国会1986年通过的《高尼法案》明确赋予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制定联合准则的职责,指导美军联合作战力量运用。参谋长联席会议第5-0号联合出版物是指导美军联合作战规划活动的准则,自1994年首次发布以来不断更新完善,指导联合作战规划作业。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军应制定和发布相应的联合作战规划实施纲要,规范联合作战规划的方法手段、作业流程、成果标准等,推动联合作战规划实施的系统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五是联合作战规划要经由实战化检验评估,以打赢为标尺。从20世纪40至50年代的联合作战体制改革,到80年代研发JOPES系统,再到21世纪初的适应性规划改革,美军历次作战规划改革的起因均来自实战化演习或直接源于实战,实战检验是评估美军联合作战规划流程、工具等可行性的主要手段。我军的联合作战规划流程、工具管不管用,同样不能坐而论道,作战计划更不能论都不论直接入柜上锁。在缺少实战检验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创造实战化训练和演习条件,以打赢为标尺对联合作战规划进行检验。
4 结束语
美军联合作战规划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运用、改革探索3个阶段,从回顾总结其发展历史可以得出,发展建设我军联合作战规划事业需注重以下几点:1)研发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规划平台,使得作业过程高效便捷。2)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建设联合作战规划系统,完备联合作战规划功能。3)以科学方法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确保作业成果可信管用。4)制定标准规范联合作战规划准则,为实施作业提供遵循。5)在审查评估上注重实战化检验,以打胜仗作为联合作战规划实施的最终目的。总之,建设发展好我军联合作战规划事业对于提高我军联合作战指挥能力至关重要,我们应综合借鉴外军发展经验,充分考虑我军实际情况,推进联合作战规划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