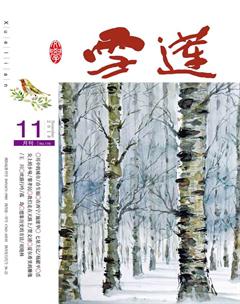冬日物象(二题)
围炉取暖
寒冬,屋外飞雪,几个汉子围在火炉旁,取暖,谈生活,聊家常。
这是我喜欢的情境。
这当然是北方。雪花覆盖了大地,汉子们闲得无事,聚在火炉旁,一边暖身,一边打发日子。
初次目睹这情景,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冬天,我不过七八岁。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回河南温县老家,看见奶奶坐在炉子上,屁股下有个小凳儿。下面围一圈她的儿孙。儿女们在围炉说话,孙子们围炉打闹。奶奶边烤火边翻动围在炉口上铁壶旁的红薯。壶水滋滋地响,奶奶拿起一个红薯掰开,分给她的孙子们吃。
奶奶看见我,欢天喜地。她吆喝开她的孙子们,让我靠近炉子。我伸出冻得肿红的小手,凑近炉子张开小手,不时摸摸泥土做的炉身,手背贴炉,烫得呲牙。
大人们笑我:小心烤熟了,我们吃你的肉。
一阵哈哈大笑,喷出嘴里的热气,屋子更暖。
那情景,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只觉得温暖,一路上的寒冷,此刻全无。慢慢长大了,方才晓得,屋子中间那火炉,凝聚着亲情。
北方这炉子必是泥土做的。泥里混有麦草。泥土的气息,麦草的气息穿胸而过。庄稼汉就喜欢闻这味道。
后来,我在关中的农人家里看到了更多的火炉,听到了炉旁的谈话内容:谁家母猪下了崽,谁家儿子生了个牛娃,谁家刚买了一辆自行车,谁家女人懒得不洗脸,谁家给老人办丧事请了哪儿的戏班子,菜油紧缺了,化肥涨价了,火柴买不到了,盐要凭票供应……聊得没话题了,就抽老旱烟,烟锅伸进烟袋,挖一锅出来,吸完,在炉身上磕磕,又挖一锅,点火。
烟抽够了,喝水。炉火上架着铁壶,长长的嘴儿,哧哧的冒气。喝水不用缸子,用主人家的大老碗,一气喝完,碗撂脚旁。
饭点到了,女人在外边吆喝自家的男人吃饭,于是各回各家。
围炉取暖,多有诗意。
秦岭的终南山,冬日也够寒冷。山农不用土炉,用瓦盆或者铁盆,里边燃烧一堆短节的木头。我在县政府工作的时候,冬日必深山问苦,有时一住就是几天。常见的情形是,一堆人围在火盆前,男的谈天,女的纳鞋底。每见此景,我必掺和进去。我刚进门,围着火盆烤火的山民便停住话头,观察着我是何方人士。我说没事,我是过路的,外边冷,进来暖暖身子。说着,我哆嗦几下身子,以示寒冷,傻傻的伸出手烤火。他们还是心存疑虑。我索性抖了自己的底,说我是个写文章的,想听听山里人说的怪话,了解一下山里人的生活。作家、体验生活,这些词他们也许不懂,但知道文化人是弄啥的,无非就是在纸上写几个字。说着,我就动手往火盆里添柴,鼓起腮帮吹火。这下,他们才放心了,给我腾出一个马扎,继续诉说着生活,不时插入山里的黄段子。我这会儿,傻傻的随他们笑几声,便是最好的表情。
山里人烤火用的是铁匠木。这东西耐烧,一盆火足以烤半天。
铁匠木烧过的灰烬,洁白如雪。
终南山人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围炉取暖,但情景相似,我也接受。
过去,东北人过冬,离不开火炉。没办法,天太冷。听说他们在铁网上架着肉,用炭火烤。还有铁锅炖鱼、小鸡炖蘑菇、杀猪菜、排骨炖豆角、鲶鱼炖茄子。炉火上烤的东西多着呢:玉米饼子、铁饼子、冷面。在沈阳,有许多朝鲜族人开的烤肉店,小炭炉上面的铁丝网,牛羊肉烤的滋滋响,还有海鲜贝类,也是种享受啊。还可以去吃杀猪菜,也就是酸菜炖白肉血肠(白肉是偏肥的猪五花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酸菜吸收了肉片中的油,蘸上韭菜花吃,肥而不腻。比沈阳更冷的延吉人围炉的吃法更多:冷面配锅包肉、手动韩式烤串、大块烤肉、各种石锅石板、各种米酒、明太鱼啤酒屋、辣白菜、桔梗萝卜条、各种韩式正宗小菜。
北方的大雪已经下过几轮了,你是不是蠢蠢欲动了?带上这些干货,去体验一把真正的东北冬天里的围炉生活吧。
北京人把過冬叫 “猫冬”。《都门杂咏》收录有一首诗,描写旧时老北京冬日取暖的景象:“雪纸新糊斗室宽,映窗云母月团来。地炉土炕重修葺,从此家家准备寒。”
老北京人喜欢吃涮羊肉。光绪十八年,曾在北京居住过的浙江桐乡人严辰缁的《忆京都词》,描摹了京人围炉涮羊肉的情景:“忆京都冬窗不透风,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不似此间风满屋,热炭又嫌樱火毒。”
聊着天,吃着涮羊肉,这情趣也不错。
欲雪的黄昏,最适合围炉取暖。炉旁的人烤着火,望着朦胧的纸窗。天色渐暗,炉火照红纸窗,有几分仙境。写下《燕京乡土记》《北京的风土》《北京四合院》的红学界元老邓云乡,在他的《忆江南》一词里对老北京此景赞叹有加:“忆京华,最忆是围炉。老屋风寒深似梦,纸窗暖意记如酥,天外念吾庐。”
清代有一部六卷本的诗话著作《围炉诗话》,为学者吴乔所著。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 本书通过对唐、宋、元、明历代诗歌的评论,提倡“比兴”,反对宋人的浅直无味;强调“ 有意”,反对明七子的“唯崇声色”,认为“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主张“诗之中须有人在”。
我对诗研究不深,《围炉诗话》只是了解些皮毛,不敢妄评。书里的句子,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围炉诗话的那种意境和惬意,却是久久在心。想想,吃着爆栗,品着苦茶,说着笑话。没了寒意,有了口香,笑话暖心,这是围炉的更高境界。
不过,吴先生书中所言,并非生活的鸡毛小事,而是说诗,那艺术观绝非平庸。可见,围炉取暖在某些有学问的人那里,演变成精神,琢磨出艺术。
提到围炉谈诗,不由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知己无需多,三两个足矣。大雪茫茫之夜,与无话不谈的朋友守着火炉,把酒谈心,是何等的畅快。聊到兴致处,抠着鼻子,挖着耳孔,更是自在。
大雪封门,没有朋友来,一个守着炉子读着自己喜欢的书,又是另种乐趣。古人云,“雪夜关门读禁书”。古时的禁书不少,清风阳光下的阅读,被人瞧见,可能会招来牢狱之灾,难免提心吊胆。大雪天就无需担心了,鬼才会登你的门。炉火是温暖的,书里的内容是舒心的。听着雪落的轻巧,体味书中的意境,摇头晃脑,揣摩风月,那才叫享受。
“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围炉读书,一切皆在自己的内心。
现在,围炉取暖的情景很少见了,我有点失落。
雪是冬天的白衣使者
若一冬无雪,北方的冬作物就会枯死,闹开春荒。
“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产”、“雪是麦田好棉被,雪多枕着馒头睡”……农谚,总是对雪情有独钟,心怀感恩。从关于雪的谚语中可以看出,小雪的节气里雪花飘飞,来年麦子就丰收,草木就旺盛。在我的家乡,一到小雪节气,人们忙着给田里堆肥,给果树剪枝,恭候雪花莅临。此刻,人之盼雪,就如渴望菩萨问世。来年的丰收,就寄托在雪花的身上了啊。
雪花,仿佛白衣少女,冰肌玉骨,冰清玉洁,婉约清丽,温柔抒情。
如果说,“立冬”拉开了冬天的序幕,那么“小雪”便是冬天舞台上的第一支舞曲。雪花身披晶莹的衣衫,舞动轻盈的身姿。越冬的小麦匍匐于泥土之上,一半是绿中带黄的麦苗,一半是晶莹的雪花,色调明暗分明。树枝落光叶子,挂着薄雪,映衬着银灰色的天空。旷野、庭院,一枚枚落叶从雪中探出头,几分神采。
冬至那日,城西涝河迷蒙浑茫,老柳身披雪花,银装,素裹,苍桑,雄奇,好似大漠。河床穿过冰雕的芦苇,凝成朵朵白花,像是祭奠,像是怀念,像是告别。河畔灌木上积雪层叠,起伏有致,宛若银白的雪龙。我所惦念的那片荷塘,厚厚的冰层中,有残荷的枝干穿出,凝成一根根冰柱。
在我看来,雪是人间吉祥的物象,然而在一个个唐代诗人的笔下,雪却成为忧伤与凄凉。
岑参有首诗,诗名《白雪歌》:“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诗人描绘的是大雪之中边塞送友人离别时惆怅的心境。诗人以雪景烘情,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雪是凄凉、阴沉的产物。边塞诗人高适由“北风吹雁雪纷纷”的情景,发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的感叹。以五言律诗擅长的刘长卿在《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中写到贫苦人家的孤寂难耐时,也同风雪结合起来,衬托出人生的凄凉和荒漠。晚唐诗人罗隐,多次落榜而显名于史,在他生不逢时的笔下,“瑞雪”成了不祥之兆。他在《雪》中这样写道:“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诗中的“瑞”对于贫苦人来说,是一种不祥之兆。
《白毛女》的电影或戏曲,对于现在六十岁上下的人是熟悉不过了。冬日雪的背景下,杨白劳正陷入苦于无法向地主黄世仁交租的悲苦。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除夕之夜,恶霸黄世仁威逼杨白劳用女儿喜儿抵债。
瑞雪兆丰年。没错,这是时令的预兆。问题的关键是,你首先要度过雪花飞舞的冬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视野里的情景,并非幻想,而是现实。
人们总是以为,雪是为北方设计的。但现在,它的足迹开始探访南方。它的初衷是让南方人见识它的模样,赏雪景,打雪仗。但很不幸,它的一厢情愿酿成雪灾。报道称,二零零八年初,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遂了南方人所愿,降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七省。仅湖南就有三十万人被大雪围困,一千三百五十九点五万人次受灾,一万一千间房屋倒塌,三万三千头大牲畜死亡,菜棚垮架,电力中断,交通停运……人们还来不及欣赏他们心仪的雪景,忽然发现大雪已成灾难。
雪知闯祸之后,才发现它和南方的人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于是追悔莫及,扼腕叹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算了,算了,我再也不和南方人玩了,还是置身于北方吧。
前些年,一位广西的文友看过一篇写雪的文章,给我发来信息:此生从未见识真正的雪花,那洁白的雪片啊,何时能滋润我的灵魂?当他经历了二零零八年那场雪后,胆怯怯又发来信息:你们西安一个冬天都是飞雪,不知道会死多少人?他说得没错,一场雪后,阳光再灿烂,也有照不到的地方,阴影里雪的踪迹还在,冰块依然晶莹。如果在秦岭,那阴沟、阴坡的雪迹会延伸至来年的初春。但,雪是不会给北方人带来灾难的。我回信息:在你们南方,雪是魔鬼,在我们北方,雪是天使,这就是区别。他有点明白了,说冬天里,雪便是南北差异的见证者啊。
雪是北方的天使。他描述的一点没错,有我的祖母為证。
平日,祖母总喊腰疼腿痛,蜷缩在热炕上,到了落雪日,她才显出精神,不是坐在门口的凳儿上观雪,就是操起扫帚扫雪。祖母乳名三儿,不像女孩的名字。她是腊月初三那天来到世上,结婚那天也是腊月初三。决定祖母一生命运的那两个腊月初三都下着雪,在地上积得很厚。这真是巧合。出生时的那个腊月初三,她不会晓得;结婚的那个腊月初三,她忘不了。她向我叙述出嫁那天的情景:雪片飘了几天几夜,迎亲的“花车”碾着积雪,载她驶向十里之遥的一个村庄,她流了一路的泪。这是告别之泪,也是迷惘之泪。这一日,将决定她一生的痛苦或者幸福。这个世界留给她最美的镜像,便是一片白茫的雪。
祖母这一生,找到了一个好“主”,祖父虽未使祖母大吉大利,却也让她没有忧伤,恩恩爱爱、平静安祥地过着日子。祖母六十岁岁那年,祖父辞她而去。那也是一个落雪的日子
雪关联着祖母一生的命运,无怪乎她和雪有着那么深厚的感情。
每当下雪的日子,祖母就显得精神。平常的日子,她总是腰疼腿痛,大多时间总蜷缩在热炕上,听见或者看见下雪就来了精神,不是坐在门口的凳儿上观雪,就是操起扫帚扫雪。
看着还在扫院中雪的祖母,我的疑惑消除了,雪和人生并非毫不关联,再广泛一点说,大自然中的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和人的喜怒哀乐联系在一起的。
祖母扫罢雪,回屋,嘟囔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歌谣:
“下雪了,拾钱了,翻个身儿过年了。”
雪是祖母不忍舍弃的生命背景。在她七十岁那年冬天,父亲带她去海南岛。那年,又是祖母喜欢的雪冬,雪将树枝压弯了腰。一下飞机,祖母又是喊热,又是喊累,岛上阳光如火,她头晕目眩。她抱怨着:这地方把人能热死了,来这儿弄啥。到了三亚,祖母向父亲说我不逛了,这地儿连片雪影都见不上,有啥意思啊?
七十三岁那年,祖母死在冬天,那也是一个落雪的日子。这场雪,为她的生命送行,她死得很安详。
止笔时,正是除夕,室外又飘起雪花。这是不是这个冬天的最后一场雪呢?我不知道。我的心思,只在阳台上妻子养的那盆兰花上,黄绿花朵,飘散出清新芬芳,与窗外的漫天飞雪,一起渲染天地间的大美……
【作者简介】赵丰,西安市鄠邑区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小说散文集10余部。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获得者,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散文》《书屋》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8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