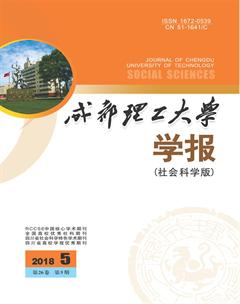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
潘如军 陶雅
摘 要: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之一,在史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史学思想以广博而多变著称。学界将他的史学思想分成了两个时期,在其后期史学思想迎来了一次“绝大的革命”。造成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因素很多,且主要的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同时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虽有批判但也有继承,对待传统史学的态度上虽有弘扬但也有批判,在此种“二重性”的视角下,更是寻求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之可能性。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更能体现梁启超“连续性与断裂性”共存的一生,也就是说对梁启超“断裂性”的后期史学思想的研究,应该置于“连续性”的视角之下。
关键词:梁启超; 后期史学思想; 转变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5-0081-06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他短暂的五十多年生涯中,除了在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建树外,其史学成就也令人敬佩。梁氏史學思想不仅是引领中国传统史学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他的史学思想“庞杂纷繁”,又“变化多端”,经常在中国传统与西来学术之间来回游走,使得后来人对他的史学研究“每每难得要领”[1]12,以至于他自己也宣称“启超之学,则未能定论”[2]90。学界一般性的认识是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分为前期与后期,李华兴在《近代中国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一文中指出,梁启超一生曾有过十次转折,第十次转折是梁“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4],这与刘东在《梁启超文存》中指出的《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在时间上基本上吻合,如刘东说言,这是梁启超“未竟的后期”[3]。关于这一时期梁氏的史学思想被看作其史学思想的后期,而《欧游心影录》也被看作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标志。其主要的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与晚清张之洞等人所提倡的“中体西用”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梁启超晚年遭受了很多批评,诸如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名流都斥其为“反复小人”“言屡易端,难于见信”[5],但仔细考察,在梁启超晚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梁氏后期史学思想,对于西学在批判中继承,对于传统史学在弘扬中批判,其所体现出的梁氏史学二重性远比“中体西用”来的更有远见。本文希望通过对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梳理,勾勒出梁启超在“未竟的后期”所展示的史学二重性,揭示梁启超晚年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的真实态度。
一、梁氏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背景与原因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西方史学思想已经不在是他在高呼“史界革命”时那般神圣与向往,而更多的是对西方史学多了一丝理性的批判,不在将其看作无可替代的学术源泉,而此时的传统史学也重新焕发出新的色彩。对于梁启超产生这个转变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归结于对西方世界的失望,或者是梁启超潜在的传统史学因子的激发可以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梁启超在后期对于西方史学的态度产生转变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梁启超所固有思想特性有关。刘东曾将梁启超的思想特性总结为“善变”与“能悔”,“如果没有‘善变与‘能悔的品格,也就没有了梁启超这位独特的历史人物,而由此他那段历史也就会失色不少”[4]10-11。从梁启超所留下的千万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善变”与“能悔”确实是梁启超一生最典型的特质,在梁氏史学思想上,“善变”与“能悔”更是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梁启超史学思想大体上是从传统史学开始,经历了从“贴括之志”“段、王训诂之学”到“南海之学”,再到西方史学,最后回归到传统史学的历程,期间无论是在梁氏史学前期,还是在后期,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从来都是适时他自己认为的“择善而从”的最佳思想,无论世人是理解还是批判。“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于公理不合于公理,彼个人之良心,常自告语之……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6]76-77,此种“善变”与“能悔”思想的流变从一定程度上为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在梁启超“善变”与“能悔”的思想特质外,“调和”的思想也不应该被忽视。“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7]7调和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是一种被他自己所称赞的品质,也是大批学者研究梁启超思想的立足点。他们将梁启超的调和思想看作他在思想上寻求平衡的努力,来凸显梁启超在各种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等对立思想之间的来回转变(1)。这种调和思想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解释了梁启超史学的“变化多端”,也反映了在梁启超最初学习西方史学的时候,虽然强烈地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但却不会彻底地割舍传统史学的因素。这种“调和”的思想也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对西方社会深入接触有关。学界将梁启超在1919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看作进入梁启超后期史学的标志,而《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在参加完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各地之后,所编撰而成的一部游记,而其内容更多的是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梁启超对于西方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理解,发现以前西方史学思想所形成的以民族史学基调的观念,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一个民族,而西方所宣扬的先进的政治经济形式,与现实又相差甚远。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在继续向西方学习,使梁启超产生了失落与疑惑,从而兴起了从传统史学中重新找到出路的可能性命题。
其三,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世界性的眼光有关。梁启超在欧游期间,考察了多个国家的文化,包括西方的史学,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性格与文化,在这种多元的氛围中,梁启超拥有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相比较而言,中国当时国内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史学”的弃之不理的做法,让梁启超产生了一种要让中国人明白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的想法。“什么是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8]25,而这种责任的基础是将本国的文化发扬光大。在这种眼光的影响下,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回归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四,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的个人对传统史学的学习历程也分不开。梁启超出生于广东一个乡村,其祖父是秀才出身,其父科举不第,二人都谙熟儒学之道。在二人仕途不顺的情况下,都回归家乡,执教乡里。二人成为了乡间民儒的代表,其父更是典型。梁启超成长的环境是中国传统的“世代耕且读”[9]12的乡儒家庭,其祖、父二人对梁启超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祖父教授“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使得梁启超成为一个讲究儒学义理的儒生,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学习传统文化。后与梁父一起“日以课之”,因为家境贫困无丰富书籍可读,其父以《史记》与《纲鉴易知录》二书作为教材,为梁启超传统史学学习奠定了基础,使梁启超吸收了充分的传统史学的养分,为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梁启超和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提供了可能与必然,并不是单纯对西方史学的失望或者是对传统史学的唤醒。
二、梁氏后期史学思想的二重性
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主要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或者是大体上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因为梁启超在这个阶段,并不是个别学者在研究中所叙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将西学和传统史学强制性的分割成两个部分。此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更多是基于西学与传统史学两个统合的角度去批判西方史学、去弘扬传统史学,同时梁启超在对西方史学批判的同时继承了其优秀的部分,对传统史学进行弘扬时又剔除了其糟粕的部分。在梁氏后期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这种复杂的情绪与视角,我们且将其称为“后期史学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不仅显示于对西方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态度中,也彰显在西学和传统史学在对立中寻求统一的思想中。
(一)西方史学:批判中继承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于西方史学的主要态度还是批判,或者说是梁启超在又一次近视整个西方世界后,对于西方史学产生的反思,与梁启超前期宣扬“新史学”时想法不同,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起初梁启超将进化理论运用到史学中,开始建立以西方“民族史学”为营养的新史学,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认为历史就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进而明白“人群进化之现象”,从而得出進化的“公理公例”[10]。他极力批判传统史学。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传统史学有“四病”“二弊”六项弊端。他说传统史学歌颂的是“朝廷”“个人”“事实”和“陈迹”,而对于“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却丝毫不在意,而且传统史学“不能别裁”“不能制作”,与西学相比相差甚远,猛烈地抨击传统史学的要害之处。在梁启超的心中,西学是“救世良方”,而传统的思想是阻碍民族取得进步的阻碍。
随着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到后期,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充满了理性的视角,他发现自己所崇拜的、认知的西学并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全貌展现给自己,其中很多不好的方面被“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外衣所掩盖,而中国的传统史学思想在片面地对西学吸收对照下,产生了不公正的对待。即使是在被认为“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11]的《新大陆游记》一书中,梁启超也已经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失落,“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12],在真实的接触下,对于西学的动摇已经昭然若揭。再到他的第二部游记,他对西学态度的转变更加明显。
梁启超的第二部游记,是他退出政坛以私人身份游学欧洲后,将其一路的见闻与思考编著成书,也就是《欧游心影录》。在书中,他再一次地近观了西方社会,如同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看到的一样,繁荣的背后总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黑暗,这一次,他不再是对西学动摇和失落,而是产生了对西方文化中“物质”和“精神”的深刻探讨。也正是这次欧洲游学,让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正是发生了转变,他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史学对于构建当时的社会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他开始着手以科学的方法去诠释传统文化的含义。
他发现近代西方社会过度地相信“科学万能之梦”,催生了各种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不利于社会的思想,称“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精神世界由此产生了混乱,而“精神”较之于“物质”更为重要,“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8],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称“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13]819,他认为以东方先哲的眼光去看西方文化,可能得到的结果是认为其浅薄。梁启超在种种的经历与思考中,开始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批判的思维。
但是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批判,并不否认西学当中优秀的成分。梁启超曾宣称“欧洲科学破产”,但他也在文中的注释标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8]5。这种理性看待西学的态度,使得梁启超对待西学在批判中也有继承。这表现在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的研究中,他并不抗拒运用西方的理念,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例,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又或者用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史学,使传统史学得到重生。总而言之,在梁启超史学的后期,对待西学虽然还是以批判为主,但是其中依旧蕴含着梁启超理性的态度,对于学中优秀的部分同样的吸收运用。
(二)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
如同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待西学的态度,他对于传统史学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倾向虽是以弘扬为主,但绝不是力求传统史学全面的回归,而是要在经过“史之改造”后,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史学,摒弃传统史学落后的、保守的思想。
自1919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文完成后,其后发表的文章多数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史学有关。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中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其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在《补篇》全书约11万字中,传统史学的色彩跟以往的著作相比更是非常浓厚,提倡要继承传统史学,而且全书很少提及西方的案例,更体现了梁启超写《补篇》的主旨,是为传统史学正名。这与前期他在如《新史学》等文中所宣扬的有着明显立场转变。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是梁启超前期的史学思想,还是后期的思想,他的远见似乎都超越了时代,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尤其是在后期。当时中国的学术洋溢着西方的“洋文化”,而梁启超却反其道而行,提出要弘扬传统,可想而知当时的梁启超要遭受多少人的恶意。但梁启超却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更深层次地去理解,而不是套用着西方史学的外衣,来美化着中国传统史学。就像梁启超曾经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14]240。他指出胡适对于中国的哲学,用西方所谓的知识论去研究,殊不知中国的哲学根本不是以知识论为立足点,到头来结果是将传统中的精华舍弃而造就了“二不像”,西学与传统史学都遭受扭曲。我们先不评论梁对于胡适的评价是错是对,但梁启超对于传统的观念,应该是值得深思的。
前面说到,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主要态度是弘扬发掘,但也要有选择的弘扬,对于糟粕的部分,要批判改造。他曾指出,中国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他解释道:“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中国学术界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精神,才导致了“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佚”五种病症,“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千年”[15]282-286。这段话来源于梁启超1922年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而写的讲演稿,文章的主旨是希望科学社为中国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却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希望能克服这样的弊端。这恰好契合了梁启超后期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虽以弘扬为主,但也要求在弘扬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改造,批判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
(三)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之可能
勒文森是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曾将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转变归结于一种眷恋故土的情感(2),但是刘东对此就提出了疑议,他认为梁启超并不是单纯地在“恋旧的‘情感与趋新的‘理性之间”[4]6来回摇摆,“恰恰相反,那心念倒是来自一种相当精巧灵动的‘交互文化哲学”[4]29。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说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相似但却有本质性的不同,按照勒文森的说法,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应当是对“中体西用”的回归,而梁启超思想中传统的因子正好也为此提供了基础,可事实上,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并不是如此,而是在两者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对西学的批判中继承、对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同时积极地寻求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的可能性。
梁启超在此种“交互文化哲学”的思想的引导下,为实现文化互补设定了四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8]27,这也是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表现的最明显的特征,认为“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的一文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可笑吗?”[8]26“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他的真相”[8]27,在尊重本国传统的时候,必须要借助其他文化优秀的方式来整合自己的文化。“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学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8]27,将自己本国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互补之后,形成新的符合自己民族、符合时代的文化。“第四步,把这新文化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8]27,这也是梁启超对于文化互补的最终设想。
而西学与传统史学遵循上述的思路,梁启超认为两者也会有相互补充的可能性,并且也付诸于实践。上文也提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但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新做法有着明显的西学治史的途径,又如《先秦政治思想史》,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可见,在梁启超后期史学中,西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由对立开始走向了融合,两者不再是时人所认为的不能共存的“敌人”,这也是对梁启超“国粹派”与“西学派”的回答。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背景等因素影响下,梁启超的后期史学看似有较为明显的转折倾向,但实际上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很多。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对于两者交互的态度,都显示出梁后期史学的二重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对传统史学自觉靠近的同时,对两者采取的“中庸思想”。“‘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于两极端,常常取折中的态度。”[16]54传达出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这一时期对于传统史学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西学,二是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又不偏不倚,对两者都进行了褒贬,并且两者在平等的地位上可以实现互补。
同时,从梁启超在前后期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态度来看,后期史学较之于前期确实有很大的改变,但也是对前期史学思想的深化,前后期不可分裂而看待,因为在梁启超史学思想中贯彻的主线始终是一脉相承。虽然笔者所论述的是梁启超后期的史学,但涉及的依旧是“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途”,“我们必须努力的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4]2。
李华兴曾说梁启超一生“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3],而对于史学而言,梁启超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爱国之心”与“以史救国”始终贯彻如一。起初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号召“史界革命”,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而批判旧史学,称其不能将史学的功用普及普通的民众,从而学习西方史学,建立可以救中国、激发国民性的“新史学”。他接受西方史学的观念,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他的史学思想处处体现着他爱国救国的热情。到后来,梁启超史学思想的重心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的时候,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更是体现着他的“以史救国”的热忱。在他晚年回顾他的史学生涯时曾这样说过,“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5]346。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善变”的史学思想中,贯穿着他一如既往的爱国热情。
总而言之,造就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因素复杂,而具体的史学思想内容又有二重性,并且在“连续性”的视角下,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也有继承前期史学观念之处。还要注意的是,任公因为“连续性与断裂性”相交替的一生,很容易导致学者片面地看待其史学思想的某一部分,将其一生中某个片段作为研究对象。在而当下,对于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探究不仅要研究转变的因素和转变的内容,还要在全局性眼光下去看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种种内涵。
注释:
(1)从调和思想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思想寻求平衡的观点,参考刘东先生《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一文,载《中国学术》第32期。
(2)参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刘伟,刘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李华兴. 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J].近代史研究,1984,(2):198-217.
[4]刘东,翟奎凤. 梁启超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5]夏晓红. 追忆梁启超[M].上海:三联书店,2009.
[6]梁启超. 自由书[M]//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梁启超. 新民说[M]//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刘东,翟奎凤.欧游心影录[M]//梁启超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9.
[9]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梁启超.新史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冯天瑜. 剪不断理还乱: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两极评断说开去[N].光明日报,2010-08-24(3).
[12]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梁启超.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词[M]//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梁启超. 梁启超演讲录[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5]刘东,翟奎凤.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M]//梁启超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梁启超.孔子[M]//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Abstract:Liang Qichao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holars in modern times and has achieved rich achiev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His historiography is famous for wide variety.The academic circle divided his historiography thought into two periods, and in his later historiography thought ushered in a “most revolution”. Many factors caused Liang Qichaos later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in feature was returned from western learning to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At the same time, the attitude towards western learning was criticized and inherited, which was carried forward but also criticized in the attitude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is kind of “duality”, it is more likely to seek the complementary possibility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nsformation of Liang Qichaos later historiography can reflect more Liang Qichao “continuity and disjunctive” coexistence of life, that is to say, the study of Liang Qichaos “broken” later historiography thought should be place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uit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later historiography thought; transformation
編辑:黄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