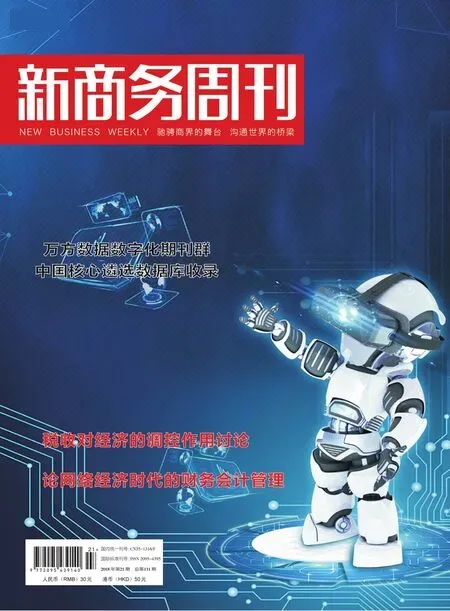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国家安全审查的风险及对策
文/刘先雨,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势头一直保持迅猛增势。2016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投资交易达到438 笔,较2015 年增长了20.94% ;而累计的交易金额为2,157.94 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了147.75% 。而这一趋势在2017则出现明显放缓,2017年前六个月中国并购活动交易总额达到2829亿美元,与2016年下半年相比降低20% 。中国企业的高歌猛进也引发了很多国家的担忧,近期在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投资的热点国家接连出现关于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或法律政策的调整,显示各国都在地收紧外国投资审批,体现了在发达国家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
1 主要发达国家安全审查的最新立法与现状
在海外并购中,很多国家都有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即对涉及国家安全或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进行严格审查。设立这一制度目的是防止一国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关键性或战略性资产(尤其是国防安全领域的资产)被其它国家的投资者所控制。但近期多个国家都对国家安全审查明显存在扩大范围和和收紧审查的趋势,使得国家安全审查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最大法律风险之一。
1.1 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
美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复审和调查的主要机构是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 CFIUS),该机构由福特总统建立于 1975 年,设立目标是协助总统就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监督。但这一机构作用的真正发挥是在 1988 年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立之后。美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立的标志是1988 年的《埃克森—费罗里奥修正案》,该部法案修订了 1950 年《国防生产法》的第 721 节,授权美国总统广泛的权利来停止“损害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外国收购、合并与兼并。
1.2 德国的国家安全审查
德国于2008 年通过了对《德国外国贸易与支付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在获得议会批准后,于 2009 年 4 月 24 日正式生效,从而建立起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根据这一立法,当欧洲境外的投资者收购德国企业或者获得其 25%以上的表决权时,如果这一收购构成对德国安全或者公共政策的威胁,则德国经济与技术部有权禁止该项交易。2017年7月18日,德国出台外商监管新政,新政在某些方面参照了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1.3 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审查
加拿大规范外国投资的专门立法为《投资加拿大法》。根据该法,收购加拿大企业或者在加拿大设立新企业的投资人必须通知加拿大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在进行投资前获得批准。2009年 3月前,该法中并不包括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的内容。但在实践中,加拿大政府仍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并购的进行,如在2004 年,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试图并购加拿大矿业巨头诺兰达公司,加拿大政府便对该交易展开严格审查,导致五矿集团最终放弃该交易。2009 年 3 月,加拿大对《投资加拿大法》进行了修订,创设了对外资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之后又制定了该法的两个配套条例——《加拿大投资条例》和《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条例》。
1.4 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
2000 年,法国曾以外资对法国科学教派的入资损害公共安全利益为由禁止该项投资。随后,欧盟法院判定法国对外资投资的禁止违背了欧盟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要求法国应清理其有关投资限制的法律。因此,法国于 2004 年制定了2004 - 1343号法律,改革了外国投资审查程序。2005 年 12 月,法国发布了第 2005 - 1739 号法令,作为《法国货币和金融法》第 L.151-3 条的配套规定。该法令明确在 11 个行业中,当外国投资者准备获得其控股权或特定部分股份时,应受到基于“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国家国防利益”的审查。
1.5 日本的国家安全审查
日本《外汇与外贸法》制定于 1949 年,并在1991 年进行过较大修改,该法是日本政府据以进行外资投资安全审查的主要法律。该法规定,政府部门在发现外国投资如有害于日本的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以及经济的平稳运行时,有权禁止外资进入或者设置条件。该法授权金融部和工业部审查外资并购,在收到外国公司收购意向通知后 30 日内审查相关交易。如果投资者在 30 日内未收到审查结果,则该收购被自动批准。但如果审查部门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延长这一期间到 4 个月。
2 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步骤与情况
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是发达国家中最为严格的,且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审查有进一步严格的趋势。
2.1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步骤
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的两个关键条件为 “取得控制” 和 “影响国家安全” 。首先,判定是否需要审核 ,要看目标公司在交易完成后是否会被外国人,尤其是外国政府 控制。根据CFIUS的规定,如果交易是 “消极投资” (一般指纯财务性质的投资)且外国人或企业收购的美国公司份额不高于10%,则不存在控制。而任何投资额度超过目标公司10%股权,或者并非为消极投资目的而进行的交易,都很可能被认定为存在控制。
其次,目标公司从事的业务是否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总的来说,涉及基础设施、信息安全、国防、通信、航空、交通、军用、能源是可能会引起国家安全顾虑的行业。近年来,除了这些传统的敏感行业之外,对一些涉及到尖端科技的行业,诸如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大数据分析等,CFIUS也加强了重视。除此之外,CFIUS对外国投资者在收购后可能获取美国居民个人信息的交易也更为警惕。
2.2 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数据及情况
根据CFIUS的年度报告,2007年仅有3起,2012年迅速增为23起,2014年有24起中国企业在美并购交易被审查,占到当年审查总数的16.3%,连续3年位列审查案件总数之首。
据统计1990—2015年间,CFIUS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干预阻挠的中国企业并购交易主要有14个。其中,8个国有企业并购交易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遭到阻挠,包括中航技收购Mamco、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石油公司、西色国际收购美国优金公司、唐山曹妃甸投资集团收购美国光纤设备制造商Emcore、鞍山钢铁投资美国钢铁发展公司、中兴通讯参与竞标美国Sprint项目、紫光收购西部数据和紫光收购美光科技,占到总数的57%。5个私营企业交易以“具有军工背景”为由加以阻挠,包括华为竞购2Wire、华为竞购摩托罗拉移动网络基础设施部门、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联手收购3Com公司、华为参与竞标Sprint项目、华为收购美国3Leaf,占到总数的36%。2 017年有多起中国赴美投资项目未通过CFIUS审查,这些项目涉及了金融服务、高新科技等不同投资领域,如: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案。
3 应对国家安全审查风险的对策
3.1 企业面临国家安全审查的对策选择
3.1.1 诉诸东道国或地区的司法审查程序。在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机构作出否决并购交易的决定后,投资者可以通过提起法律诉讼的方式,启动对安全审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司法审查的好处在于,通过法院诉讼的程序,可以减少在安全审查中概念与认定的模糊性,从而降低政治因素的干扰。目前,德国、日本和法国均规定,针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机构作出的决定,可以提起司法诉讼。另外,在欧盟内部,尚可以针对其成员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在欧洲法院提起司法程序,从而改变该国不恰当的法律规定。
3.1.2 诉诸WTO 规则。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在面对不当的国际贸易保护方面可资利用的国际协定之一。因此,当中国的海外并购的目标是 WTO 成员国并且为服务领域公司之时,如果遭遇不当的国家安全审查贸易保护之时,可以申请启动 WTO 的争端解决程序。应注意的是,在海外并购时,适用服务贸易总协定防范国家安全审查会遇到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服务贸易总协定仅适用于外国实体获得目标公司控制权的情况,因此,在并购仅涉及到较少股份时无法适用该协定。第二,服务贸易总协定包括部分例外情况,如对政府部门提供服务的例外情况等。
3.1.3 应对投资国的国家安全审查进行充分的分析和预判。一些过往对中国没有严格审查或限制的国家现在发生转变,而一些传统上非敏感性行业也成为审查焦点,这需要中国投资者特别关注。投资者在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时也需特别关注,是否涉及政府合同、敏感资产、敏感信息等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充分评估与国家安全审查相关的风险。
3.1.4 在设计交易架构时应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因素。例如,很多国家的法律对国有企业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审查程序。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尽量通过市场化的企业或基金结构进行并购、主动剥离敏感资产(如涉及军工或政府合同的业务)、或者在东道国寻找合作伙伴联合行动等,以减轻东道国政府的顾虑。
3.2 建立健全我国政府对跨国并购企业的保护制度
3.2.1 应加快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的步伐。这部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其中内容包括: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则、海外直接投资管理制度、海外直接投资主体范围和投资形式、海外投资的法律责任规定,以此形成了一个以海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为主体,各种单行法律和机关配套为辅的调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
3.2.2 成立专门的管理境外投资的机构。由商务部牵头,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委共同派员组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管理委员会,在宏观上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协调、规划,彻底扭转了以前各个部门彼此之间缺乏协调、权责界限不清的局面。
3.2.3 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严格规定海外投资企业的风险投资限额和投资资格的评估制度;强化对海外企业的后续管理,加强税收、外汇、财务制度的监督;对国有资产的海外投资项目采取投资责任主体制度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即“谁投资,谁负责”原则;同时,把民间投资主体的海外企业纳入政府监管范围,接受政府部门的审批或备案,防止资产的境外流失。
3.2.4 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这项制度重点对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承保险别、合格东道国和代位权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对合格东道国不应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覆盖到与我国有投资往来的发达国家。而且对投保范围、投资本身的性质、保险金额、保险费等内容也做出适合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特点的规定,使其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我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