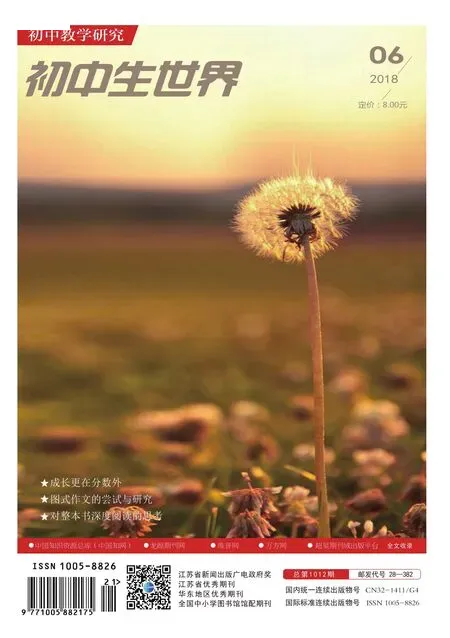“硬读”,是一种别样的陪伴
——以《一个人的村庄》整本书阅读为例
■陈 怡
一、走进村庄:感受别样的乡村
深秋,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郑重地把58本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交到全班同学手中,期待开启一段新的阅读旅程。为了增进孩子们与此书的感情,我请他们抚摸了书的封面,感受其质感,又一起品读了封底的文字。
就这样,让孩子们与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牵手,我可以像往常一样先退到一边慢慢欣赏孩子们与作者进行心贴心的交谈了。然而读了一周,孩子们纷纷开始抱怨了。
初次捧起它的脸颊,品读它的心声,我的脑海里却是一团麻。这到底算什么文体?记叙文?故事却往往说得令人摸不着头脑。散文?它却不像平常所读的一些大家笔下的文章。它围绕着黄沙梁这个村庄,说着这个村中的狗马牛驴和花草树木,却说得无厘头,有些像周星驰的电影,动不动就蹦出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让人着实想不通。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乱七八糟。但老师却不管,硬让我们读下去。我也是硬着头皮照做了。(周文熙)
这本书确实不似以往阅读经典那么顺水行舟进入文本。学生在江南小城快节奏地学习生活久了,突然闯入西北农村的慢生活,产生了阅读的陌生感;在心灵鸡汤式的散文阅读中平面滑行久了,突然遭遇有深度的阅读,再加上刘亮程独特的个性化表达带来的不适感,孩子们走进村庄步履艰难。但我相信,慢慢啃,终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了让孩子们更快速地“走进”村庄,我寻找到“硬读”的第一个触发点:抓住孩子们猎奇的心态,利用文本阅读过程中的陌生感、新奇感,请他们找一找黄沙梁迥异于我们平日所处环境的独特风貌。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边疆独特的风景,诸如无垠的荒野沙漠、起伏绵延的沙梁、“东荡西荡”的风、慢驴快马、家狗野鼠不断进入视野的时候,孩子们渐渐走进了刘亮程的“村庄”。孩子终有领悟:
刘亮程就是在给我们讲黄沙梁,讲黄沙梁中的每一件事,大至一头牛,几群狗;小至一只蚂蚁,几缕风。其实,他就是在讲自然。刘亮程以一种充满乡土气息却不乏细腻朴素的笔调为我们勾勒出他家乡的大自然,使人眼前能瞬间浮现那一个个充满生机的场景。他以谦卑的态度面对自然,赋予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以灵性,再向它们学习、讨教,悟出哲理。(蒋宇彤)
因期中考试,阅读中断一周之后再次开启,有孩子流露出对这本书的依恋:
时隔一周,再次翻出这本书来阅读,还真是有些怀念。有些怀念作者刘亮程随性的文笔,同样也怀念黄沙梁。拿出书,“哗哗”翻几页,很快,目光停留在那个红蜻蜓书签夹着的一页,手指轻轻地在页脚翻了一页。哦,又要开始新的一辑。(蔡琬仪)
二、走进村庄:体悟独特的个性化表达
渐入佳境,我构筑了“硬读”的第二个触发点:体悟独特的个性化表达,汲取刘亮程的文笔精华,锤炼感知周遭事物的慧眼、聪耳、灵性。
孙绍振曾说,对于作品分析来说,最为精致的分析就是在经典文本中,把潜在的、隐秘的、个人的创造性风格分析出来。所以,品读刘亮程的文字,我们没有仅停留在好词佳句的赏析、修辞的妙用上,没有去挖掘深层次的难以琢磨的意象,如黑夜、火、门、钥匙等,而是尽可能地寻找作者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独到且有见地的思想和情感。
经过交流探讨,我们粗略地概括出刘亮程语言的三大特色:
1.众生平等的视角。
在常态的散文用笔中,众生平等的概念往往只停留在推己及人的人文层面。人在与自然万物的相处中,人至多只是个冷眼或热心的旁观者,如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看“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的瓢虫,丰子恺《清晨》中赏“扛着镬焦西行,好像一朵会走的黑瓣白心的菊花”的蚂蚁。但在人畜共居的黄沙梁,刘亮程却与驴互通心性,对一朵花微笑,陪伴一只小虫走完最后的“虫生”……黄沙梁滋养了刘亮程细腻而悲天悯人的情怀,赋予了他与黄沙梁万物相通、众生共享的灵性。
2.慢艺术的领略。
“我没有太要紧的事,不需要快马加鞭去办理。牛和驴的性情刚好适合我——慢悠悠的……许多年之后你再看,骑快马飞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
这种慢悠悠的表达在《一个人的村庄》中随处可见,在刘亮程的笔端,时间仿佛放慢了自己的脚步,黄沙梁一切人、物、事都慢了下来,呈慢镜头式。
诚如刘亮程答《文艺报》记者问时所说:“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细的,是停下来细观慢察的。我喜欢那些停下来不动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到。”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急吼吼地往前赶,以至于落下了灵魂,忘却了当初为何而出发。而刘亮程的“慢”文字,“慢”表达,恰恰给了我们从容关注周遭的人、物、事的启迪。的确,“在心中珍藏一个磅礴日出,比存多少钱都有价值”。
我也常常在闲下来的时候,去青果巷走一走,从这一头,数砖头的个数,一直数到那一头。数着数着就被一辆慢悠悠的自行车铃儿打断了,再开始也不记得数到哪儿了,随便想一个继续数下去,反正数砖头这种活计我也不是非得要干,只是这样我的时间就满了,干了很多事儿的样子。(陈佳立)
作者觉得牛、驴的慢性格适合自己,生动表达出自身对慢生活的无限向往。时间流逝,慢一点,留心周遭的一切,不要心急,你会发现更多的美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这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吧。(俞佳希)
读《一个人的村庄》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什么事情都是慢的,仿佛那里的人们从来不用担心秋天的丰收、来年的粮食,他们只活在当下。(蔡琬仪)
在慢艺术中,我们跟随“乡村哲学家”刘亮程,用哲学的眼光审视黄沙梁的一朵花、一株草,一粒小虫、一匹逃跑的马……逐渐悟出哲理,跟着作者漂泊经年,终于明白,“我没有天堂,只有故土”。
3.“声音”的独到捕捉。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刘亮程有一对聪耳,各类“声音”流淌于字里行间。
一个听烦市嚣的人,躺在田野上听听虫鸣是多么幸福。大地的音乐会永无休止。
夜晚的田野虫声连片,各种各样的虫鸣交织在一起。“有一丈厚的虫声。”虫子多的年成父亲说这句话。“虫声薄得像一张纸。”虫子少的时候父亲又这样说。
将文本中的声音归类,我们发现,这些声音中有黄沙梁的各类虫鸣鸟叫牛哞驴嘶;有人们日常生活劳作发出的声音;有祖祖辈辈血肉精神传承的声音。倾听的时候需要屏声敛气。漂泊多年后刘亮程又是多么渴望重新融入黄沙梁,于是借助“声音”独具匠心地传达回归精神家园的心声。
声音真的是最神奇的感觉之一。视觉的信息最多,可听觉却让你更由心底感到情绪、感到气氛、感到存在。听到鞭炮时,立马可以想到大年初一的早上。可你看到鞭炮,就只是鞭炮了。(陈柘宇)
都市里灯红酒绿,充斥大街小巷的流行乐,喧闹而又刺耳,令我远而避之。黄沙梁这个地方,也充斥着喧嚣:虫子的呢喃,父母的话语,早起的问候,半夜的鸟鸣,都在风里消失、远去,化作一片寂静。我在寂静中听到了生命的声音,那是温情的,细腻的,它是刘亮程的心声。(周雨婕)
声音无处不在,刘亮程在声音上加上了感情,是童年的捉迷藏,抑或是回乡的一声叹息。《一个人的村庄》记载着作者家乡的隐退,但是却在作者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子。声音是家人之间情感的交流,是各种性格的碰撞。性格差异,声音不同。回忆声音,便是回忆亲人,思恋家乡。(孔喆)
三、走出村庄: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一种方式进入世界。我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首先是从一个村庄开始的”。
我们跟随刘亮程走进他的“村庄”,感知了他进入世界的原点——黄沙梁,但我们自己进入世界的原点又在哪儿呢?是走出刘亮程的村庄,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
有了前面的大量输入,输出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一个人的村庄》共读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别了,朋友——《一个人的村庄》”阅读分享课。
本以为一本书读完了,它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可是一本好书却绝不仅仅如此。《一个人的村庄》是读完了,但它却仍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我从前是个不爱观察的人,走路于我来说便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一种方式,可是最近却总不爱“好好”走。那朵被其他云甩在身后的孤独的云,是没有意志力继续长跑还是因性格古怪别人都在排挤它?那片随风飘落的叶,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自由的热爱,还是其他叶嫌它太占位就残忍地将其逐出家门?我以为自己过于多愁善感了,但又觉得不像。思来想去才知道,我是被刘亮程给“传染”了!(周文熙)
村庄已经拆了很多次,以前的田野变成了店铺。小街里,偶尔遇见几座危房,上面已经有人不留情面地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家,记忆又浮现在眼前。那是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年龄小,没作业,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去,住在充满田野香气的屋子里,心情也愉悦了起来。小孩子不懂事,家里的墙十分空,看着不舒服,当时正迷上了公主住的城堡,便想在墙上画个城堡。说做就做,小小的我十分吃力地从田野里搬来几块不大不小的石头,随手一摔,石头碎了,我捡起小石头,用来画画。刚想画,却发现颜色过于单调,便拿来蜡笔,准备上色。一切准备就绪,开始画。先画了两个近似长方形,做一楼和门,又画了一个“田”字做窗户。拿起蜡笔准备上色时,突然发现城堡太小了,于是又加了几个大的长方形做二楼和三楼,可惜那时的我太矮了,够不着,便搬来了小板凳,站在上面画。画了一会儿,拿出蜡笔,一支、两支、三支、多支暖色系的笔在我手中绽放,让家里更加绚丽。粉色,红色……那城堡便像一朵花,带着我童真的幻想在墙上怒放。这个如花一般的墙,很快就被妈妈发现了,那哭笑不得的表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王晗渝)
跟随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走个来回,我发现,逼着孩子们在文本中捕捉文字的内涵和作者独特的个性化表达,是可以达到“心灵渐通”的;还能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结合生活体验,个性化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尽管他们对“村庄”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也许有失偏颇,但孩子们生成的札记、创作的文字,却是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