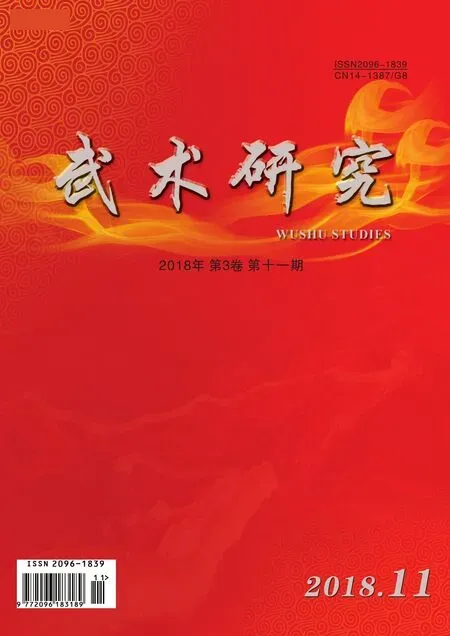中西方竞技体育胜负观比较研究
王艳艳 李海燕
南京工程学院体育部,江苏 南京 211167
1 前言
全球化以来,中西方价值观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但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积淀与形成过程不同,古代中西方在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体育作为一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化,也同样折射出中西方竞技体育价值观的异同,其主要表现为中西方竞技体育胜负观的差异。
2 古代中西方体育胜负观比较
2.1 古代中国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造就了华夏文明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广阔的平原,农产品的相对丰富使中国人过上了定居的农业生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血缘机制得以延续,军事征服后产生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大国,继而是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反映在思想方面,即推崇不争。老子曰“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庄子曰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相对,争之无益,君子矜而不争。在古代中国,在这种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下,在这种“不争”思想的影响下,很难产生竞技体育,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较多见。礼射是古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竞技项目,但在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下很难存在公平竞争,以大射为例,天子可用3侯(虎侯、熊侯、豹侯),诸侯用2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只能用1侯(豹侯),所以礼射的主要目的是“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1]中国古代体育鲜有竞争,在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下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比较典型。
2.2 古代西方公平竞争的体育价值观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地处地中海东部,自然地理条件多山环海,土地多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客观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希腊人以商贸航海为主体的经济,也造就了希腊文明勇于开拓善于求索的外向型文化。[2]曲折的海岸线,复杂的丘陵山地,多变的地理环境使得希腊人多从事商业贸易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蒙昧时代的血缘关系纽带被流动性很强的生活方式冲破了,形成了以地域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和比较健全的民主政治,反映在思想方面就是希腊人推崇平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希腊人在航海贸易中经历着自由贸易中公平的竞争,反映在体育赛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很好的诠释了希腊的公平竞争,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竞技者可以在竞赛规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己的实力充分展现自己的天赋去争取比赛的胜利。公元前561年,哲学家卓罗斯参加了奥运会比赛,并在原有竞赛规程上为奥运会草拟了一份更为庄严的赛程规则,即“竞技赛会的仲裁委员会由宙斯神殿中专职祭司及其经过选举产生的裁判人员共同担任,以保证运动会的绝对公正”。古代奥运会早期比赛的胜利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与美并搏得神的欢娱,胜利者得到的奖品只是诸如橄榄枝桂冠和月桂冠的奖励,但人们对于他们的尊敬却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到了后期,运动员的争胜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更多的是为了既得利益,《奥德赛》中就曾赤裸裸的揭示了运动员参加竞技的动机“你一定参加过许多英雄的葬礼,为了尊祭死去的王贵,年轻人束扎准备,为争夺奖品,参加比赛”。[3]
3 中西方近代竞技体育胜负观比较
3.1 中国近代竞技体育胜负观
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社会变革对价值观念的改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世纪中期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在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4]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传入的科技文明成果,并意识到只有接受西方的文明价值观,才能完成向近代社会转变,从而达到与西方国家同等的发展水平。西方的竞技运动项目也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传教士的涌入传入中国,中国在运动场上接受了西方公平竞赛的价值观,西方的奥林匹克思想也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胜负价值理念中,并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被逐步接纳,1932年中国参加了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近代竞技体育是在民族危亡时被动从西方引进的,因此它被深深打上了“救国图存”的烙印,这也使中国在国际比赛中比较重视比赛的胜负,以努力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近代竞技体育的胜负往往与民族解放、民族自强联系在一起。
3.2 西方近代竞技体育胜负观
中世纪前期的西方体育被基督教所封杀,只有骑士教育中侥幸存有体育因素。骑士比武前都要祈求上帝的掖助,并且往往把胜负归之于上帝的倾向。虽然骑士比武享有很浓厚的宗教情感,但仍是在公平的竞争机制下进行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使体育从宗教的禁锢中走出来,现代西方竞技运动项目应运而生,奥林匹克运动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西方社会思想文化运动开展的大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随之产生,它表达了运动员在赛场上面对强手不断进取,勇于斗争,敢于胜利,超越自我的拼搏精神。与此同时,奥林匹克运动提出了“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至理名言,这是以全人类不断完善自己为出发点,绝非仅仅是号召人们单纯的为了夺取桂冠和金牌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5]但是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竞技体育进入了职业化阶段,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假球、黑哨、兴奋剂事件层出不穷,突显出体育职业化阶段人们对胜负价值观的理解发生了扭曲。
4 中西方现代竞技体育胜负观比较
4.1 中西方现代胜负观评价标准的差异
胜负价值观既体现了人们对竞技体育的价值追求,又内含了人们对竞技体育的评判准则。中西方现代竞技体育胜负价值观围绕各自不同的基本价值目标(或取向)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这体现了中西方在对竞技体育胜负观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分析中西方竞技体育胜负价值观评价标准的差异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1.1 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
政治制度和思维方式是影响中西竞技体育胜负观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思维方式对各自竞技体育的胜负评价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在西方客观评价则更多地运用逻辑,思维缜密严谨,有理有据,严格求证。西方在对运动员胜负成绩进行评价时,理性思辨和实证分析是评判竞技体育胜负观的两大特征,同时也是西方体育文化与生俱来特点,所以往往能对成绩做出较公正的评价,从而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胜负,并在评价过程中比较注重应用与实践。与西方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及其不同的政治制度相比,中国的评价思维更着重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习惯基于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直觉指引,有时会掺杂个人情感和个人认知,来实现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的判断,有时会忽略细节和过程,所以当客观现实不能实现主观愿望时,就会影响胜负的有效判断。因此,迫切需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对竞技体育胜负观及其评价进行综合评价。要客观合理地评判输赢。二者各有优劣,因此把两者有机结合,是中西竞技体育文化的“和合”。
4.1.2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
我们在进行评价时往往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把定性放在首要地位。因此在评价胜负的时候,要注重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比赛过程中的具体表现,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想结合。在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说话,强调评价客体的可度量性,注重把握事物推进的节奏。西方人在看待成绩的时候,往往不是以胜负来评判,而是以数字为记录的量化评价。一方面,以世界记录为依据分析冠军比赛成绩的含金量,另一方面,运动员自我超越的进步也被视为胜利。
4.2 中西方现代竞技体育胜负价值观比较
4.2.1 为国争光与服务于人
中国文化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一和群体利益的维护。[6]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重集体主义,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先。这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国家主义呈现的必然性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技体育由国家财政出资,竞技体育更多是作为了一种强化国家形象,提高国家威望,振奋民族精神的工具。同样奥运会比赛的胜利往往都会归结为国家和民族进步的一种体现,中国国家运动员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离不开他身后祖国的支持。因此,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运动员的各项利益也应予以保证,从而避免运动员退役后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现象出现,例如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现象便引发了社会对此现象的诸多思考。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国的蔓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均衡发展,我国运动员的利益也得到了有效保障,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从西方体育文化而言,是以个性发展和个体生命能力弘扬为主体,个人得到充分发展才能有社会的进步,服务于人作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体本位的意识是西方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具有最高的价值。西方注重通过个人奋斗来取得自我的成功,促进社会的发展。[7]而在西方,只有个人追求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促使社会的充分发展。西方国家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现阶段以不再将竞技体育的优异成绩作为宣传的工具。运动员的各项权利得到相对完善保障,运动员可以全面系统的接受竞技能力及潜力的培养,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培养,从而塑造了相对全面发展的运动员。[8]运动员在学校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毕业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适应社会,而且西方运动员在从事竞技体育运动时往往都有运动职业规划,这为他们退役后顺利走向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西方运动员在比赛中受伤,往往会停止参加比赛并休假疗伤,直至完全康复。不管比赛会为国家争得多大的荣誉还是为自己赢得丰厚奖金,运动员都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运动生涯做赌注。但是西方重人本主义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国家利益,运动员在职业比赛中赚取的奖金,这使得部分运动员排斥进入国家队,有的甚至拒绝为国参赛。例如NBA球星奥尼尔、卡特、邓肯、科比、加内特等因个人原因拒绝了美国篮协的邀请,导致昔日冠军梦五队雅典奥运会上的溃不成军。因此西方这种从个人出发来立论,所以个人与集体就会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
4.2.2 金牌至上与重在参与
当今竞技体育高度商业化,当竞技体育不断职业化、商业化、产业化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体育竞技成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突破口,市场经济的功利化原则和理念在竞技体育领域同样得到渗透,由于竞技体育成绩的获得不仅可以给运动员带来掌声、赞美、荣誉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整个团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加之历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就存在“成王败寇”的观念,因此,金牌的归属就显得重要。
西方注重参与的价值取向是大众文化的一种体现。纵然奥运会夺金是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最高体现,但西方人认为体育比赛重在参与,认为只要是参与了就是胜利者。西方深知比赛中的冠军只有一个,有些运动员受自身能力或客观条件的限制,比赛中并没有冲击金牌的能力,但是却因为参与其中而受到社会的肯定。西方运动员这种重在参与的精神这与西方国家学校实行的奖杯主义教育不无关系。在奖杯主义教育中,参与比赛的运动员都可以得到奖杯,这是对他们参与比赛的充分肯定。观众不仅给予胜利者赞赏,对于其他运动员也毫不吝啬的给予掌声,并不忘献上赞许。
4.2.3 荣誉至上与拜金主义
在中国,竞技体育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誉的思想渗透于人们精神意识的深层。中国人把荣誉置于物质利益之上,甚至把荣誉和物质利益对立起来,割裂开来。[9]1995年7月国家体委颁布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振奋了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10]体育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把运动场上的优异成绩与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这种荣誉至上的价值观,激发了运动员斗志,激励运动员创造了优异的运动成绩。
20世纪工业社会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价值观也影射到竞技场,金钱成为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的重要驱动力。西方把竞技体育推向了市场,商业化、职业化使运动员为获取最高经济利益而进行体育竞赛。以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为例,冠军可以得到丰厚奖金,国际田联决定从1993年起,从大奖赛中抽出四站举行“黄金大奖赛”,如果运动员连续四站获胜,可分割20千克黄金,后来又由黄金改为100万美金。物质欲望的膨胀导致运动员价值观念的变异,使得原本公平、公正的竞技体育所蕴涵的精神价值被人们遗忘,这种巨额奖金的诱惑让运动员产生了拜金主义思想。在金钱利诱的驱使下,马里昂·琼斯、蒙哥马利、加特林、卡尔·刘易斯、钱伯斯、杰罗梅·扬等这些叱咤田坛的风云人物,不惜吃兴奋剂来提高成绩,为了获取奖金不择手段,使得赛场丑闻屡见不鲜,兴奋剂事件层出不穷,这严重背离了体育竞争的公平、公正的原则。
5 结语
中西方历史文化积淀、追求的利益点以及评价标准的不同,致使中西方竞技体育对待胜负产生了不同,并形成了两种各具特点的文化形态,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对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既要认识到两者冲突的一面,也要探寻相互融合的一面。中西方胜负价值观的比较警示我们,不应狭义的理解为以奥运会取得金牌的多少为衡量标准。而应该争取优异成绩的同时客观对待胜负,淡化金牌的象征性,特别是媒体要正确引导观众的奥运金牌观。在新的历史时期,胜负价值观将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努力做到“以人为本”,以实现我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