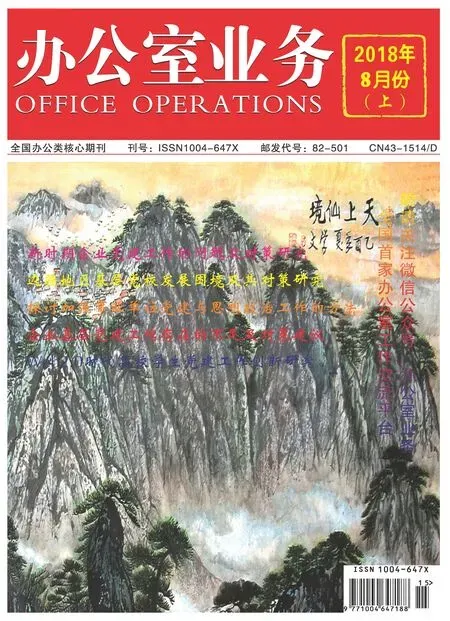论苏轼公文的创作特色及现实意义
——以《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为例
文/扬州大学文学院 许安苒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眉州眉山(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臣,谥号“文忠”。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团练副使,这成为苏轼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听政,苏轼重受重用,后因其抨击旧党执政中的弊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而再度请求外调。元祐年间,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政敌对苏轼的嫉恨,外化为对他的攻击,让他始终处于政争漩涡中。从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去世开始,到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出知杭州为止,攻击一波接着一波,为此,他不得不多次上疏辩白、自请外放。从本质上看,苏轼被攻击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体制原因。在宋代的权力架构中,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对于相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是维持权力制衡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自熙宁时期王安石首开利用台谏驱逐、清除政敌之风,到了元祐时期便愈演愈烈,台谏因而成了权臣们巩固势力的工具。台谏的性质日益扭曲,苏轼也成了个中受害者。细数当时苏轼的政敌,如孙升、朱光庭、傅尧俞、梁焘、韩川、贾易、王彭年等,这些人无一不是台谏人员。“从元祐更化到车盖亭诗案这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朔党台谏左右着政局的发展,朔党台谏在整个台谏力量构成中最有发言权和对统治者决策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而这段时间正是台谏对苏轼攻击最频繁的时期。
其次,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是苏轼四面受敌的重要原因。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去世,旧党失了首领,必需一位能挑此重担的继任者。苏轼深谙历史、吏事精通、才华出众,深得统治者赏识,无疑是最具可能的人选,这在朝中已然是公开的秘密。当时封建政治生态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严格限制了高层的人数,更是加剧了这种权力上的争斗,也使苏轼落入困境成为必然。
最后,新旧两党的“交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轼作为旧党一员对新党实施的新法颇有己见,《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也大致能够反映苏轼对新法、新党人员的态度和真实想法:“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这无疑会招致新党的反感,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近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无所不至。”
迫此种种,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自请外放,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虽已外任,朝中政敌仍对他攻击不断,四月十七日,苏轼写下《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上议此事、陈己见。
《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条理清晰,目的明确。首先,苏轼假托臂疾,引出台官“强加”其罪状之事。其次,苏轼就此次“不得不辩”给出了三点原因:“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陛下曲庇小臣”却“使人上议圣明,以谓抑塞台官,私庇近侍”,这对陛下来说,损害不小;就小臣自身来说,并未做过不义之事,只因揭露奸回而被人无端诬陷,不得不辩;台谏沦为新旧党争的工具,若不严加治理,必纵使小人横行,朝臣惧之,不利朝政。进而苏轼提出自己的建议——“尽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
这篇札子反映出苏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文通篇虽未用典故,但所引“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等语,皆出自儒学。宋朝实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大大促进了文化的高涨和繁荣,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界,亦出现儒释道三家进一步融合的趋势。这种社会文化倾向导致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出入于儒释道三者之间,苏轼作为宋代文人最杰出的代表,其思想也体现了对三家学说的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但他自幼所受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决定了他始终是以儒为本的。自唐季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日渐沦丧,被儒家视为圭臬的伦理纲常遭受巨大挑战。北宋建立以后,为挽救颓丧、重整社会秩序,便将儒学视为正统学问,尊儒崇文之风盛行。与尊儒崇文之风相应,宋朝士大夫普遍抱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情怀。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在此精神的引领下,宋代士大夫若为民,则“位卑未敢忘忧国”;若出仕,则敢于为民除害,解民倒悬。苏轼不仅能在庙堂之上树立他的立朝大节,以天下之重为己任,尊君忠主,在民间也能体验民苦,以为民解忧为为官之道,爱民护民,任何时候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种特立之志是封建社会儒家士人终身所追求的高尚人格。儒学对苏轼的影响反映在了公文中,即使身处逆境,亦不忘国事,《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中表达出的因台谏沦落而产生的为国为民的担忧与焦虑跃然纸上。儒家的仁政爱民等思想,便是他积极用世,向陛下提议彻底治理台谏官章疏的思想动力。在当时社会以儒释道为主的思想潮流面前,苏轼以此入手进谏哲宗,则是再合理不过了。
札子,又作“劄子”,是北宋始出现的一种重要公文文种。其依托宋朝严密、细致的政治体制而产生,程式简单,受限较少,较之其他文种更加简便灵活,能够满足宋朝的治政要求。宋代官员向上呈奏的札子一般称为“奏札”。奏札首称不写官职、不用“右”,一般以“取进止”为结束语,意思是听由皇帝定夺行止,有的前面还有“臣等不胜区区之意”以示诚心。苏轼所写《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就以“意切言尽,伏候诛殛。取进止。”作结,情深可见。宋人奏札多有贴黄。宋代大臣奏札皆用白纸书写,如正文意有未尽,或者所奏不允,以黄纸摘要另写,附于正文之后,称贴黄。宋人文集中,贴黄之文甚多,其字数也不限多寡,有时一奏札后附十数条,字数几倍于札子正文。苏轼的《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最后便有两处贴黄:“贴黄。臣所闻台官论臣罪状,亦未知虚实,但以议及圣明,故不得不辨。若台官元无此疏,则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又贴黄。臣今方远去阙庭,欲望圣慈察臣孤立,今后有言臣罪状者,必乞付外施行。”皆为对原文的补充。
在这篇札子的论述中,苏轼注意穿插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如摆事实:直言自己任中书舍人时“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因而招致诬陷,并具体指明吕惠卿、蔡确、周穜等人,有据可查。讲道理:论述了放任此种谗构之事的后果:“若隐受其言,不考其实,献言者既不蒙听用,而被谤者亦不为辨明,则小人习知其然,利在阴中,浸润肤受,日进日深,则公卿百官,谁敢自保”。合潮流:“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故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之语。而爵位利禄,盖古者有志之士所谓鸿毛敝屣也。人臣知此,然后可与事君父,言忠孝矣。”这些陈述都契合了宋代社会的道德文化风气。当时儒家思想盛行,重名节、轻利禄更是“君子之道”,这是人之共识,宋哲宗也定会接受。不同手法的运用使这篇公文的论述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行文如行云流水般自由,亦不乏稳重浑厚,富于文学色彩。其坚守的文学观念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认为,文章好比行云流水,开始并无固定目标,常常是该行就行,不得不止就止,这样文章才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且平易流畅。此奏札通篇读来并无典故,只仅仅围绕自己被人污蔑之事,直接陈述事件缘由,便少“掉书袋”之累赘冗繁;且不用比喻、拟人等修辞,只以最朴实无华的语言,直陈事理,亦少工于雕琢之嫌。这让其文含思辨之美,议论与文采交融,感情与理智并注,读来亲切自然、明快畅达。如文中出现较多说理之辞:“人主之职,在于察毁誉,辨邪正。夫毁誉既难察,邪正亦不易辨,唯有坦然虚心而听其言,显然公行而考其实,则真妄自见,谗构不行。若隐受其言,不考其实,献言者既不蒙听用,而被谤者亦不为辨明,则小人习知其然,利在阴中,浸润肤受,日进日深,则公卿百官,谁敢自保,惧者甚众,岂惟小臣。”这些理论性的说辞增强了公文的客观性和思辨性。
其选择的表达方式也很有特色,这主要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苏轼议事,并非直入主题,而先假托臂疾,感谢圣恩,进而婉转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之事,通篇只以皇帝为上,情深意切,至情至理。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帝王的权力至高无上。要让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上书的内容有所采纳,臣下写公文时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既要用真知灼见来“晓之以理”,又要用真情实感来“动之以情”,还要有文采,语言动听耐看,才有作用。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苏轼的札子能如此明显地表现出对圣上的毕恭毕敬而近趋于卑躬屈膝了。
苏轼在札子中多角度的论述严密有理。为使圣上接纳将台谏官章疏交给有司彻底治理的建议,苏轼分别从陛下、自身和朝臣的角度给出了三点原因,此番论述层次清晰,合情合理,考虑周全,让人难以反驳。最后,行云流水般的论述造就了文章节奏的不紧不慢,顺其自然。从自身情况入手一点一点推进,进而论及遭人诬陷之事,辅以真实例证,最终提出解决的办法,层层递进,明白顺畅。
通过对苏轼《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一文的分析,可见其公文创作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他在公文中提出的建议、措施等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时,陷于元祐党争中的苏轼虽无奈地多次请求外任,但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现。苏轼对当时的朝政问题看得是比较透彻的。“台谏”沦为权臣相争的工具,由他们执笔的章疏怕也不尽为实情,无人核查,这对朝廷治理危害极大,不仅朝中大臣深受其压迫,甚至还会危及皇权。这样看来,苏轼提出将台谏官的章疏交付给有司进行彻底的核查根治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苏轼的公文不仅为当时的朝政治理提出了宝贵建议,还可让后人窥见其创作技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苏轼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学言之有物、积极向善的优良传统,对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文学风格也有良好的继承和发展。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公文文笔纵横、雄辩滔滔;立意新颖、论述严密;见解深刻、感觉敏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等方面,推崇温润和谐、端庄朴素之文风,自觉采用一种委婉俯顺的文学手法,这对后世来说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苏轼一生所作大量公文,文种体式和写作风格多样,几乎都是针对当时的现实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政论”和“政见”,不仅针砭时弊,能让千年后的我们透过他的公文洞悉宋代的社会状况,还对后世的公文创作提供了高质量范本,于后人的创作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