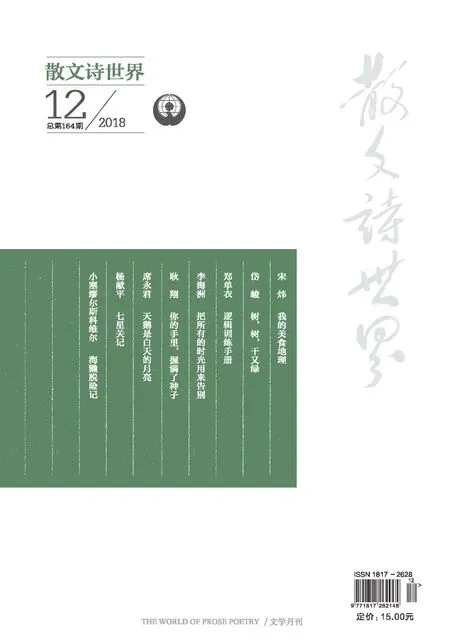七星关记
杨献平
站在巨大石碑下面,张目四望,四周皆是高山,虽然不大,但沟壑异常雄奇,如南面两村之间的那一道,两边山坡如旗帜状缓慢升起,巨大的峡谷之间,还有清水奔泻;左侧有一面斜斜的草坡。两个村子,牛郎织女般分居在峡谷两边。参差不齐的房屋,袅袅而升的炊烟,偶尔的摩托车和农用车在其中穿梭。一切都没有声音。静得好像一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加工的油画。倒是那断开的山脉,犹如铡刀倒置,顶部显得雄浑而又锋利。
宇宙和地球,其自有伦理,与各自布局的方法,以及操作的规程甚至律令。而人和人在其中,包括我们所创造的,也是这宇宙和地球的必然的一部分。而在两者之间清澈聚集和流动的,则是闻名遐迩的赤水河。大自然之中,有些事物往往生来自带神秘,如这处在北纬28°16′~28°46′之间的赤水河。俗气一些说,仅仅这条河流域才盛产酱香型白酒。而同在一条地理位置上的金沙江,则生产浓香型白酒。毫厘之差,天壤之分。这种神奇,端的是令人惊愕。附近的四川合江县是著名的晚熟荔枝之乡,据当地县志记载,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便出自此地,其品种,曰妃子笑。当地人说,除却处在准南亚热带的合江县,甚至五公里之外的地方,也栽种不了此物。
天地之间,总有一些匪夷所思,但却被人习以为常。自古以来,比邻而居、结伴生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有利于通婚,这赤水河,更有利于力所能及的各种方式的合作。无论是哪个人和哪个群体,在这个地球上,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尽管有些地方,被人为的行政区划无意识地隔开了,无论这种“隔开”如何强大和有效,但那里的人及其现实生活却无法真正地被“隔开”。如处在云南昭通镇雄县和威信县,四川泸州市叙永县和贵州毕节的鸡鸣三省村。
鸡鸣这种自然声响,显然是农耕时代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人民安定生活的一种鲜明象征。鸡鸣三省村的这种一衣带水的生活状态,肯定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在这漫长的光阴当中,谁也无法说清这一具有诗意和高度概括性的村子除了自然的变迁,人和草木动物的生命更迭之外,又发生过一些什么。在时间当中,真正迷蒙的不是人的来龙去脉,而是人所在这个世界上遭遇的苦难与不幸。可以肯定地说,人从内心,甚至从天性当中,即非常善于遗忘经受的痛苦,而总是在痛苦之后,用一种无限欣悦的方式,去期待更好的生活。
然而,就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场浩劫当中。斯时,希特勒上台,开始建立法西斯专政。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和“丰台事件”。世界的西方和东方,或可预料的暴风雨与黑暗天日,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这一年的一月份,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旋即又北上,准备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创立新的川西根据地。但由于没有摸清敌情,在土城遭到失败。先是在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召开会议,继而又在鸡鸣三省村继续召开。
这样一个偏僻之地,先前只在民间流传,近乎自生自灭的小地方,居然在近代,忽然之间,就与整个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机缘,也是可圈可点,可以说是一种造化。当然,每一寸土地上,都是与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有关的。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一个为整个国家民族探索出路的人,在这里重新调整人事和战略方向,从而从失败走向胜利,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
高大的纪念碑之上,是无限苍天,飞动的流云,湛蓝、洁白、黧黑之色混杂之中,似乎可以看到这宇宙与人世的沧桑,也能够觉得人类命运的诡异。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此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联想起其中的主要人物,任谁都要感慨万千。也会觉得,大地上的每一个生灵,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生来就有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当然,也有自己的苦难与愉悦。有很多时候,我想回到战火的年代,以英雄的铁血姿态,去为更多的人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而,这显然不是一个英雄的时期,而英雄,最好从此绝迹。人类已经经历了太多创伤,和平、仁爱、互助,应当成为我们这个世界最恒久的状态和主题。尽管这不可能,但每一个人,都应当作如是之想。
由鸡鸣三省村再去七星关,途中大山之间,蜿蜒的道路逼仄危险,上到海拔1600米之后,久在低地生活的人会有些不适。曾有人说,毕节这地方,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可眼前丰厚异常的植被,不时在空中飞溅的鸟儿,以及峡谷坡地上苗族、彝族乃至汉族人的村落和田地庄稼,却在日光下显得黝黑葱绿。不时有农人扛、提或者背着东西在走,有的用农用车运输。我蓦然觉得,其实,大地的每一处,都可以有人生活的。那些无法让人安置的,也为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资源。在蒙昧时期,大量的野生动物,为人带来食物和衣服;于农耕时期,大地又慷慨地捧出庄稼和各种奇珍异果。现在的信息时代,无论怎样的科技,其原料仍旧出自于大地,如稀土、稀有金属等等。
现在的七星关,早就是一个遗址了。孤立在一座山头上,今人用水泥做成石碑,刻下古人当年的行迹。据说,七星关与诸葛亮南征有关。诸葛武侯这个人物,悲剧性与伟大性兼具,智谋和失误相当。但他的个人品质却接近完美。这一位常以管仲、乐毅自比的豪杰,小国的良相,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能冠军,其志吞天,而时运梗阻,若是在西汉之初或者隋唐之际,此人之功业,当不会比高颎、李靖、李世勣等人逊色。但在弹丸之地的西川乃至西南,诸葛亮的个人才能施展空间是受到严重限制的。
七星关之初,乃是诸葛武侯于公元225年(蜀建兴三年)来到的。当时,处在今云南曲靖的彝族首领雍闿“跋扈于建宁(即曲靖)”,杀掉太守正昂,又不听都护李严所劝,桀慢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后归降东吴,为永昌(即今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保山坝子偏东北的隆阳区金鸡乡金鸡村、东方村、育德村境内,以及可能包含缅甸克钦邦、掸邦的一部份,始于东汉。)太守,并联合本族民族首领孟获、越嶲夷王高定(《华阳国志》作高定元。驻地在今西昌和攀枝花一带)反叛蜀汉。素有异志的牂牁太守(辖地今贵州省大部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朱褒也起兵响应。雍闿家族乃是益州(今成都)之大姓,其先祖为雍齿为东汉什邡侯。及至蜀汉,雍闿素有二心,在南中(即今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南部地区)骄横狡黠,阴阳不定。诸葛亮苦于蜀国无人担当征伐重任,遂亲自率兵南征。
三国时期的“南中”,为西南夷杂居之地,其最大,当是牂牁(夜郎国前身),并雍闿与朱褒等,前彝族(六祖分支)、苗族、侗族、僰人等势力也颇强大。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用马谡之言,以攻心为上,驯服这些桀骜之民族。令人没预料到的是,诸葛亮大军还在途中,雍闿就被高定的部将所杀。随后,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乱。这个七星关,乃是诸葛武侯当年在此举行祭旗礼禳星之处。关于祭旗礼,古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为“祃牙”,意思就是出兵前祭旗的仪式。此外还有建牙,意为有一定级别的武官自己组建的卫戍部队。
诸葛亮南征,得到了与雍闿等人不一致的水西彝族头领济火(妥阿哲)的帮助。为纪念这次结盟,诸葛亮在七星关祃牙七星。七星关之名,大致是由此而来的吧。在血与火的冷兵器年代,或者说在神话刚刚落地成为人们可见之物的公元三世纪,关于祭祀的传统仍旧是蓬勃的。诸葛武侯这个人,其学养和精神当中,融合了儒道法兵等各家各派,因此,他给人的印象始终是驳杂的,治世能臣、精通方术的统帅、善于作战的谋略家、辅佐皇帝的忠心臣子,如此等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的形象。当然,祭祀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招抚与鼓舞。不管是集体性的,还是家族和个人性的,祭祀一方面体现了古人敬畏天地祖宗的内在思想,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明确位置并且寄希望“正道”来进行自以为正当的一切事情。
这也算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式,刀刻般深入中国传统。当然,其他民族和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即使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国家和民族当中,此类现象像是一条柔韧的绳索贯穿于人类的历史进程。沿着山岭向下,可以看到马蹄印迹明显的古道遗迹,这也是南丝绸之路的另一条道路。深深的马蹄印里,积着一些清水。脚踩上去,似乎能够感觉到当年千万马蹄敲打石头的脆响,也似乎可以看到牵马和步行的商贾、行者、军人与逃难者的趔趄而又劳累的身影。人类的历史进程在每一个空间当中,其景观是迥异的,但又是高度雷同的。数千年以来,人类乃至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还没有逃脱捕杀、采撷、以货易货、异地搬迁、逃遁与安居的基本形式和性质。
茶马古道的石墙上,有许多镌刻,但都因为年代久远,风雨日夜洗涮,使得字体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想想,大抵是记叙和颂扬此路和诸葛武侯之武功政治之类的高蹈之词。尽管如此,可也觉得,人和人,总是有区别的。类诸葛亮之列,其功业虽然建立在大多数的死难和苦痛之上,但其留下的事迹,尤其是当世作为,却是令人敬仰和鼓舞的。
下到半山腰,侧面住着两户人家,右边是一条公路,河流之上,是一座石拱桥,据说,这样的石桥在全国极其少见,茅以升曾带人来此考察过。当地的朋友还说,这条路,是328国道的旧址,其实是民国时期修建的接通滇缅公路的组成部分。
滇缅公路的修筑,是当时蒋介石政府为抢运从国外购买及他国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但后来,滇缅公路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抗日之路。国人大都还记得,在缅甸朗刻地区作战中受伤,并在缅北茅邦村殉国的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将领戴安澜将军,还有数以万计的在缅甸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人。一条路的旧址竟然让人想起如此沉重慷慨的历史往事,被时间镌刻的中国军人,在彼时年代,确切地体现了一种伟雄节烈的精神,以及中国军人在战争年代远赴异邦,誓死决战法西斯的忠勇与伟大。
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是古今衔接的,绝不是单独孤立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在蒙昧时期还是在工业革命及其后期,虽然中断过,但也还是连续的。因此可以说,无论是诸葛武侯的南征,还是戴安澜将军的远赴,都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民族的尊严与精神上的凌厉和丰盈。在桥上,我站了很久,看着已经平缓,而且幽蓝的江水,脑海里,一时间,出现无数的影像。其中有徒步负重的挑夫,牵马赶骡的小商贩,更有持枪举旗的将士。时间这条泥沙俱下的江河,携带的再多,也不见其半点喘息。唯有人,一茬茬,一批批地,踉踉跄跄由此而去,却鲜有人原路返回。
如此引申,万物万事莫不如此。
离开七星关时候,日照中空,端的热烈异常。只见窗外的草木叶子打卷,蔫蔫的。按照周易的阴阳理论,正午乃是老阳,过三点,便是少阳。如此轮转,不休不息。去拱拢坪森林公园的路上,在一处高坡上还吃了一些桃子。此地的水蜜桃,汁多皮薄,甜意四溅,入口温润。然后转到拱拢坪,深入森林。这些树木,是二十多年前栽种的,现已苍翠葱郁,棵棵参天了,而在之前的那些,在大炼钢铁年代,基本被伐砍殆尽。
林子里空气甜润,丝丝入喉,遍及全身。这样的环境,在贵州境内海拔最高的毕节市辖区,也颇多。一行人漫步而下,说着这样那样的话。我在其中,忍不住放声大喊。喊声在林间穿梭,但回声几近于无。唯有那些不知名儿的鸟雀鸣声,轻捷、发脆,充满灵性,透射出丝丝不断的生机。人本来与草木鸟兽一般,为山林崖洞之物,现在以掠夺的方式,占据大地,自以为王,我们自己说,这是进化和进步的结果,而在草木鸟兽的眼里,人也不过是会修筑庞大巢穴,且会发明和利用更多工具的同类而已。
拱拢坪森林之中,有一神奇之地,便是回音八卦。我和另一位同行者站上去,无论是耳语还是自言自语,对方均能感觉到震耳欲聋的回声。这种神奇,传说也和诸葛武侯南征有关。我想,大地之大,奇形异状事物和现象之多,盖非人全能破解。拱拢坪的回音八卦似乎包含了某种神意,亦或是八卦之中华先民智慧创造于此地的一个试验点。紧邻回音八卦的是吞天井,其实是崩塌性的大型漏斗,上宽底窄,据说,在底下望天,有巨口吞天、浅龙入地之意境。我趴在阑干上看了看,觉得这等奇异地貌,虽不觉得惊奇,但也能引发人的绮丽的幻想,如神仙居所、蟒蛇修行、隐士洞府等等,充满了神话色彩。
与之相连的,还有芳草溪、疏林草地、阳鹊溪等等,颇为静美的自然景观。这样的一个地方,是避暑之胜地,倘若有两个人,或者几个好友一起,在此消磨时光,当然是美妙无比的。清风穿林,摇动花草,夕阳余晖,映照溪水,其情其景,应当是人在自然之中无上的享受吧。趁着落日初斜的柔光,众人拍照,一片喜悦之声。
由此再去毕节七星关区燕子口镇大南山苗族村。贵州之苗族,也称为蚩尤之后。以此推断,其实,无论苗族还是侗族等,其未出华夏民族之范畴。而彝族,则是羌族在南迁的过程中,逐渐与西南诸民族融合之后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羌族尽管年代久远,其历史甚至长过匈奴及其后来的突厥裔和东胡的鲜卑、乌桓,但其始终生活、游牧在中华民族版图,故也可视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关于民族的源流,我始终觉得,在中国,无论哪一个民族,原本都是同族同宗的,只是气候环境的不同,导致了语言风习、文化传统的迥异,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与气候》中首先提出气候影响历史的推测,他指出,文明往往随着六百年的气候周期而崛起或没落,恶劣气候往往造成游牧民族大量出走,例如匈奴向西的迁徙等等历史事件。
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往的阅读中,朦朦胧胧地预知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但苦于没有任何学术理论和研究的支撑,一直不敢公开说。偶然的机会,读到亨廷顿这本书,以及瑞士学者许靖华的《气候创造历史》,才觉得自己的预知完全正确。
大南山苗族村堪称这一带苗民之核心,因为,这个村子的苗语才是正宗的,许多他地的族裔前来学习,以大南山苗族之语言为最标准。无论怎样的民族,处在不同的地方,其语言就会发生变异。汉族也是如此。因此有十里不同音之说。我们进村,见十多个苗族妇女坐在小凳子上,有的在分麻(蓖麻的皮)。这使我想起幼年时候,奶奶、大姨、小姨、母亲乃至村里妇女常搓麻绳,以纳鞋底的情景。
就地取材,很好地利用自然给予我们的各种资源和材料,是人智慧和高贵之处。有一些美丽的苗族女子和结实的汉子,在场上表演舞蹈。从他们的动作中,我忽然明白,他们舞蹈的基本动作,就是“爬”,即爬山,和“涉”即涉水的动作简化与再创造。每一个地方的人,无论是哪一种行为、习性和艺术,都与其生活环境,气候地理有很大的关系。
人毕竟是地域产物。人和人交往,如联姻、农事和工业合作,也是一种相互改造和促进的过程。这两年,因为在这里的诗人彭澎,我多次来到毕节,数天或者几天时间,在不断的走访与体验、冥想与感悟之后,对这片人居之地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即在这夏季清凉之地,混迹在她的诸多历史和现实,人文和自然之间,一个外地人,内心充盈着的都是对她的好奇,也在试图了解她,进入她的内心。毋庸置疑,毕节已经深入到了我的生命当中,我呢,或许也能够被她记住。因为,一片土地也是整个世界,一个人也是整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