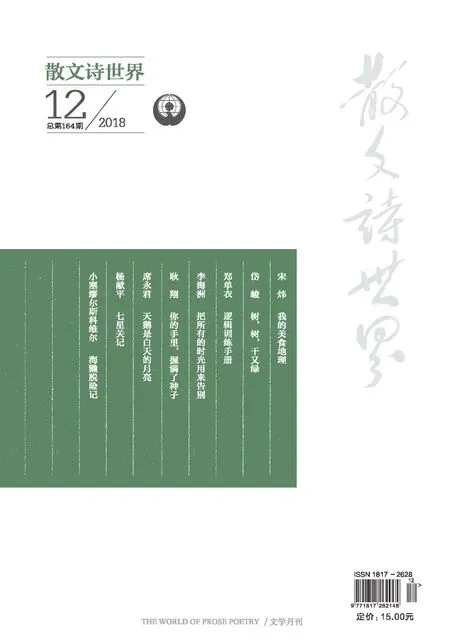西辽河
犁夫
一
掬起一捧河水,指缝间便流淌出千年的传说。
那清粼粼的碧波,泛起一圈圈的涟漪。故事细节,随着传奇潮起潮落。
撒开的网,牢牢地网住一颗心,也网住了泥土里的根。
船工号子,吼唱出绝唱;
马背上的长调,跌落进了河水的波涛。岸上的风景和波涛里的旖旎,绵延着一首古老的牧歌。
在巴林草原,在科尔沁沙地,亘古洪荒的预言,在马头琴上演奏,历史的沧桑,留痕在曲曲弯弯的河床上。
马奶酒暴烈的性格,和宽厚的心胸,承载着一切风雨。
打鱼的小船,装满金色的阳光,九曲回环的激流,荡漾着蔚蓝的神奇。
一条古老的河道,沉淀了千古泥沙。
大漠苍穹,蔚蓝的遐想,去捕捉一条鲜活的灵感。
奔腾,一往无前。
哦,西辽河,远走他乡的孩子,咬破无名指,鲜血滴落在乡愁里,溶进河水,洇化。
二
我不知道,那些传说在西辽河的淤泥里沉睡了多少个世纪,今天醒来的故事里,是否还有朦胧的眼神。
流域上考古时代的时空框架,构筑了这些传说和故事的来龙去脉。
夏家店下层的石城,是否坚不可摧,锐利的攻击与侵扰,唯有那些过火的石头知道。
夏家店下层的青铜器锈迹斑斑,彩绘陶器的纹饰和符号,又在诠释着曾经的标识。
精美的玉器,包浆上的痕迹,也在释放着古老的智慧的灵光。
仔细审视画着涡旋纹眼睛的人面岩画,对视着千古的疑问与诉求,在眼眉和眼睛中传递神秘莫测的暗示。
涡旋纹眼睛人面岩画,那可是凌厉凶猛、飞翔捕猎的鸮,在历史的源流里啸啸长鸣。
殷商的玄鸟,落在西辽河的岸边,也和涛声一起,回答今天的疑问。
有人感慨:辽河之水自何来,塞外三峡峭壁开。
南源的老哈河与北源的西拉沐沦河,汇合在流图,然后翻越开鲁、科尔沁、双辽、昌图,在福德店与东辽河汇合,成为辽河干流。
有人惊叹:辽河曙光在何处,古老河床育文明。
由西向东,西辽河奔向大海,一路的山丘草原和丘陵,都不能阻止水流的浩浩前行。
干旱,暴雨,植被不良,水土流失,泥沙浑浊。但,西辽河仍在奔流。
大兴安岭南麓,松涛阵阵;燕山北麓的夹角,发出沉闷的回声。
历史抬高了河床,河床上文明开始诞生。
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策源了中国古代北方的文明。
三
潢水,土河,沙里河。这些土生土长的名字,就是西辽河的多个乳名,它们把神秘的自然现象和多重的人类关系链接起来,让那些神话和传说,成为大河的浪花,在历史的深处翻卷,涤荡着浑浊和粗野。
与其说西辽河是一条河,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历史的走向。
这个走向就是从远古到未来。谁也不能改变历史,西辽河的自然力量,存在于天地之间。
漫过滩涂,溢出河岸,冲出峡谷,奔流着。
在跨天接地的彩虹中,升腾着金蛇狂舞般的霹雷闪电,其实那是自然的呐喊,也是红山先民的心愿。
西辽河孕育了图腾,创造了龙。
这是中华民族的梦。
刀耕火种,史前原始种子在汗水里萌芽生长,耜耕的歌谣,从小河西的黄土丘陵台地里跳荡着喜悦的音符。
兴隆洼的洼地里,孵化了原始农业文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牛皮鼓的铿锵鼓点,在大兴安岭东南麓的山前丘陵平原骤然敲响。
赵宝沟的犁杖和石锄,耜耕了谷子,金灿灿的小米,哺育了草原的汉子和红脸蛋的姑娘。
红山,赭红色的山峦,辉映着原始农业。
科尔沁沙地以南的黄土丘陵台地,闪耀着青铜的光泽,夏家店上层的牧鞭,放牧着成群的牛羊,羊咩牛哞的吆喝,成为不朽的祝词,刻进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
民歌,在战国西汉时期北上;长调,南迁在燕秦汉长城以南。
农业滋补了畜牧业,畜牧业给农业强筋壮骨。西辽河的水,浇灌着草原农耕文明的绚丽花朵。
四
传承着永远的牧歌,点燃草原的篝火,在民歌跌宕的曲调里,流淌着奔腾不息的西辽河。
在河岸上回眸,以船夫曲作证,喊一声西辽河,渤海的波涛,就再次依依回首,席卷堤岸。
荷锄的人,在田垄里劳作;
打鱼的人,用船桨做歌。
我坐在辽代的沙里河岸边,掬起粼粼水波,把神的暗示和水的隐喻,都放进衣袖,在月光下舞蹈。
我是一尾亘古的鱼,我是一支古老的歌。
在西辽河的浑厚颤音里,我打捞逝去的岁月残片,弥合一段历史。
西辽河,河水洗濯着耶律阿保机的马蹄,也冲击着他的心,让他澎湃,让他睿智,囊括四海,并吞八荒。
西辽河,浪花溅击着成吉思汗骏马的鞍韂,也推拥着坚强的意志,让他崇高,横刀跃马,雄霸四方。
西辽河思念着大海,穿越关山,削开龙蹯虎踞的把守,绕开怪石险滩,滔滔东去,浩浩前行。
在山崩地裂中,涛声拥抱着命运,生死兴亡。
萨日朗,芳香伴随着一段东流,悲伤而又浪漫,纷涌而至的思绪,都被民歌的音符,跌宕出巨大的漩涡。
雕花的马鞍,在一阵阵急促的脚步里,追求着远大的抱负和不朽的功业。马鞍,是西辽船帆,追求汪洋恣肆的自由,在冻不死封不住的信念里,纵横驰骋,风驰电掣。
西辽河,在一首首蒙古歌里酣醉;
西辽河,在晨钟和暮鼓中,把远古的门扉,一扇扇打开,坦露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