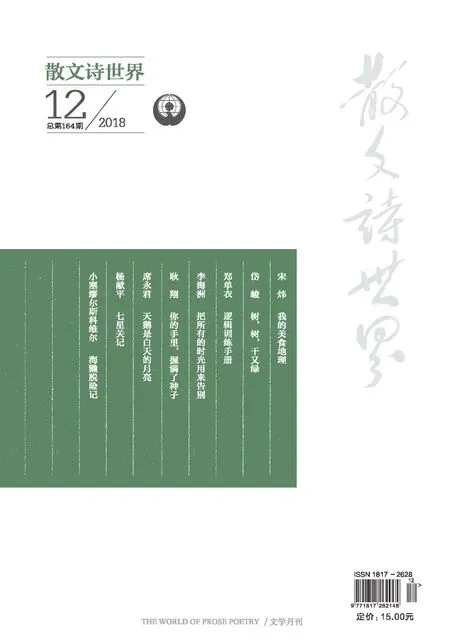你的手里,握满了种子
耿翔
1
我那么有力,让我在风里,先啄破身体的外壳。
然后头顶泥土里的愤懑,向上生长。
还是去年的原野,还是去年的风物,还是去年,被熟人的镰刀收割后,我以种子的身份,回来复读生命。而我的那些伤心,只有吹打过我的风雨,才会抚摸。比起更多的人间食粮,我不想让泥土,再把我养育一次。
跟着原野生长的日子,是一粒种子,跟着灾害一起生长。
而一粒粮食最庄严的时刻,是跟定人类,在血液里不留遗体地死去。
让我认下,我的过去。
我复读生命的日子,不能没有你一贯的,风吹雨打。
2
在你手里,我是种子。
我是食尽,人间烟火的种子。我是用死亡,追赶着季节,追赶着地点,食尽人间烟火的种子。我的身体,不是谁都能捏造,我的肤色,不是谁都能涂染。
知道我基因的那个人,已经很久不在我身边。
只有季节露出的真情,才让我知道,把我不舍地捏在手中,然后抛撒出去,最终在哪片泥土上落下,你还没有签约。而踩着阳光,要抛洒我,你就要保证,在大地上,谁也不能拿我演示。
在你手里,我是种子。
我是被你,捏出罪孽的种子。
3
我爱马坊,也爱它抢先生出的所有草木。
我的身体,贴着它们早晚呼吸。
告诉你,庄稼围着人群生长,庄稼如故人。虫鸟,围着人群生长,虫鸟如故人。草木也围着人群生长,草木也如故人。
我的这些微体验,像我身体里的天气预报,它不影响什么,但它会加重马坊的忧愁。
也让一朵野花,开得更加揪心。
我爱马坊,透支掉身上对所有草木,会缩短生命的怀念,也要继续。
4
云在头顶,我们在地面上,每挣扎出来一个动作,都被云捕捉。
你在南山,你不用穿越,也有可能看见,我们在北山,猎杀一只野鹤的场面。你得感谢那些过路的闲云,它们血淋淋地捕捉到生命,被瞄在枪口上,怎么呼吸?
而这样的时刻,云也慌张。
有些时候,我们在云里,会倾听到万物,发出地动山摇的声音。头顶的云朵,谁也说不出天空压在身上的重量。
这个时候,有一只燕子,会把云的语言,代替南山,传给北山。
你要知道,我们从身上脱下一件衣裳,就像从天空脱下一朵,自己的云。
5
在河流的转弯处,我坐下。我要看河流,怎么转弯。
我看见,所有的村庄,都被河流怀抱了上千年。一定在阳坡,停止向河床滑动的地方,一定在湿地,又不被泛滥的河水冲走的地方,人住在窑洞里,神住在庙里,庄稼住在地里。
我也看见,黄河上的大地之湾,把天上的星斗,整体地顶在头上,或散乱地放在脚下。
夜风吹来,神也在人间睡下了。
却把万物,交到种地人有温度的手里,再用铁器催生。
在心脏的转弯处,一条父母之河,怀抱我的身体,不止千年。
6
我那么悲哀。我在土地上劳动的时候,从我身边走过的人,把我当风景看时,对我心怀这样的忧愁。
我的内心,却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的内心,被庄稼乘着季节之势占满。我也知道,它们简短的一生,只记住自己是一种粮食,记住落在身上,鸟儿的目光总是俯冲下来。
而我的仰望,在弯下腰,才能服务土地的劳动之中,也很罕见。
因此,在庄稼身边,我没有什么悲哀,可以说出口,让不懂得种庄稼的人,下乡时掉眼泪。这么大的山,就站在身后,欣赏它们,只是转身的事。坐在家里,推开窗户,就能把河里的水声,用手撩起。
我要告诉,从我身边走过的人,人类最好的日子,是学会种地。
尽管现在,我无地可种。
7
下到大年初一,这场隔着一夜的大雪,下过了两年。
推开一村的门,不是大雪,也不是跟着大雪回来过年的人。
那些从血肉里带走我们一生的悲伤,而绝命他乡的人,才是大雪一路纷飞着,要带回村里的人。
这个时候,他们不分年龄和辈分,都在我们头顶的大雪里,带着祖先才拥有的目光,看着我们。而逼着他们,穿一身白衣,回到马坊,是这场隔年的雪。
我们顽固地守在大雪里,很想看清,他们从哪里来。
8
背上,云朵很轻,天空很重。
爬在羊肠一样的路上,我的心里,全是我从山下带上来的汗。
我在山中,山下的被风吹得,越来越瘦的土地,还会恩重如山地,替我在陈旧之年里,种出新麦?锁在上房里,和墙皮一起老掉的祖先们,还端坐在牌位上,看我,如何挣扎下去?
我在山中,我看见山下的人,把在田野里无法藏身的神,一律用很干净的泥巴,塑在山路上。
走累了的人,会看见。
饥饿的狼虫,也会看见。
而我,装作没看见。因为有些泥胎,让我背上的云朵,重了起来。
天空是我,挣扎过的重。
9
三月的风,如果再不带来雨水,果树下的人,脸色就更加难看。
天不下雨,果树下的人,气息奄奄,果树上的残花,也被他们的脸色吓坏。这时在田野上,不管你走近哪里,都看见生长,是很难受的事,都有风的手指,不停地抓伤,季节的衣衫。
这个时候,果树下的人,想着这一年,怎么活下去。
头顶上的花,如果开不出一家的尊严,就会等着,果树在苍老之中,先压垮天空,接着压垮,享受过果树的人。
三月的风,如果再不带来雨水,果树下的人,就先让自己死去。
10
青草爬不上去,青草,就在你的脚下,今年跪着死去,明年跪着,活过来。
你不知道,这些死去,活过来的青草,是我越来越老的替身。我能饮恨天地,我能葬身他乡。我的身后啊,青草连天。
青草,也连着你的墓碑。
我的身上,有再重的罪孽,只要被一叶,基因很仁慈的青草闻见,隔着再远再旧的,山河岁月,生我时的风,会吹来,生我时的雨,会落下。
青草爬不上去,青草回过头的时候,看见我跪下去,看见自己,跪下去。
11
等我懂你的时候,只有一块石头,立在村北,却没人敢在上面动手。
你是石匠。你让多少命比草木凋零的人,敢在一块石头上,端坐下来,把生前短暂得不够风吹雨打的光阴,年年留给从遥远的地方,要赶回来的人。
你是石匠。你的手上,握有山体被凿痛的哭泣。村后就一座能陪伴一村人的大山啊,你每凿一次,都像从自己身上,凿最后一块骨头。
因此,你凿的墓碑,都很简陋,只能放下死者的姓名。
借着月光,你能回到人间的话,对着那块石头,你就自己动手。
12
在你手里,我是种子。
我的乾坤,被流年的日光,粉碎得失去原形。
我的不幸,是我没有一次出生,所需要的生命密码。你就是从手里,灿烂抛出我的那个人,隐藏心底,你劫后余生的那些善良,那些仇恨,都是让我痛苦选择或排除的基因。
我的幸运,也是我在哪片小山河里落地,全部由你决定。
一片乡野,是你指定给我的一片国土。
被手握农具的人,一路护送到,开镰的日子,躺在田野上,我用一身金黄,打造他们的土地。
在你手里,我是种子。
我的生死,要在我身边人的生命里,留下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