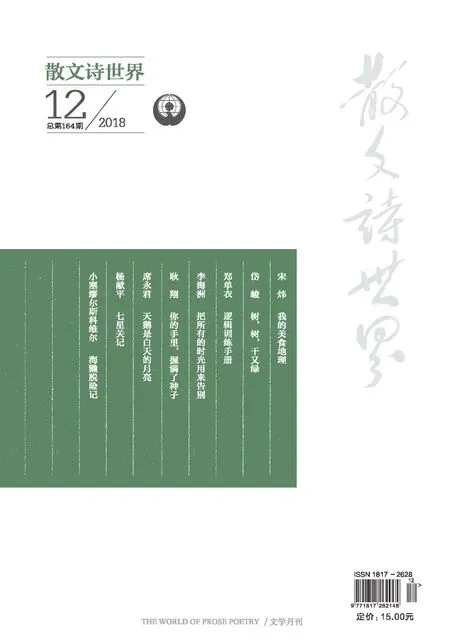鸟话 组诗
老房子
鸟鸣、眼皮和长翅膀的它们
清晨,鸟鸣准时跳进眼皮深处
幽会。忘记
是毁约最好的闺蜜
理由充分,或完全不可理喻
规律要遵循,有时未必
人间可以创造奇迹
比如她和她的闺蜜何等默契
再比如夏蝉
越是聒噪,越是心烦
舒适的标准似乎就只闪现在一对薄翅里
还比如吸血不发声的母蚊子
餐桌上突然而至的绿头苍蝇
蝴蝶的翅膀一旦煽起凡尘,抖落
即一个所谓效应
见与不见
不会像放之四海的真理
心知肚明的话
一脱口,随时可能响起一声闷枪
击中天籁
趁眼皮和嘴唇尚未张开,梦游
最好呈弹性地进行
而不像蝉蜕将来的脆裂
鸟话
憋黑了一个整夜。大清早
突然亮出一腔高调
依稀之喙
啄噪依稀之人事
竟都如此尖刻
必须回应。所有的回应
都小心翼翼
把无法笼络的朦胧搂得很紧
匿于耳膜薄壁
偷窥一条出路
梦是迫不得已的起义者
把沿途的俘虏一一释放
如果要审讯它们
语言和肢体皆无从沟通
远近皆叫响欲望
我想去把鸟鸣捧回来
我们去鸟鸣
——去和它们交流
它们无拘无束,我们异想天开
它们有世上最尖锐的嘴,最不知疲倦的喉咙
而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些各色的喙有益无害
能够撬开最坚硬的灵魂
在神灵面前婉转
不要再依赖人机对话
语言和语言何其差异。同一种语言
尚且词不达意,冲突甚至上升到肢体
成为议会大厅椅子、茶杯们
民主程度最高的语言
不同语言的表达更加诡吊
面部丰腴和内心枯燥。随时
断电。死机
一场沙漠风暴
所有五官形同陌路
我们去鸟鸣
——去和它们交流
云雀、 百灵 、画眉、 灰椋鸟,还有麻雀、布谷
多么和谐的大家庭。夜莺是它们中的贵族吧
我还是喜欢歌剧里的声音
可它们是最胆怯的
一个眼神便会惊飞,飞在
十二星座之外,十二生肖之上
告诉我,有什么好办法
我想去把鸟鸣捧回来
一张口,更加重了边界的孤独
昨天和今天的边界
此时,已空无一人
梭巡至此,驻足
月光与灯光对视
谁也不想退让一步
僵持,是熬苦的睡眠
觊觎浮肿着遗憾
眼膏越来越浓
“他们怎么可以
引用彼此的方言”
一张口
更加重了边界的孤独
树叶举起晨曦的鸟鸣:
“一切语言不必到此”
蛙呢,鸟呢,蝉呢
蛙呢,鸟呢,蝉呢?
此处无声
河水哗哗
有人捕鱼。你在树梢?他在田里?
我无处可寻
鱼也,吾之所好,熊掌呢?
此处风声鹤唳
月比你们
高了一座山,低了一溪水
山涯恶劲草
叫嘛,那些个东西
“一定要把薛定谔引为知己”
唯有鸟鸣,才是真的
感觉到了寂静
梦,掀开黑色睡袍
灰白肚腹
如果
此时正在打腹稿
一阵紧似一阵的鹧鸪,高亢又单调的布谷
从声音里分辨眉眼的画眉,以及
杂乱起伏的群呼或者互怼
懵懂经不住惊吓
狗吠鸡鸣
猫的脚步踩到了吊诡。悄无声息
降临。最恐惧的是
那把锤子和放射性物质
“一定要把薛定谔引为知己”
他终究模仿不了
霍金坐姿爱因斯坦眼神
只得把不安分
晾在被鸟叫分了杈的时间上
自行其是
梯子
傍晚的阳光
抬着刺眼的梯子:
“爬上来,可以见到奢望”
一匹黑影贴着地面
鬼祟,尾随
交错的脚步
越踩越薄
秋雨
开始滴下省略号
乌鸦“呱呱”躁动的黑氅
一件一件陨落
我把梯子抽走
替夏天行道
湿透了的降落伞,要占领这儿的
傍晚
收复风的失地
众生喜极而泣
鸟声,蝉声,蛐蛐声
蛙的一声......
喇叭花张大惊愕
草木深呼吸
水车俯下又撑起
半个后腰一览无余
被偷觑的捣衣妇舞起棒槌
替夏天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