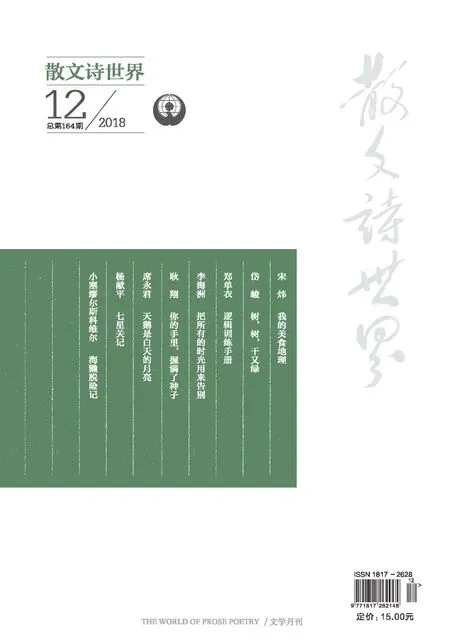我的美食地理
宋炜
文武之间:西北美食的精致与粗砺
幼时,在一册以精美小楷手书的《华秋苹琵琶谱》中,我初次见到了中国最古老的琵琶曲《海青拿天鹅》,并勉力习之。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神奇的工尺谱。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诗云:“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说的正是北人用一种叫海青的猛禽猎取天鹅的情景,而琵琶的那些胡乐特有的性格:嘈切、硬朗与清冷(也可以根据速度、节奏与指法的变化随时转化为必要的热烈),正好呈现出海青的勇武:是夜,明月彻照,葡萄酒的琥珀光在猎鸟上下翻飞的乱影之下也显得寒冷。一弹之下,果然是朔风凛凛的凉州曲。那时,我对曲名中的两处用词感到讶异:一是“海青”。此前我并没有听说过如此古怪名字的大鹏,初读时,甚至误念成了“青海”,我想,哦,是在青海拿天鹅,青海湖可能也是一个天鹅湖!接下来,便是这个“拿” 字了:它跟我们平常的用语也颇不同,不是捉,也不是捉拿,就只是“拿”,显得轻巧,得来全不费功夫,并且有自上而下、垂手即得的画面感,甚至还有点轻薄和戏弄的意味——海青显然一律是男性化的怪物,天鹅则全是女性化的弱者。总之,这个奇怪的曲名没有一点透露出内容中的搏斗与周旋之苦。但它显然又有古意,听起来莫名其妙地舒服,让我觉得古人下字之怪,真是匪夷所思。后来虽然知道这首凉州曲描写的是内蒙、甘肃一带(凉州者,武威也),但最初的误读还是让青海的意象挥之不去,并且,乐曲中携带的一系列信息:鸷劲,沉雄,羊角而上,直薄云霄……所谓“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赵讽),“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赵秉文),如此种种,也深入头脑,与我读到的众多边塞诗相互印证。我往往在弹奏了《海青拿天鹅》(武曲)之后,立即再弹一首《塞上曲》与《昭君怨》(文曲),三弄之下,仿佛边塞风光就尽在弦上了。
海青,又名海东青。从历史上看,海东青主要是由世居当地的女真人豢养的,大辽的契丹人把它们引入蒙古地区,女金人灭辽建立大金后,更进一步将它们带到塞外,遍布于整个大西北,当然也包括被我误读的青海地区。康熙皇帝曾有诗称颂这种被其先人视为图腾的巨隼:“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虽然《滦京杂咏》中的滦京指的是位于蒙东的元上京,但史书说杨允孚“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莫不以诗歌记之”。《滦京杂咏》可谓元初时西北生活的诗体百科。因为他还“曾为尝食供奉之官”,我便在其诗中寻找当时人们饮食生活的种种细节,发现了许多有趣的描写,有的在今天还在传承并使用,比如“诈马宴”与“马奶子宴”;但更多的却消失了,比如用“异品黄羊”做的“八珍汤羊”。当我读到汉字先生的《格尔木:昆仑山下的野性美食》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在青海,在昆仑山与柴达木盆地之间的格尔木,形态粗砺的原生饮食因不能登大雅之堂而逐渐式微,外来的食物则遍布大街小巷。当你在格尔木觅食时,随处可见的是川菜、湘菜乃至于精致的淮扬菜与粤菜,而传说中的筏子肉团(制作工艺考究,原料为猪或羊的内脏,因成品外形与羊皮筏子相似而得名)、老鸦峡锅榻(一种需要专门饿上两天两夜后才能吃的馍馍)、发菜蒸蛋(发菜是青海高原上独有的山珍,少而贵,唐以来即是皇室贡品,过度采集会破坏草地生态。用以蒸蛋成菜,号称“黄金白银乌丝糕”)……这些原生美味,实在难得一见。细究个中缘由,除了原生饮食因缺少系统性而难以光大之外,移民文化的影响更甚。西北历来是移民的聚集地,但最近几十年的力量,无疑超过了此前千年。套用琵琶曲中的武曲、文曲之分(琵琶本身也有这种分野:琵,通批,向外弹,属阳,武;琶,通拔,向内拔,属阴,文。琵琶即批拔),我们似乎可以把西北的美食作类似的划分:原生的,武曲,属阳;外来的,文曲,属阴。只是一分之下,我们难免会有阴盛阳衰之叹。好在一旦离开城市,我们还是能在遥远的乡村找到原生美食充满野性与活力的源头。
其实,这就足够了。我们并不奢望在昆仑山中游走时,真有一台西王母或孙悟空的蟠桃宴出现,而是一些适时来到的帐房小吃:牧民手制的氽灌肠与烧羊肝,青稞甜醅与麦面酿皮。当我们在察尔汗盐湖的万丈盐桥上目睹海市蜃楼中的阆苑异珍时,心中念及的也只是鹿角菜、油馓子与羊肠面而已。它们适度而为,从不锦上添花,犹如海青的飞翔与翦扑,简单,直接,正好与我幼时对它的想象相合。
山家清供,或宇宙尽头的餐馆
天时开始暄热起来的四月,我约了几个朋友出行,到贵州、湖南、广西、云南等地游走。此行颇让人意外的,是一路上有许多饭店都在公开售卖各种野味,生意红火,却几乎——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无人过问其合法性。我们仅就所见粗略统计了一下,也有二三十种之多,其中,不乏国家保护动物。因为同行的一位老饕是一个资深的野味爱好者,因此一路上都强烈要求天上飞的、山里跑的、河头游的都要逐一吃遍,且对其他人的反对颇不以为然。
他说:美食家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山家清供”,说的就是这些上天赐予我们的恩物。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在笔记本电脑上遍搜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在里面找出了野物数十种。他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存与灭绝都是由优胜劣汰的原则决定的。人也是这个大环节中的一链,只要不过分破坏这一链的上下文关系,完全可以适度地吃一些野生动物。
但怎样才算适度,他却没能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应根据该物种存活数量的变化来决定是否可以猎杀或进食,足够多时就行,少时则不可。他举了一个例,说是重庆一区县某年开始禁猎野猪,可不久之后,野猪就泛滥成灾,破坏庄稼不说,偶尔还袭击村民,为患一方。当地政府不得不小范围开禁,以为平衡。另一个观点显得同样模棱两可:如果什么都被限制,就谈不上一个地方的特产和与该特产有关的饮食文化了。试想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近水楼台得不了月,“美食地理”,犹其是“地理”又从何说起?
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两年前英国政府禁止猎兔,数万名狩猎爱好者与从业者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收回成命。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猎装的查尔斯王子。据信,他是在保护一种贵族的文化,同时,为英国数万只猎兔犬不至于失业而最终灭绝。
因此,他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不该禁吃,而应大力整治水土。禁吃是治标不治本之举,而且难以执行。因为相对贫穷的农渔者不会放过挣钱的机会,同时越来越迷信“绿色食品”的吃客也很难管住自己。
二是让该消失的物种消失,不必勉强留存。正如治沙,有的学者就很绝望,认为羊群与发菜并非我国沙尘暴的根源。因为从更大的视界来看,沙漠本来就是地球正常生态中的一个元素,就如海洋、山脉或湿地一样,都有其生成或消失的自然规律。同样,大量物种的消失也是正常现象。而聪明的物种则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繁衍。比如狗,与其说是人驯化了一部分狼,从而进化为狗,还不如说是一部分狼选择了人,通过与人共生的方式使自己得以生存。相反,猪采取了另一种更惨烈的方式,依靠众多个体被人吃掉而得以保证种族的大量繁衍。所以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否在有人类存在的地球上存活下去,就全靠它们的求生本能与本领了。一切都是天择。
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念起苏轼的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也的确令人心喜,但若是转念一想,号称长江四鲜的鲥鱼、刀鱼、江团与河豚几乎都已绝迹,又怎能真的高兴起来?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生存环境早已今非昔比。破坏总是迅速的,恢复则格外缓慢。用那个睿智的印第安巫师唐望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停顿世界”。不然,重建与破坏相抵销所得的不止是零,而是巨大的负数。我们只可能坐吃山空。
当然了,吃,甚至饕餮,本身并不是坏事,反而还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好事。这种人之大欲使我们能在这无际的宇宙中存活下去。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其系列作品《银河系搭顺风车漫游指南》中,幻想地球毁灭后,人生的三大要意从“如何?为何?到何处去?”变成了“如何才能吃到东西?为何要吃东西?到何处吃午餐?”于是,在《宇宙尽头的餐馆》里,一家终极酒店便孤立在时空寂灭的临界点上,那些搭顺风车穿越时光隧道到达的人们,一边享受有这家餐馆的美食,一边观赏宇宙毁灭那一刻的壮美。
当然,故事并没有这样完结。这并不是最后的晚餐。因为毁灭的同时也是起源。我们还可以再一次像古人那样,百无禁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地球上任何一家餐馆放怀享受真正的山家清供。这是肯定的,正如该书的封面上用了“大而友善的字母”告诉我们:“不要恐慌。”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深处的天堂镜象
小时候,我曾在一本插画书中读到过一个英国旅行家的冒险故事。那本书在到我手中时早已被别人翻看得缺破不堪,既无开头也无结尾,我甚至不知道书名是什么;但它的内容却令人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一些很小的细节。那个幸运的主人公走遍全球去寻找人间天堂,有一次他跟一个贵妇谈到天堂的一些基本要素,其中之一是说,天堂的植物应该是高大而茂密的热带雨林,而非低伏浅薄的灌木丛。于是我想,西双版纳的样子应该算是长得像天堂了。多年以后,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等待航班时,看到袁运生取材于西双版纳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礼赞》,不期然地想到了儿时对天堂景象的那个猜忖,不觉解颐而乐。
其实,那时我并不了解版纳,但正如保罗克利所说的: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一个从那儿还乡探亲的知青告诉我,在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遍地是孔雀与水果,大象与雨林(他还特意提到了知青们手植的橡胶林)。人们说着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吃虫与青苔,衣着光鲜而奇特,住在积木搭成的竹楼里。尤其是妇女们,全都美若天仙:高高的个子,裹着紧身的筒裙,走路像是一朵小云在寨子与田坎之间袅袅地飘……我听得张口结舌,感觉完全是天方夜谭,因为实在是太有异国情调了,像是假的——只不过那个异国不是一般的异域,而是隐身于人间的仙境或天堂。
现在想来,西双版纳几乎是配得起我对它的神往的。即使是在那个艰难的时期,版纳天生的富足也使它所庇护的生民衣食无忧。同是远赴云南的知青,在别的地区可能生活极度艰辛,而在版纳,森林旁边有江河,江河边有竹丛,竹丛深处有竹楼,而竹楼周围到处是花草果树——这么多的香草野物与鱼虾瓜果,虽不是唾手可得,至少是不会让人忍饥挨饿的。他们时不时会在割完橡胶之后的某个夜里,打起火把,提着缅刀,或捉山鸡,或炸野鱼。一个自然资源如此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正暗合了西双版纳的古称“勐巴拉纳西”的本意:一个“神奇而美好的理想国”。
以后的版纳之行更加印证了这一点:这“十二千块稻田”(西双版纳傣语的原意)是如此富饶,你要是种庄稼,无需施肥它们也能茁壮长成。果林似乎是自愿或自动长出来的,全然未经人手,各种千奇百怪的果子就累累垂枝了。犁水田与打谷子,这是一个男人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舍此以外,他们天天晒太阳、喝米酒,享受妇人们的贴心照料。由于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每个男人都必须要出家去做一回和尚,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还了俗,娶妻生子,修造一座属于自己的竹楼——那时整个寨子的男人都要前来相帮。而女人们也并不比男人更辛劳,她们只是跟随季节,用各种奇花异草来缀饰居室、帮补厨房,并且,穿着最美丽的衣裳——水傣、旱傣服饰的艳丽并不亚于花腰傣。这些只有热带的美丽山水才可能孕育出来的美人,热情、明丽甚至有时显得华美,却又纯洁如水,过着她们孔雀盛放的彩屏一般招展而光明的小生活,对时日之逝浑然不觉。
有个英国记者曾将他在版纳之所见,与非洲某些部落的生活情形作比:也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原,除了集体狩猎以外,并无多事可做。他们随意出门采摘,都必有所获,仿佛上帝在每双伸出的指尖下都存放了一个果园。这使得他们不思进取,每天除了聚餐、巫术、晒太阳,就是跳舞与繁殖。但稍加思量,你会发现二者本质上的不同。那种未开化土著的懒惰与无心,与版纳人的闲适自得,境界有天壤之别。且不说傣族人发达的语言、文字系统乃至古老而精确的天文学,只消看食物一项,就不可同日而语:那个非洲的部落人茹毛饮血,唯一的烹调行为只是对烟草的加工与吸食,而版纳的所有民族都各有其异彩纷呈的烹饪术,以此与他们所处环境中食材的多样性相呼应。在就地取材这一点上,版纳人无疑是做得最彻底的,他们尽情享用上天的恩赐,并且用心烹调,绝不暴殄天物。
只是在有一点上,那个英国人是对的:小国寡民的生存状态(往往表现为一种富裕的贫穷或贫穷的富裕)在应对现代社会的浸透时,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自己就亲历过两种相反的状态:一种是过度拒绝,比如,我在大凉山深处游历时,发现从山上迁入政府建在坝上新居的彝人,在用完所有免费提供的物品后,重新回到了山上;另一种则是过度接纳,比如,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商业化的旅游开发已使原本是自然生发的民俗乃至节庆,全都成了程式化的表演。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古天真之世只是过往的记忆。我最喜欢的那些香料有许多是从雨林深处采来的,而我最近看到的一篇科学报告预言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地球上所有的热带雨林将在2050年前后消失——但愿到那时,西双版纳仍然是北回归线沙漠带上最美的一片绿洲。
藏边之远,或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二十年前,有个长途货车司机告诉我,驾车从成都出发,经川藏线进入西藏,就像是在进行一次时间旅行:华西坝子的温润与青藏高原的冷酷倒不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反差,这之中致命的转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世界仿佛是毫不相干的两个,各自处在时空的两端,而他,有幸在两者之间穿梭。最近,另一个刚乘新通车的青藏铁路从西藏归来的旅行者,也毫不与时俱进地用同样兴奋的语气向我报告了她的“时间旅行”。对我所表露出的惊讶,她显得有点不屑,因为在她看来,区区二十年时光,对亘古长存的青藏高原来说,只是一刹那而已。它一直在那儿,既古老又新鲜,在消逝的同时又发生着,其大无外,甚至就是时间本身。
但是,事物之间的不同带来的强烈反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我幼时分别住在四川成都与川南小城沐川,现实生活中,体验不到任何可谓之为文化多样性的东西;以至于稍长识字后,知道了在沐川以南便是彝人的领地,成都以西便是藏人的天下,完全颠覆了我对四川的地理与文化在汉人这个传统概念上的基本认同,不免大感惊讶。我悲哀地发现,中国是如此之大,而除了阅读,我见不到任何盆地以外的事物。书本之外,则是种种随之而来的意想天开,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道听途说。当然,无可奈何之下,有一点似是而非的空想,也总比逆来顺受地闭目塞听好些。而在所有对世界面貌的胡乱猜忖中,西藏以其天赋的神秘感首先征服了我,当然,这是极不专业地通过数册民国版《蜀山剑侠传》的残书,和几本零星的文史资料开始的。我对动辄就有高帽和尚出没的“藏边”这个词非常着迷,它意味着隐秘与遥远,一个不可捉摸的边界,再往外,世界似乎就可有可无了——如果它不是经由自己的屋脊直接上了天庭的话。这个神奇“藏边”的地理看似缥缈,实则具体而微,由一些名字惹人遐想的地方构成:打箭炉,打滚,炉霍,道孚,大藏,年古,恶古,古学,博美,八美,觉吾,弃戈……其中“打箭炉”三字尤其令我心生想象中风貌特独的藏边之思,急欲一探究竟。诗人张哮在其系列散文《消失的省份》中写到过昔日西康省被称为“康藏”的广大区域,在我看来,那便是藏边,或一个广义的藏边的组成部分。
那个有幸梦游于时光隧道的长途货车司机,有一次从藏边给我带回来一块黑不溜秋的东西,说是绝好的下酒物,不过,在我享用以前,我得猜出它是何物。当时我正从《蜀山别传青城十九侠》中读到一种出自藏边的异兽,叫做狗猩的,便想当然地认为是狗猩。当然不是。于是我猜它是太岁,也就是《山海经》里提到的与“息壤”异曲同工的“视肉”,具有食之不尽的异禀,我以为此生余下的日子,就仰仗这一块似硬亦软的恩物了。结果自然让人失望:那只是一块猪肉罢了,而且,正式的名号颇不雅,叫“臭猪肉”。据说,这是一种康藏地区独有的烹饪手法,虽然原始而粗放,却比我们常吃的腊肉殊胜。猪用的是几乎野养的藏猪,宰杀时不放血(勒死的),以麦秸杆和青稞杆燎尽毛后,从腹部开一小口取出脏器,然后塞入小麦粉、干豌豆、干青稞草、干圆根叶(后者最为关键,彝人也爱用它做酸腌菜)等物,再用细绳将之缝合,最后用火塘灰兑水,搅成浆糊状包裹猪身,深埋于火塘灰中至少一年,方能吸走水分。届时或数年后取出,高悬于屋顶横梁之下,让风去收拾它——这一挂往往又是数年。风吹之下,猪肉得了天气浸润,再次发酵,变臭之日即可食用。按当地人的说法,是越陈气味越臭,吃起来却反而越香,存放时间最长而不腐者,号称有30年之久。
可以想象,在经过如此这般一番解密后,我对这块来历不凡的仅5年风龄的大肉肃然起敬。它是从整猪上切割下来的一块后腿尖,洗净之后,色呈金黄色,用文火细细炖了,汤色浓白如乳,肉色依然金黄。入口,汤鲜美无匹,肉则初感微苦,继而香气四溢,确实比我吃惯了的腊猪脚厚道许多。当时便写了一篇短文为祭,题名抄袭了林纾译的狄更斯,叫《块肉余生记》。
这样,从胃开始,我对藏边的好奇心得到了具体的满足。其后的一切便顺理成章地到来,都与一些奇异的食物有关:藏药生拌牛肉酱、霉奶皮裹风干肉,酸奶子羊肉沙拉、羊血肠蒸蕨麻饭、干拌吹肺、新年酒羹、羊腿爆糊,等等,不一而足。食物之外,我也因工作之便,编辑或出版过一些与藏边有关的书籍: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张宓的《藏地民间书》,贝嘎的《康巴的诱惑》,陈小璐的《尼泊尔八日》……但我知道,所有这些光影闪烁的东西之于我心目中的藏边,都只是乱我心曲的皮相幻影而已,在它们难以企及的底里,才是潜伏在时间深处的一种对生与死、宇宙图景乃至整个大千世界所有事物的秘密知识。显然,我并不敢奢望仅凭这一点菲薄的缘法,就能在某一天福至心灵,一举获致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许它深奥如一座坛城,明了如一页贝叶。
鸭头记:另一个金陵春梦
北京春寒料峭的时节,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的辰光。因此,当我多年的老友——诗人、小说家兼出版人张小波,邀我与张氏三兄弟驾长车回其老家江苏南通饕餮淮扬菜时,自然是欣然领受。很显然,接下来的长途跋涉是值得的,因为有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小欢喜在那儿等着我:黄酒,龙井茶,醉虾,温蟹,泥螺,河蚌,刀鱼,鮰鱼,河豚,茨菇,药芹,草头,马兰头……更不消说那些让人心软的缥缈烟水与滟涟流光了——我心念中的江南实在是具体而微,在生活的低处与白居易、杜牧、柳永甚至祝允明或唐寅的江南暗合:一个优裕而清明的江南。
那是多年以前一次浮光掠影的小游历。在经过了沿途略嫌粗糙的德州扒鸡与道口烧鸡的铺垫后,我们终于在华灯初上之时来到南京,而南京作为一个六朝或十朝旧都,它对我们的款待当然是精致而雍容的。这种气度即使在一家排档式的酒家,也是表露无遗。这家24小时营业的店叫“八方客”,是当地人喜欢宵夜的地方,主打的招牌菜均与鸭子有关。在北京饱受烤鸭的丰腴之累多年后,一下子吃到盐水鸭这般清丽可人的美味,令我有点受宠若惊。鸭子是水禽中的极腥之物,以浓酱掩盖易,惜失其香;以清鲜之法炮制,去腥留香,则难矣。而盐水鸭庶几近此。南京人以嗜鸭著称,不止做法多样,盐水鸭之外,尚有板鸭、水晶鸭、琵琶鸭、烤鸭、酱鸭等品,同时也善于把小小的一只鸭子给拆散了,条分缕析地细细吃来。其中我以为最让口舌满足的不是别的要紧部件,而是鸭头;鸭头之中,精华又在鸭舌。也有整盘的鸭舌供选,但那么直接吃又不如从鸭头中搜出来吃有味了。这一餐我们吃的几乎全都是鸭:鸭头、鸭舌、鸭颈、鸭肫、鸭肠、鸭肝、鸭四件(翅与爪),甚至还有鸭油烧饼;当然,整只的盐水鸭也是有的,鸭血粉丝汤更是不能缺席。
对此行而言,如此丰盛的夜宴也不过是一个前奏而已。第二天我们就开赴南通、如皋,一呆就是好几天,我预见中的所有欢喜之物一一到口,其中印象尤深者有四:食河豚中毒而又侥幸得救为一,在定慧寺吃素面、喝天水茶为一,每晨必至“孟家早点”吃大只蟹黄包为一,品张家兄弟自制的醋烧鮰鱼为一——鮰鱼在长江流域被叫作江团,虽不如刀鱼名贵,但自有别味。此鱼在川渝地区以乐山平羌江所出为上品,多用于清蒸。但在淮扬菜系中,则爱红烧。张家兄弟烧鱼时大量用醋,我在旁观厨,也自惊骇,但怪的是吃时只闻醋香,不见酸气,风味奇佳。如此这般日日沉湎,风车斗转,倒把南京的鸭头给淡忘了。
忽一日,张氏三杰要去沪上置业,亦请同行,我却想起那只清鲜有味的鸭子来了,于是独自又去了南京。这一番算是有备而来,由一位当地老饕导游,专攻鸭头。在整个鸭头阵营中,我最受用的还是盐水鸭头,至于同样著名的酱鸭头,乃至香酥鸭头与麻辣鸭头,窃以为都不能与之并列,正如南京板鸭与盐水鸭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我先去鸡鸣寺吃了一餐午斋,然后找到传说中的清真韩复兴板鸭店,买了十来只新出卤的盐水鸭头,再到夫子庙,在秦淮河边找了个露天茶座,开始细品。正得味,旁座一个清瘦老者发话了:小兄弟是哪里人,也吃得如此尽心?我答:四川。他便笑:难怪,成都人吃兔头。他说他是如皋人。
原来,如皋除了美食,还有三个可以一说的名堂:拥有全国最大的花卉市场与宠物市场,是中国排名前三位的长寿之乡——还真是一个适合拈花惹草、走马斗鸡的所在。我想这老者正是这样一个玩家吧,交谈之下,果然令人钦服。据他说,现在的盐水鸭其实已大不如前了。以前都是由苏北人将一种绿头麻鸭在端午节前开始赶出门,一路走,一路吃道旁田里的麦子,到得南京城出卖时,鸭子长得刚刚好,精壮肥实,但做成菜以后肥而不腻。他小时候就赶过鸭子,也吃过鸭子。那时去店里买盐水鸭,店家会用一张荷叶包鸭子,鸭子上还浇一点鸭油,最后用小麻绳捆上,拿回去一打开,全家人都要发出尖叫!
未待我相邀,老人已移位过来,自顾拿起一只鸭头啃将起来。事毕,他擦净手,小心翼翼从一只挎包中取出一只砚,自问自答:知道这是什么石头的砚台吗?鸭头绿!今天刚淘到的。鸭头好啊,他说,有一种荔枝,桂花味的,也叫鸭头绿,是极佳的品种。我说:正是,盐水鸭也叫桂花鸭,并且,有一个词牌也叫鸭头绿!老者一听,面容耸动:是吗?想起来了,南京旧时有一种翠裘,还是叫鸭头绿,《石头记》里面都提到过——鸭头果然好啊!
和这位爱屋及乌的老寿星别过,我去到一家叫“罗汉池”的澡堂泡澡。看过江南形胜之地以后,泡澡是一堂必修课。正好老板是我的朋友,他特意在我的木盆里放了一些雨花石,说是可供按摩之用。我想,到了南京这座石头城,既然说到鸭头,就不得不顺便说到石头。于是突然想起,其实我连石头都是吃过的,那是在川滇交界处的雅砻江边,与船工在河边用江水现煮的鹅卵石,烫得嘴起泡。当捕鱼不得时,吮一吮石头,他们就能送下半斤白酒。现下想来,虽然那并非鸭头而是石头,不过味型倒还相同,也是盐水的。
在梦中吃遍长江
我的一个幼时一道长大的朋友有个充满野心的饕餮大梦,妄图从长江源到入海口,整整一路,尽数吃鱼——顺流而下或随波逐流,从冷水鱼吃到洄游鱼。这听起来未免有些残忍和夸张,但细想下来,却也在情理之中。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吃鱼就十分重视,“鲜”之一字,便是从“鱼”而来(“羊”与“鱼”合而为鲜只是讹传)。人们除了以为鱼是终极美食,还认定它具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宴上有鱼,即有馀也。无鱼不成宴,即便穷舍邀酒,亦必上鱼,不然会被责为简慢怠客。《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一文,言冯在齐国孟尝君家作门客,宴不见鱼,知其轻慢,乃弹剑作歌曰:“长铗归去乎,食无鱼!”可见鱼之要紧。
但要后浪推前浪地从长江源吃到入海口,难度却是甚大。再想一想一路上汇入长江的众多支流,以及支流的支流,就几乎令人断了念想。好在人都是颇能随缘的,做得到逮一段水面吃一段水面,就已然口福不浅了。我那位嗜鱼如命的朋友后来成了一位浪迹江海的行脚僧,数度探看过长江源,还在崇明岛住过一年多,算是大致实现了梦想。可惜他不喜著述,也不爱摄影,自言只是“搜尽江鱼打腹稿”,否则我就可以更直观地分享他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吃遍长江”之旅了。
惭愧的是,对我来说同样是魂牵梦萦的长江源,至今都还没去过,但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岷江、嘉陵江、乌江、赤水、湘江、汉水、沅水……等大小河流中的鱼,却吃过不少。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鱼类良多,诸如金沙江的肉石巴,雅砻江的细甲鱼,大渡河的猫儿鱼,青衣江的丙穴鱼,岷江的江团、泉水鱼与岩鲤,沱江的鲢鱼,嘉陵江的水密子与胭脂鱼,乌江的青波,湘江的黄鸭叫,等等,无不令人回味。在江苏南通,诗人张小波带同我拚死吃河豚时,还发生了一起中毒事件,不得不在当地人民医院的急救室里洗胃,在短短15分钟内先喝后吐了一巨桶冷水,累得几乎虚脱。不过,最让我难忘的,是在雅砻江下游的二滩电站水库,先吃了包括长江鲟(养殖品)、绿浪鱼、油鱼在内的美味后,去参观二滩水电站博物馆。只见一排又一排的博物架上,尽是泡在满水杯的福尔马林液体中的各种鱼类标本,它们多达百余种,大部分都因电站的建立而消失了。正巧,我那个嗜鱼的朋友是当年收集这些濒临灭绝的鱼种的生物学家之一。他在电话中说,那一段日子,是他唯一一次守着众多珍奇的鱼类而不敢也不忍动箸的时候。水电工程固然能造福生民于一时,但其对环境的破坏,却可能是永远都难以恢复的。我在云南跟另一个玩奇石的朋友去长江一条叫普渡河的支流找石头时,发现不仅鱼种少了,就连奇石也将在蓄水后的平静中面临灭绝之灾,因为没有水流的冲刷,好石头就不可能再有了。在著名的“长江三鲜”(刀鱼、鲥鱼与河豚)中,因为余生也晚,加之三者都是扬子江的洄游鱼,在地理上与我老家所在的川江有首尾之遥,三鲜之中,也就只得其二。真正的鲥鱼是再难寻觅的了。据资料显示,1955年的江阴县,年出产刀鱼20万公斤、鲥鱼47万公斤、河豚6.5万公斤,而现在,野生鱼几乎已全部绝迹,其中鲥鱼的境况最为堪忧,年产量不足500斤。而人工繁殖方面,只有河豚取得了成功,然风味却远远不逮矣。
遥想当初,苏轼贬于黄州,因见山水秀美,风物殊胜,虽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厄,仍满心欢喜,脱口咏出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佳句。这种见河及鱼、见山及笋的联想,中国人是尤其丰富的。多年前,我曾有一段时间住在诗人万夏位于成都青龙巷的家中,一日正看电视“动物世界”,万夏的母亲从旁脱口而出:“这只老虎的前蹄炖出来肯定是满满一大锅!”少顷又言:“这只天鹅的颈子好长,卤出来可以装一大盘!”最后,终于看到了一条扬子鲟,立即十分内行地赞叹:“看啊,一身好有嚼头的脆骨!”虽然当时被我和万夏一阵讪笑,但细想之下,跟苏轼的诗并无二致,语言更直捷了当罢了,如果哪一天老虎天鹅们多得成灾,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