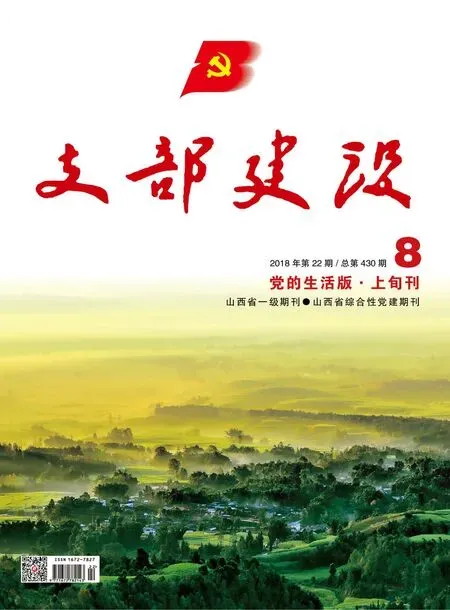恩师留给我的永久思念
——怀念敬爱的马作楫、姚奠中老师
■ 何其山
近年,我省诗坛和书法界的泰斗和领军人物姚奠中、马作楫两位老先生相继辞世,巨星陨落,母校山大蒙受了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他们的学生,我在极度哀伤、惋惜之后是深深的回忆和久久的思念。
马作楫先生是我大学时的写作课老师,他讲的诗歌写作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批改过的作文我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因为那精批细改中可以窥见先生教书育人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其间凝聚着恩师多少心血和汗水啊。马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上可谓功深艺湛,深得学生喜爱。他除了课堂上精心讲课之外,无论课下、课间,还是上下班的路上,便是周末家中也总是围聚着不同班级的诸多讨教者,他从来没有厌倦和嫌弃过,总是那么认真地回答每个学生的提问,用商榷的口吻给你破解难题,让你满意而归。我们这届大学普通班的学生,文化水准参差不齐,但他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从不偏三向四,更不嫌贫爱富。记着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召集我们十几个同学说:“想请你们为这届考生中选出的优秀作文各写一篇评论文章,然后结集成册出版发行。”他看出我们有畏难情绪,就用鼓励的语气说:“我相信你们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倾尽心血完成好这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努力写出了较高质量且有板有眼的评论文章。书不仅如期出版了,并且广得好评。后来,马老师负责编写一套大学读本中的诗歌分册,他又让我们几个同学参与,这次是对中国文坛巨匠的作品作评论,我分得的是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我很胆怯,虽然平生非常喜欢诗人这篇佳作,但真正要写有深度的评论文章则感到诚惶诚恐、力不从心。后来,有马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多方指导,总算保证了这套丛书按时出版。我上学时马老师对我们几个酷爱文学的同学一直是关爱有加并寄予厚望,后来涌现出了获得首届艾青诗歌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的郭新民等佼佼者,而我却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在文学创作上没有什么成就,毕业离校后我一直羞于去见马老师。一次开省文代会时,我遇见了马老师,红着脸吐露了自己的愧疚之感,没想到马老师坦然一笑说:“其山,不要这么想。在文学创作上成才需要各方面的条件,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况且,中文系也并不是单单要培养诗人和作家的。”老师一番掏心窝子的开导和教诲,不仅使我甩掉了心理包袱,而且重新鼓起了我业余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勇气。我暗暗下定决心近期出版一本自己的文学集,并请马老师给写个序。2016年秋季我们大学同学聚会时,马老师还应邀出席并且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看他红光满面,身体倍儿棒,思谋我的心愿必能兑现。谁曾料想,这次聚会不久,他竟那么快地和我们诀别了。真是痛彻心扉。我其后出版的作品集《漾舟掬澜》是请他的得意弟子、我的大学同学郭新民写的序。这里尤为感人的是马老师自己的作品集出版时,有那么多文学泰斗级的人物他不用,却执着地让自己的学生郭新民来写序。我们知道,敬爱的马老师一生爱学生,敬学生,他总是把学生举得很高很高,为了学生他甘愿当铺路石和垫脚石。他是永远耸立在教育战线的一座丰碑。他的人品永远值得我们追随。
另一位可亲可敬、值得我久久怀念的是姚奠中老先生。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负责编辑出版一本干部职工的文学艺术作品集,取名《飞舟撷浪》,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想请素有“山西书法第一人”的姚老先生给题写书名。尽管山西大学是我的母校,虽然说我认识姚老师,听过他的大讲座,但姚老师没给我们班带过课,并不认识我,况且那时先生的名气如雷贯耳,蜚声文坛艺界,他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书法家,有诗、书、画、印“四绝”大家之称,著书等身,桃李满天下,而且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书法协会名誉主席等要职,我们这样冒昧地上门求字能行吗?恐怕不是碰壁就是被婉拒。犹豫再三,我们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前敲开姚老师的家门并说明来意,没想到老先生非常热忱,一口应允,当即请我们进屋喝茶,并说稍等即取。说罢走进书房,片晌手持写好的墨宝笑吟吟地走了出来,尤其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先生竟然写了两幅,一幅是横着排列,另一幅是竖着排列。他说:“我写了两幅,你们看哪幅适用就用哪幅。都不合适我再重写。”我们接过这墨迹未干的题字,字写得漂亮极了!书法高古大气,沉雄典雅,不愧是三晋第一笔啊!特别是题字之外,我们被老师那善解人意和儒雅可亲、平易近人的风度和人品感动得热泪盈眶。
《飞舟撷浪》出版后,不少行家里手赞叹这出自大家之手的书名题字隽秀潇洒,为作品集着实增彩不少。当我们向他们讲述了求字过程后,大家无不折服于姚老先生过人的才识和优雅高尚的品格纷纷为其点赞。
姚奠中老先生2013年辞世,享年101岁,马作楫老先生2017年辞世,享年95岁,他们都已进入耄耋和期颐之年,仍然关心和扶持新人,从不恃才傲物,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很庆幸一生中曾与这样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有过亲近接触,亲耳聆听过他们的教诲,亲眼目睹过他们的风采,也让我的人生道路有了璀璨的路标。我会一生一世缅怀他们,敬仰他们,学习他们。